小说欣赏|村上春树【日本】:双胞胎女郎与沉没的大陆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双胞胎女郎与沉没的大陆
村上春树作 林少华译
01
照片上的双胞胎穿的不是印有“208”和“209”号的运动衫(和我一起住的时候总穿来着),这回衣着相当潇洒得体。一个身穿混纺连衣裙,一个身穿质感很强的布夹克样的衣物。头发比以前长了不少,眼圈甚至化了淡妆。
但我一眼就看出是那对双胞胎女郎。虽然一个扭头向后,另一个也只看到侧脸,但在打开画页的一瞬间我就看出来了。就像耳朵捕捉到听了不知几百遍因而彻底灌进脑海里的唱片那最初一个音符,我在刹那间便一切了然于心——原来她们在这里!
照片照的是一家刚在六本木边缘开业的迪斯科舞厅里的光景。画报以六页篇幅专门介绍所谓“东京风俗最前线”,第一页便是双胞胎女郎。
照相机是以广角镜头从稍高些的位置拍摄的,加之舞厅挺大,若无文字说明,较之迪斯科舞厅,恐怕说是别具一格的温室或水族馆更令人相信。因为大凡一切都是玻璃的。除了地板天花板,无论餐桌、墙壁还是装饰物无一不是玻璃制品,并且到处摆有堂而皇之的观赏植物。
用玻璃间隔开来的单间,有的里面有人斜举鸡尾酒杯,有的里面有人舞兴正酣。这使我联想起精密透明的人体模型,每一部位都按其规定运作无误。
照片右端有一张硕大的卵形玻璃桌,双胞胎即坐在那里。两人眼前摆着一对煞有介事的热带饮料玻璃杯、几个装有一点儿炸薯片等小食的碟盘。两人中的一个双手搭在椅背上整个转过身去,出神地看着玻璃隔墙对面的舞池;另一个面向邻座一位年轻男士在诉说着什么。假如没有那对双胞胎,照片本身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场景,无非两个女郎同一个男士在迪斯科舞厅桌旁喝酒罢了。舞厅名叫“玻璃笼”。
我拿起画报纯属偶然。进这家酒吧等一个工作上的朋友,碰巧时间多了出来,便拿起店内杂志架上的杂志啪啪啦啦随手翻阅。若不然,根本不至于特意看什么已过期一个月的画报。
双胞胎的彩照下附有极为平常的文字说明:“玻璃笼”是时下播放东京最流行音乐、聚集最新潮男女的迪斯科舞厅。舞厅内一如其名,玻璃隔墙纵横交错,甚至使人联想起透明的迷宫。里面各类鸡尾酒应有尽有,音响效果也考虑得周到至极。入场者在门口受到甄别,衣着不整或无女伴者不准入内。
我向女侍要了第二杯咖啡,问她是否可以把这个画页剪下带走。女侍说现在负责人不在,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过这东西剪下来怕也没什么人理会的。于是我用塑料菜谱将那页齐齐裁下,折成四折揣入衣袋。

回到事务所,只见门大敞四开,里面空无一人,桌面上文件乱七八糟,洗碗槽里杯盘狼籍,烟灰缸里满是烟头——事务员女孩因感冒已三天没来了。
我心里暗暗叫苦。就在三天前还一尘不染的办公室,现在简直成了高中篮球队的衣帽间。
我用壶烧了开水,洗一只杯子冲了杯速溶咖啡。找不到咖啡匙,便用看上去还算干净的圆珠笔搅拌着喝。味道绝不美妙,可总比喝白开水多少有些滋味。
正坐在桌边一个人喝咖啡,隔壁牙科诊所负责收发接待的打工女孩从门口探过脸来。长发披肩,身材小巧,真是漂亮。只是皮肤黑些,最初见面以为混有牙买加人或其他什么人种的血统,一问,原来出身于北海道酪农家庭。她自己也不明白肤色何以如此之黑。总之,穿上这白大褂就更是黑白分明了,活脱脱成了阿尔伯特·施韦兹(德国考古学家。)的助手。
她和我们事务所打工的女孩同龄,有空时常过来闲聊,我这边的女孩休息没人时还给听电话做记录。电话一响,她就从隔壁过来拿起听筒。所以,我们不在时总让门一直开着。反正小偷进来也没什么可偷。
“渡边出去了,说是去买药。”她说。渡边升是我的合伙人的名字。当时我和他开了一间小小的翻译事务所。
“药?”我有点儿吃惊地问,“什么药?”
“太太的药。胃不好,说要用一种特殊的中药。到五反田那儿的药店去了。说可能耽误些时间,叫你先回去。”
“唔。”
“还有,你不在时有几个电话打来,都写在那儿了。”说着,她指了指压在电话下的白色便笺。
“谢谢!”我说,“幸亏你在。”
“我这边的医生建议买个录音电话。”
“讨厌那玩艺儿,”我应道,“冷冰冰没人情味。”
“不买也好,无所谓。跑跑走廊我也可以暖暖身子。”

******
女孩留下英国猫一样的笑脸离去了。我随即拿起便笺,打了几个要打的电话:明确印刷厂发货日期;同承接翻译的临时工商定翻译内容;请租赁公司修理复印机等。
如此回完电话,我就无事可干了。无奈,便将堆在洗碗槽里的餐具洗了;烟灰缸里的烟头扔进垃圾篓;校准停了的时钟;把“日日翻”式的日历翻好;桌面上的铅笔插进笔筒;文件分门别类整理妥当;指甲钳收进抽屉。这么着,房间总算像个普通人的办公场所了。
我坐在桌边环顾房间。“不坏不坏。”我出声道。
窗外舒展着一九七四年四月阴沉沉的天空。云看上去宛如无缝平板,简直像给天空整个儿扣上灰色的巨盖。薄暮时分淡淡的天光如水中尘埃在天空缓缓漂移,无声地填满钢筋混凝土和玻璃构筑的海底沟谷。
天空也好街道也好房间也好,一律给涂上湿乎乎的灰色,哪里都看不到接缝。
我又烧水冲了杯咖啡,这回可是用咖啡匙搅拌的。按下收录机开关,嵌在天花板里的小音箱流淌出巴赫的琉特琴乐曲。音箱和收录机和磁带都是渡边升从家里拿来的。
“不坏不坏。”这回我不出声地来了一句。巴赫的琉特琴乐曲非常适合这四月间不冷不热的阴晦的黄昏。
尔后,我端坐在椅子上,从上衣袋摸出双胞胎的照片,在桌面上打开。在台灯明亮的光照下,我有所思无所思地怔怔注视了好一阵子。蓦地想起抽屉中有照片放大镜,便用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扩大来细细察看。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却又想不出此外还有什么可做之事。
冲着年轻男士的耳朵诉说着什么的双胞胎中的一个——我永远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左臂置于玻璃桌面。那分明是双胞胎的胳膊:细细光光,没戴手表没戴戒指。
相形之下,听她诉说的男士神情总好像郁郁寡欢。男士相貌堂堂,身腰颀长,身穿颇显气质的深蓝衬衫,右腕套一个纤细的银镯。他双手放在桌面,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细腰玻璃杯,仿佛那饮料乃是足以改变其整个人生的重大存在,而他正被迫就此作出某种决定。杯旁的烟灰缸升起一道形状像是诅咒什么的白烟。
与在我公寓时相比,双胞胎略显瘦削,不过我看不大准。或者是摄影角度和灯光使然亦未可知。
我一口喝干所剩咖啡,从抽屉取一支烟擦火柴点燃,开始考虑双胞胎到底因为什么在六本木的迪斯科舞厅喝酒。我所知道的双胞胎并不属于出入俗不可耐的迪斯科舞厅或描眼圈那一类型。两人如今住在何处,何以为生呢?那男士又是何许人也?
我把手中的圆珠笔杆转动了约三百五十次,转动期间始终凝视着这张照片。随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男士乃双胞胎眼下投宿处的房主。就像以前对我那样,双胞胎抓住一个偶然机会定居在了这男士的生活中。这一点只消细看一下冲男子说话的那双胞胎嘴角漾出的微笑即可了然。她的微笑犹如洒落在无边草原上的霏霏细雨一般同她本身融为一体。她们物色到了新的住处。
我可以在脑海中推测出他们三人共同生活的每一细节。由于所去之处的不同,双胞胎也许会像流云一样改变其行为方式,但她们骨子里若干赋予其特征的东西绝不至于改变,这点我一清二楚。她们恐怕现在仍然咀嚼咖啡味饼干,仍然没完没了地散步,仍然在浴室地板上不厌其烦地洗衣服。这就是双胞胎。
奇怪的是不管怎么看照片我都没对那男士产生嫉妒,不光嫉妒,连兴致都未产生。他仅仅作为状况而存在。对我来说,那无非是从另一时代的另一世界里切分下来的断片性场景。我业已失去双胞胎,再绞尽脑汁也不可能失而复得。
我多少费解的是男子脸色竟那般阴沉。能有什么理由摆出那么阴沉的脸色呢?你拥有双胞胎女郎,我没有。我失去了双胞胎,你还没失去。迟早你也会失去,但那毕竟是日后而又日后的事,何况你想都没想到自己或许会失去她们。不不,你有可能困惑。这不难理解。任何人都时常困惑。问题是你现在品尝的困惑并非致命性困惑。这一点想必你自己迟早也会意识到。
但不管我怎么想,都全然没办法传达给他。他们置身于遥远时代的遥远世界。他们就像浮游的大陆,在我不知晓的黑暗宇宙里不知其归宿地彷徨不已。

等到五点渡边升也没返回。我把需要联系的几点事项记在便笺上,做回家准备。正准备着,为隔壁牙科医生负责接待事务的女孩又一次跑来,问可不可以借洗脸间一用。
“随你怎么用。”我回答。
“我们洗脸间荧光灯坏了。”说着,女孩挟着化妆包走进洗脸间,站在镜前用梳子梳头,涂口红。由于洗脸间的门一直没关,我就坐在桌子的一端似看非看地看她背影。脱去白大褂,只见她双腿真是诱人得很。稍短些的蓝色毛质裙摆下,可以看到膝后的小肉窝。
“看什么呢?”女孩边拿纸巾调匀口红边对着镜子问。
“腿。”我说。
“中意?”
“不坏。”我实言相告。
她妩媚地一笑,把口红装回化妆包,走出洗脸间带好门,然后在白衬衫外披一件天蓝色对襟毛衣。毛衣如云絮一样轻盈柔软。我把手伸进粗花呢上衣袋,又看了一会儿她的对襟毛衣。
“我说,是在看我,还是在想什么。”女孩问。
“我在想,这毛衣真是不赖。”
“是啊,贵着哩,”她说,“可实际没那么贵的。这以前我在一家小时装店当售货员,什么衣服店员都可以打折买。”
“干吗不卖时装偏要来牙科医生这里干呢?”
“时装店工钱低,又都用来买衣服了。比起来还是在牙科医生这儿好,又能差不多免费看蛀牙。”
“那倒也是。”
“可你穿衣服的品位也够可以的嘛。”她说。
“我?”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就连早上挑什么衣服穿的都记不清了。一条上大学时买的驼色布裤,一双三个月未刷的蓝旅游鞋,一件白色开领衫,加一件灰粗花呢上衣——便是如此装束。开领衫倒是新的,但上衣由于手总是插进衣袋,形状早已崩溃得无可救药了。“无可救药啊!”
“配你倒蛮合适的。”
“就算合适也称不上品位,不过裹住身子不出洋相罢了。”我笑道。
“那,买套新西装,改掉手插衣袋的坏习惯不就成了!是坏习惯对吧?好端端的上衣硬是给弄得没形没样。”
“是没形没样,”我说,“工作若是完了,回去一起走到车站好么?”
“好啊。”
我关掉收录机和增音器,熄灯,锁门,沿下坡路往车站走去。我习惯不带东西,双手仍插在上衣袋里。几次想听从女孩的劝告尝试把手换到裤袋,结果未能如愿。两手插进裤袋总好像不踏实。
女孩右手抓着挎包带,左手像是打拍子似的在体侧轻轻摇摆,由于她挺直腰杆儿走路,看上去比实际身量要高些,步履也比我轻盈得多。
或许因为无风,街上静悄悄的,就连身边驶过的卡车排气声建筑工地嘈杂声也变得含糊不清,仿佛透过好几层幕布传来。惟独她的高跟鞋声像是往春日迷蒙的夕霭上有板有眼地打着光滑的楔子。
我不思不想地只管倾听这鞋跟声,差点儿撞在拐角里飞出的小学生自行车上。若非她用左手猛地拉住我的臂肘,我肯定会撞个正着。
“好好看着前面走嘛,”她非常惊讶,“走路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我做个深呼吸说,“只是发呆。”
“够让人操心的了,你这人。到底多大岁数了?”
“二十五,”我说,“年底二十六。”
她终于把手从我臂肘上拿开,我们重新沿坡路下行。这回要集中精神走好路。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
“没说过?”
“没听清。”
“May,”她说,“笠原May。”
“May?”我有点儿意外。
“五月的May。”
“五月出生?”
“哪里,”她摇一下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
“你何苦叫什么May?”
“想知道?”
“可能的话。”我说。
“不笑?”
“我想不会。”
“我家养山羊来着。”她淡淡地说。
“山羊?”我更觉意外。
“山羊可晓得?”
“晓得。”
“一只脑袋瓜非常聪明的小羊,全家像对待家人一样喜爱它。”
“山羊的May。”我复述似的说。
“再说我是农家六姐妹里的第六个,名字之类大概叫什么都无所谓吧。”
我点头。
“不过好记吧,山羊的May?”
“的确。”
到车站时,为感谢笠原May帮看电话,我邀她吃晚饭。她说和未婚夫有约会。
“那么下次好了。”我说。
“嗯,我等着。”笠原May应道。
我们就此分开。

******
看到她天蓝色的对襟毛衣像被下班人流吸入似的消失不见,她再不会折回之后,我依然手插衣袋,朝适当方向走去。
笠原May的离开,使得我的身体仿佛再次笼罩在那全无接缝的呆板的灰色云层的阴翳中。抬头仰望,云仍在那里。模模糊糊的灰色调中加进了夜的黛蓝,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那里有云。但云依然如一头蜷身不动的巨型盲兽劈头盖脑地压着,将月和星挡在身后。
简直就像在海底行走,我觉得。前后左右看起来毫无差别。气压和呼吸也好像跟自己过不去。
剩下一个人,食欲已不翼而飞。什么都不想吃,宿舍也不想回,却又别无可去之处,只好在街头闲逛,逛到想起什么时为止。
我不时停下脚步,看武打片广告,看乐器商店陈列橱窗。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边走边看擦肩而过的行人面孔。数千之多的男女在我面前忽儿出现忽儿消失。依我的感觉,他们好像从意识的此岸向意识的彼岸迁徙。
街是一如平日的街。交融互汇而失去各自本来含义的嘈杂人语,不知何处持续传来随即穿耳而过的支离破碎的音乐,闪闪烁烁的信号和唆使它的汽车排气声——一切的一切都如天空永远滴落不尽的墨水洒在这夜幕下的街上。行走之间,我觉得诸如此类的嘈杂、光亮、气味、兴奋实际上并不存在,几分之一都不存在,而只是来自昨天、前天以至上星期、上个月的渺远的回声。
然而我还是无法从这回声中捕捉到曾有所闻的东西。它是那样辽远,那样依稀。
我不清楚自己走了多长时间走了多远距离。我清楚的只是有数千之众与我擦肩而去。我还可以推测这数千之众在七八十年之后将确切无疑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无一例外。七八十年并非多么漫长的岁月。
看行人脸也看得累了——自己大概是想从中找出双胞胎的脸,因为此外没有任何看别人面孔的理由——我几乎下意识地拐进有些冷清的一条窄横路,走进时常一个人来喝酒的小酒吧。在调酒台前坐定,仍像往常那样要了杯加冰块的巴奔威士忌,吃了几口奶酪三明治。酒吧里没什么客人,沉寂的空气已完全渗进颇有年月的木料和石灰中。几十年前流行的钢琴三重奏爵士乐从天花板音箱里轻轻淌出,酒杯相碰声和冰块切割声不时同其混在一起。
我促使自己这样去想:一切已然失去,或应该继续失去。一度失去的东西再不可能复得,任何人都徒呼奈何。地球是为此才绕太阳转动不止的。
我想我所需要的是现实性。地球绕太阳转,月亮绕地球转——便是此类现实性。
假定——只是假定——自己在某处同双胞胎不期而遇。那么往下如何是好呢?
能向她们提议再一同生活吗?
其实我很清楚,这种提议是毫无意义的。无意义的,无可能性的。她们已经通过了我。
假定——我做出第二个假定——双胞胎女郎同意返回我这里。这固然是异想天开,姑且这样假定。那么往下怎么办呢?
我嚼着三明治旁边的泡菜,喝了口威士忌。
无意义可言,我想。或许她们在我房间住上几星期、几个月以至几年,但某一天还是要消失不见,像上次那样既无前言又无后语如被风吹散的狼烟遁往某处。无非故伎重演而已,毫无意义。
这就是所谓现实性。我必须接受没有双胞胎女郎的世界。
我用纸餐巾拭去台面水滴,从上衣袋掏出双胞胎照片放上去,随后一边喝第二杯威士忌,一边猜想双胞胎中的一个到底向身旁那位年轻男士诉说着什么。细看照片,她简直就像往男子耳朵里吹送空气或肉眼看不见的细雾状的东西。至于男子察觉与否,从照片上难以判断。估计男子怕是什么都没察觉,正如当时完全稀里糊涂的我一样。
当我在脑袋里捏弄多少有些失真的记忆残片时,作为如此劳神带来的必然结果,我觉得两侧太阳穴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酸怠感,就像关在我脑子里的一对什么活物扭动身子急于挣脱出来。
我想这照片恐怕该烧掉才是。但我烧不成。如果有烧它的气力,压根儿就不至于钻进这样的死胡同。
喝罢第二杯威士忌,我拿着记有电话号码的手册和零币走到浅红色电话机前,拨转号码盘。但信号音响到第四遍时,我又转念放下听筒挂断,而后拿着手册盯视一会儿电话机,但仍无良策浮上心头,只好折回调酒台前要了第三杯威士忌。
最后我决定什么都不再考虑。考虑也无济于事。我暂且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往那真空中倾注了几杯威士忌,倾听头顶音箱流淌出的音乐。这期间不由得非常想抱女人睡觉,可又不知道抱谁合适。其实谁都无所谓,只是没办法将其中的某一位具体设定为性交对象。谁都可以,但某个谁却是不好办。得得,我心里叫苦。倘若我所知道的女人全部集中混作一个肉体,我想我是可以同其交合的。但不可能找到如此对象的电话号码,无论我怎么翻动手册。
我叹口气,一口喝干不知第几杯加冰威士忌,付款出门。出门站在街头信号灯前,思忖“下一步该做什么”,仅仅是下一步。五分钟后、十分钟后、十五分钟后,我到底做什么好呢?去哪里好呢?想做什么呢?想去哪里呢?势必做什么?势必去哪里呢?
我想不出答案,一个也想不出。

02
长时间闭目合眼,觉得自己竟好像以微妙的平衡飘浮在不安稳的空间。想必是赤身裸体躺在软绵绵床上的缘故,再一个原因也许是女人身上强烈的花露水味儿。那气味儿如羽虱潜入我黑暗的体内,使我的细胞伸缩不止。
“做梦时间也大体固定,凌晨四五点钟——天快亮的时候。一身大汗翻身坐起,四周还黑着,但又不是彻底的黑,就那种时候。当然每个梦都不完全一样,细微之处每次各有不同。
“背景不同,角色不同。但基本模式相同,出场人物相同,最后结果相同。就像低成本的系列影片。”
“我也经常做噩梦。”说着,女人用打火机开始点烟。响起火石的摩擦声,传来香烟的烟味,接着又响起用手心轻轻拍去什么的动静。
“今早做的梦里出来一座玻璃墙大楼,”我没理会女人的话,继续说道,“好大好大的楼,像新宿西口的那么大。墙壁全部是玻璃的。梦中走路时我碰巧发现了那座楼。不过还没有最后竣工,大致建完了,还在施工。人们在玻璃墙里忙这忙那。楼里只有隔墙,基本上空空荡荡。”
女人以空穴来风般的声音吹了吹烟头,轻咳一声。“喂,我是不是要问点什么才好?”
“不问也不碍事,只要老实听着就行。”我说。
“也好。”
“我闲着没事,就站在那大玻璃墙前静静看墙里面的作业。我看的房间里面,一个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砌富有情调的装饰砖。因为他一直背对着我工作,看不清脸的模样。从身材和举止看来,像是年轻男子,瘦瘦高高。那里只有他一个,不见别人。
“梦中空气格外浑浊,就像篝火烟从哪里混了进来,灰蒙蒙的。但细细注视之下,空气竟一点点透明起来。至于是真的透明,还是眼睛习惯了不透明,我也弄不明白。反正我因此得以更清晰地看见房间的每个角落。年轻男子简直就像机器人,以相同的动作一块接一块地砌砖。那房间面积相当大,但由于男子砌得那么麻利,那么有条不紊,看样子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能砌完。”
我歇口气,睁开眼睛往枕旁玻璃杯里倒啤酒喝。女人为表示在认真听我讲话,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的眼睛。
“男子砌的砖墙后面本来是有墙的,就是那种粗粗拉拉的混凝土墙。这就是说,男子是在原有墙前砌装饰性新墙。我要说的,你可明白?”
“明白。做双层墙,对吧?”
“对,”我说,“是做双层墙。细看之下,原来的墙同新墙之间留有大约四十厘米宽的空间。不知为什么特意留此空间,因为这样一来房间岂不要窄小许多。出于好奇,我更加目不转睛地看那作业。岂料,看着看着竟好像有人影出现,就像浸入显影液中的照片上有人影现出一样。那人影夹在新墙和旧墙之间。
“原来是双胞胎!”我继续下文,“是双胞胎女郎。十九、二十或二十一岁,也就那个年纪。两人穿着我的衣服。一个穿粗花呢上衣,一个穿深蓝色风衣,都是我的衣服。她俩被关在四十厘米宽的空隙里,姿势显得很别扭,却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出自己很快就要被封死在里面,两人一如往常地喋喋不休。工人也像是没注意到自己正在把双胞胎封死,只管闷头砌砖。注意到的大概只我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工人没注意到双胞胎?”
“反正就是知道,”我说,“梦中反正就是知道好多事情。这么着,我心想无论如何非让这作业停下来不可。就用两个拳头狠狠敲击玻璃墙壁,敲得胳膊都麻了。但怎么使劲敲都没一点儿声音。不知怎么回事,声音彻底死了,工人自然意识不到。他仍以同一速度一块又一块机械地往上砌去。左手填缝,右手放砖。砖已砌到双胞胎膝盖那里。
“于是我不再敲玻璃墙,准备走进楼去阻止这项作业。可是找不到入口。那么庞大的楼居然一个入口也没有。我使出所有力气奔跑,绕大楼跑了好几圈。结果还是那样,还是没有入口。活生生一个巨大的金鱼缸。”
我又喝口啤酒润润嗓子。女人依然凝视着我的眼睛。她转了个身,乳房紧贴住我的胳膊。
“往下怎么样?”她问。
“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我说,“真的不能怎么样。怎么找都没有入口,声音又死了。我只好双手按在玻璃上干瞪眼看着。墙迅速变高——双胞胎的腰部、胸部、颈部,不久便将其整个儿淹没,直达天花板。这是转眼间的事,我完全奈何不得。工人堵上最后一块砖,收拾好东西去了哪里。惟独我和玻璃墙剩了下来。我真的奈何不得。”
女人伸出手,摩挲我的头发。
“经常如此,”我自我辩解似的说,“细节不同,程序不同,角色不同,但结果相同。那里有的只是玻璃墙,我没办法把什么告诉给别人,每每如此。睁眼醒来,手心总是玻璃墙冷冰冰的触感,好几天好几天都留在手心不退。”
我讲完后,她还在用手指摩挲我的头发。
“肯定是累了,”女人说,“我也同样,一累了就做不好的梦。但那同现实生活是不相干的。不过是身心疲劳罢了。”
我点头。
随后她拉起我的手按在她的下部。下部温暖而湿润,但这也引不起我的兴致,只是心里觉得有点儿奇妙。
我多给了她一点儿钱,说是对她听我讲梦的谢意。

“是我想付。”我说。
她点头接过钱,塞进黑色手袋,“咔”,随着一声满好听的卡口响,手袋合上。我觉得我的梦也好像被她塞了进去。
女人下床穿上内衣,套上长筒袜,裙子和短衫也都穿好,站在镜子前梳理头发。站在镜前梳发时的女人看上去全都一个样。
我赤裸着在床上欠起身,呆呆看着她的后背。
“我想,那肯定只是梦。”女人临出门时说。她把手放在圆形拉手上想了想,“应该没有什么值得你放在心上的寓意。”
我点了下头,她随即走出,传来“嚓”一声关门响。女人身影消失后,我仍然仰躺在床上,久久注视房间的天花板——随处可见的廉价宾馆的随处可见的廉价天花板。
透过窗帘缝隙,可以看见色调似含潮气的街灯。不时掠过的强风把十一月冻僵的雨滴不经意地摔打在玻璃窗上。我伸手想拿过手表,又嫌麻烦而作罢。现在几点并非大不了的问题。想来,我连伞都没带。
我边望天花板边想古代传说里沉没于海中的大陆。何以想起这个,却是不得其解。大概是十一月冷雨拍窗的夜晚没带伞的缘故吧。抑或因为以仍残留着凌晨梦境凉意的手拥抱姓甚名谁都不知晓的女人的肢体——什么样的肢体都想不起来了——亦未可知。惟其如此,自己才会想起远古沉没于海中的大陆传说。光线惨淡,声音沉闷,空气湿重。
已经失去多少年了呢,到底?
可我已无法记起是哪一年失去的了。想必在双胞胎离我而去之前便已失去。双胞胎只不过向我告知了这一点。在我们能够对已经失去的东西予以确认的时候,所确认的不是失去它的日期,而是意识到失去它的日期。
也罢,从头开始好了。
三年。
三年这一时光把我带到了这个十一月的雨夜。
但我有可能一点点地习惯这个新的世界。或许要花些时间。时间会使我将自己的血肉骨骼一点点塞进这沉甸甸湿漉漉的宇宙断层中。归根结底,人会使自己同化于任何环境,纵使再鲜明的梦,终归也将为不鲜明的现实所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曾有过那样的梦这一事实本身,迟早都将无从记起。
作者介绍

村上春树(1949— ),日本著名小说家和翻译家,在世界文坛享有较高的声誉,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出生于京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电影戏剧系。代表作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1Q84》等,并有大量的美国文学译作。曾获群像新人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弗朗茨·卡夫卡奖、耶路撒冷奖等多种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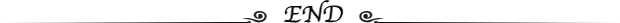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