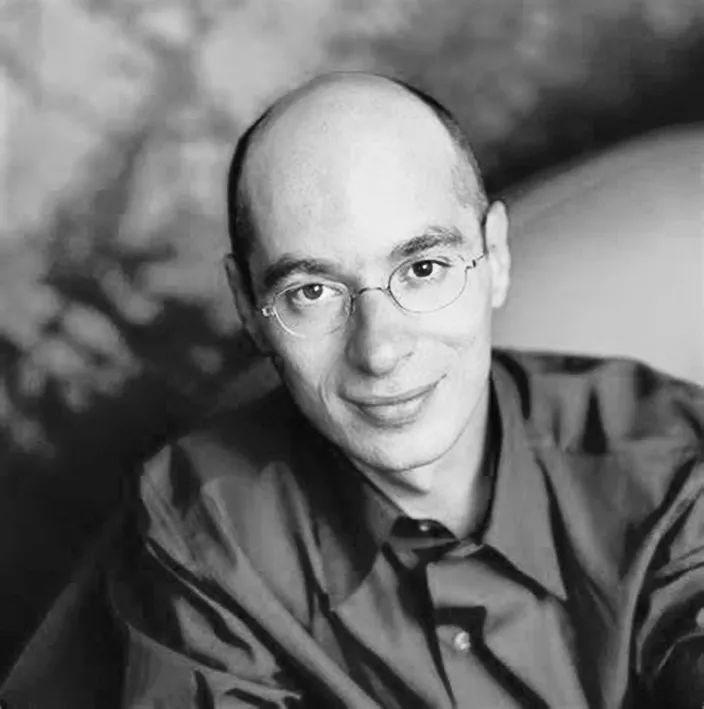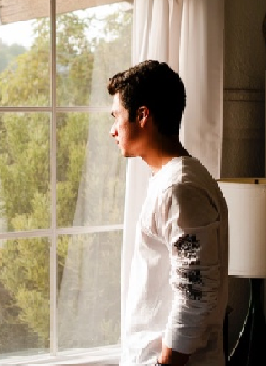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后疫情时代下的生活:法国小小说四篇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法国《读书快报》网站2020年4月举办了一次小小说征文活动,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下的生活”。四十位犯罪悬疑小说家试图每天用一个短篇来想象未来。
活动负责人除了要求作家们将篇幅控制在3到6页之间,还希望他们的作品尽可能地乐观——对犯罪悬疑小说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但征文的作者之一——法国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贝尔纳·韦伯——却说黑色小说作家的作品未必一定悲观或消极:“我总是在写作中尝试积极的态度,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让人焦虑,而是为了给出替代方案。在看起来是绝路的地方,我想告诉大家,还有路可走。我相信文学的拯救功能,也相信文学的逃避和幻想功能。我最起码可以写一个小小说来表现这种想象的力量。”
此处选译的四篇小小说,都是作家蘸着反思和想象的墨水,写下的对后疫情时代的预想和希望。贝尔纳·韦伯(Bernard Werber)让人类迁往地下展开新的生活;大卫·卡拉(David Khara)邀请我们在这个被四面墙限定的世界里,与势所必然的孤独结下情谊;英格丽·阿斯提尔(Ingrid Astier)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分享中,找到了抵御媒体疯狂输出的焦虑情绪的免疫力;让-克里斯托夫·提克西耶(Jean Christophe Tixier)则暗示,当经济从疾驰的马背上跌落下来时,人类或可考虑一个优选项:纯粹简单的田园生活。
译者
贝·韦伯(1961—),法国作家,其影响力最大的作品《蚂蚁帝国》三部曲被国际书评界誉为幻想文学的巅峰之作。
他们说,这要持续三个星期。
说这话的时候是三年前。
最后,大家习惯了闭门不出的生活。
其实,人类能适应一切。
我们已从智人变成了被禁足的人。
史前人类走出洞穴,遍布整个地球,最后发现自己被困在客厅里——这个能解决生存全部问题的空间:沙发、电视、遥控器、电脑、智能手机、罐头、冷冻食品、微波炉,还有无人机配送保证供给。
但这种病毒越来越不像“一场简单的流感”,而是愈发成为一种难以理解的“复杂玩意儿”,何况它还在不停变异。
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还有一些街区爆发骚乱,起因是穷人袭击了杂货铺和药店。
终于,管控措施不得不进一步升级。
政府宣布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共和国安保隔离”,简称CRS计划。
“共和国”“安保”“隔离”——三个词中的每个词都相当让人安心,但“共和国安保隔离”计划却是指迁往地下生活。
一开始只有地铁线被征用。他们进行了清洁和消毒,然后在隧道里安置住宅。
所谓住宅,就是一种圆形的塑料小房子,有两间卧室、一间带电视的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
医生们以为缺少光照会让人抑郁,实则不然,因为他们还装了视屏假窗,能不间断地投放天空、山川、花园、森林的影像。
至于地铁的出入口,全被封死了,这样就不会有人试图回到地面了。
于是,在危机爆发三年后,全人类都转入了地下生活,有人称之为“鼹鼠高度”的三年。
统治者终于能够掌控一切,我们终于靠着地下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百分百隔离。
但要管理好在特大城市地铁线上的八十亿人,实属困难。需要出台全球性战略。被称为“包厢”的住宅,由连接它们的通道隔开。
站台充当广场,是食物和药品的来源。
还是那句话,人的适应能力比政要们想象的强。我们习惯了透过假窗心满意足地观赏椰树摇曳的海滩。
就这样,一种新兴人类——“鼹鼠高度”人类——逐步在地下安家落户。
等这个阶段终于整合好了之后,病毒的影响才开始减弱。仿佛这只怪兽终于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让人类从地面消失。
出乎意料的是,新兴人类在地下的新环境中过得还不赖。大直径钻头使得在隧道以外扩建新的通道成为可能。
使得建立更宽敞的“包厢”成为可能。
至于地表上的生命,好吧,人类一不在,野生动植物自然就复辟了。
借助无数潜望镜,我们得以窥探它们。
有自由奔跑的马,有像狼那样成群结队的狗,还有狼、熊、野猫、猞猁。鸽子——这种过去最常见的鸟——与成千上万叫声惊人的无名珍禽争鸣。园林已长成植被更加丰沛的茂林。从酸度下降的海水中冒出的鱼儿洋洋大观。珊瑚礁又形成了。气温下降后极地的冰盖重新出现,幸存的北极熊得以繁衍。


大·卡拉(1969—),法国作家,前法新社记者。他的小说擅长在史诗般的情节中混合历史与幻想元素,其最新作品为《D-X计划》。
她在封城前不久来到我身边。
带着伊娜丝·德·拉·弗拉桑热【1980年代最出名的法国模特,法国政府曾以她为原型塑立玛丽安娜(法国的“自由女神”)雕像】的优雅气质、芬妮·阿尔丹【法国演员。因主演法国新浪潮大师特吕弗的最后两部作品而登上国际影坛,也是特吕弗最后的人生伴侣】的高贵笑容。不讳言地说,我不曾有一秒钟觉得自己可以拒绝得了她。
纵是在这个爱与柔情都要被控以反人类罪的时代,只要她在,就足以让我幸福。
当清点感染和死亡人数的铡刀随夜幕落下时,是她握紧了我的手。
当虚假新闻的炮制者及其无脑的兜售者使我的怒气蹿火时,是她让我平心静气。
当有人恬不知耻地戴着医护人员急需却不得的口罩和手套、推着装满鲁斯图【一家法国知名食品公司】的食物和厕纸的购物车时,是她叫我息事宁人。
是她给我以希望,当为致敬医护人员的掌声响彻窗口时,万众而一心,我们再也不准“白衣战士”独自阻抗命运。
是她借我以肩膀,好让我为在意大利上演的悲剧【应是指2020年春天意大利新冠疫情爆发、一时成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段时期】垂泪,即使这个我全心全意热爱的国家打败了齐达内【法国著名足球运动员】的法国,即使好为人师的法国在轮到自己大难临头前曾对它大肆嘲讽。
我与她一道分享了无尽空间的永恒沉默——多年来我都沉浸其中、至死不二,以致忘记早在病毒出现之前,利己文明就已病入膏肓、人将不人。
她支持我戟指小说家的失格,他们在花园环绕的豪宅里倾吐禁足生活的折磨,还能有廉租房里的读者捧场。
当伟大的医生和无名的护士因睡眠不足而双目通红、因被迫做出谁死谁活的抉择而不得安生时,她陪我一起为之流泪。这条依仗他们筑起的战线上还有多少险滩?我们这些躲在背后的人无力想象。
当阿斯克勒庇俄斯【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的信众历经数周苦战,令共和国总统下达解封令时,她用尽全力拥抱了我。
当我开门去见久违的挚友时——这些跟我一样对我们宇宙的构成充满热爱和好奇之人——她用调皮的目光看着我,许诺我来日再见。
她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爱情。
是我的孤独。

英·阿斯提尔(1976—),法国新一代犯罪小说家,代表作有《地狱站台》《死亡天使》等。
翌日,暴风雨来袭,恐将天空撕破。雨从云里溅出,似要刺穿高空。世界随波逐流,再无人掌舵。谁还能指望这个该死的地方?谁去管它谁就摊上了信使的脏活。“不要杀信使”【古代波斯一国王只愿意听信使带来的好消息,若信使带来的是坏消息,便直接将其杀掉。久而久之,信使不再给国王带回负面消息,沉浸在好消息筑成的幻觉中的国王最后走向了亡国】这句源自希腊悲剧的警句已融入了日常生活。自三月十七日起,我们不再隔岸观火,而是身临其境。这下子,那些令人丧气的坏消息,人人都听了个够,一些人更是收到了致死剂量的噩耗。
雨可不在意。它有自己的意志。也许它忙着洗涤城里的污糟之气。风扇打着窗户,雨点噼啪作响。巴黎在灰暗中隐没。
然而,封城已经结束。官方发布,白纸黑字。吉鲁简直不敢相信,他在等着辟谣。解禁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屋外,雨势越来越大,仿佛在警告人们不要轻信。远处,建筑物不知所措地站在雾中。
吉鲁驱散满脑的迷雾。他把视线移向街道,好把自己锚定在现实里。人群吸引了他的注意。有些人向天空张开双臂,迎接弥赛亚的圣雨。吉鲁套上长袖T恤,眼睛却无法从窗外移开。雨雾中影影绰绰有一些黑影。这些居民,平时哪怕牛毛细雨,都避之不及,现今却对雨天的魅力毫无抵抗力。
街道在朝他们呼喊,自由在向他们召唤。
又是一阵暴风压城。
天刚亮,消息就得到了证实。“结束”一词有股独特的味道,就像影片刚放映完毕。这条解禁通知,吉鲁在手机上反复确认。离开这该死的影院还要点时间。没人能不用适应就走出封城令下漆黑的包厢。
是的,需要花些时间,方能寻回生活坐标。
方能不再对希望抱有怀疑。
他打过跑步的主意,却还是没有行动;他安抚自家的狗,却并未拿它作出门的借口。勇敢的鲁皮,勇敢的边境牧羊犬。封城一个月后,邻居们纷纷按响他家门铃,说要轮流以遛狗为由出门。鲁皮也不计较,它叫唤着迎接每一次出门。
维尔达还在睡觉。他不敢叫醒她。并不是他不想告诉她解封的消息,而是因为他心有所忌。这几个月,某个词的根须已经不断疯长,它捅入了他们的内脏,带来百般折磨;这个词不再只关联单个国家,而是牵涉整个世界。
必须承认,吉鲁害怕的就是好消息。每念及此,他就深深自责。哪种药能把他毒哑,好让他不敢说出“终于要重新规划了”这句话?他们像狗一样挣扎,才在精神抑郁与经济衰退伴生的诅咒中苟活下来。开车去海边,就像维尔达反复念叨的那样。迎接泡沫,迎接拍在布列塔尼圣马太岬角上的万钧波澜。他们会登上灯塔塔顶,甚至可能会去到莫莱讷岛。忘掉过去只能享受一小时的阳光、一小时的新鲜空气。他会租一辆车,车上载着维尔达。鲁皮终于要见到大海了。
就他们目前的状况而言,养鲁皮比养孩子更理智。他们缺钱用。如有必要,他们会在睡袋里将就,可能还会搭顺风车回家。至于吃的,就靠罐头解决,他们比任何时候都了解罐头的品牌。但大海,他们得亲自去看。要是为此不得不吃两天海藻沙拉,他们也将照吃不误。
吉鲁仔细听维尔达的响动。在这间窄小的公寓里,任何声音都能被快速分辨。但是没有动静,她还睡着。禁足让他们疲惫不堪。有天晚上,她焦躁得不行,吉鲁不得不夺过她的手机。在这之前,恶对他来说就像是《指环王》里黑魔王索伦用烈焰与钢铁铸成的魔戒,以及那座饥渴的摩多火山。随着冠状病毒的爆发,他才恍悟,噩耗这支大军才是人类更大的祸害,它比死亡人数还可怕,后者尽管恐怖,但仍是一个事实。然而,谣言不止于此。毫不夸张地说,维尔达在各种信息的轰炸下,日渐枯涩。
恐惧令她上瘾。她的大脑就像被嫁接到了手机上,一刻都不离开。吉鲁受够了在维尔达晃眼的手机屏幕作伴下入睡,受够了每晚都要劝她别喝到烂醉。
舆论的纷争、恐惧和焦虑支配着维尔达的生活节奏。黑色潮水般的新闻冲走了她的思考,除非她能关掉手机。他们不再谈爱情、论未来,而是一起倒数着剩下的日子,或争论拉乌尔医生【法国传染病学家。法国新冠疫情期间,曾公开痛批法国抗疫不力,但也曾向公众力荐未经证实有效的新冠治疗方法】是救世主还是巫师,或打赌能不能买到洗衣粉和卫生纸。每隔一小时,他们就要确认一遍家人有没有被感染、朋友能否挨过难关。他们难以容忍条件式【法语条件式表示猜测、想象、不确定的语气等】,无法接受被告知“很可能”或“有可能”……生活中一切皆有可能,说不定就有一只手拉住脱缰的世界,让经济一夜之间停滞。
吉鲁还记得那天,维尔达得知巴黎有五十四个地铁站关闭,连快铁【在巴黎,地铁指小巴黎市内运行的地铁,快铁指联通小巴黎和大巴黎之间的交通】也遭停用,只剩高速火车还在转移病人。交通,作为贯通庞大国土的血液,正在凝固。似乎一切都在报废。
就是那天,吉鲁看着维尔达把自己封闭起来,渐渐流失了笑容和幽默。忒修斯的黑帆,让埃勾斯死于非命【埃勾斯之子忒修斯准备前去克里特岛杀死怪物弥诺陶洛斯,为雅典解除进献童男童女的可怕贡赋。临行前埃勾斯与忒修斯约定,若忒修斯成功杀死了怪物,返航时就在船上换挂白帆。忒修斯成功解决了弥诺陶洛斯,却忘记了与父亲的约定,由于忒修斯所乘船只在起航时挂的是黑帆,在海边盼归的埃勾斯见船上挂的仍是黑帆,误以为儿子已死,在悲痛中跳海自尽。埃勾斯所投之海因此得名爱琴海,意即“埃勾斯海”】……媒体何时才能明白他们所散布的痛苦?你不能往火药桶里硬塞而不顾爆炸的危险。
当吉鲁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成功使一棵仙人掌断了气。那可是经得起上万个暑热天的家伙。面对发育不良、彻底干瘪的仙人掌,他意识到自己何等白痴,又何等愧疚。他为怠惰无为而自责:他那时满脑子寻思的都是找人喝酒、考试和钱包,却不愿为了一株植物的生死而每天多花两秒钟。最难的是把仙人掌扔进垃圾袋。塑料袋发出病态的窸窸窣窣声……他将它扬起,再松开。虽然这很傻,可他在打结的时候,意识到了“责任”二字。
维尔达绝非仙人掌。她是他遇到过的最温柔的女人。刺都被她藏了起来。在钢筋水泥楼里经历了一个月的禁足后,他们成功地化解了压力。吉鲁控制住了局面。生平第一次,他在手机上遍寻菜谱。为什么他会去做玛德莱娜蛋糕?只有心理医生知道。
总算,面团鼓出了漂亮的金色胸脯,馨香缭绕。吉鲁甚至还往里面加了橙皮,公寓里的味道不输任何香薰蜡烛。神圣的气息在维尔达身上施展出奇效。她满怀爱意与惊喜亲吻了他,嘴唇上的黄油味道让吉鲁一生难忘。
两个月的禁足期后,吉鲁有三个朋友要分手了。这是新冠造成的附带伤害。感情的战争,让禁足在家成了地狱。不是人人都能适应同居生活的高压锅。皮埃尔,他最亲近的朋友,仅在禁足两周后就听见妻子说,做他的狱友,忍无可忍。他在掰着指头数着日子。
吉鲁回过神。门后,床板木头咯吱作响。维尔达马上就要醒了。屋外雨势渐弱。但他还是害怕,胃像是打了结。阳光迟迟不敢露脸。
鲁皮烦躁地叫着屈。小狗不明白,难道自己不是已经可以出去玩耍了吗?吉鲁拍拍它的脑袋,要它别叫唤。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跳到那些受苦受难、那些夜以继日拯救生命的人背上开派对,不,绝不能这么做。但今天确乎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他们在四月不曾有过的春日。真正的花蕾,含苞待放。
吉鲁在找好消息,不会在乱风中被刮跑的好消息。他在找吹开夏日门扉的春日煦风;在找能让他从冲垮他的大风大浪中挺身而出的办法。
他在找一句能让人直面希望而不却步的话。
他去到卫生间刷牙,看着白沫,竟笑了。焕然一新的感觉真好。他已经把这种快乐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找到了他要宣布的好消息。
他边咒骂开裂的地板,边追着想第一个跳上床的鲁皮,他凑近维尔达的耳朵,用手指卷起心爱之人的一绺发丝,缠在自己的无名指上。一枚神圣的婚戒。
他想要一个第一天,一个真正的一天。
迈向明天的一天。
“维尔达,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个好消息,不会在任何屏幕上被报道。


让-克·提克西耶(1967—),法国侦探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耽误十分钟》系列荣获多项文学奖。
疫情爆发后的日子与此前没太大区别。可能迫切感更明显了,但还不至于引起震荡。筐里的土豆多装了一点,生菜少放了一点。平日爱迟到的访客亦纷纷早起。
我收好货款,帮客人把商品塞进已满满当当的后备箱,里面的卫生卷纸与大包小包的面粉、面条挨肩擦背。莫名的焦虑,可耻的脆弱,当这些通常会被谨慎埋藏、小心掩饰着的东西暴露出来时,我竟觉得心有所动。
等车开走后,我关上谷仓大门,喂狗,检查羊圈,再到温室转一圈。太阳也落山了。
第二天,气氛已然不同。焦躁、苛求、非难、刻薄。从十几公斤土豆,到二十几公斤土豆。当有人开口要五十公斤土豆时,我的指关节都绷开了。那人喃喃地找了个什么借口,回到车上,飞飚而去,扬起的砂砾在拖拉机车棚的瓦楞铁门上撞出不和谐的乐音。
撞出最后的挑衅、最后的响动。
我喂了狗,检查了羊圈,去温室里转一圈。完事后,我卷好一支烟点上,西向而望。一只母鹿越过田沟,停在树林边缘。听到狗吠,她立即跑开。我闭上眼,仰头,又睁开眼,面朝宇宙的浩瀚。只见天上亮起第一个星点,转瞬又冒出了其他闪光。
早上,我把能摘的都摘了,然后装进筐,再竖几块小板,标上每公斤或每捆的价格。可不见来人。不论是那天还是之后的日子。
我继续摘生菜、挖胡萝卜、挖土豆、割韭菜以及第一茬小红萝卜。我又编了些筐,把价签贴在上面。要想改掉三十四年的陈规旧习是不容易的。我给几日前的菜筐换上刚摘下的菜,把不新鲜的搬到推车上,去林子边的田沟里倒掉。
一连几日重复同样的步骤。摘菜、装筐、倒光。
我疲惫地关上大门,用铁链上锁。
后来,有几位访客兼买家在我这儿吃了闭门羹后纷纷折返。有一人还按了喇叭,一连三次,其中一次按得特别执着。当然,他还是同其他人一样离开了。谣言漫天飞也好,至少能让人打发无聊。
我给狗解开链子,它不解地望向我,还一路跟在我身后,捕捉着我的每一个手势。
在温室里,我给自己腾出一个角落,围好短木桩和栅栏。然后我打开羊圈,放它们自由进出。
狗盯梢久了,就累了。它跑去林子里,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回来。
空气里不再弥漫柴油的气味。空中不再残留飞机的尾痕。附近路上不再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在那些坑坑洼洼的林中小路上,不再忽闻摩托车或四轮车的爆音,不再见到一个猎人,不再听到一声小孩的尖叫。
只有越过越长的日子,徐徐升落的太阳,叶芽,花蕾,找寻细枝和羊毛的飞鸟,以及越来越不着家的狗。
终于在某天,屋外反成了最生气蓬勃的地方。我没有再回屋吃饭睡觉。外面的世界就是我的家。至少有一部分属于我。
有鸟,各种的鸟,越聚越多。还有鸭子不时经过。白鹬也过来溜达,啄食着前天晚上刚被一群野猪翻过的地面。我看到了野兔,也瞥见了狐狸。
还有我的山羊,他们已经认不出我了,一副傲慢的自在模样。
蜗牛和蛞蝓回来了,象虫也是。我们相互对视,套着近乎。虫子喂饱了小鸡和刺猬。小型啮齿动物最后都进了猫头鹰和蛇的肚子。
不等黎明的曙光,我就在唧唧喳喳、咿咿呀呀的鸟叫中醒来。一只动物征服了另一只动物。虞美人舒展开片片花瓣。
到处都长满了杂草。我的胡须和头发也是。
无论东西,亦无所谓南北。只有一条地平线和太阳无尽的运动路线。没有了小时或分秒,没有了日子或星期,只是时间在流逝。
我开始梦到从未见过的风景,它们不用像人类绘制的地图那般轮廓清晰。我想象大自然无休无止的高潮,任何农药都没法令它消停。嫩芽顶开一条条切割自然地貌的沥青公路,愈合着每一处修路遗留的创口。藤蔓攀上柱石,勒断了以坚不可摧著称的水泥;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由彩绘大玻璃锻造的大教堂,曾供奉着人类为信仰永生而召唤的各路神圣,如今亦纷纷折腰。有时,巨大的撞击声打破了平静。有什么倒了,一座塔还是一座桥。总之是些为传世而造之物。传一世之时,这速朽的一世。然而这个世界,只要一粒种子就能长成一棵树,而一棵树又能播种下新树,其浓荫又泽被其他动植物。植物、野兽和昆虫不再现身于任何课堂,因为没人再以了解它们的名义而去识别、登记或解剖它们。每只小虫子节欲知足,吃得不多也不少。
某天清早,飞机在空中拉出一道尾迹,汽车的杂音盖过大自然的低语。风为我带来了远处某只管弦乐队的回响。
我把自己不大的地盘周围的木桩和围墙拆了,呼叫还没回来的狗,接着点上一根烟。
我回屋将百叶窗一一关上,临了检查一下是否已锁好了入口大门。
庆典,借着重获自由的名义。去放纵,以驱散累积数周的颓丧。去躁动,以营造生活恢复如初的幻梦。
又要开始捣乱了,又要重启对世界的毁灭了。但不必有我。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5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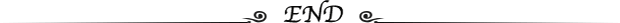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