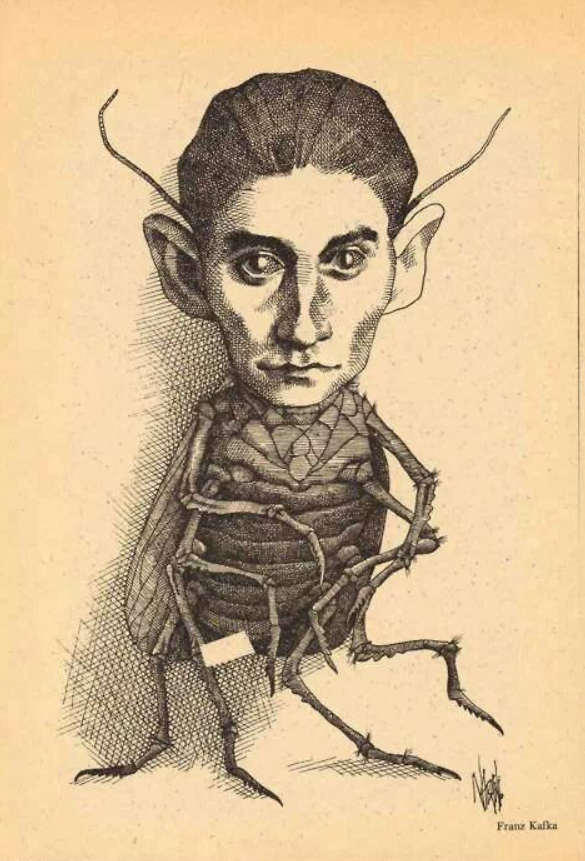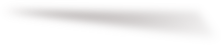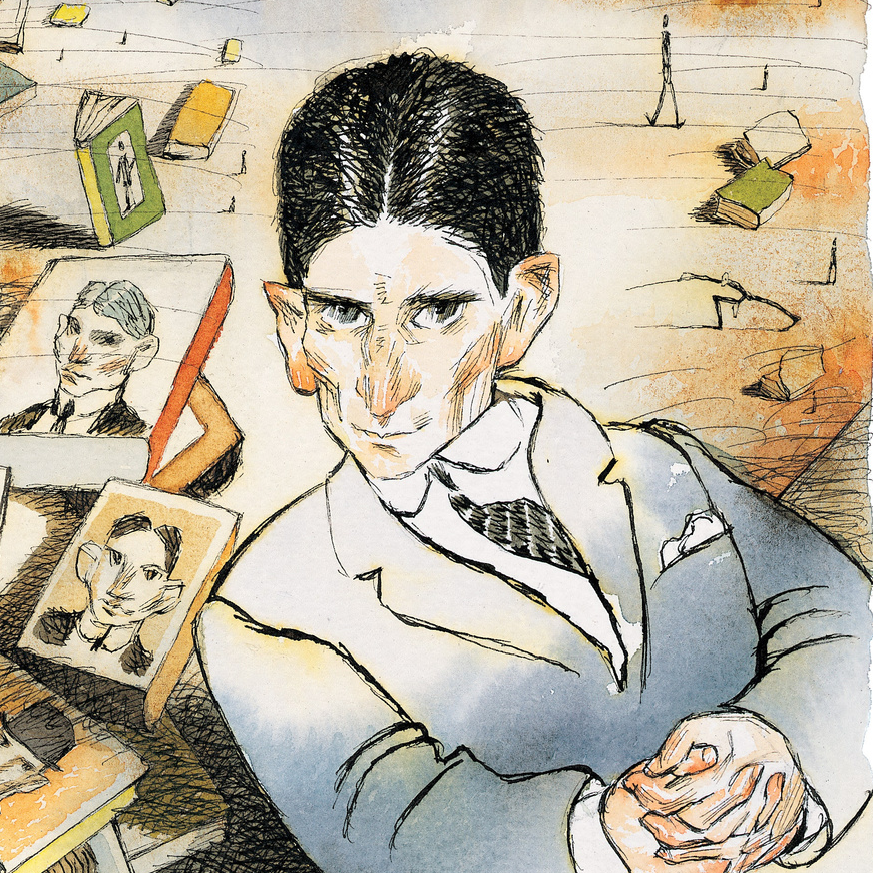一个农夫在公路上拦住我,求我跟他一起回他家里去。或许我能帮个忙——他跟他妻子闹翻了,他俩一直争吵,毁了他的日子。他还有几个笨笨的小孩,不太有出息;他们老是游手好闲,要不就恶作剧。我说我很高兴跟他一起回去,不过我陌生人一个,能否帮得上他这个忙,令人怀疑;我也许能让孩子们做点有用的事情,不过对于他妻子我大概会束手无策,因为妻子动辄吵闹通常是由丈夫的某种品性所致,而且他对眼下的情形不满,说明他大概已经尽力改变过自己但没能成功,那我怎么可能会更加成功呢?至多,我能做的就是把那妻子的怒气转移到我自己身上去。一开始,我更多的不是冲着他而是冲着我自己说话,可后来我问他,他会用什么来补偿我的麻烦。他说,我们会很快达成某种协定;如果发现我确实管用,我想要什么可以自行要价。冲着那话,我停下来说,这种含糊的承诺是不会让我满意的——我想跟他就每月能给我点什么达成一个明确的协定。他对我竟然向他开口要什么月付工资感到惊讶。而反过来,我对他的惊讶也感到惊讶。难道他以为花我两个小时就能修好他们俩花了一辈子搞砸了的事情,难道他指望我在那两小时过后领一袋干豌豆、亲一下他的手以示感谢、束紧我的破衣烂衫、在结满冰的道路上继续赶路?绝对不成。农夫默默地听着,低着头,但神经紧绷。我告诉他,我是这么看的,我得花很长时间跟他待在一起,先摸熟了情况,考虑各种可能改进的地方,然后我得花更长的时间确立适当的秩序,如果事情有可能做到这一步,而到那时我会是又老又累,什么都干不了,只能静养和领受有关方面的谢意啦。
“那是不可能的,”农夫说,“你刚才在这里提议住到我家里去,甚至有可能最终把我赶出家门。到那时我的困境岂不比现在更糟。”
“除非我们彼此信任,否则我们无法达成协定,”我说,“难道我还没表明我对你的信任吗?我能得到的不过是你的口头承诺,你该不会出尔反尔吧?我按你的意愿帮你安顿好了一切,你该不会无视你所有的承诺,让我卷铺盖走人吧?”
农夫看着我说:“你绝不会让那样的事发生的。”
“你想做什么随你便,”我说,“愿意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但别忘了——我是出于友谊才对你说这番话的,男子汉之间不讲假话——如果你不带我回你家去,你在家里也忍不了多久。你怎么跟你妻子和那些孩子继续生活下去?而且,如果你不想冒这个险带我回你家去,那你何不放下一切,放下在家过日子还继续会有的所有麻烦,跟我走。我们一起上路,你对我心存疑虑我不怪你。”
“我没有那样做的自由,”农夫说,“我跟我妻子一起生活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一直很不容易,我甚至搞不懂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可尽管如此,在还没试遍可能让她变得让人受得了的所有办法之前,我不能就这么遗弃她。然后我在路上看到了你,于是我觉得我也许该做最后一次努力,和你一起。跟我走吧,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的。你想要什么?”
“我要的不多,”我说,“我并不想乘人之危。我想要你雇我给你做一辈子的长工。我能做各种各样的活儿,我对你会非常的有用。不过我不愿你像对其他劳工那样对待我——你不要对我下命令,必须允许我去做我喜欢的活儿,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什么都不做,随我的便。你可以叫我去做某些事情,只要你温和有礼,而且,如果你察觉到我不想去做,你就得接受事实。我对钱没要求,但会要符合当下标准的衣服、床褥和靴子,必要时换新的;如果哪样东西村里买不到,你就得进城去买来。但不用担心,我现在穿着的衣服应该还能再穿好几年。我能得到标准劳工的价钱就满足了,只不过我要求每天有肉吃。”
“每天吗?”他插问道,似乎对所有其他条件都还满意。
“每天。”我说。
“我注意到你的牙齿非同寻常,”他说。为了替我对报偿非同寻常的要求做个开脱,他甚至还把手伸进我嘴里去摸我的牙齿。“非常锋利,”他说,“像狗牙。”
“呃,不管怎样,每天都有肉吃,”我说,“加上跟你一样多的啤酒和烈酒。”
“那可太多了,”他说,“我酒喝得很多。”
“那样更好,”我说,“然后,你要是勒紧你的裤腰带,我就会勒紧我的裤腰带。也许就是因为你家庭生活不愉快,你才喝得那么多。”
“没有,”他说,“那些为何要扯到一起呢?不过我喝多少你就有多少喝,我们一起喝。”
“不行,”我说,“我拒绝跟别人一起吃饭喝酒。我要求一个人单独吃喝。”
“单独?”农夫惊讶地问道,“所有这些愿望让我头晕目眩。”
“不算太多,”我说,“而且我快说完了。我要灯油,好整夜在我边上点一盏油灯。我这里带着盏油灯,只是很小的一盏灯,几乎不费任何灯油。实在不值一提,我只是为了完整起见才提一下,以免我俩之间以后发生争执;我不喜欢在涉及报酬的事情上出纰漏。其他任何时候,我是个最温和的人,可要是先前商定的条款遭违约,我会发脾气的,记住这一点。我要是不能丝毫不差地拿到我赚取的一切,我有能耐趁你睡觉时放火烧了你的房子。但你无需否认我们已经明确达成的共识,尤其是如果你偶尔出于关怀之心送我点礼物——不必值多少钱,零碎小玩意儿就行——我会倾尽所有办法对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并帮上你的大忙。除了我刚给你讲过的以外,我没有其他奢求,不过八月二十四日,我生日那天,还要一桶两加仑的朗姆酒。”
“两加仑!”农夫叫了起来,双手合在了一起。
“是的,两加仑,”我说,“那不算多。你大概以为你可以逼我降价。可我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限度,当然是出于对你的考虑;如果哪个陌生人听到我们的谈话,我会难为情的。我们刚说过的那些话,在陌生人面前我是不可能说得出口的。所以没人会听到我们的协定。得了,无论怎样又有谁会信呢?”
但那农夫说:“你最好还是赶你自己的路去吧。我呢还是回家想办法跟妻子和好。没错儿,我最近经常揍她——我想对她少动点拳头,她或许会感激我——我也经常打那些孩子;我总是从马厩拿鞭子来抽他们。我会稍稍手下留情一点,或许情况会好起来。坦白地讲,我以前那样试过,但情况一点也没变好。可你要价太高了,即便那不算高的话——但是不,它是这交易无法承受的,不可能的,每天有肉吃,两加仑朗姆酒,就算有可能办到,我妻子永远也不会允许的,如果她不允许的话,那我可做不到。”
“那干什么还讨价还价这么长时间。”我说。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