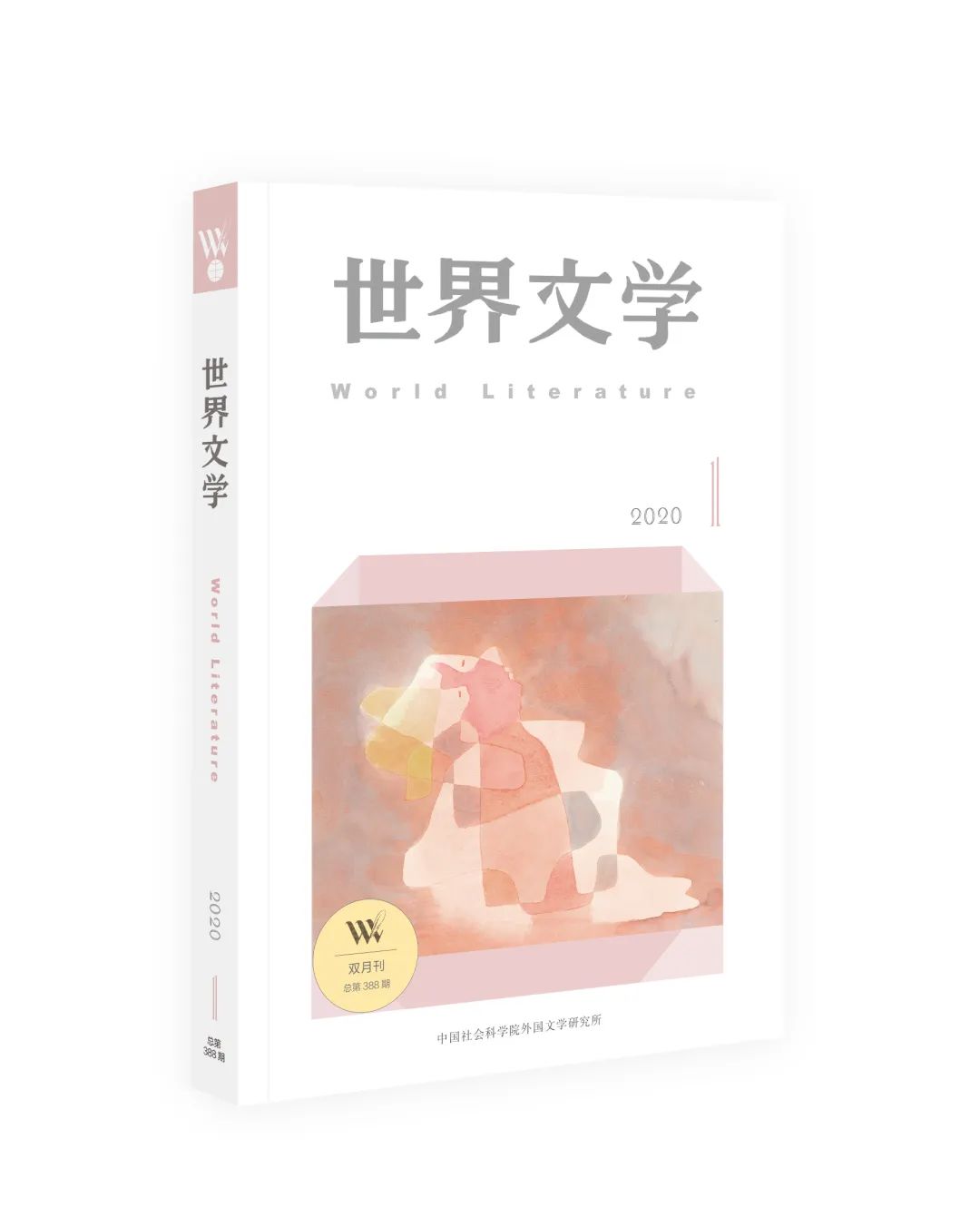众家言说 | 李少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吗?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近年来,中国诗人们接二连三地获得了一些国际奖项,比如多多获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北岛获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花环奖”,杨炼获意大利卡普里国际诗歌奖,翟永明获意大利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日前,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获得了“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其颁奖词是这么说的:

他的诗富有文化内涵,事实上深深植根于彝族的传统。他的诗歌创作也提升了通灵祖先的毕摩祭司所把控的远古魔幻意识。……他诗中的每一抒情场景均成为一则部落故事之延续,似在特意宣示他的部落之荣光。诗人意识到,他的作品脱颖而出,正是为了完成他渴望的使命。……他本可围着篝火舞蹈,站在山巅远眺,可他的命运却是跻身于世界诗人之列,宣示他那偏居地球一隅的故土和人民之荣光;他本可在小茅屋里歌唱,远离寒冷的宇宙,聆听长辈和巫师讲故事,可他的工作却是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存在的基本真理:“我是彝人!”
这一份颁奖词透露了一些很有意味的内容。文学界早期曾强调“文学是民族的秘史”,人们以抒写本民族的传统、历史和现实命运为目标,潜入研究,精心构画鸿篇巨制。但后来风气一变,后现代主义将一切宏大叙事彻底解构,出现一种无根无魂的小轻松小伤感的所谓国际型文学和诗歌。从此,突出所谓无主题无中心从而无主体的“漫游情调”和“普遍人性”的现代书写,贬低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传统,虚无主义畅通无阻,并成为时尚和潮流。可是,这一次,吉狄马加赢得尊重的,却恰恰是其“民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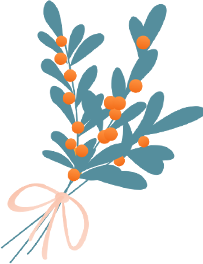
吉狄马加是一个彝族诗人,背后有着强大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其诗作也有着浓郁的史诗性和民族风格,并夹杂着彝族独特的创世神话和文明特色。吉狄马加的一些诗歌里,总是透露着彝族民族性的一些独特元素,比如吉狄马加经常写到“火”,了解彝族历史文化的人都熟知,彝族有崇拜火的传统,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这样叙述火的来历:
天上坠下一个火球,掉在恩接介列山,燃起熊熊大火。九天烧到晚,九夜烧到亮。白天烧得黑烟滚滚,夜晚烧得火光闪闪。天是这样烧,地是这样烧,为了创造人类燃,为了诞生祖先烧。
火是彝族的神圣之物,彝族用火作为图腾符号,甚至有专门的“火把节”。背后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彝族长期刀耕火种的历史,再加上山高天寒,火既可抵御野兽攻击,也可防寒驱寒,所以彝族对火的依赖性很大,火团结凝聚了彝人,有火的地方就有人,就是家。吉狄马加经常写到“火塘”这个词,因为彝族有“生于火塘边,死于火堆上”的说法,人的一生都离不开火。在《彝人谈火》一诗中,吉狄马加写道:

给我们的血液,给我们土地
你比人类古老的历史还要漫长
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慰藉
让子孙在冥冥中,看见祖先的模样
……
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你都会为我们的灵魂
穿上永恒的衣裳。
“给我们的血液,给我们土地”这两句,可以理解为火既让人热血沸腾,充满生命激情,同时,彝人也借助火战胜其他物种,开拓领地。而最终,人会在火中获得永恒,“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你都会为我们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因此,火是神秘的,它甚至是诗的源头,吉狄马加在《被埋葬的词》中说:“我要寻找的词/是祭师梦幻的火/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吉狄马加的诗歌里,处处都有彝族生活的痕迹和对周边事物的歌咏,比如他写大凉山的岩羊的诗歌《古里拉达的岩羊》:

在我的梦中
不能没有这颗星星
在我的灵魂里
不能没有这道闪电
我怕失去了它
在大凉山的最高处
我的梦想会化为乌有。
在这里,神奇的岩羊,成为诗人的寄托和希望,总在山顶高出的岩羊,仿佛一个精灵,携带着诗人的梦想,也激发诗人的想象力,唤起诗人内心的激情。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彝族的爱情表达方式也是独特的,在《回答》一诗中,一位女子的绣花针丢失了,请诗人帮忙找找,而诗人如此回答:“我对她说:/那深深插在我心上的,/不就是你的绣花针吗?”诗中随时透露出彝族特有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吉狄马加的诗,奇妙地显现了民族性的传统是如何在当代优秀诗人的个人笔下得到充分的展示、表达和提升的。诗,真的可以成为民族秘密的传递通道。




二十多年前,汉学家宇文所安就有所预见,他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批评中国某些当代诗人们的“世界诗歌”幻象时,尖锐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在塑造“世界诗歌”方面,尤其在第三世界诗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有趣的角色。诺贝尔奖的光环有时可以是巨大的:它标志着“国际”(也就是西方)的认同,这种认同给获奖者的国家带来荣耀,并且让原本受到很少关注的地方文学暂时成为全球注意力的中心……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宇文所安还批评某些在西方受欢迎的中国诗人的热衷创作适合翻译的诗作,但缺乏“中国性”,他们的诗歌,遮去国籍,可以看作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诗人的诗作,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
当然,就如前面说过的,由于现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末前夕,解构主义思潮横扫中西方思想文化界,中国文学界也不能幸免,一时,一切宏大主题、历史人物、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都遭到贬斥、嘲笑中恶搞,人们在娱乐至死中狂欢,然后,就只留下一片精神的荒漠和废墟,焦虑、绝望的情绪弥漫,诗人自杀和自我毁灭的现象此起彼伏,成为世纪末的一个标志。这一虚无主义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但聊可安慰的是,在这样一股潮流中,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不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却是逆潮流而上的,本能地有着为民族代言和写作史诗的创作冲动,他们高扬民族主体性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他们歌咏和肯定本民族的特性和传统,赞美和弘扬本民族的辉煌历史和文明创造,他们在洪流般自我否定丢盔弃甲的文明溃败的场域里挺身而出,骄傲地喊出类似“我是彝人”的口号。在整个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文化景观中,他们显得如此另类,与众不同,但他们很坚定,坚毅的面容显示特有的倔强。就像里尔克所说的:“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对此,我们真该庆幸中华文明还有一支这样坚强的诗歌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持到了新的历史时刻,他们终于等到了新世纪的曙光,认识和发现到他们意义和价值的人越来越多。
吉狄马加《布拖女郎》
专辑名称《吉狄马加的诗》
作诗 : 吉狄马加
作曲 : 曲比哈布
演唱 : 彝人制造
出品:战马时代
从这一诗歌历史变迁中也可看出,二十多年了,中国诗歌界本身对所谓“世界诗歌”的想象和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诗人们不再为某一种所谓时尚而写作,也不再为取得某个圈子的某种喝彩而写作。诗人们更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和土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方向和道路。像吉狄马加这样的诗人被越来越广泛接受,就可以看出一种诗歌走向和趋势。那就是,中外文学界如今都开始反省和反思,重新正视诗歌、文学与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传统的深层关系。
很多年前就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性。这句话曾被认为是文学的金定律,但也引起过很多质疑和争论。但有一段时间,解构主义思潮盛行后,甚至基本不提这个说法了。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诗歌面临新的境遇和挑战的时候,我们不妨再来思考一下这个堪称重要甚至重大的问题。


首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果这个定义完全成立,那么,越是个人的,越是民族的,也成立。因为,诗歌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精神劳动和创造,是个人酝酿积蓄并最终独立完成的艺术。但是,强调个人性,并不等于弱化民族性、普遍性,恰恰相反,个人性唯有吸纳民族性、普遍性,才会强大。只有深厚、丰富、开放、强盛的个人性,也才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就像一座山峰,只有越高才能被越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一个概念:境界。境界其实就是指一个人的认识层次和精神水平,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确实,只有达到更高的境界,才可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达到相当的境界,才可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诗人要达到高境界,就不仅要有深厚的修养,还要有开放乃至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建基于民族与传统当中又有所超越的全球化意识,需要一种建基于个人深刻体验的对人类共性的深层思考,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担当,以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和维护。
其次,虽然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肯定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性都能世界化,就像地方方言、私人话语若不经过翻译就不能被别人理解,也无法进入对话和交流。只有那些经过筛选之后的有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符合人类共性和世界化规律的部分,才最终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此外,民族性的精华也不是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出的,而是经过比较、或者说经过他人的眼光打量之后才能发现的。就像一个人的特点是经过和他人比较后才确定的,一个民族的长处和优秀之处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些民族性特质和优长,由于有益于人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呵护,并最终有助于人类的自然发展和繁荣。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和挖掘个人或本民族的独特性和长处?现在科学界都在研究基因,但真正优秀的古老的基因,其实不是肉眼可以发觉的,而是要使用大量高科技手段的鉴别探测分析才能发现。诗歌也是如此,诗人要想创作出优秀乃至伟大的诗歌,需要在忠于个人内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学习古今中外经典诗歌的精髓,不断提高提升自己的水平,突出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美学特质,并最终得以自我超越,使个人性成为民族性乃至普遍性的代表。



中国当代诗歌从1970年代中期算起,已历四十年。先后经过了向外学习的阶段,在翻译诗的启蒙下开始现代诗歌探索的历史,朦胧诗等一度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出现,被誉为“新的崛起”。北岛和舒婷,一个代表启蒙、怀疑和批判精神,一个代表对日常生活和人性之美的呼唤与回归,风靡一时。然后,当代诗歌又开始了向内寻找的阶段,在“文化寻根”和“国学热”的引导下,内地和港台都产生了新古典主义的诗潮,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内地年轻诗人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等诗作,被广为传诵。诗人们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第三阶段,则是一个向下挖掘的阶段,诗歌的“草根性”兴盛,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底层草根诗歌、女性诗歌等诗歌现象此起彼伏,当代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兴起和相互竞争的阶段,各种诗歌主张和思潮开始走向深入和成熟,但也面临着缺乏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诗歌思想和诗作的状态。所以,向上超越,呼吁新的美学思潮,建立新的现代意义世界的时候到了。如何创造既葆有本民族特质,又为人类提供普遍共同的新价值和新思想的优秀诗作,就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当代诗人思考的问题,成为每一个具有抱负和创造力的诗人努力的方向。

李少君,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神降临的小站》《我是有背景的人》等,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居北京,任《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3期,责任编辑:杨卫东
附:
吉狄马加诗选
布拖女郎(双语版)
就是从她那古铜般的脸上
我第一次发现了那片土地的颜色
我第一次发现了太阳黄色的眼泪
我第一次发现了季风留下的齿痕
我第一次发现了幽谷永恒的沉默
就是从她那谜一样动人的眼里
我第一次听到了高原隐隐的雷声
我第一次听见了黄昏轻推着木门
我第一次听见了火塘甜蜜的叹息
我第一次听见了头巾下如水的吻
就是从她那安然平静的额前
我第一次看见了远方风暴的缠绵
我第一次看见了岩石盛开着花朵
我第一次看见了梦着情人的月光
我第一次看见了四月怀孕的河流
就是从她那倩影消失的地方
我第一次感到了悲哀和孤独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在大凉山一个多雨的早晨
一个孩子的初恋被带到了远方
Butuo Lass
It was from the bronze of her complexion
That I first discovered the color of the land around me
I first discovered pale yellow tears of the sun
I first discovered tooth marks of seasonal winds
I first discovered the timeless quiet of a glen
It was from the touching riddle of her eyes
That I first heard muted thunder of the highlands
That I first heard dusk push open a wooden door
That I first heard the sweet sigh of a fireplace
that I first heard a watery kiss beneath a headscarf
It was from her calm placid forehead
That I first saw twining currents in a storm-front
That I first saw boulders bloom with lush flowers
That I first saw how the moon dreams of her lover
That I first saw a river’s pregnancy in April
It was from something about her that has faded
That I first felt real sorrow and loneliness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In Greater Liangshan, on a rainy morning
A child’s first love was taken to faraway places
秋天的眼睛
谁见过秋天的眼睛
它的透明中含着多少未知的神秘
时间似乎已经睡着了
在目光所不及的地方
只有飞鸟的影子,在瞬间
掠过那永恒的寂静
秋天的眼睛是纯粹的
它的波光漂浮在现实之上
只有梦中的小船
才能悄然划向它那没有极限的岸边
秋天的眼睛是空灵的
尽管有一丝醉意爬过篱笆
那落叶无声,独自聆听
这个世界的最后消失
秋天的眼睛预言着某种暗示
它让瞩望者相信
一切生命都因为爱而美好!
日 子
我知道山里的布谷
在什么时候筑巢
这已经是很早的事情
要是有人问我
蜜蜂在哪匹岩上歌唱
说句实话
我可以轻松地回答
谈到蝉儿的表演
充满了梦幻的阳光
当然它只会在
撒荞的季节鸣叫
唉,一个人的思念
有时确也奇特
对于这一点我敢担保
假如命运又让我
回到美丽的故乡
就是紧闭着双眼
我也能分清
远处朦胧的声音
是少女的裙裾响动
还是坡上的牛羊嚼草
山 中
在那绵延的群山里
总有这样的时候
一个人低头坐在屋中
不知不觉会想起许多事情
脚前的火早已灭了
可是再也不想动一动自己的身体
这漫长寂寞的日子
或许早已成了习惯
那无名的思念
就像一个情人
来了又来了
走了又走了
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
她是不是已经到了门外
在那绵延的群山里
总有这样的时候
你会想起一位
早已不在人世的朋友
追 念
我站在这里
我站在钢筋和水泥的阴影中
我被分割成两半
我站在这里
在有红灯和绿灯的街上
再也无法排遣心中的迷惘
妈妈,你能告诉我吗?
我失去的口弦是否还能找到
被埋葬的词
我要寻找
被埋葬的词
你们知道
它是母腹的水
黑暗中闪光的鱼类
我要寻找的词
是夜空宝石般的星星
在它的身后
占卜者的双眸
含有飞鸟的影子
我要寻找的词
是祭师梦幻的火
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
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
我要寻找
被埋葬的词
它是一个山地民族
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
那些最隐秘的符号
骑手
疯狂地
旋转后
他下了马
在一堆岩石旁躺下
头上是太阳
云朵离得远远
他睡着了
是的,他真的睡着了
身下的土地也因为他
而充满了睡意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
他的血管里
响着的却依然是马蹄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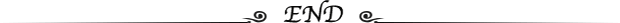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