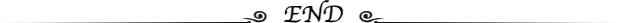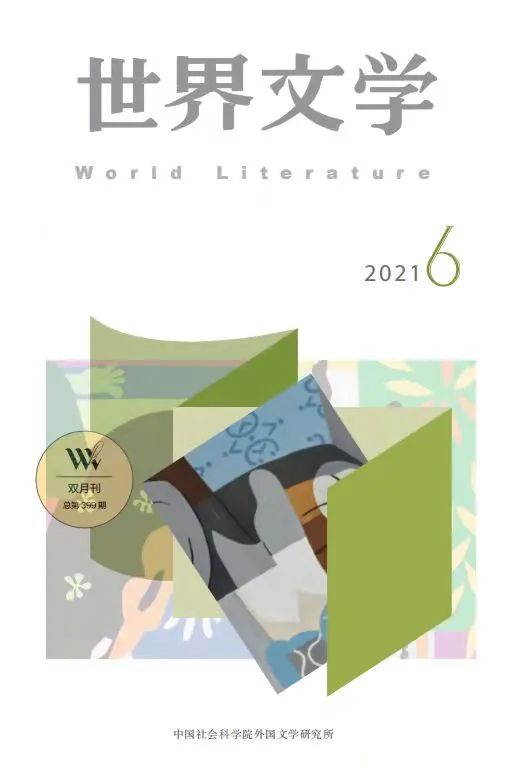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第一读者 | 莉·马希尔【南非】:封禁:并非笑料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2021年7月,南非爆发了1994年解除种族隔离以来最大的骚乱。一条导火索就是日趋严重的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参与打砸抢烧的民众大多已经到了无业可就、无米下锅的境地。从2020年南非初现疫情时起,这场动乱的火种就已在社会底层酝酿。从2020年初南非作家对封城生活的记录就能感知这种紧张不安的气氛。南非政府最早从2020年3月27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最严格的“五级”封城措施,为期21天,后来这项政策又延长了两周时间。在封城举措启动前夕和实施期间,出版人梅琳达·费格逊邀请数十位作家书写对疫情的体验和思考,讲述禁足期间发生的故事,并将他们的文章编成两部选集《封城:新冠纪事》和《封城延期:新冠纪事》。这两本先后问世的电子书于2020年6月合并为《封城选集》(Lockdown Collection)出版。《封禁:并非笑料》(Lockdown:No Laughing Matter)出自这个文集。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南非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时,在互联网最具爆炸性和创新性、号称“黑人推特”的角落里,爆发出一大堆别名、噱头和笑话,以我们所知的最好方式——笑破肚皮的幽默——迎接终局的开始。这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南非人是地球上最逗乐的一群人。我们的讥嘲感和讽刺感是在不断变痛苦为光明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此刻我们的所作所为同样带着这种感受力,一如曾经面对艾滋病大流行、雅各布·祖马与古普塔家族的政商关系、种族隔离暴行、政府腐败、白人至上主义、赖付抚养费的父亲等悲剧时。我们关上大门,一家人笑得东倒西歪。你能责怪我们吗?即使有人责怪,我们也不在乎,因为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怎样应对那个如同兔子洞【兔子洞纵横交错、结构复杂,可能会让人迷路。这个典故出自《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般的历史和现实景观?这种幽默来自倾听叔叔阿姨重温酷刑故事。你理智上并不想对着这类段子发笑,但它们不由你不捂着肚子忍住眼泪,一边咯咯大笑。关于有人被扣押在约翰·沃斯特广场【约翰·沃斯特广场为南非约翰内斯堡中央警察局所在,是种族隔离时代的标志性机构】,关于矮胖的布尔人警察(他举起平底锅大小的巴掌,把一名干瘦而热诚的活动分子扇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大肚子就悬在皮带扣外边抖晃)。一天一夜漫长的庆祝活动之后,到了凌晨,一些很不合适的玩笑——比如,变节的黑人警察如何将我们英雄的睾丸夹在木抽屉之间,然后猛然将抽屉合上又抽开,来回不断——便会从年长者的嘴里飞出来,看来,他们的创伤后遗症还没有平复。我们开各种嗜癖的玩笑,因为我们是一个上瘾的社会。我们嘲笑亲戚们烂醉的面孔和混乱的生活,他们扮演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宫廷小丑,而塑造这种态度的则是所有人对心痛的集体反应。尚未有人以应有的情感尺度来解释我们共同家庭原型所呈现的苦痛,因为悲伤总是挥之不去。我们是坚韧的民族,那些纠缠我们的恐惧,一直在重新合成。我们承受着相似的恐怖,它们以不同的面目和形式纷至沓来。因此,我们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我们通过笑声实施抵抗。新冠肺炎首次在南非现身时,它有着白人和精英的面孔,明白这一点是有助益的。它是乘坐飞机进来的,破旧不堪的护照上悬挂着一六五二年的行李【欧洲人在南非最早的一个殖民地是开普敦,而开普敦始建于1652年,这是荷兰殖民者入侵南非的开始】。它击中了极少数的人。这些人在学年【南非的学年从1月开始,到当年12月结束】开始后不久还有足够的钱去欧洲度假。每年头三个月都是人们财务上走钢丝的日子,他们的腰包早就被十二月份漫长的假期搜刮一空,而一月份还要添置新校服,还有全新的文具。正当我们开始从一年一度的财务打击中恢复过来时,一场瘟疫到来了,就在崭新的十年期诞生之际;它似乎瞄准了那些曾害得我们无法获得安全感的人群,就在这片属于我们但我们并未拥有的土地上。也许真有一位上帝,也许他真的爱黑人。从笑话本身就可以看出是谁在讲笑话,是谁在发笑。南非共和国是一座房子,靠种族隔离制度建造起来,而我们正在努力摧毁它的基础。扩大我们仇外心理的倾向,将南非的华裔也包括进来,给了我们另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其他”,另一种可用来彼此中伤的武器。各种笑话继续飞传,与此同时,这部分有购买力的人群开始囤积口罩和消毒剂。瓦次普应用上的视频独白纵横穿梭于网络世界,给出的解释是:这不是那些吃拉马牌人造黄油、印度腌菜、波罗内香肠和马斯酸奶的人会染上的疾病。这也不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痛风、糖尿病、普通肺炎和结核病的人会染上的疾病。这是一种去过英国圣公会私立学校的疾病,操着上流社会的口音。这是一种从未涉足出租车候客队列的疾病。“小冠冠”【作者在该文里多次用网上流传的绰号来指称新冠肺炎。此处的“小冠冠”,以及下文的“麦克冠仔”“可可冠五”“可可蕾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自有它的目标市场。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永远魁伟性感的伊德里斯·厄尔巴和他同样美丽、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萨布丽娜一起,在“照片墙”上向世界公开宣布他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黑人推特整个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用说,伊德里斯是一位富有的超级巨星,但这位半加纳半塞拉利昂血统的英国人,在如黑檀木雕刻的迷离状态中,证明了“麦克冠仔”也喜欢“巧克力”。随着更多病例出现,随着全国宣布关闭学校,随着南非零工经济因为政府批准社交隔离禁令而垮塌崩溃,常态的车轮令人吃惊地停顿了。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并非例外。我们也很脆弱,于是许多人开始害怕了。“可可冠五”通过我的职业一步步逼近我的私人世界。我一直在准备九十月间伦敦、尼日利亚的巡回演出,可是在七十二小时内,演出被无限期暂停。原定于四月底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演出被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我一直为一家印度制片公司做研究、角色开发和翻译工作,可这家公司在印度封禁之后就暂停了生产。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南非已经封禁三个多星期,此刻我本应该在印度安排前期制作的,但这已是恍如隔世了。
我习惯于生活在跨越时间表、时区、项目和演出会的多重世界里。在任何特定时刻,我都是拥有独立附肢的千足虫,每条附肢都沉浸在自成一体、滋养着我生命织锦的现实中。我并不孤单。这个世界满是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创意工作者、企业家和现场表演艺术家。我看着新冠病毒把我的同行们彻底打趴下,因为他们的海外巡演被取消,而眨眼间,我发现自己也落到了同样境地。在社交隔离禁令宣布前几天,我在南非还剩下好几场演出,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将是我为现场观众表演的最后几次活动,在过去二十年里,我越来越喜爱这种方式了。我不知道那些零活是我向现实的告别。艺术家感知到空气中有什么在慢慢渗透,并催生了这一切。历史上看,革命常常是由重大的创造性转变推动的。政治与艺术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就此而论,新冠肺炎自然首先且凶残地冲击了创意经济。社交隔离意味着再也没有超过五十人的聚会——也就意味着不再有现场演出。这个星球其他地区是这种情况,南非也不能自外。表演者、声光技师、舞台监督、服装设计师、布景设计师和搭建者、引座员、售票员、布景迁换员、后台工作人员、制作人、作家、广告员、经纪人、艺术经理、剧院工作人员、节会策展人、承揽公司、行政人员、餐饮服务商、装潢供应商、司机,以及表演现场外围每一家出售节目单、小商品、鸡翅、炸薯条和南非香肠卷的独立摊贩;这些人员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创意价值链,如今都没了工作。好运也没了。我立刻进入“争抢模式”,追讨待付发票的款项。这种情况很快升级为“战斗模式”,当时我硬怼了一位经纪人,他想扣下我的资金用于他们自己的现金流,此外,我还要对抗演出公司糟糕的支付程序——它们的官僚金融系统早就在我的脖子上松松地套定了一道绞索。这件事暴露出一个有毒真相,涉及许多自由职业者、艺术家和个体经营者的工作方式。在任何特定时间,都有一沓钞票以尚未付款的发票(虽然服务已交验)形式存在,就悬在我的头上,像漫画里的内心活动泡泡一样。这笔钱我看得见,却摸不着。我知道这是我的钱,因为是我挣到的,然而不在我的账户里。当我向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客户索要自己的酬劳时,我总是在对抗无休无止的供应商表格和供应商数据库表格,对此我已经习惯了。为了弥补现金短缺,我在过渡期间追逐更多工作。整个职业生涯我一直在这样的跑步机上面奔跑。从来没有时间检查它的弊端的系统根源。“可可蕾拉”毁了我的演出。现在我有时间了。在拉马福萨总统宣布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社交距离的政令之后,第二天,文化领域的几名大腕面见了体育、艺术与文化部部长纳蒂·姆特什瓦。在新闻报道中,我迅速瞄了一眼这次会议,就注意到整个房间都是由男性行业人士主导的,从国家资助的剧院首席执行官,到唱片公司老板,再到该部雇用的公务员,不一而足。为响应总统宣布的即将到来的全国封锁,部长于一个多星期后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结果。其中的一些建议,如使用国家资助的剧院录制现场表演然后实现在线流式传输,在封锁期间就已完全不可行了。
体育、艺术与文化部今年第一季度的预算为一亿五千万兰特,已经拨出用于提供援助。这些资金,总额相当于若干艺术节和重大体育赛事的总预算,将由两个不同部门分享,即体育司,外加艺术和文化司。这是两个先前独立的政府部门于二○一九年合并的结果,目的是精简在祖马执政期间变得臃肿不堪的内阁。现在,艺术家发现自己没有了工作。运动员发现自己也在同一条船上,与此同时,许多运动员还被困在世界遥远的角落,希望在政府帮助下回家。看起来,这笔钱不太可能解决这两条很不相同的价值链问题,而这些问题因为新冠肺炎而更加凸显。体育、艺术与文化部在三月的最后一周发布简讯,要求人们量化因新冠肺炎而损失的收入。这些数字需要附带发票和合同形式的证明文件,以证明丢失工作并非杜撰。当我知晓这些政府简报时,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来整理必要的证明材料了。在封锁的最初几天,想追着客户和同事索要合同,却寸步难行,一筹莫展。打印店不营业。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丢失或损坏了,也难以找回或修复。我花了六天时间追讨与自己最大笔合同相关的支撑材料,等文件终于到来后,我提交了申请书,比截止时间晚了三十分钟,有人立刻告知我,他们将不会考虑我的申请。为什么本行业的从业人员只获得一周时间来申请这些资金?为什么在疫病国际大流行期间竟然还设有最后期限?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封锁期间申请可以制作的创意节目的要求。这些项目必须在线传播、数字化并能够盈利。封锁令一下,很多艺术家,譬如我本人,就开始尝试如何在线共享作品。像“脸书”和“照片墙”这样的平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命线,他们需要找到创意表达的渠道,不然就要疯掉了。全世界的创意人士都干上了恰恰是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极力抵制的事。我们开始在线免费奉送我们的作品,以获得曝光量。尝试新的线上模式,从现场社交媒体表演到Zoom等私人访问平台,是至关重要的,有利于在这个充满变数、不知何时到头的时期开发新的工作方式。政府将支持在线创意模式的想法顺应了时代潮流。这些项目在早期探索阶段就必须盈利的观念则令人担忧。在我们的创意产业中,种族隔离时代留下的痛苦后遗症之一,是对知识产权的剥削态度;黑人、穷人和妇女往往受到最不公正的盘剥,因为这群人获得资本的渠道最少,难于独立开发内容。例如,“多选台”“南非广播公司”等单位定期发布简讯,要求制作人以电视节目的形式提供新内容。这些节目是由广播公司出资制作的,因此广播公司拥有它们的创意产权。节目制作人因为付出了劳动以及制作成本而拿到报酬,但是除此以外,无论节目多么成功,他们都不能进一步从中获利,因为知识产权归投资方广播公司所有。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编创故事的作家和把故事演活而家喻户晓的演员。通常,这些节目会在南非和很多遥远地区多次播放。《一代代》【一部南非肥皂剧,1993年在南非广播公司首演】是牙买加最受欢迎的肥皂剧。剧里的演员并不会因为重播而收到表演版税。没有人能收到。在这个国家,名人的去世,按照惯例,常成为思考问题的契机:这种对知识产权的不公态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我们习惯性地质疑为什么观众如此钟爱的人,却死于抑郁、毒瘾和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收不到重播版税,出名或拥有热门节目并没有什么长远好处。
当政府发布简讯征集新的在线盈利节目时,它在扮演这个国家的广播公司一直在扮演的角色。为什么中央政府应该是任何人的创意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怎么可以将此视为救助陷入困境的产业的一种尝试?政府怎么可以声称它正服务于某种转型路线,而它的行为却与现状毫无二致?(现状便是让挥舞资本大棒的广播公司受益,为此牺牲努力工作的创作者的利益,使他们几乎沦为一架专为剥削而设计的机器上的创意原材料。)为什么政府首先要充当广播公司或制片商?体育、艺术和文化部经常把自己放在这种位置上,充当起预订代理或赛事主办公司的角色。为什么政府表现得像是这个行业中的竞争者,而不是通过规范该行业来消除持续的不公正现象?体育、艺术和文化部的存在是为了履行一条宪法条款:该条款赋予每个人参与自主选择的文化生活的权利(《南非共和国宪法》第三十节)。无论种族或阶级,南非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在步行范围之内获得充满活力、多种多样且十分便利的文化空间。艺术和文化是转移一代人创伤的前线,如今,随着暴力犯罪、腐败、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高企不下且继续攀升,这种创伤越发显现出来。在这个国家,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艺术家,我每天都要面对这样一小群同行和同事的作品:他们正全心投入“不适区”的中心,试图为新的理解方式指引出路。在一个文化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的国家,只有少数人才能沉浸于此类艺术经验,这足以说明政府未能理解自己的作用就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文化生活繁荣且便于每个国民参与的环境。为什么一个年创利数十亿兰特的产业,却没有在与金融片区相关的议会小组里占有一席之位?假如体育、艺术和文化部的官员出席这个重要的决策片区,他们应该能够充分阐明我们产业的生产价值链有多么庞大,有多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倚赖它生活。在一个灰色产业——它常常与零工经济交叠——构成经济主要部分的国家里,救济和筹资模式需要考虑人们是如何工作和挣得收入的。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在四月十八日,也就是进入封锁之后第二十二天,救济资金申请截止日期已过去两周;此时,纳蒂·姆特什瓦部长最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它将决定救济资金如何分配给体育产业。而对于那些申请艺术和文化救济的人来说,目前还是没有一个说法。我们国家的多样性、复杂的层次影响力以及相互交织的历史,意味着我们是创造力的沃土。南非生产艺术家的速度超过了维持他们的能力。由于新冠肺炎,如今我们要把网撒到国外去已经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锁定在一个物理位置。我们终于有了机会进行反思,安静下来,看一看堵塞我们公共机构的淤泥。新冠肺炎暴露了长久以来什么还在有效运作,什么已经不顶用了。它将一面强大的放大镜置于整个国家的公有和私营体系之上。我们是一个垃圾等级的国家,紧随着五十年的种族隔离和三百年的殖民主义,猖獗的政府掠夺弄得她步履蹒跚。在这个地方,上至大气层面下至原子层面,暴力无处不在。这种暴力是我们真实的病毒。新冠肺炎有望迫使我们最终处理它。
谁来揭示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谁来分析一下后民主时代黑人主导的政府是如何同时成为历史的受害者和恶棍的?谁来解说一下一九九四年大选前的囤积者和二○二○年新冠厕纸囤积者之间的连接脐带?谁能搞清楚新冠肺炎是如何从一种经由飞机传入我国的疾病转变成这样一种病毒:它必须以种族隔离的方式在贫穷的黑人社区派驻警察和军队来加以控制?谁会帮助我们理解曾经从小酒馆蔓延到全国各地急诊室的暴力行为,如今已在这些地方消失,不料却出现在家庭里,针对妇女和儿童的身体而越演越烈?当家庭不是安全可靠的地方时,当我们被迫待在家里,却因为无法工作而付不起房租时,当政府说过在此期间不允许强制驱赶租客,而我们却看到这种情况正发生在西开普省的穷人和赤贫者身上时,谁能明确表达出此间的矛盾?这是当下关心公平正义、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人士要从事的心灵工作。做一名艺术家,我从来没有如此自豪过。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所需的技能,是我们为了生存必须老早就在武器库里磨好的工具。新世界要求敏捷度、敏感性、适应性、创造力、不断的重新设想,以及重新发明。这就是创意者的任务。我们从无生有。我们解读周遭环境并做出回应。我们将新平台和载体整合到现有的实践中。我们本身就是精神豁达与坚忍不拔的最佳定义。我们持续的创意成长和生存,对这个国家共同体在此期间以及解封之后所需的精神和情感支持至关重要。据估计,三百万南非人将因新冠肺炎失业。他们中许多人将进入零工经济。往后,如果零工经济难以活命,我们的国家也不能活命,不能前行。我们可以讲一百万个笑话来润滑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路径,然而封禁期间以及解封之后的生活现实,却绝非笑料。莉波·马希尔(Lebo Mashile,1979—)是知名南非作家、评论员、表演者和制片人,出版过剧本《维纳斯与现代性:沙提婕·巴特曼的一生》(2019),诗集《戴着节奏的丝带》(2006)等。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责编: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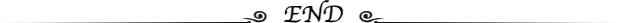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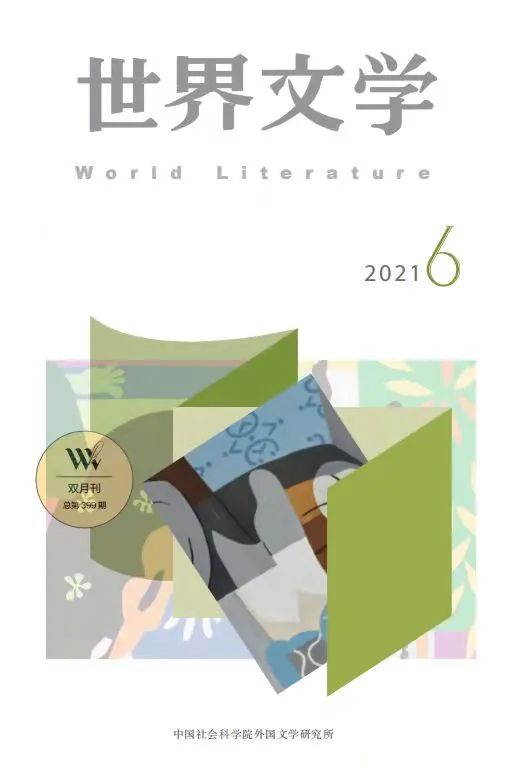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