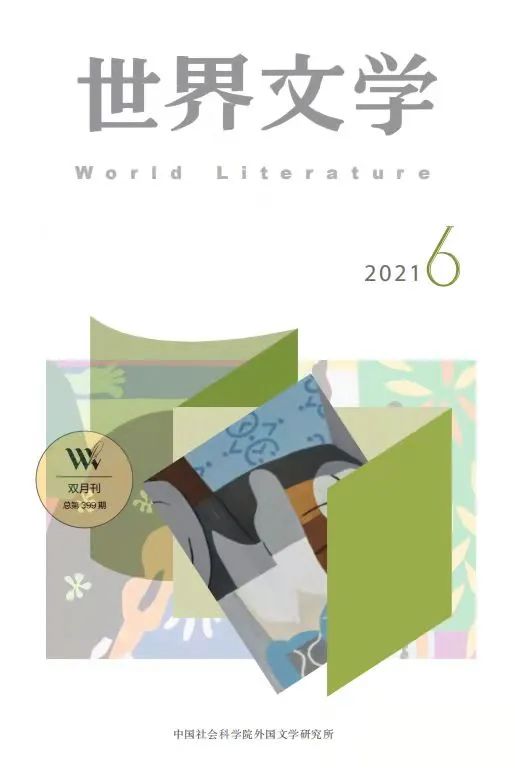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萧萍:人间四月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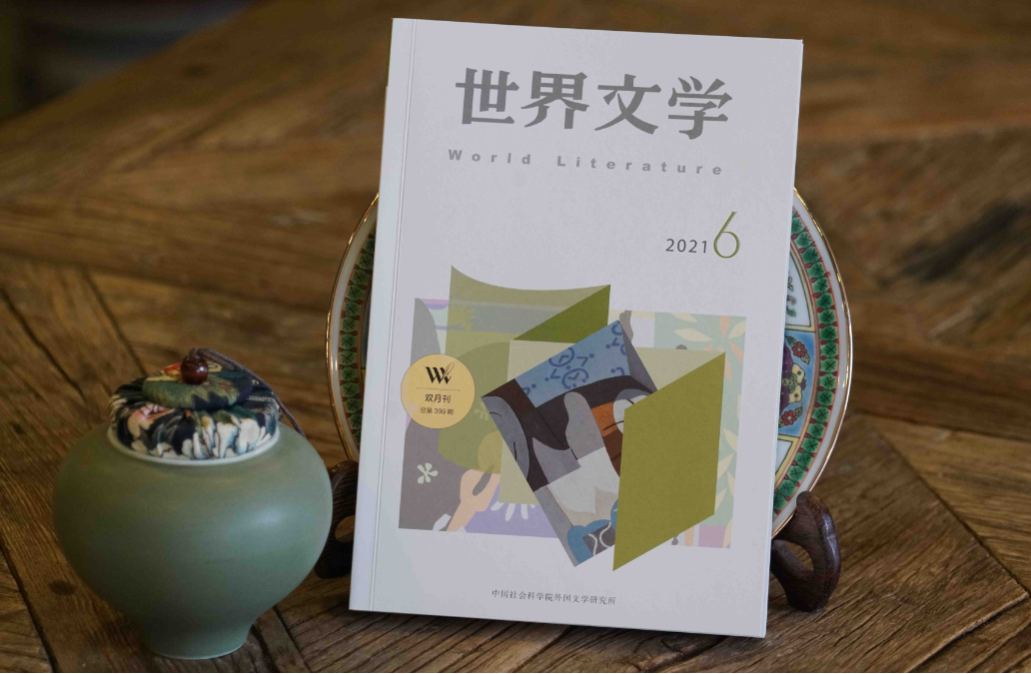
理论上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现实中病毒让人群、阶层、种族、地域、国家的
差别分野更鲜明,后果更严重。
然而,这个微小到只有英文句点万分之一的
球形冠状病毒,以其执拗的存在,
迅捷的传播,
致命的威力,
正告所有因特权保护
而暂时免于灾祸的群体:
让全世界每一个人平等地免于病毒侵害,
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萧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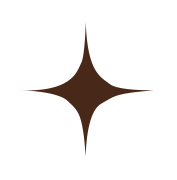
萧萍
它到我家时,是四月。于是叫它“四月”。
发不好它原来英文名中那个饱满的双元音,我偷偷给它换了个中文名。好在“四月”对从这个四月开启的新生活,我给它的新名字,中英文混杂的新指令,二娃三猫的新家庭,四段楼梯的新居所,似乎是无缝对接地适应了。爬楼梯于它颇是挑战,但绝不独自在楼下享受孤独的决心会让它克服困难,上得楼来。虽然明知它是能够爬楼梯的,每次听到它细碎的脚步,看到它出现在书房门口,我还是会惊喜,大声说:“四月!你来啦!”
“死亡来到了美国。”扎迪·史密斯在二○二○年七月出版的散文集《端倪初现》中写道。她在打包准备离开。楼下大堂已经堆了很多行李。楼外是待发的车。她任教的纽约大学,同事们大多来自某个其他地方,大疫当头,同事们得赶在飞机停航之前回去那些其他地方。她还没有口罩。把袖子扯长了裹住手去摁电梯按钮。她在离开前得去自动柜员机上取点现金。在街口她遇到曾被她写进文章的轮椅上的流浪汉正对着手机大笑:“看看他们,就跟沉船上没头没脑乱窜的耗子一样……为的啥呀?不就一感冒?这些人都疯了。他们惊慌失措得就像这是世界末日……”芍药和郁金香的季节。蒲公英初现的季节。她写的是纽约的四月。她将前往伦敦的四月。
新冠肺炎大约在二○二○年四月全面登陆欧美各国。人们使用战争词汇来描绘它,甚至有人称之为引爆了一枚社会性核武器。而此时,中国的每日新增已降至零。仿佛是摁了一下遥控按钮,电视就换了个台。主角和群演从亚洲面孔变成各种肤色的人群。或是在裁判拉长的哨声中,上半场切换到下半场,竞技者队伍从球场这一端走向另一端。人流和口罩包裹的流向正相反。二三月份刚搜集到的口罩还在运往国内的途中,国内朋友已开始着手给我寄送装满口罩和防护品的邮包。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留学生们晒机票。二月底:上海—多伦多;北京—伦敦。四月底:多伦多—上海;伦敦—北京。就算很难抢到票。航班一而再再而三被取消。票价高企如天价。航班熔断。需要在欧洲转机。过境、入境政策瞬息万变。酒店隔离两周。国内舆论汹涌。家长望眼欲穿。一切不可能中锻铸的可能。最终留学生们还是到了机场。个个穿得像宇航员。和同伴们比剪刀手合影。加上文字:留学生天团。
留学生们回国后,留下来众多猫猫狗狗。有一只,到了我家。我叫它“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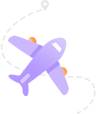
迈克尔·柯林斯,宇航员,于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九十岁。
然而,迈克尔似乎惬意于这偶尔的暂停。偶尔的被遗忘。如果是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呢?如果是很多很多的人被遗忘呢?不是宇宙运转的暂停,是人类活动的暂停。不是被死亡遗忘,是被人群遗忘。一时间,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成了史上最孤独的人。一时间,我们陷于末世的寂静。如果末世有可能是寂静的。
充满了声响的寂静。白天在家中回荡的主要声音是从一楼一年级学生其嘉上课的房间传出。印裔女老师带口音的授课声。夹杂着学童们稚嫩的闲谈。毫无保留地叙说自己有限经验中的一切。电脑里时而传来一段激荡劲爆的舞曲,好让孩子们在各家有限的小空间里跳腾舞蹈。而位于二楼八年级学生淇奥的房间却通常安静得出奇。她窝在床上,戴着耳机,摄像头关闭,iPad藏于枕头下,猫咪们在她的抚摸下舒服地呼噜。放学后才会听到她的声音从她房间传出,听起来总像在长篇大论地演讲,不知道是在跟朋友聊天,还是在参加和朋伴们组织的业余辩论赛。四月的吠叫声如同段落中的逗点。窗外每每有人和狗经过,或有车辆在门口熄火暂停,四月便会跃上沙发再至窗台,对着它臆想中的威胁狂吠。猫咪们是安静的。我和书本的交流也是安静的。
如加缪所言,我们流放于自己家中。是囿于自家的囚徒。
所有教学改成线上,砖头混凝土的学校改成虚拟学校,对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是巨大挑战。这一年印裔老师说得最多的就是,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我们都在学习中。最早的几周里,老师一度崩溃到当着同学们的(还有家长们的)面痛哭。那几周时间,家长们基本上都得陪上课。打印资料。听懂老师指令。帮忙拼写单词。慢慢地老师学会了更多利用网上资源,作业可以在网上做,网上提交。孩子们不仅学习了传统教育中的读写和算数,艺术、科学和社会学,还提前进入电子时代,编程,玩游戏,制作图文并茂还配音乐的电子书。
石黑一雄最新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克拉拉与太阳》里,未来教育就是远程教学,学生在家里跟教授通过“矩形平板”上课。一对一。新冠期间的教学尚存班级,一个班级就是电脑屏幕上一个个方格中各种扭曲坐姿的小孩子们,背景是各家各户的房间。工业革命后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工作和家庭分离、教育和家庭分离的模式,因为疫情被中断。家,再次成为多功能集中地。也成为你无可逃离的宿命。《经济学人》的一期播客里,一位嘉宾说所谓的度假时光,就是不在孩子视线和干扰范围内的片刻时间,从你帮后座的孩子绑上安全带,关上车门开始,等你绕过车屁股在驾驶座坐下就结束了。估计这句话会得到全世界父母们的共鸣。全世界父母们,都被迫与在家上网课的子女共度史上最长的亲子时间。当孩子不在眼前时,或者尚未出生时,你或许会在脑海中浮现无穷种和孩子的对话,再写下来,像卡尔·欧夫·克瑙斯嘉尔德那样,写下一本又一本的书。《春》《夏》《秋》《冬》。在书里跟小宝宝说:“智识,是我们用来描述理解各种关联的能力的术语。”掰扯从哲学到日常、从感官到感悟的种种体己话。然而我不知道,在大流行之际,在被迫居家的现实中,当孩子存在于你的每一分钟每一视线可及之处,你是否还有言说的灵感。
每天下午放学后,带着四月,带着骑滑板车的其嘉,去到马路对过的教堂停车坪。教堂早已停止任何现场活动,草坪上的荧光屏显示出每次线上活动的内容和时间。停车坪空无一物。但这是其嘉唯一可以活动的地方。所有带游乐设施的小公园都挂了封锁带。如果有其他小朋友来,比如那个骑自行车的十一岁男孩,或者那个四岁的小女孩苏菲,六岁的其嘉会在这里待得更久一点。要保持安全距离。两米。六只加拿大鹅。男孩乐于向小妹妹们炫技,双手脱了把手,两臂在身侧展平,一条腿亦在身后平伸,借着滑行的自行车作滑翔状。还有攀爬到教堂侧面镶嵌彩色玻璃的高阔窗户上去。还有最古老的游戏:爬树(人类已知历史始于六万年前好奇的露西爬上树又从树上掉下来)。陪同的家长们隔着大半个停车坪聊天。何时来到多伦多。从哪里来。或是一起看着教堂一侧的小径,夹道是繁茂盛开的白色海棠花树,孩童们的喧笑声由远及近,先是男孩子骑着自行车从花树下疾驰而来,然后是其嘉踏着滑板车努力跟上,最后是苏菲和她红色的小三轮。四月朝着他们吠叫,独自撑起一个拉拉队的声势。苏菲的小妹妹在婴儿车里安静地睡觉。
一片什么都没有的水泥平地。孩子们要靠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来玩出顶级的快乐。这也是我自己的童年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小县城里,只有工会有一片大大的但什么都没有的水泥平地,放学后我们都飞奔去那里。红领巾从脖子上摘下来扎到胳膊上,从一只胳膊上解开,飞跑过去给另一只胳膊扎上。硬邦邦有节奏撞击水泥地面的跳绳,震慑着那些口里念着儿歌的孩子。小心脏怦怦跳动,计算着何时冲上前才不会被跳绳抽到,而能和着节奏在跳绳最中心的位置跳跃几下,再飞跑出来,位置让给下一个。牵皮筋的已经惦着脚尖伸直手臂把皮筋举到不可能的高度,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飞燕一般的女孩子们高抬脚尖轻轻一勾,高傲的皮筋就得乖乖儿降低身段到她们脚底下,到尘埃里缠绕绻曲。环绕工会水泥平地的矮墙上几个鲜红的大字:紧张活泼,团结奋斗。



新冠疫情下的封锁。再发达再富裕的国家都秒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小镇孩童没有什么物质支撑下的单纯的快乐。紧张活泼。自由自在。我和我的孩子,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近在咫尺的博物馆、水族馆、科学馆、音乐厅、剧院、马戏团、会展中心的大型游乐设施、有酷炫过山车的奇幻乐园、湖心岛的轮渡帆船游艇、八月的加勒比海文化节、十二月的圣诞大游行,还有贯穿一年四季散布城市各处的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体育美食节日活动……啪!没了!其嘉大约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些玩乐的可能。而我也快不记得它们的存在了。似乎全世界皆如此。不管你家近旁就是比萨斜塔,还是从自家窗户能看到自由女神像,我们都要回归远离世界的小镇生存。在一片空无一物的水泥平地上找快乐。依赖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来生存。从不多的几样东西几件事情里领略生活的小确幸。就是这些在富足喧闹的时候看来平淡无奇的小时刻,在我们一生昏昏的记忆中闪着亮光。比如我自己小时候,每隔几天,跟着爸爸,拎着暖水壶,去家近旁新开的冰厂买冰咖啡;比如现在,我带我的两个女孩子,每隔几天,戴好口罩,去家近旁的超市买巧克力。隔着四十年光阴,隔着整个太平洋,此刻和彼时,此地和彼岸,似乎并无不同。
那时候,街上没有什么店铺。而现在,沿街所有店铺都是关闭的。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店家写在小黑板上的暖心留言:想念你们;不久后见;确保安全。小黑板旁边的绿植已有了黄叶。小店,在寻常时期,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在非常时期,是一个城市的善意。BUY LOCAL:街边的公益广告。【Buy Local是买本地货的意思。这个短语与Bye Local同音,言外之意是不买本地货,本地不好过。】玻璃窗上贴着告示,顾客可以扫码到小店网站上购物。提供送货或路边自取。有一次惊喜地看到每每路过赞赏却不得而入的美丽花店里有人,还是个说普通话的大陆女孩,我们隔着窗玻璃聊了几句。她说生意都转到网上了,依旧很忙。网上,一个神秘的平行世界,为这个世界保存着活力和善意。淇奥其嘉学习大提琴小提琴的音乐学校,校长发来的邮件说,我们在疫情中不仅活了下来(surviving),还活得精彩(thriving)。季度音乐会改成了线上,孩子在家里整面书墙前演奏,黑白的猫咪在黑白的钢琴上趴着,坐在后院草地上拉大提琴,孩子的小提琴妈妈的钢琴伴奏,淇奥的大提琴低沉的呜咽声中混杂了四月低低的呜咽声……把家庭背景带入的线上音乐会,较之往常教堂里正式着装正襟危坐的,又别有一番趣味。
这是爱·摩·福斯特一九○九年科幻短篇小说《机器停了》里的世界。在福斯特的反乌托邦世界里,“公共聚会的笨拙系统早已被弃用”,每个人住在一个私人小房间里,“像蜂巢的六边形构造”,食物、用品、娱乐都会由一个类于亚马逊的“气动邮政”自动快递到门口。人人通过视频会议讲话。不过,福斯特敏锐地预见并诊断了这个科技发达的未来社会(也就是我们现今的社会)的缺失。“他停顿下来,她觉得他表情忧伤,”福斯特写道,“她不确定,因为机器不能传输表情的微妙之处。机器只能提供有关人的笼统概念——这倒足够应付所有实际用途。”然而,无法满足人的情感和智识对“微妙”的需求。人是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是对的。福斯特呼吁人与人之间更密切的联结:“唯有联结……”而后欲言又止的省略号,是自由人文主义者福斯特对现实对人性的足够清醒的犹疑。



所幸即便是在疫情肆虐中,我们还被允许出门,遛狗。四月牵着我走过斑马线。一个已经超过我们走到前头的男子,突然回头对着埋头在地面走着的四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清晰道出:PO ME RA NI AN。他瘦削的脸,暗淡的金发,灰色的工装裤,他那因为看到四月而突然绽放的饱含爱意的笑容,浮雕一般悬于他的身份特征之上。或许他家里也有一只和四月长得一样的白色博美犬?或许他来自欧洲中部那个叫波美拉尼亚的古老地区(博美犬源自此地并以此地命名)?他像是从一百年前穿越到二十一世纪多伦多街头的来自中欧的建筑工人,从加拿大斯里兰卡裔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身披狮皮》中走出来的人物之一。软装本书皮上的黑白图片,并不那么黑白,也不算泛黄,近处是横陈的木板,和木板成直角构图的是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桥。从木板下方探出半个身子的工人戴着帽子,露出一段黝黑的后脖颈,木板遮挡了他正在做的事情。他近旁的工友差不多是全身像,窄檐帽下是一张没有面目只有阴影的脸,你想要像划拉手机屏幕放大图像好看清那张脸,但书封页上的那张脸凝固在历史记录中,只是一个阴影中的侧影。没有面目。他两只手合握一个像家用电钻大小的工具,在桥侧一条水平缝隙处作业,他的脚下是横搭着的两条窄窄的长木板,木板悬空着,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顿河河谷。小说里有个情节,几个修女不小心闯入这片未完工大桥的工地,其中一个被强劲的大风(呵,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多伦多的大风)吹下了尚未装上护栏的大桥边缘。这是历史档案中的真实事件,一个修女从尚未完工的大桥坠落。而小说故事里,这个不幸坠落的修女被图片中这样一个正在作业的工人拦腰抱住。文学,让历史中没有记载的和历史记载中没有面目的人们,有了自己的悲欢和故事。爱德华王子大桥。建成于一九一八年。当时世界第一大桥。由来自中欧的移民建造。移民建造了这个城市。过去是,现在依旧是。我们在文学里阅读当下。


西方文学始于一场瘟疫。天神阿波罗愤怒的箭矢先是射向骡马,射向“转圈儿的狗”。而后掉转箭弩,箭镞飞驰,射向人群,人们成群被撂倒,“为尸体堆起的焚葬堆不停燃烧,日以继夜,无休无止”。“悲伤无以言语——/疾病在人群中蔓延,摒绝/解药的发明——凋敝/于荒芜的土地,/生之荒凉的痛苦——/野火中一个又一个生命扬翼/迅捷飞入黑夜,/无以言说,城市/死亡遍布街道,死亡——弃绝/哭泣,她的孩子们死去,/无人在身边怜恤。”这一年,我读了比往年多很多的书,因为世界砸向我的困惑如此巨大,阅读是我一点一点凿去其混沌与沉重的趁手工具。这一年,看到太多“焚葬堆不停燃烧”的图片,听了太多“死亡遍布街道”的新闻与分析,读了太多“悲伤无以言语”的虚构与非虚构的文字。然而我的小小书斋一如漂浮在二十五万英里之外的哥伦比亚号太空舱般疏离于现实世界。我知道世界在颠簸动荡,很多人在苦难中沉浮。而我的存在之境几近静止甚至静好。只有文字、图像和声音符号,构筑着“混乱的纯粹性”。
是的,我的故事里没有死亡。不是说死亡没有来到加拿大,没有来到多伦多。只是我的私人故事里没有它。就像翁达杰的一九一八年多伦多故事里没有大流感。就像一九一八年伦敦街头巷尾童稚的声音传唱的儿歌里没有死亡。有的是一只叫恩扎的小鸟,打开窗它就会飞进来。【儿歌的全文是:“我有一只小鸟,/它叫恩扎,/我打开窗户,/恩扎飞了进来。”最后一句的英语原文是In flew Enza,发音接近于Influenza(流感)。】死亡在新闻里,在传闻里。在图片里,在视频里。在电脑上下单、亚马逊快递送到门口、摆在书桌上读到一半的书本里。肯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在这过去的一年半里,读或重读加缪的《鼠疫》,笛福的《疫年日记》,库切的《灾年纪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秧鸡与羚羊》,艾米莉·曼德尔的《第十一站》,迈克尔·刘易斯的《预兆:一个大流行故事》,劳伦斯·赖特的《大疫之年》,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奇斯的《阿波罗之箭:新冠对我们生活的深远影响》……文学家们是预言灾难的卡桑德拉。社会科学家们在灾难之中和之后勉力分析谨慎预测。最后的最后,是玛丽·雪莱的《最后一人》(1826),两百年前预言了二十一世纪末的一场大瘟疫,伴随着极端气候、宗教狂热和内战,人类整体灭绝:“大自然的狂野失序,令四野皆荒,万国绝迹……美洲的巨大城市,印度斯坦的肥沃平原,中国人熙熙攘攘的居所,全都遭受彻底毁灭。那些不久前还忙于寻欢作乐或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的麋集之地,如今只听得哀嚎凄鸣。空气皆毒,每个人吸入的即是死亡……瘟疫已然成为世界的女王。”主人公,亦即唯一的幸存者,独在人间,写了一本书,作为纪念。他的唯一伴侣,你猜对了,是一条狗。


我和四月的“灾年纪事”平静得近乎荒诞。我们走在社区鲜花盛开芬芳怡人的六月里,看到其他行人和狗过来,就穿过马路去到对过,同时对我们避开的人和狗微笑和吠叫致意。公园草地上,四月时遍地金黄的蒲公英花,五月化成雪白一片的蒲公英钟(dandelion clock),六月已寥寥所剩无几。四月以前喜欢冲进草地,用鼻子顶散蒲公英钟,在散落蒲公英种子的草地上打滚,自己身上也挂了许多带翼的种子。现在草地上略显无趣的四月,尾巴盘成一个硕大的毛茸茸的蒲公英钟,黝黑粗壮的毛毛虫误入酣眠,四月也不在意。我的耳机里播客主持人和嘉宾或凝重或诙谐地讨论着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现在正在发生的,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未来将要发生的,此地的,远方的。华盛顿特区卫生官的声音: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区没有新增阳性(positive),所以我感觉乐观(positive)。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声音:我们十二岁以上至少接种一针疫苗的人口百分比在G7、G20和OECD(经合组织)国家里排名第一。多伦多总医院重症监护室女医生的声音:我们的第一例新冠是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今天我们新冠清零!
“享有尊优特权群体”的暂时胜利?“特权”概念是当下西方文化大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这次疫情中尤其扎眼。理论上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现实中病毒让人群、阶层、种族、地域、国家的差别分野更鲜明,后果更严重。然而,这个微小到只有英文句点万分之一的球形冠状病毒,以其执拗的存在,迅捷的传播,致命的威力,正告所有因特权保护而暂时免于灾祸的群体:让全世界每一个人平等地免于病毒侵害,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有人说,新冠将在这个夏天终结。
有人说,新冠将长久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而我和四月相依相伴、如影随形、寸步不离的日子,也将有个始终。这个始终,约等于多伦多新冠时期的始末。
2021年6月作于多伦多

萧萍,原《世界文学》杂志编辑及社科院外文所英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英国现当代文学。主要译作有《英伦独语》(合译)、《伏尔泰的椰子》(合译)、《翡翠城》(合译)、《教堂建筑的秘密语言》。曾协助三联书店、译林出版社等编辑《汤姆·斯托帕戏剧集》和《最佳欧洲小说》等。现居加拿大多伦多。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6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疫情现场”相关阅读(点击圆图旁的箭头,即可跳转阅读):

第一读者 | 莉·马希尔【南非】:
封禁:并非笑料

第一读者 | 后疫情时代下的生活:
法国小小说四篇

第一读者 | 帕·马克斯【美国】:
休闲每一天
——疫情时期的“邋雅”生活风

第一读者|汗漫:
在狮吼与熊舞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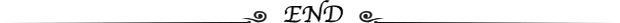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