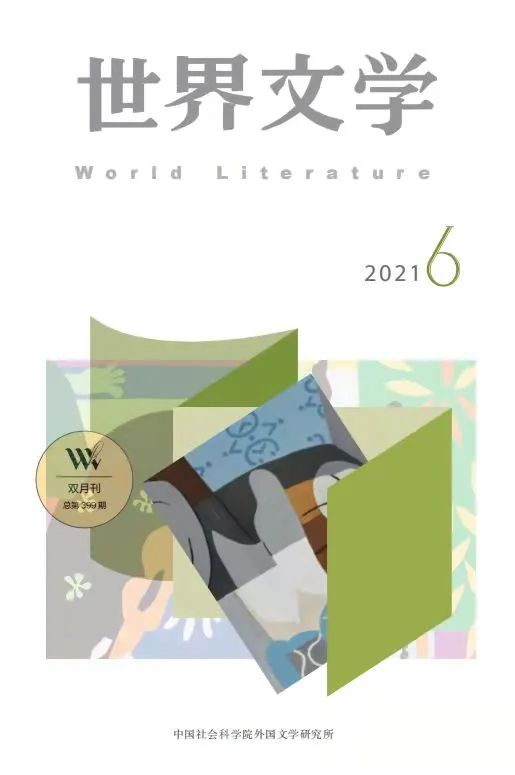小说欣赏 | 金劲旭【韩国】:天国之门

人们为什么非要清除尘土?因为我们终将回归尘土,从尘土中来,到尘土中去;从光中来,回到光中去。你知道星星和人的成分一样吗?其实星星就是宇宙灰尘的结块。我们惧怕黑暗,是因为它提醒我们最终会回归光的真相。惧怕黑暗时,其实我们真正惧怕的是光。
天 国 之 门

做好出门的准备后,她走向水槽,往马克杯里倒了满满一杯大麦茶。大大的杯子上描绘着北欧神话里的动物,她很久以来的梦想就是去北欧看极光。她慢慢地喝了几口,大麦茶还剩下一半。要是为了解渴,半杯本已足够,剩余的是父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只要是入口的东西,父亲都要让她先尝尝,因为他怀疑有毒。
打开手机盖,她久久地盯着手机键,轻轻咬了下嘴唇。她不知道要不要通知家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虽然每次只是给妈妈和妹妹各打一个电话,却让她觉得好像打了二十来个。已经嫁给别人的妈妈态度冷淡,在国外生活的妹妹疏离淡漠,好像是听别人家的事。
女人长按了一下数字键“2”,这是出租车客服中心的电话。父亲总是在深夜犯病,以前只是在电影或电视里看到的急诊室早就成了她常去的地方。随着精神崩塌,父亲的身体也迅速衰败,先是肺出了毛病,接着是心脏和肾脏。
十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司机接单。这个时间本来出租车就少,她无奈搬来的这个小区又十分偏僻,出租车格外少。女人背上包,匆匆离开了家。
“永登浦。”
焦急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女人终于打上了出租。
“永登浦哪儿?”
司机看着后视镜,大声问道。
低低的棒球帽外露出花白的头发,收音机里播放着老歌。
女人说出了疗养院的名字。
“哪儿?”
“不好意思,请把音量调小一点。”
司机关上广播,她一字一顿地说出疗养院的名字。
“那是哪儿?”
自己明明每个周末都坐出租车去探望父亲,却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但女人随后意识到,这是个错觉,自己每次都是坐公交车去医院,只有回家时才坐出租。每次看到父亲嘴里塞满糖块,呆呆地坐在病房的窗前,她都会浑身无力。出租车费不便宜,可她实在没有气力倒两次车了。在饱经沧桑的面孔之下,父亲到底在想什么?他真的在想些什么吗?纷乱的念头最后总会归结于对灵魂和死亡的疑问——人有灵魂吗?如果有,人死后会怎样?这总是让女人更加乏力地走下出租车。


“叫什么医院?”
“常青医院。”
“这名字可真稀奇。”
司机慢吞吞地一笔一划输入目的地。
“没这个地方呀。”
司机突然提高了嗓门,好像受了冤屈。
父亲也总是在记忆恍惚时提高嗓门,数字是导火索,词语是雷管。
医生让父亲跟着念这三个词,告诉他过一会儿要再问。之后,医生让父亲从一百开始做减法,每次减七。三次之后,父亲报出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数字。医生让他停止做算术,问他刚才念的哪几个词。
父亲有时候用“食油”代替“冰块”,用“绿豆”代替“野菜”。医生解释,对食物的执念是典型的痴呆症状。不过,父亲每次都会把“江流”说成是“江陵”。江陵这个地方与父亲的人生毫不相关。她忍不住问父亲是否去过江陵,那里是不是有亲戚朋友。父亲一时露出茫然的眼神,随后就扯着嗓子大喊,“怎么还不上饭?”问他不是刚吃了饭吗,他就大怒,说饭被邻居家的婆娘偷吃了,你是不是打算饿死你爸。
“请稍等。”
女人开始在包里翻找,前天刚交了一个月的住院费,发票应该在里面。翻了好久,她没找到,最后却发现夹在护照里。女人总是随身携带护照,护照有效期限只剩几个月了,上面却一个章都没盖。
女人看着发票,说出了医院地址。
“不是‘常青’,是‘尊荣’,尊荣疗养院。”
司机指着导航大声说,好像在说:“你看,我说得对吧。”
女人这才突然想起来,“常青”是疗养院的附属殡仪馆。真奇怪,医院和殡仪馆名字竟然不一样。
痴呆病房的男护士悄悄告诉她,这是医院为死者家属的处境着想,很多人不得不顾及别人的看法,所以不想让人知道父母是在疗养院去世的。谁也想不到,过去两年她和这个男护士只是点头之交,如今却面对面坐着聊天,就像没人想到父亲会夺过水果刀,大声叫嚷着“放我出去,不然就把你们全杀光”。那一刻所有人都呆住了,只有那个男人做了什么,父亲便突然四肢瘫软,倒在了地上。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一处灵堂,男人解释说自己按了他的一个穴位,以前自己曾经给人针灸。“越是这时候,越要吃东西。”男人把瑟瑟发抖的女人带到了疗养院的附属殡仪馆。男人朝死者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女人呆呆地望着死者的家属,就像被叫到教务处的学生一样畏畏缩缩。男人却泰然自若地在刚摆上饭菜的餐桌前落座,就像顾客找到自己预定的座位,动作流畅自然。
“是认识的人吗?”
女人问。男人把米饭泡进了牛肉汤。
“不是。”
男人耸耸肩,似乎说那又如何。
此后,每次探视父亲,女人都去见见那个男人。第一次是为了表达谢意,第二次是觉得就这么回去不大好,从第三次开始,就似乎变成了必须履行的程序。这不是约会,他们只是坐在藤蔓下的长椅上,喝着咖啡聊几句。女人很好奇,除了扎根马尾,男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他那份自信到底来自哪里呢?回想起来,他在病房里的表现也有些与众不同,打针、换导尿管,细致又自然,让看着的人很安心,显然不仅是手法娴熟使然。


路上灯火通明,司机话很多,而且大都让女人难以回应。司机说,要不是看她文静,自己不会停车,接着便打开了话匣子,唠叨起深夜开车遇到的一些乘客的丑态,什么打仗的事啦,其中还提到有人把纸牌当信用卡结算的事。
“那人瞪着眼催我用纸牌结账,简直让人发疯。那牌还不是什么好牌,是张晦气的小牌……”
司机咂舌。
听说打牌对治疗痴呆有效,女人也陪父亲打过牌。认真端详手中的牌时,父亲好像回到了过去。那时候,他在开车前总是认真查看地图,下班回家会确认鞋子是不是摆放得整齐。
司机再次打开广播时,女人正在为该通知谁而苦恼。她应该上不了班了,所以必须告诉幼儿园。问题是该不该通知朋友们,她拿不定主意,而且她也想不出该请谁来帮忙发布父亲的死讯。

环境不会改变,解决之道在于改变自己。
这是女人学生时代经常哼唱的流行歌曲。看着车窗外的灯光,她思索着在那大片乌云的尽头,在死亡的背后,究竟有什么。
那个男人说,死亡就是变成光的一部分。
“流淌的江水在汇入大海的那一刻最静谧,因为它返回了源头。不对,是它成为了源头的一部分。在最后的瞬间,我们被温暖轻柔的光包围,像羽毛般飞起,成为无尽光芒的一部分。无数的光粒子像尘土一样漂浮在空中,巨大的光芒不断变幻着色彩,起伏荡漾,美不胜收。”
男人轻轻闭上双眼,仿佛在描绘眼前的景象。
“就像极光吗?”
女人眨了眨眼睛,想起之前看过的旅行纪录片中的场景。
“对,就像极光。”
男人嘴角带着微笑。
“你怎么这么肯定?”
男人似乎陷入沉默,却又突然睁开了眼睛。
“要是我说自己亲眼见过,你信吗?要是我说是自己被卡车撞到,心脏曾经骤停的几个小时里经历的事呢?人们为什么非要清除尘土?因为我们终将回归尘土,从尘土中来,到尘土中去;从光中来,回到光中去。你知道星星和人的成分一样吗?其实星星就是宇宙灰尘的结块。我们惧怕黑暗,是因为它提醒我们最终会回归光的真相。惧怕黑暗时,其实我们真正惧怕的是光。所以我们不必畏惧死亡。”
这次女人轻轻闭上了眼睛,认真倾听男人的声音,皱巴巴的心脏似乎一点点舒展开来,其中包括女人在痛苦、委屈和负疚中偷偷想象父亲死亡的瞬间留下的痕迹。
女人从背包中掏出粉饼,补了补妆。
深夜的医院和允许探视的白天空气大不相同。死一般的沉寂中断续传来低沉的咳嗽声、呼噜声、拖鞋拖地的声音,还有马桶下水的声音。这些熟悉的声音过于真实,反倒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泄漏出来的,极为不真实。
气味没变,是奶味、尿骚味、消毒水味儿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奇怪的腥膻。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她在幼儿园每天都会闻到的气味。肋下挂着输液袋或尿袋的老人们住的地方竟然散发着幼儿园的气味,要么是她在疗养院嗅到了新生的气味,要么是她在幼儿园嗅到了死亡的气味,二者必居其一。又或者,生与死的气味原本就是同一种。
女人穿过昏暗的走廊和台阶,走向父亲的病房,只有紧急出口和卫生间透出灯光。父亲在家时,卫生间的灯也总是开着,这是因为父亲前列腺增生。敞着门蹲在座便器旁边小便的父亲像极了警惕地扫视四周的野兽,就像当年无声无息失踪的妹妹第二天手上带着烫伤出现时那样。
她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年纪一把了还要离婚,母亲提起了十多年前的事。
“卖养乐多的大婶把你妹妹带了回来,说是看到她在市场入口大哭。可那个大婶一走,你爸爸就在我耳边悄悄说:‘那个女人,我们是不是该报警?’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觉得透不过气来。”
从那时起,妈妈决心和父亲离婚,当时她十岁,妹妹八岁。妈妈一直等到了妹妹大学毕业,她留在了父亲身边。实际上她别无选择。妹妹抢先表示要一个人生活,妈妈已经有了新对象。最早表示要独立的人是她,希望去日本留学、渴望去有极光的国家旅行的也是她。可是,实际上去日本留学、在那里遇到日本男人结婚、和去日本旅行的芬兰男人再婚、坐上飞机飞往赫尔辛基的人,是妹妹。每当忧郁让内心掀起巨大波澜时,女人总感觉有人窃取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真正的生活似乎在别处。只要不是这里,哪里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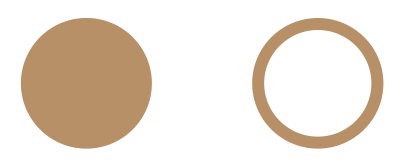

父亲在沉睡,呼吸很浅,眉头紧皱,好像不太高兴。医疗仪器在正常运转,帮助病人度过又一个夜晚。女人仔细端详着父亲的脸庞,像是在寻找什么。她摸索着冰冷的墙壁,打开了灯。天花板上的日光灯闪烁了几下,驱散了黑暗。虽然脸色确实比白天衰败,但父亲看上去并不像是熬不过今晚。
突然,女人觉得天花板似乎低了一些。如果幼儿园小朋友这么说,她就会说“是你长高了”。孩子的世界里没有模棱两可或者无法解释的东西,答案都是明确的。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哭,要么是肚子饿了,要么是尿裤子了;稍微大一点儿的孩子哭,要么是因为玩具被抢了,要么是因为抢不到玩具。
女人走向护士站。
值班护士正抱着双臂打瞌睡,是个男人。在痴呆病区,男护士并不少见,告诉她父亲病危的也是低沉的男中音。
护士似乎察觉到有人,睁开眼睛,问怎么回事,女人讲述了跑来医院的来龙去脉。她话音未落,护士“唰”地站了起来,朝病房跑去,甚至来不及听女人说来了却发现父亲没事。护士检查完父亲的身体,追问女人是不是真的接到了电话。这可太荒唐了。但女人能够做出的最强烈的反驳只是没有底气地问对方没打电话吗。
“我?”
“真有人给我打过电话。”
“可真是的!”
护士掏出手机,开始到处打电话确认。他每次都问“你确定吗”,这个问题重复得越多,瞟向女人的眼神就越凌厉。
“没人打过电话。”
“你的意思是我瞎扯喽?在这个时间,我坐出租赶到医院,就为了这个?”
女人也拿出手机,翻找最近的通话记录。记录不多,她很快就找到了,就是出租车客服中心下面的一条。
“你看,这儿……”
“来电号码未知。”看到这几个字,她也迟疑起来。
“你确定是医院打的电话?”
“电话里明明说父亲撑不过今天晚上。”
“不管怎么说,您父亲没什么大碍,这就行了。”
“请给换一下日光灯。”
“什么?”
“你没听到灯管的噪音吗?”
不知为什么,她觉得无处发泄心头的委屈。
“不好意思,我是照顾病人的护士,不是换灯管的师傅。”
护士似乎觉得很荒唐。
“这个声音让病人睡不好,不也有害健康嘛。如果是那位,二话不说就会给换。”
“哪位?”
“算了。”
“现在请回吧。”
“既然来了,我待会儿再走。”
“已经过了探视时间。”
两人沉默不语,气氛紧张起来。
“我都到医院了,怎么能就这么走呢?”
女人突然用哀求的语气说,双颊绯红。她既不主动也不擅长吸引异性,每当这种时候就会脸红,反而时常因此引起男人们的关注。虽然有足够的潜力,女人在这方面却很迟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有罪恶感,大都是不必要的罪恶感,女人在这不必要的罪恶感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这也是她在不知不觉间拒绝寥寥几个追求者的方式。当最为耀眼的青春之光——婚姻离她最近的时刻——女人坐在咖啡馆里,仿佛漂浮在日落时分的大海上,求婚戒指摆在面前。她却仍然想起了父亲,父亲的三餐,父亲的失眠,父亲病情发作,总之都是父亲造成的阴影。
“这很难办……”
护士挠着头走出病房。
女人坐在父亲身边,认真思考是谁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是恶作剧吗?知道父亲住院的人不会做这种坏事。是新型诈骗手段吗?电话里没说要钱,会不会想趁家里没人去偷东西?她摇了摇头。这也太荒谬了。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她还是觉得有点害怕。


现在看来,父亲好像比在家的时候胖了点。女人忽然心里一阵发冷,就像看到整天急着吸引人注意的孩子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实际上,消瘦下来的是女人。自从开始一个人生活,她就经常在等公交或是挑海鲜、浇花时像从梦游中惊醒的人一样,一惊一乍地环顾四周,因此经常听到别人问“你没事吧”。她一个人的晚饭越来越敷衍,最后变成了一个蒸土豆果腹。傍晚时分,在昏暗的半地下厨房里,女人一口口地往嘴里塞土豆,仿佛是个荷兰画家画作中的情景。她期盼着,只要甩掉父亲,自己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换上最新型号的手机,上英语口语补习班,去看极光。只要没有父亲。
吞咽土豆时,女人偶尔会被噎到,与此无关的是,她好几次产生了接父亲出院的冲动。父亲每次转入重症监护室,她就被迫搬家,一步步搬到市郊、小房子、贫民窟,后来为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她不得不搬进了半地下室。如果再搬,就只有上天或者入地了。但是,她没有信心承受父亲随时爆发的暴力行为。
父亲挥舞锤头打碎镜子的那天,女人光着脚逃出家门,冲进公共电话亭,给妹妹打了对方付费电话。但让女人更为震惊的是,妹妹反应平淡,似乎并不认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看来姐姐小时候没挨过打啊。我可是动不动就被暴揍一顿。”
女人不相信妹妹的话,就像妹妹说不记得失踪事件的时候。
不知什么原因,她的父母对这件事总是遮遮掩掩,只有在吵架时才会提起,而且每次都会牵连到她。父亲骂她连唯一的妹妹都照看不好(女人当时只顾和朋友玩耍,没发现妹妹不见了),母亲并不为她辩解,认同了父亲的说法。女人觉得委屈。她和妹妹提起那件事,大概也是想从妹妹那里得到原谅。如果仅仅出于好奇,她不会开头就说“当时在家的我快吓死了,更何况你呢”。
“你在说什么?”
妹妹却像毫不知情,不悦地问道。
女人把自己记得、不记得的都说了,从那天的天气到穿着,可直到最后,妹妹也没能想起任何相关的记忆。女人无话可说。最开始她目瞪口呆,后来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妹妹当初该是多么害怕,多么想忘掉这件事,才会变成这样?她同情妹妹,但并不能缓解自己的难过。越是回想妹妹的反应,这种情绪就越发明显,清晰得就像妹妹手背上的烫伤。女人得出结论——妹妹还在怨恨自己。不过,当她从突然爆发的父亲眼中看到陌生的灵魂火花和生疏的生命阴影时,不能不重新思索妹妹的话。到底哪个是真的?我熟悉的父亲去了哪儿?
女人守在父亲身边。她觉得应该这样待到天亮。父亲两手整齐地放在胸前,像是等待入殓的尸体。可能是因为窗外闪耀的霓虹灯,父亲的双手发青。在不时变幻色彩的灯光里,女人感到筋疲力尽,真想立即卸妆,躺进热气氤氲的浴缸中。霓虹灯就像深夜的彩虹一样耀眼。
“我看到了极光。姐姐也该来看看的。”
想起看到极光后兴冲冲打来电话的妹妹,女人愈发疲惫不堪。
她把胳膊肘拄在父亲床边,两手并拢。刺痛像条毒蛇,盘踞在极度的疲惫之中。小腹滚烫、坠胀。如果这预示着要来例假,那就比上次早了十天。她看过一篇报道,说越是不生育,闭经会来得越早。此后,她就开始对例假的周期变得很敏感。她合起双手,撑起额头,看起来像是在恳切地祈求什么。然而,她甚至连祈求的力气也没有了,泪水沿着两颊流淌,疲惫时像有魔力般给予她安慰的前生故事(那个男人说,她前生是被送到元朝作人质的高丽公主,父亲是守护自己的武士)也毫无效果。女人哽咽抽泣,害怕吵醒父亲。


寒气让女人打个寒颤,睁开了眼睛。电暖器一直在散热,寒气的源头是父亲,他手脚冰凉。女人揉搓着父亲的手脚,突然摸了摸父亲的额头——冰凉,她又试着把手放在父亲的鼻子下方——没有呼吸的迹象。
“来人呀!来人呀!”
女人跑到走廊,朝护士站大喊。
“什么事?”
走廊另一头传来睡意朦胧的声音。
“父亲,他不对劲。”
护士跑进病房,检查父亲的身体状况。
“这样多久了?”
护士的声音里透着焦急。
“不,不知道。刚才我打了个盹儿,醒来发现……”
护士似乎在呼叫值班医生,不一会开始用两手用力按压父亲的胸口。
医生连白大褂的扣子都没扣,气喘吁吁地跑来。他先号了一下父亲的脉搏,又翻开父亲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
“心肺复苏做了吗?”
“没效果。”
“ADE除颤!”
护士拿来电击除颤仪,这时又跑来一个女护士。女护士解开父亲的上衣扣子,连上了电极板。
“二百!”
医生搓着手中的电极板喊道。
男护士旋动了除颤仪的电压调频钮。“哔”地一声之后,医生把电极板按在父亲胸口,父亲的身体猛地弹起。
“脉搏!”
“没反应。”
“三百!”
父亲的心脏依然毫无反应。
“三百六!”
父亲的身体弹得更高,蓝色电子屏幕上的白色直线一动不动。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护士们用隐秘的眼神相互交流——都结束了,抢救失败。只有女人还没明白眼前的情况。医生无力地放下除颤仪,木然地看着手表,毫无感情地宣告病人死亡,她却仍未反应过来。
父亲眼角下垂,嘴角微微上扬,分明是在微笑。父亲这一辈子总是神情严肃,就像个对自己的角色不满意的演员。这样的父亲竟然在微笑?女人差一点就要喊出“父亲在笑”。
女人好像受到了意外一击,身体摇晃了几下。她有些恶心。父亲的微笑背后分明隐藏着什么,需要查明,那笑容里隐含着不平之处。身边的女护士想扶住她,女人摆摆手,摇摆着手臂走出了病房。
不见了父亲的微笑,女人依然一片茫然。父亲究竟经历了什么?竟然露出那样幸福的表情?那种幸福的表情,就像一下子打开了天国之门。
忽然,一段话像闪电一样划过女人的脑海。
针灸高手们也会接屠宰场的活儿——为了摆弄出祭桌上用的猪头。在头顶心深深地刺上一针,猪就会微笑。其实这只是肌肉的机械反射,并不是真的在微笑。只有人会笑,笑才是灵魂存在的证据。人身上有个穴位,可以让灵魂脱离肉体,被称为天国之门。在这个穴位上深深扎一针,人就会陷入沉睡,微笑着去往另一个世界。

女人好像知道了是谁打的那个电话。那个隐藏电话号码的声音是说“撑不过今晚”,而不是说很难撑过今晚,或是可能撑不过今晚。女人打开紧急出口,走进楼梯间,确认周围没人后掏出了手机。等待对方接听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道想说什么,想知道什么。
冷静下来想想,她的疑心缺乏有力的证据。仅凭肯定的语气就能断定是那个男人吗?父亲的微笑?仅凭这就能断言是那个男人干的吗?女人没有了自信,甚至开始怀疑父亲是否真的微笑过。
那个男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人皱起眉头。上周,她探视了父亲之后向那个男人提议一起喝一杯。为了支付这个月的住院费,她不得不停止每月一直存三万韩元的养老保险。父亲却始终没有认出她。女人想一醉方休。
“那个人是谁啊?我的父亲呢?他去了哪儿?”
女人勉强喝下几口烧酒,借着酒意发泄不满。
男人一言不发,只是喝酒。
“人死后真的会变成光吗?”
女人追问。
男人缓缓点头。
“真的变成光吗?所有人,不管以前怎么过的?”
男人再次点头。
“没有任何痛苦?”
女人再次发问,好像要确定什么。
“是的。从肉体的牢笼中解脱的瞬间,会感到喜悦。”
“也就是说……”
“没错,就像打开了天国之门。”
男人直勾勾地盯着女人回答。
女人有些脸红,避开了男人的视线。
该不会是……女人像被自己的影子吓到的孩子一样,身体抖个不停。她感到不寒而栗,却又说不清具体的原因,原因不明让她更是脊梁骨发凉,好像她害怕的什么不知何时已经变成无法挽回的现实。
女人重新拿起电话,她想听那个男人说“这简直荒唐”。她觉得,如果听到他特有的沉静声音,自己就能像以前一样,平复这纷乱的心绪。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害怕,如果听到了可怕的事,该怎么办?
仿佛会一直响下去的电话铃声停了下来,响起了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请发送短信。”殡仪馆的灯光映入了女人的眼帘,或许……?她朝殡仪馆走去,脑子里回想着男人的话——坐在祭奠陌生人的灵堂里,内心会变得平静;理不清头绪或心情沉重的时候去灵堂,心里会莫名其妙地轻松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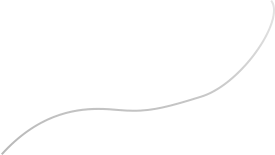
真的来到殡仪馆门前,女人却踌躇起来,恨不得扔一枚硬币,正面朝上就进去,反面的话……她很矛盾,既希望那个男人在,又希望他不在;既想当面质问他,又不想这么做。如果掷硬币决定,她觉得自己似乎能够坦然接受。
不知不觉间,女人已经开始在殡仪馆入口的电子屏幕上寻找遗属名单最长的灵堂。女人曾问男人,有没有被发现过是陌生人,他笑着说“选遗属最多的地方,就算看到了陌生人,他们也会认为是其他兄弟姊妹的朋友”。
女人挑选了一位有三个儿子、儿媳、两个女儿、女婿的死者,走上台阶。
三层贵宾室被走廊分为灵堂和接待室两部分。接待室里坐着零零散散的吊唁者,就像即将打烊的餐厅一样冷清。
在接待室入口脱鞋的女人突然停止了动作。那个男人坐在角落里,面朝着墙,正在喝酒。女人踉跄一下,扶住了鞋柜。本以为已经按捺下去的呕吐感又在腹部深处蠢蠢欲动,这只是前兆,似乎有一股寒气袭来,接着却是一股强烈的灼烧席卷全身。要吐了,因为她想起了早就忘却的一段记忆。
那是在一门名为“现代诗歌理解”或者“现代诗歌赏析”的大学选修课上,年轻的老师用低沉柔和富有魅力的声音让女人朗诵一首英文诗,作者据说是一位把头伸进煤气炉自杀的女诗人。老师让从第一排学生开始,每人朗读一节,并做出解释,所以不能说是特意指定了她。不过,随着次序越来越近,女人脸颊发热,呼吸急促,这并不只是因为仰慕这位老师。女人努力让剧烈的心跳平静下来,她站起身来开始朗读最后一节。
一根木桩,
扎在你肥硕的黑色心脏。
村民们一边跳舞,一边践踏着你。
他们一直都知道是你,
他们从来不曾喜欢你。
问题是下一行。沉默在持续,却又似乎随时会被打破,对于张不开嘴的女人来说,就像是某个人的一生。二十来岁的女学生坐满了剧院式的讲堂,一片静默,好像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或许是感觉气氛有些尴尬,老师做出一副戏谑的表情,开起了玩笑。
“别担心,我们不会向你父亲告状。”
语气很夸张,像是在安慰孩子。女生们大笑,对老师的机智表示赞赏。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笑。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情绪像雷电一样,击中了女人。她最终也没能说出口的最后一行诗是——
爸爸,爸爸,你这个混蛋。
从那以后,女人很长一段时间和父亲连招呼都不打,不过并不是出于愧疚。
女人调转了脚步。走出殡仪馆,她立刻掏出手机,按下数字键“1”,手在颤抖。或许是因为按得太久,电话打到了第一个快捷键——那个男人的号码。女人慌忙挂断,重新开始拨号。这时候,她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的那种可怕情绪是遭到羞辱的感觉。那首诗真正的结尾还有一行——
爸爸,爸爸,你这个混蛋。我,完了。
女人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终结,仿佛父亲咽气时也带走了她的余生。
女人再次拨打电话,给警察局。


金劲旭(1971— ),韩国当代著名作家,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戏剧创作系教授。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谁杀死了科特·柯本?》《神没有孙子》《女朋友的父亲们》,中篇小说《照镜子的男人》,长篇小说《金苹果》《童话一样》《千年王国》《棒球是什么》《豺与犬的时间》等。2016年,短篇小说《天国之门》获得第40届李箱文学奖。
金劲旭的作品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他擅长从其他文学作品、电影、音乐等艺术作品以及新闻报道中寻找灵感,发掘素材,“以电影式的想象力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篇章”。其文风平实、洗练,多以客观冷峻的笔调剖析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天国之门》讲述了老人的赡养与死亡,揭示出现代社会中共同体的解体、人的孤立以及隐秘的欲望和暴力等问题,以严密的结构、精巧的细节描写、过去与现在的交叉叙述以及对死亡的新颖阐释独树一帜,被称为“里程碑式的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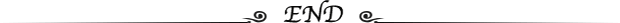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熹微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