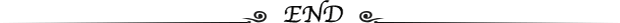国际妇女节 | 钱满素:只有当男人不再是原先的男人,妇女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觉醒之后
觉醒之后
——《我,生为女人》编后感
英国女作家多萝西·L.塞耶斯(1893—1957)说过一句话,令人深思。她说:“时间和磨难会驯服一个自在的青年女子,但一个自在的老年妇女是任何人间力量都无法控制的。”许多女人只是在扮演完社会要求于她的性别角色后,年过半百,才获得独立的意识,才发现被淹没的自我,才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她卸下女人的包袱,又不必受制于男性所感到的压力,如此,确实还有什么人间力量能去控制她呢?
回顾人类社会历来对女人的控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近至本世纪初,缠足之风仍在中国盛行,它象征着中国妇女从生理到心理的被迫就范和畸形扭曲。私塾的门、科举的门、仕途的门,门门对妇女紧闭,留给女人去建功立业的只有一块阴惨惨的贞节牌坊,这可是天底下没一个男人会去争的。秋瑾女士这样描述当时的女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敬告姐妹们》)这位中国女权的先驱别号“竞雄”,以明自己“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之志。作为女性,她不得不在两条战线同时抗争,一面“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一面痛心疾首奉劝女界,务必长点志气,自立自主,切莫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可是在她两万万女同胞中,呼百是否能有一应呢?取媚依附于男人是社会派给女人的“天经地义”的谋生方式,先知先觉的秋瑾免不了做一个身首分离的孤胆英雄。


左为多萝西·L·塞耶斯 右为秋瑾




宗教淡化后,在美国取而代之的是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它和清教的灵魂说一样,也有利于促成两性平等。立国之初,亚当斯夫人便提醒革命领袖在制定法规时“记住女士们”,请他们“切切不可把无限的权力置于丈夫的手中”,因为“倘若可能的话,所有的男人都会成为暴君”。她警告说,“如果不给女士们专门的关怀和关注,我们就决心煽动一场反叛,并且决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的约束”。将《独立宣言》中的革命原则运用到妇女解放事业,亚当斯夫人是第一位。
从那以后,美国女界精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两性平等的斗争。她们中有写《论两性平等》(1790)的默里,有写《论两性平等之信札》(1837)的格里姆凯,有写《19世纪妇女》(1845)的富勒,更有为女权奔走呐喊的社会活动家安东尼、莫特和斯坦顿等人。这些女权先驱人物均为出类拔萃之辈,画像中一个个目光炯炯,英气逼人。她们受过良好教育,性格刚毅,人格高尚,富于理性和正义感。作为第一批进入社会的妇女,她们对两性不平等现象必然观察体会得最为清楚,但她们既不自卑,又不情绪化,可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她们反复强调的是男女人格和智力的平等,苦苦追求的是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奋力拼搏的是女性的经济独立和人格尊严。她们的努力终于导致美国第一次女权大会的召开(1848年于塞尼卡福尔斯),会上发表了由斯坦顿起草的《女权宣言》。它以《独立宣言》为蓝本,宣布男女生而平等,并声称“人类的历史是男子为了对妇女实行专制的暴政统治而对她一再侵犯和伤害的历史”。宣言认为,“造物主赋予妇女同等的能力,她同样意识到发挥这些能力的责任。显然,她和男子一样有权利和义务以一切正当的途径弘扬一切正当的事业。”宣言要求让妇女立即获得她们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大氛围中,一个半世纪前的美国妇女便懂得如何联合起来,用宣言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公布于世,并力争法律的认可,这充分显示出她们世界领先的政治觉悟。


在文学上,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致力于表现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如肖班、吉尔曼、华顿等人。其中肖班的长篇小说《觉醒》(1899)尤为引人注目,它除了肯定女性的人格觉醒和独立的人生价值外,还非常超前地表现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进入20世纪后,美国涌现出成批的职业女作家,她们的作品涉及到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描写了生为女人的苦恼,又突出了女性追求平等的意识和顽强不懈的奋斗。到了20年代,独立自主的女性不仅能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受到推崇。斯泰因便成了这样一位传奇式女性,这倒反令她抱怨美国公众对她本人的兴趣超过了对她作品的兴趣。对她这样的女性来说,男女平等的字眼由于已经成为事实而不再那么重要了。
重提过去,倒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想提出一个与现实有关的问题:既然当代女权运动的许多观点在一个多世纪前便已提出,那么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还要再来一次觉醒和解放运动呢?
1963年,弗里丹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女性奥秘》一书,被认为是引发了这场妇女运动。从1957年开始,弗里丹对从母校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满十五年的校友进行调查,了解她们的实际生活与所受教育的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妇女中潜伏着一种巨大的不满,社会对女性的一般观念并不符合她们的人生经验。弗里丹发现,大约在二次大战后的十五年间,美国社会重新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她不再是具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而是依附于丈夫、惯于自我牺牲的郊区家庭妇女。她甘愿放弃学业,放弃事业,只为找个好丈夫,建立家庭,当好贤妻良母。舆论一再鼓吹,“真正具有女性本色的女人并不想要事业、高等教育、政治权利——并不想要过时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之斗争的独立和机会”。这一关于女性的流行观念被弗里丹称为“女性奥秘”,它在战后迅速形成声势,成为支配美国妇女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准则。它的成功除了传统的原因外,战后的经济、社会、心理状况,弗洛伊德性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所肯定的两性互补的功能说,教育界的性偏见,商界庞大的销售攻势等等,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如何把妇女打发回家又使她保持心理平衡呢?答案是通过名目繁多的家用设备把家务劳动复杂化,使之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使每个从事它的妇女都能骄傲地在职业栏中填上“家庭妇女”这个词。


傅立叶的名言是“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妇女的解放既是文明的标志,又受制于文明的发展。在许多贫困国家的妇女看来,美国郊区家庭妇女的生活也许十分令人向往,求之而不得。但美国的女权运动偏偏正是从这批受过高等教育、吃穿不愁的中产阶级中发起。看来禁果还是不吃为妙,开发智力和保持奴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早看到了,并且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话,便把无才美化成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矛盾。美国人又要妇女受教育,又要她满足于琐碎的家务,于是不能不生出许多的不满来。这种不满并非由于物质的匮乏,甚至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而是由于人性的提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自我本质的危机,是物质和精神达到一定水准后才会出现的文明病。美国妇女被这个“无以名之的问题”困惑骚扰多年后,终于石破天惊,发现身陷“女性奥秘”之囹圄,急需突围而出。她们找到了共鸣,变他信为自信,变怀疑自己为怀疑社会,联合起来向社会发难。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迸发出的是长期压抑后积聚起来的巨大能量,觉醒唤起的力量汹涌澎湃,冲击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觉醒是痛快的,而且极富正义感,使人体会到道德升华所带来的崇高,但觉醒并不给人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觉醒后无路可走,可能比不觉醒还要痛苦。鲁迅曾经说过:“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然也还有别的路,比如死,比如凄凉度日。《觉醒》的女主人公爱德娜敢想敢做,准备去自食其力,置舆论于不顾,但遗憾的是,她的解放仍然需要一个男人的理解和配合,当她爱的男人不能承受这一重负时,解脱的方法就是消灭自己,投身大海便成了她觉醒的下场。格雷斯·佩莉在70年代初发表了《长跑者》,写一位中年妇女在自我意识觉醒后,“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憧憬!”但未来到底如何呢?我们再来看看她在80年代末写的《朋友》,几个当年志同道合的女友至今仍在相互安慰支持,但已经是在临终的病榻前。她们回首往事,显然哀伤多于欣慰。觉醒后的问题不解决,妇女难免要一次次地反复觉醒,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19世纪上半叶的女权运动似乎在发表女权宣言后便画上句号。南北战争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家庭在农业社会中作为自给自足生产单位的功能逐渐消失,妇女作为生产力的地位也随之失落。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日益明确后,女子越来越成为处于从属地位的消费者。在中产阶级标榜的“可爱的家”中,要求妇女更多的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美德,诸如虔敬、纯洁、忠贞和顺从。一次大战后,美国妇女齐心协力争得了选举权,但目的达到后便偃旗息鼓,花了半个多世纪争取来的选举权却不知如何使用。二次大战后,“女性奥秘”居然又能盛极一时,征服了绝大多数女性,这些都是足以令人思考的史实。甚至在六七十年代激进的女权运动过后,“欢迎回家”的浪潮又伴着“维护家庭”的呼声在90年代向美国妇女悄悄袭来。行在前途崎岖的路上,往回走一条容易的路,大概也是人的本性。说到底,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才是妇女解放最关键的问题。


内在的阻力又有两层:一是思想上的障碍,千百年的从属地位一直在摧残着女性的独立和自信,使她们难以自拔,觉醒就是冲破这层阻力。但内在的阻力除了“破”,还必须“立”,必须明确女性的人生价值所在,女人一生的中心所在。觉醒是破旧,立新才是目的,不知道该立什么,又如何去立?自我本质危机不解决,女性便将永远地徘徊彷徨。弗洛伊德用了半个多世纪在分析女人,到了77岁却还在问:“女人需要什么?天哪,她们需要什么?”弗洛伊德是他自己文化的囚徒,相信女人天然不如男人,他当然不能解开这个谜。不过,谁又能否认,这个谜至今尚未解开。男人必须在社会上奋斗,这是一致公认的,从未有过异议。而女人是否需要进入社会,则不仅在男人中颇有反对者,女人对此也持不同看法。认为妇女应该在家庭中完成自己的观点一向很有市场,如果说男人是为了维护夫权而支持它,那么女人为什么也赞成呢?难道她们不希望独立自主,取得平等的地位吗?80年代初,弗里丹就说过:“60和70年代的许多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使妇女运动要功亏一篑的正是妇女自己。”(《第二阶段》)
又是一个为什么。我想,困难大概在于女人进入社会后并不能停止做女人。当然,男人也不停止做男人,但对男人来说,社会和家庭不仅不矛盾,而且往往相辅相成。可是对女人来说,这两者却常常不可兼得。当社会严格地以性别分工时,男人承担全部社会工作,女人则养育子女,承担全部家务。当妇女外出就业,社会上的那份工作并不因为她是女性而减轻分量,而如果她还要家庭的话,又免不了生儿育女,家务缠身,势必承担着原先两个人的工作。换句话说,这时的她既非以前的男人,又非以前的女人,而是男女合一的女超人。世上毕竟凡人多哪,大部分女人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在哈佛出版的《美国现代著名女性》一书中,共收入从1857年到1943年出生的四百四十二位妇女人物,其中终身未婚的几乎占百分之四十,结了婚又离异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她们的单身比例远远高于妇女总人口中的比例。如果这是一本著名男性人物辞典,其单身比例决不会如此之高。美国历来女性就业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献身事业的知识妇女,她们往往单身;一类是成了家的劳动妇女,大都迫于经济需要而工作。大部分妇女只要有条件,就不外出工作。只有事业没有家庭的女人显然缺少了做女人的那部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成了第三性,这种前景自然令其他妇女望而却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必须作出选择时,绝大部分妇女会选择家庭。如果妇女愿意待在家里,那么别人又怎么去“解放”她呢?


男人自艾自怨时,常说悔不该做人,却不说悔不该做了男人。而女人不幸时却大都自问为何偏偏做了女人。妇女的解放迟迟疑疑,反反复复,其中确实悖论不少,略举几个为例:
悖论一:妇女进入社会是解放/妇女进入社会不是解放。
什么是妇女的解放?是从两性不平等中解放呢,还是从双重负担下解放?换言之,由从属地位转为双重负担或“第三性”算不算妇女的解放?




传统的性别角色已经被打乱,这一点毫无疑问。原先的行为准则也已失效,妇女在觉醒后必须成为新的女性才能生存。这新女性既非原先的女人,也非原先的男人,也不是两者之和,而是一种完全新型的人。女子在重新塑造的过程中,男人也必然而且必须随之改变。事实表明,大凡在两性较为平等和谐的地方,大则社会,小则家庭,改变的绝不能只是妇女。只有当男人也不再是原先的男人,妇女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否则的话,不是出现所谓的“阴盛阳衰”,便是女人醒了以后再回去做梦。人类的两部分是不能不同步的,在经历了母系和父系社会后,难道不该迎来两性真正平等互补的时代吗?迪第恩在《妇女运动》一文中引了富勒的一句话“我接受宇宙”,以区别她与当代某些偏激的女权主义者。正是这位富勒,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便在召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时将“允许两性相互影响,并以一种更有尊严的关系互相促进”,男女双方都能发展完美和谐,相得益彰。到时,人们再也不必带着“任何热情或痛苦”来谈论他(她)们的性别了。人类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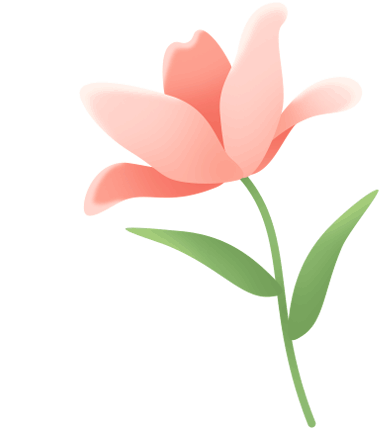
钱满素,1946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著有《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美国文明》《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论文集《飞出笼子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过《年轻的美利坚》《我有一个梦想》《我,生为女人》《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过不少有关美国历史、文学、政治的论文和文章。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5年第2期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