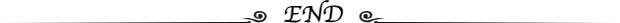疫情现场 | 周雅:这个世界,一口咬下去嚼个稀烂再吐出来,会不会变得好一点?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新冠的出现似乎传递了一些信息,地球好比是广袤银河里一座小小坟冢,曾被挖掘出来的我们坐上开往地底的葬船,即将再次被埋葬,恒久凝固在失去意义的时间里,等待再一个一千年。

周雅



这让我想起春天开始每日清晨在家门口十字路口等我打招呼的智障老人,一手撑着手杖斜靠在自家庭院外的栅栏边上,等我骑车路过的时候,挥挥拐杖说声“おはよう、おちゃん”(早啊,小姑娘)。说完看我走远就慢慢挪回屋里。一开始不知道老头儿是专门等我的,后来有一天早上老人多说了一句“今天这么晚,要迟到了”,我才意识到老人每日的等待。



感染人数减了又增,感染趋势柱状图高了又低了,京都人的神经也随着岁月越变越细,小心、克制、易受惊又脆弱。京都新闻报道感染新冠病毒的中年女性在家疗养期间撇下还未长大的孩子选择自杀,生前记事本上还写着“会不会传染给女儿呀”这样的话。古都的人啊,心脏都装着发条鸟吧,一圈一圈……再一圈上紧发条,突然有一天,他们带着孩子的戾气一下子把小鸟的头拧断下来,时间终止了,心都搅裂了。新冠没有终结她,她选择自我终结,新冠给了多少日本人离开的理由,好像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想存在过。



二〇二一年的这个春天还是戴着口罩,我骑自行车沿着鸭川寻找这座城市里恒长的坐标,或人或物,或强或弱,好比寻找京都的脉搏。我很喜欢每当好天气的下午固定在鸭川边午睡的一对夫妇。三条大桥南边一点的鸭川边上,夫妇二人和衣而眠,来来往往嬉笑怒骂的人,蹦蹦跳跳的狗,熙熙攘攘的自行车,天地不动,他们不动,两块坐垫,一样色系的冲锋衣,一样的动作,一样的朝向,两点到三四点,睡够了拍拍衣服一起开心回家。我时常觉得,只要夫妇俩能和川边草丛的鸭子一起继续在鸭川睡着,古都的梦多少都不会被惊扰,他们像一枚枚桂花的十字针脚,缝合这座古城精致易碎的衣角。




新冠的出现似乎传递了一些信息,地球好比是广袤银河里一座小小坟冢,曾被挖掘出来的我们坐上开往地底的葬船,即将再次被埋葬,恒久凝固在失去意义的时间里,等待再一个一千年。一千年以后,大象是寂寞的,老虎是寂寞的,飞鸟是寂寞的,新冠病毒是寂寞的,地球也是寂寞的,他会挖开地下的葬船,送我们回地上。一千年前上船在鸭川遇到的人,一千年后还是想遇见吧。生生死死一条河,天地从没缺过什么,一落地就缺了的是人。命里缺的那些捶打着我们嘶吼着挣扎着寻求补完,我们折腾过喧闹过,登上一艘、下一艘轮回的船。




眼下,龙安寺站停下的五十五路公交车上,涌进车后排的一群不戴口罩的小伙子丝毫不在乎车里人投过的责备目光,嚷嚷着,仿佛要燃起大和魂与新冠病毒对抗到底;靠近车头前排爱心座位上的唐氏综合征女孩流着口水,不耐烦地踢着座椅底部,哼着听不清的语言,她双手悬在半空里比划着我们看不见的什么物体的形状,口罩被口水浸湿了,一旁母亲样的人满脸尴尬与无奈。经过女孩下车的时候,女孩看着我嘟囔着,似乎解释着一些什么,“新冠病毒这么大一个,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我猜测着她大概想说出声的话。这个时节,窗外挤进来的春风是女人微汗的甜腥味,车后排张牙舞爪的健康听上去多少带着一些年少气盛的残忍。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5期,责任编辑:秦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