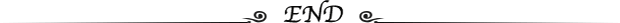读者来稿 | 刘梦园:抗衡孤独与黑暗——看《世界文学》400期直播有感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与凄凉并存。读书可以使人在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暂时远离现实的泥淖,从书中汲取慰藉和力量。
窗外春寒料峭,直播就要结束了,意犹未尽,有一首诗浮现在我眼前:“我自由独立,世界就在眼前。”

抗衡孤独与黑暗:
看《世界文学》400期直播有感
2021年10月1日,《世界文学》编辑部向广大读者发起“‘从眼缘到情缘’出刊四百期征文活动”,我要给学生上课,没有顾上投稿。但毕竟在探索发现异域文学的路途中,与《世界文学》有过美好的邂逅,驻足相伴过,读了外国作家独特的作品,想了解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进而延伸阅读与他们相关的人和事,包括他们住过的房子和走过的街道。得知《世界文学》编辑部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期刊分社举办“‘从眼缘到情缘’线上直播分享活动”,2022年3月2日晚,我早早做好准备,眼睛盯着直播界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直播终于开始。《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老师讲话,他希望《世界文学》成为一面旗帜,永远保持自己的青春活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梁艳玲发言:“有趣的灵魂,终将相遇和相识,有趣的灵魂互相欣赏和感染。”余静远编辑回顾征文策划选稿的过程:最终有17篇稿件登在《世界文学》第400期上,用了50多页,可见编辑部对读者反馈的重视。直播现场连线诗人桑克、学者沈喜阳、公务员孔天骄,他们讲述了自己与《世界文学》的故事。叶丽贤副主编和法语文学编辑赵丹霞老师分别对第400期的科幻作品和《宅游记》进行了精彩解读。



这次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纪念老翻译家 。在场的编辑提到了几位近期去世的老翻译家,特别是2022年2月22日离世的罗新璋先生(享年85岁)。赵丹霞老师介绍罗新璋其人其艺时,我赶紧在直播评论处写下:“古今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即刻有文友呼应,连说:“对,对,对!”
我读过罗新璋翻译之路的文章。他从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分配的工作不如意,无法发挥专长,想改变环境谈何容易,但他深知抱怨没有用,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人。他上大学时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觉得译笔高明,击节叹赏,由此产生了对翻译的兴趣。现在每天不得不面对萧索的现实,磨砺志气,积极抗争,下班后,只要有点空,就一边读,一边抄写傅雷翻译的外国名著,在原文下面,把傅雷的译文一句一句抄下来,二百多万字,仔细阅读,得其真传。日复一日,默默地努力,他给傅雷写信求教翻译问题,傅雷回信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张,即翻译要化为我有,就是要设身处地,进入角色。他后来之所以能跳出原有的环境,全靠了自己过硬的翻译本领。
应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约请,罗新璋于1991年2月到1993年2月期间翻译《红与黑》。年过半百的他迎难而上,只争朝夕。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译到七点去上班,再利用工作空隙进行校正修润。他译《红与黑》时每天看傅译取经,把字里行间的意思译出来,兼顾上下文,把文气理顺。每天翻译一千字,初稿放开译,不受拘束,到修改时才拉回来。翻译从初稿到定稿,一共改了好几遍,改一遍抄一遍,抄了三四遍,精益求精,至臻至善,请求出版社宽限半年交稿时间。交稿后,又专程去杭州,因书尚未发排,又誊改在发稿本。这一道改,多余的字,尽净删去,以求简洁,这样,文字就干净多了。难怪一个大学生说:“下此苦功,译得好,没有什么稀奇;译不好,倒才奇怪!”
伟大的作品都是在孤独中磨砺出来的,罗新璋老师是下功夫的楷模。事实上,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成功需要积累,在春华秋实岁月的流转中,珍惜时间潜心积淀,一定会收获成功的果实。


直播中有读者问高兴主编文学的作用,他回答了两点。其中一点是对抗孤独,每个人都是孤独者。我想到世界级的名家总能发现孤独体验的不同寻常之处。如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所示,那个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三十五年的打包工汉嘉,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独自一人体味阅读的快感。“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到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身处孤独的人是了不起的,他远离世间的纷扰,与书同处一室,感受着深沉和欢喜。于是,有限而短暂的个体在阅读中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热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
高兴谈到的另一点是抗衡现实中的阴暗。我立刻在直播评论上写下:“抗衡,暂时远离现实的阴暗,还有美好和光明。”这句话在屏幕上停留了几秒钟,那一刻我跟线上的编辑和读者共鸣了。
在西安疫情封城封社区那一个月,我足不出户,手捧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读了又读。赫尔岑年青时为反抗沙皇暴政,被监禁流放。后来,为了摆脱警察的严密监视获得自由,他从俄国黑暗专制统治中挣脱出来,心头充满了憧憬,开始了客居异乡的流亡生活,又经历了朋友背叛自己,婚姻生活出现危机,母亲和他的一个儿子遭遇海难,妻子病逝,妒他的人不断从阴暗的角落发出冷箭。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的出路在于工作,我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在伦敦筹建俄文印刷所。”他用文字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唤醒人民解放意识。《往事与随想》写了十五年,他说:“多年来,它代替了我的亲人和失去的一切。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在遭遇一连串打击之后,赫尔岑因为写作而没有消沉,他清醒地意识到,把不为人知的经历写下来,不至于淹没,是他人生的凭依。他认为:“我们不想在信仰中变得更愚昧,便得在怀疑中变得更聪明。”这个观念令人深思,耐人寻味。
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与凄凉并存。读书可以使人在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暂时远离现实的泥淖,从书中汲取慰藉和力量。
窗外春寒料峭,直播就要结束了,意犹未尽,有一首诗浮现在我眼前:“我自由独立,世界就在眼前。”


《世界文学》400期直播之夜,读者们热情高涨,争先恐后,踊跃评论互动,热闹非凡。我站在古城西安的土地上,写的文字到了北京《世界文学》直播间。参加这次直播活动后,这两个评论被精选上了,在《社科期刊网》和《世界文学》回顾直播的文章里,留下了踪迹。难忘受到编辑的精彩发言激发,立刻写下自己心得的瞬间。那个夜晚不会再来,那一刻定格在记忆中。《世界文学》是我订的唯一杂志,它是通向最新的世界文学的桥,连接世界的纽带。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刘梦园,原名刘哲,祖籍浙江诸暨,生长于陕西西安,语文教师,热爱写作,文章多次被省市电台选用并登载在杂志上,省市征文获奖者。
相关阅读:

点击本图,跳转阅读:
直播回顾丨错过了直播,千万不要再错过这篇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