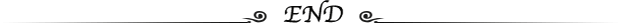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世界读书日 | 每一本书上面都蹲着一个幽灵:《世界文学》里的书店故事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对于每个热爱读书的人,书店想必都是绕不开的存在。西班牙当代作家豪尔赫·卡里翁将书店描绘为一个不可替代的空间:“在这里,在某一个美妙的时刻,有血有肉的人和被赋予了某些特性、有分量的并且唯一存在的物品之间真正地相遇了。”这样的相遇激发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为不少文学作品提供了灵感,如《岛上书店》《查令十字街84号》《风之影》等等。在本期推送中,我们从过往的《世界文学》中选取了九篇与书店有关的精彩片段,也欢迎读者朋友们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自己经历过的书店情缘。书店的人为了酬谢他,给他一根酸棒糖。正当店员们忙着穿大衣时,他却悄悄地溜到后面,躲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大家都想着晚上如何消遣,谁也没有留意他。他在那里等呀等呀,足足等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才敢出来。书店里一片漆黑,他摸索着电灯开关,白天他可没想到这一层。他找到了开关,正要往下按时,又忽然害怕起来。他心想,也许灯一亮,街上就会有人发现他,把他送回家。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但是不能看书,这真是莫大的不幸。他把书一本本取下来翻阅着,有些书名还能辨认出来。后来他又爬到梯子顶上,想看看书架的最上层究竞藏着什么秘密。有一次他从梯子上摔下来,嘴里却说:我一点儿也不疼!地面是硬的,可书是软的,在书店里人总是跌倒在书上,他本来是能够把书一本本地垒成一座塔的,但他觉得杂乱无章是一种鄙俗的表现。于是,他在取下另一本书以前,先把原来那本放回原处。他感到背部酸痛,或许是疲倦的缘故吧。要是在家里,他现在早就入睡了。在这里他却兴奋得不想睡觉,可是眼睛连最大的书名也认不出来了,这使他很生气。他估量着,倘若一个人既不上街,也不去上那讨厌的学校,一直在这里看书,要多少年才能把这些书读完。为什么他不永远留在这里呢?要是他事先积蓄下买一张小床的钱就好了。这时妈妈一定在为他担惊受怕;他也有点害怕了,因为四周是如此寂静,街上的煤气路灯全熄灭了。幽灵在到处移动。幽灵确实是有的。在夜里它们全飞来,蹲在书本上面,在那里读书。幽灵是不需要灯光的,它们的眼睛很大很大。一想到此,他再也不敢去摸书架上面一层的书了,就是放在底下的书他也不敢再碰一碰了。他爬到柜台底下,吓得牙齿格格作响。这里有成千上万本书,每一本上面都蹲着一个幽灵,因此这里才如此寂静。他有时仿佛听到幽灵们翻书的声音,它们看书似乎同他一样快。对于幽灵他本来已经习惯了,但现在这里有上万个,他想其中也许有一个会咬人哩。一旦你触及到它们,它们就会以为你是在戏弄它们,便要发怒。所以他尽量蜷曲着身子,好让幽灵们从他的身上飘忽而过。选自《迷惘》,原载于《世界文学》1983年第3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拉塔注意到,那个高个子青年的黑发有点儿卷曲,略微有点鹰钩鼻,相貌很是英俊,他似乎对诗歌也像对数学一样感兴趣。因为几分钟以后,拉塔发现他也来到了诗歌书架前面,浏览着那一本本的诗集。拉塔意识到他的眼睛不时地朝她身上溜,很有点儿着恼,所以故意不抬起头来。等到她无意之中一抬头,却发现他正规规矩矩地沉浸在阅读之中。她忍不住扫了一眼他手上那本书的封面。那是一本企鹅版的《现代诗选》。这当儿他抬起头来,她立刻处在下风了。她还没有来得及低下头,他已经开口了:“一个人既喜欢诗歌又喜欢数学,这真是很少见的呀。”“噢? ”拉塔说。随后,她意识到年轻人说的是她先前随便从书架上拿下来的那本数学书,便说了句“真的吗? ”以表示交谈到此为止。但那个年轻人却兴冲冲地不肯罢休。“我父亲说的,”他继续说,“并不是指专题的深度,而是它对……嗯,专题的各个方面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我父亲在大学里教数学。”拉塔朝四周望了一眼,看玛拉蒂是不是在听。不过玛拉蒂正在书店前厅专心看她的书。也没有其他的人在偷听,书店在这个季节,或者说一天中这个时候顾客并不很多。“我其实对数学不感兴趣。”拉塔说,她的口气表明她不想再多谈下去了。年轻人显得有点儿沮丧,接着他又鼓起勇气,友好地说:“哎,我也一样。我是学历史的。”拉塔很有些奇怪,这个人怎么拼命想要缠住她,她盯住他的眼睛说道:“我得走了,我朋友在等着我呢。”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禁不住发现这个卷头发的小伙子十分敏感,甚至有点儿脆弱。这同他方才那种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大胆表现截然相反,他竟然未经介绍就在书店里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搭腔讲话。“对不起,看来我是打搅了您了吧? ”他道歉说,似乎识透了她的心思。“没有。”拉塔说。她正要往书店前厅里走, 他脸上带着紧张的笑容又匆匆说道:“要是那样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您的名字? ”“拉塔,”拉塔随口回答,尽管她看不出“要是那样的话”与此有什么逻辑关系。“您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年轻人问,他咧开嘴友好地笑了。“不。” 拉塔很客气地说,她走到玛拉蒂身边,后者手上拿着两本平装本小说。选自《如意郎君》,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1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在巴黎的圣康坦街甲三十七号,有一个叫玛蒂娜的少妇。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尖下巴,披肩发,苗条的身材,纤细的脚踝,当她走在玛让塔林荫大道的便道上时,就像一只蜻蜓在池塘上点水。她在旧书店工作,该书店为圣德尼区的老主顾们推荐有血淋淋封面的警探故事和失去清新的爱情诗文集。书店里,光线昏暗的书架向好奇者提供更吸引人的书籍:世纪末的杂志、装饰着稚拙和博学的版画的古老的科学论著,给少年人看的饰有纹章的精装小说,甚至有莫泊桑的,或者保尔·布尔热的几乎是首版的书。书店当时属于一位上年纪的珍本收藏家,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巴黎大区的那些顶楼里,发现一卷珍本图书比把整套的马德莱娜·德·斯居代里全集卖给一个天真汉还要高兴。玛蒂娜有一个叫西蒙的音乐家男朋友,此人靠多种方式谋生:上午做钢琴家教,下午在保罗-博伊舍尔乐器行给艺术家们排练,在气候宜人的季节,从晚上十点到子夜在巴士底广场那些露天咖啡座旁演奏手风琴。《小女王》《珍妮弗华尔兹》和《水晶珠饰》让战前出生的那些顾客浮想联翩,掏出腰包。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当玛蒂娜踏着舞步,穿着花裙子在桌子间穿梭的时候,十法郎的硬币下雨一般落进她的草帽。四月的一个下午,在打开旧书商早晨带来的一箱书时,玛蒂娜发现了一本封面褪了色的薄书,其书名页毫不客气地用埃勒泽维尔体的活字印着:“在一个老妇人那里,她住在共和国广场旁边的墨水瓶街。她说箱子是一个原籍夏尔维尔的姑姑,某个伊莎贝尔·佩里雄或者贝里雄给她的,而她从来就没有打开过。”“当然打开过,我的孩子。我们不买装在口袋里的兔子。但是我还没有全部检查过。”“我带走这一本。”玛蒂娜说,“我明天把它带回来。”当天晚上,西蒙排练后回到家时,看见他的女朋友沉浸在对瓦术士的《九十九个秘诀》的专心研究中。“你看起来心不在焉,我的心肝。”音乐家说,“什么样的诗人或学者有幸让你皱起了眉头?”“别笑,没脑子的家伙,要不然我把你变成癞蛤蟆,变成械树,变成瓦拉斯饮水器!”“一只癞蛤蟆,这有点让我不安。可是你用一个饮水器干什么用啊?”“等一下,我来找一找最适合你的。找到了。准备接招吧:我要让你呆若盐雕!”“Eugnilev arterviu ovenidru ossunaru!”她带着一种德国腔念起经来。“今年,真奇怪,盐都不硬了。”西蒙挖苦说,“甚至,我这有毛病的肘关节都不再咔咔响了。”“我肯定你没有找到正确的发音。毕竟,编秘诀的是一个瓦隆术士。让我试试。”小伙子拿起小书,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慢慢地,清晰地发出:“Eugnilev arterviu ovenidru ossunaru!你看,这样要好多了……”玛蒂娜完全僵化了,瞳孔大张,下巴扭向右边,胸口没有了一丝颤动,左脚正准备抬起,保持在一种难以描绘,并且可说是奇妙的平衡姿态上。选自《定身术》,原载于《世界文学》2005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半个小时以后,我来到一家旧书店。我走进旧书店的时候,有一种无法确定的预感,只是模模糊糊地想找到一本关于预言未来的旧参考书。“你们这儿有没有关于黑色魔怪方面的书?”我问一位女售货员。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她看见了我那溅满血迹和泥浆的脸,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好像立马就尿了裤子。我就当作没看见她,开始自顾自地、歇斯底里地在书堆里翻找起来。偶然间,我翻到了一本《库尔斯克州医士诊断手册》。我翻到了我所需的部分,飞快地浏览起来,突然,我一声惊叫:关于我的病症,也就是萨巴奇金在我耳旁悄悄说出的那个病症,出现的字眼根本不是那个不祥的“癌症”,而是“便秘”。我差点没乐死,几乎不相信自己还有这样的运气,我简直无法承受,可是又有点担心,不禁颤抖着喃喃自语:“我竟然会这么幸运,我简直难以相信,这简直不可能。”我又一头扎进那些厚厚的学术书中查找起来。关于我的病症,所有的书上都写着那个令人愉快的、光辉灿烂的字眼——“便秘”。我又到另一边随便浏览起来。缩在墙角里的女售货员,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也在喃喃自语,听上去如同在祷告、颂诗:“啊,在白色的世界上幸福地生活着……”“如今,我打算原谅萨巴奇金的一切。”我心花怒放地走出了书店。选自《死神就在我们身边》,原载于《世界文学》2008年第5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日本有一家淳久堂书店,在其池袋总店,曾经内设一个大江健三郎书店。看到这个消息,我有些绝望,又有些怀疑:这位作家,他的书,即便搜罗各种版本,恐怕也难以撑起一个书店吧,即便能撑起,他会同意开办这样一个书店吗? 接下来我才晓得,除了部分大江的书,这个书店主要摆放和出售其他作家的书,不过都是由大江来推荐和选定: 从《伊利亚特》到 《薄伽梵歌》,从马克·吐温到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从布莱克、坡、艾略特到奥登。这是一个行为艺术般的另类展览:个人的、内在的、时间的书架,在这里转换成众人的、外在的、空间的书架;恍惚的、过去时态的书架,在这里转换成木头或铁皮的、将来时态的书架。就在四面环绕的书架之间,大江常去做讲座,他与男性护理师、大学生和纽约来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分享了他的阅读史。系列讲座终成为系列语音书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充满回忆快感和孤独想象力的书店,异于其他所有书店,因为在此卖出的每本书,都在大江的私人阅读史里边遭遇过个人化的含咀: 大江之薰不断散发自各个册页,混合着其他作家的初衷、虚晃、佯谬和吞吞吐吐的辩解。选自《大江健三郎书店》,原载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2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我不知道弗洛伊德会对这怎么解释,反正有三十多年时间,我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一些我从前根本不认识的书店或者我正在光顾的熟悉的老书店。其实那些熟悉的书店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在巴黎,离火车北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对于那里一条上山的长街尽头的一家书店,我有着非常生动鲜明的记忆。那是一家有着许多高高书架、门进很深的书店(我得用梯子才能够到那些书架的上头)。至少有两次我搜寻遍了它的每一个书架(我想我在那儿买到了阿波利奈尔的《法尼·西尔》的译本),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我去那里寻找那家书店的努力却是归于徒然。当然,那家书店可能已经消失了,甚至那条街道本身也不在那儿了。此外在伦敦有一家书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能够非常清楚地记得它的门面,但是却记不得它内部的情况了。它就坐落在你来尤斯顿路的路上,在夏洛特街后面的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走进去过,但是我肯定如今那再也没有这么一家书店了。我总是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从这样的梦中醒来。对于收藏家来说,毫无疑问,比起那种寻找的兴奋,比起有时这种寻找把你带到的那些神奇陌生的地方来说,收藏品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倒变得次要了。就在最近,我和我的兄弟休(他收藏的侦探小说的范围包括从维多利亚时期到一九一四年,所以我们经常结伴淘书)曾经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坐落在一片废弃地区中的令人优郁的利茨街周围,那地方简直就是格里尔森绝望的纪录片的一部分。我们寻找着一家书店,它曾被收入一本很可靠的指南。但是随着我们在那些废弃的工厂之间身上变得越来越湿淋淋的,我们对那本指南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那家肯定曾经存在过的书店时,那里一扇挪了窝儿的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书店”,其中“书”字的前三个字母都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地板上神秘地乱扔着一些孩子的靴子和鞋,还有一些好。难道这是什么小孩黑手党的聚会地点吗?好像是在那类地方,发现了一些新酒吧和过去从来没有尝过的啤酒,倒也是对淘书者的某种奖赏。选自《旧书店》,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一九九四年,于我不仅是命运的分水岭, 也是阅读史上的里程碑。从此, 阅读成了头等大事, 并影响了我的写作乃至生活。那一年, 我考上大学, 摆脱了父辈修补地球的西绪福斯式的命运, 也接触到了货真价实的图书馆及各式各样的书店。书店有不少好书, 我节衣缩食一本一本买回来。到了寒假,我将购于省城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选》(唐荫荪等译)及《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选》(戴启篁译)带回乡间。在阴郁的南方冬日, 我遽然跌入了爱伦·坡暗黑、神秘的叙事漩涡。他的小说犹如乡村上空升起的乌云, 隐藏着幻想与虚构的风暴、雷电和大雨。他成了我接受现代派文学的入口。至于屠格涅夫的小说, 我也觉得《初恋》等唯美酸楚 , 但感触不深。一九九五年初, 我在中山大学东门外的一个小书店 (已倒闭多年) 买了本《外国二十世纪纯情诗精华》 (王家新、唐晓渡编选, 作家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版),首次读到了史蒂文斯、约翰·阿什伯利、W.S.默温、狄兰·托马斯、泰德·休斯等等,还有诗歌中的博尔赫斯。他们使我听见了神秘而清晰的诗歌声音。一年多后,此书被人有借无还。直至二〇一三年六月,才于旧书网重购。一九九六年,我在一个小书店跟《世界文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不期而遇,小说有“纳博科夫短篇小说两篇”(于晓丹译)、“夏多雷诺短篇小说四篇”(徐家顺译)、《跳房子》(胡·科塔萨尔作,孙家孟选译),还有余中先选译的《理想藏书》(后来我购得此书,由此买了不少好书)。那是我首次读纳博科夫,之后读了惊世骇俗的《洛丽塔》《爱达或爱欲》等。他热衷于文体实验,叙事繁复,含意深刻。作者宣称只考虑艺术,而对道德说教嗤之以鼻。许多公认的作家对他来说简直不存在,例如泰戈尔、高尔基和罗曼·罗兰。他认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文学石膏像,必须用锤子来砸碎;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则因形式平庸而像肥皂剧。该杂志太好了,遂每期必购。到一九九八年大学毕业后,订阅至今,成了我向文学青年推荐读物的首选。我还设法搜集了以往杂志及《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等系列图书。不少我热爱的作家都是在《世界文学》上首次接触,譬如科塔萨尔、萨拉马戈、伊·卡内蒂、凯·安·波特和麦克尤恩等等。选自《阅读简史》,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2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酷爱读书(读书是在他们的生活里插进一把刀),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读:童话,连环画(我收藏有许多连环画),康普顿百科全书,波布希双胞胎和其他斯特拉特梅尔丛书,关于天文学、化学和中国的书,科学家的传记,全套的理查德·哈利伯顿游记,还有相当数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作品。四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图森市中区的一家卖文具和贺卡的商店闲逛,在商店的后堂,我就像一下子跌进了一口装满书籍的深井,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现代图书馆出版的书籍。这里有各种流行书刊,在每本书的封底有我的第一份书单。我只好买来读(小的九十五美分一本,大的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一本),每本书都像木匠的尺子一般,让我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到达洛杉矶后的一个月之内,我找到了一家真正的书店,这是我沉醉于书店的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家:好莱坞大道上的“匹克威克”书店。我每隔几天就要在放学以后到那里去,站着阅读更多的世界文学作品。有钱的时候就买,胆大的时候就偷。每次偷了书,我都要责骂自己好几个星期,害怕将会因此受到惩罚而带来屈辱。但我只有那么一点点零花钱,我又能怎么办呢?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到图书馆去读书,我一定要得到那些书,看到它们整整齐齐一排排地摆在我那小小的房间的一面墙前。它们是我的守护神。我的宇宙飞船。选自《朝圣》,原载于《世界文学》2005年第1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到处疯狂地买书,春季秋季书市,中山公园,地坛,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出版社门市部和降价书店,有时不仅把吃饭钱用来买书了,还把公共汽车票钱也买书了。脸皮厚的时候逃票蹭车,脸皮薄的时候走路。从长安街或者朝内大街走回北太平庄是家常便饭。这时的外国书,不仅有文学的,还有哲学的、电影的,比如英格玛·伯格曼的剧本《夏夜的微笑》,而再次见到他的《冬日之光》则是几年之后了……当然文学是核心的核心。我开始买《世界文学》了。虽然穷得要命,但是书不能不看。不可能期期都买。即使买,有时买了《世界文学》,就不能买《外国文艺》了。还是老办法,用笔抄。何况湖南和广西出了一大堆外国书,都是要钱的。有一回,我写的一篇什么文章得了一个什么奖,奖金不是现钱,而是三联书店四十块钱的购书券,发了一笔横财,换回一大堆想买而买不起的书。我曾在新街口书店多次恳求营业员拿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看一看,因为当时还不流行开架售书,读者和书之间隔着台湾海峡一样宽的柜台,我只看不买,营业员终于忍不住对我发火了,你到底想不想买?我仓皇逃窜。所以我一直和聂鲁达没缘分。现在一看到聂鲁达的名字就心酸,就想起当年的窘状。选自《我的门,我的窗》,原载于《世界文学》2012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对于每个热爱读书的人,书店想必都是绕不开的存在。西班牙当代作家豪尔赫·卡里翁将书店描绘为一个不可替代的空间:“在这里,在某一个美妙的时刻,有血有肉的人和被赋予了某些特性、有分量的并且唯一存在的物品之间真正地相遇了。”这样的相遇激发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为不少文学作品提供了灵感,如《岛上书店》《查令十字街84号》《风之影》等等。在本期推送中,我们从过往的《世界文学》中选取了九篇与书店有关的精彩片段,也欢迎读者朋友们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自己经历过的书店情缘。书店的人为了酬谢他,给他一根酸棒糖。正当店员们忙着穿大衣时,他却悄悄地溜到后面,躲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大家都想着晚上如何消遣,谁也没有留意他。他在那里等呀等呀,足足等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才敢出来。书店里一片漆黑,他摸索着电灯开关,白天他可没想到这一层。他找到了开关,正要往下按时,又忽然害怕起来。他心想,也许灯一亮,街上就会有人发现他,把他送回家。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但是不能看书,这真是莫大的不幸。他把书一本本取下来翻阅着,有些书名还能辨认出来。后来他又爬到梯子顶上,想看看书架的最上层究竞藏着什么秘密。有一次他从梯子上摔下来,嘴里却说:我一点儿也不疼!地面是硬的,可书是软的,在书店里人总是跌倒在书上,他本来是能够把书一本本地垒成一座塔的,但他觉得杂乱无章是一种鄙俗的表现。于是,他在取下另一本书以前,先把原来那本放回原处。他感到背部酸痛,或许是疲倦的缘故吧。要是在家里,他现在早就入睡了。在这里他却兴奋得不想睡觉,可是眼睛连最大的书名也认不出来了,这使他很生气。他估量着,倘若一个人既不上街,也不去上那讨厌的学校,一直在这里看书,要多少年才能把这些书读完。为什么他不永远留在这里呢?要是他事先积蓄下买一张小床的钱就好了。这时妈妈一定在为他担惊受怕;他也有点害怕了,因为四周是如此寂静,街上的煤气路灯全熄灭了。幽灵在到处移动。幽灵确实是有的。在夜里它们全飞来,蹲在书本上面,在那里读书。幽灵是不需要灯光的,它们的眼睛很大很大。一想到此,他再也不敢去摸书架上面一层的书了,就是放在底下的书他也不敢再碰一碰了。他爬到柜台底下,吓得牙齿格格作响。这里有成千上万本书,每一本上面都蹲着一个幽灵,因此这里才如此寂静。他有时仿佛听到幽灵们翻书的声音,它们看书似乎同他一样快。对于幽灵他本来已经习惯了,但现在这里有上万个,他想其中也许有一个会咬人哩。一旦你触及到它们,它们就会以为你是在戏弄它们,便要发怒。所以他尽量蜷曲着身子,好让幽灵们从他的身上飘忽而过。选自《迷惘》,原载于《世界文学》1983年第3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拉塔注意到,那个高个子青年的黑发有点儿卷曲,略微有点鹰钩鼻,相貌很是英俊,他似乎对诗歌也像对数学一样感兴趣。因为几分钟以后,拉塔发现他也来到了诗歌书架前面,浏览着那一本本的诗集。拉塔意识到他的眼睛不时地朝她身上溜,很有点儿着恼,所以故意不抬起头来。等到她无意之中一抬头,却发现他正规规矩矩地沉浸在阅读之中。她忍不住扫了一眼他手上那本书的封面。那是一本企鹅版的《现代诗选》。这当儿他抬起头来,她立刻处在下风了。她还没有来得及低下头,他已经开口了:“一个人既喜欢诗歌又喜欢数学,这真是很少见的呀。”“噢? ”拉塔说。随后,她意识到年轻人说的是她先前随便从书架上拿下来的那本数学书,便说了句“真的吗? ”以表示交谈到此为止。但那个年轻人却兴冲冲地不肯罢休。“我父亲说的,”他继续说,“并不是指专题的深度,而是它对……嗯,专题的各个方面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我父亲在大学里教数学。”拉塔朝四周望了一眼,看玛拉蒂是不是在听。不过玛拉蒂正在书店前厅专心看她的书。也没有其他的人在偷听,书店在这个季节,或者说一天中这个时候顾客并不很多。“我其实对数学不感兴趣。”拉塔说,她的口气表明她不想再多谈下去了。年轻人显得有点儿沮丧,接着他又鼓起勇气,友好地说:“哎,我也一样。我是学历史的。”拉塔很有些奇怪,这个人怎么拼命想要缠住她,她盯住他的眼睛说道:“我得走了,我朋友在等着我呢。”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禁不住发现这个卷头发的小伙子十分敏感,甚至有点儿脆弱。这同他方才那种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大胆表现截然相反,他竟然未经介绍就在书店里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搭腔讲话。“对不起,看来我是打搅了您了吧? ”他道歉说,似乎识透了她的心思。“没有。”拉塔说。她正要往书店前厅里走, 他脸上带着紧张的笑容又匆匆说道:“要是那样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您的名字? ”“拉塔,”拉塔随口回答,尽管她看不出“要是那样的话”与此有什么逻辑关系。“您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年轻人问,他咧开嘴友好地笑了。“不。” 拉塔很客气地说,她走到玛拉蒂身边,后者手上拿着两本平装本小说。选自《如意郎君》,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1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在巴黎的圣康坦街甲三十七号,有一个叫玛蒂娜的少妇。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尖下巴,披肩发,苗条的身材,纤细的脚踝,当她走在玛让塔林荫大道的便道上时,就像一只蜻蜓在池塘上点水。她在旧书店工作,该书店为圣德尼区的老主顾们推荐有血淋淋封面的警探故事和失去清新的爱情诗文集。书店里,光线昏暗的书架向好奇者提供更吸引人的书籍:世纪末的杂志、装饰着稚拙和博学的版画的古老的科学论著,给少年人看的饰有纹章的精装小说,甚至有莫泊桑的,或者保尔·布尔热的几乎是首版的书。书店当时属于一位上年纪的珍本收藏家,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巴黎大区的那些顶楼里,发现一卷珍本图书比把整套的马德莱娜·德·斯居代里全集卖给一个天真汉还要高兴。玛蒂娜有一个叫西蒙的音乐家男朋友,此人靠多种方式谋生:上午做钢琴家教,下午在保罗-博伊舍尔乐器行给艺术家们排练,在气候宜人的季节,从晚上十点到子夜在巴士底广场那些露天咖啡座旁演奏手风琴。《小女王》《珍妮弗华尔兹》和《水晶珠饰》让战前出生的那些顾客浮想联翩,掏出腰包。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当玛蒂娜踏着舞步,穿着花裙子在桌子间穿梭的时候,十法郎的硬币下雨一般落进她的草帽。四月的一个下午,在打开旧书商早晨带来的一箱书时,玛蒂娜发现了一本封面褪了色的薄书,其书名页毫不客气地用埃勒泽维尔体的活字印着:“在一个老妇人那里,她住在共和国广场旁边的墨水瓶街。她说箱子是一个原籍夏尔维尔的姑姑,某个伊莎贝尔·佩里雄或者贝里雄给她的,而她从来就没有打开过。”“当然打开过,我的孩子。我们不买装在口袋里的兔子。但是我还没有全部检查过。”“我带走这一本。”玛蒂娜说,“我明天把它带回来。”当天晚上,西蒙排练后回到家时,看见他的女朋友沉浸在对瓦术士的《九十九个秘诀》的专心研究中。“你看起来心不在焉,我的心肝。”音乐家说,“什么样的诗人或学者有幸让你皱起了眉头?”“别笑,没脑子的家伙,要不然我把你变成癞蛤蟆,变成械树,变成瓦拉斯饮水器!”“一只癞蛤蟆,这有点让我不安。可是你用一个饮水器干什么用啊?”“等一下,我来找一找最适合你的。找到了。准备接招吧:我要让你呆若盐雕!”“Eugnilev arterviu ovenidru ossunaru!”她带着一种德国腔念起经来。“今年,真奇怪,盐都不硬了。”西蒙挖苦说,“甚至,我这有毛病的肘关节都不再咔咔响了。”“我肯定你没有找到正确的发音。毕竟,编秘诀的是一个瓦隆术士。让我试试。”小伙子拿起小书,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慢慢地,清晰地发出:“Eugnilev arterviu ovenidru ossunaru!你看,这样要好多了……”玛蒂娜完全僵化了,瞳孔大张,下巴扭向右边,胸口没有了一丝颤动,左脚正准备抬起,保持在一种难以描绘,并且可说是奇妙的平衡姿态上。选自《定身术》,原载于《世界文学》2005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半个小时以后,我来到一家旧书店。我走进旧书店的时候,有一种无法确定的预感,只是模模糊糊地想找到一本关于预言未来的旧参考书。“你们这儿有没有关于黑色魔怪方面的书?”我问一位女售货员。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她看见了我那溅满血迹和泥浆的脸,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好像立马就尿了裤子。我就当作没看见她,开始自顾自地、歇斯底里地在书堆里翻找起来。偶然间,我翻到了一本《库尔斯克州医士诊断手册》。我翻到了我所需的部分,飞快地浏览起来,突然,我一声惊叫:关于我的病症,也就是萨巴奇金在我耳旁悄悄说出的那个病症,出现的字眼根本不是那个不祥的“癌症”,而是“便秘”。我差点没乐死,几乎不相信自己还有这样的运气,我简直无法承受,可是又有点担心,不禁颤抖着喃喃自语:“我竟然会这么幸运,我简直难以相信,这简直不可能。”我又一头扎进那些厚厚的学术书中查找起来。关于我的病症,所有的书上都写着那个令人愉快的、光辉灿烂的字眼——“便秘”。我又到另一边随便浏览起来。缩在墙角里的女售货员,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也在喃喃自语,听上去如同在祷告、颂诗:“啊,在白色的世界上幸福地生活着……”“如今,我打算原谅萨巴奇金的一切。”我心花怒放地走出了书店。选自《死神就在我们身边》,原载于《世界文学》2008年第5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日本有一家淳久堂书店,在其池袋总店,曾经内设一个大江健三郎书店。看到这个消息,我有些绝望,又有些怀疑:这位作家,他的书,即便搜罗各种版本,恐怕也难以撑起一个书店吧,即便能撑起,他会同意开办这样一个书店吗? 接下来我才晓得,除了部分大江的书,这个书店主要摆放和出售其他作家的书,不过都是由大江来推荐和选定: 从《伊利亚特》到 《薄伽梵歌》,从马克·吐温到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从布莱克、坡、艾略特到奥登。这是一个行为艺术般的另类展览:个人的、内在的、时间的书架,在这里转换成众人的、外在的、空间的书架;恍惚的、过去时态的书架,在这里转换成木头或铁皮的、将来时态的书架。就在四面环绕的书架之间,大江常去做讲座,他与男性护理师、大学生和纽约来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分享了他的阅读史。系列讲座终成为系列语音书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充满回忆快感和孤独想象力的书店,异于其他所有书店,因为在此卖出的每本书,都在大江的私人阅读史里边遭遇过个人化的含咀: 大江之薰不断散发自各个册页,混合着其他作家的初衷、虚晃、佯谬和吞吞吐吐的辩解。选自《大江健三郎书店》,原载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2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我不知道弗洛伊德会对这怎么解释,反正有三十多年时间,我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一些我从前根本不认识的书店或者我正在光顾的熟悉的老书店。其实那些熟悉的书店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在巴黎,离火车北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对于那里一条上山的长街尽头的一家书店,我有着非常生动鲜明的记忆。那是一家有着许多高高书架、门进很深的书店(我得用梯子才能够到那些书架的上头)。至少有两次我搜寻遍了它的每一个书架(我想我在那儿买到了阿波利奈尔的《法尼·西尔》的译本),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我去那里寻找那家书店的努力却是归于徒然。当然,那家书店可能已经消失了,甚至那条街道本身也不在那儿了。此外在伦敦有一家书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能够非常清楚地记得它的门面,但是却记不得它内部的情况了。它就坐落在你来尤斯顿路的路上,在夏洛特街后面的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走进去过,但是我肯定如今那再也没有这么一家书店了。我总是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从这样的梦中醒来。对于收藏家来说,毫无疑问,比起那种寻找的兴奋,比起有时这种寻找把你带到的那些神奇陌生的地方来说,收藏品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倒变得次要了。就在最近,我和我的兄弟休(他收藏的侦探小说的范围包括从维多利亚时期到一九一四年,所以我们经常结伴淘书)曾经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坐落在一片废弃地区中的令人优郁的利茨街周围,那地方简直就是格里尔森绝望的纪录片的一部分。我们寻找着一家书店,它曾被收入一本很可靠的指南。但是随着我们在那些废弃的工厂之间身上变得越来越湿淋淋的,我们对那本指南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那家肯定曾经存在过的书店时,那里一扇挪了窝儿的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书店”,其中“书”字的前三个字母都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地板上神秘地乱扔着一些孩子的靴子和鞋,还有一些好。难道这是什么小孩黑手党的聚会地点吗?好像是在那类地方,发现了一些新酒吧和过去从来没有尝过的啤酒,倒也是对淘书者的某种奖赏。选自《旧书店》,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一九九四年,于我不仅是命运的分水岭, 也是阅读史上的里程碑。从此, 阅读成了头等大事, 并影响了我的写作乃至生活。那一年, 我考上大学, 摆脱了父辈修补地球的西绪福斯式的命运, 也接触到了货真价实的图书馆及各式各样的书店。书店有不少好书, 我节衣缩食一本一本买回来。到了寒假,我将购于省城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选》(唐荫荪等译)及《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选》(戴启篁译)带回乡间。在阴郁的南方冬日, 我遽然跌入了爱伦·坡暗黑、神秘的叙事漩涡。他的小说犹如乡村上空升起的乌云, 隐藏着幻想与虚构的风暴、雷电和大雨。他成了我接受现代派文学的入口。至于屠格涅夫的小说, 我也觉得《初恋》等唯美酸楚 , 但感触不深。一九九五年初, 我在中山大学东门外的一个小书店 (已倒闭多年) 买了本《外国二十世纪纯情诗精华》 (王家新、唐晓渡编选, 作家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版),首次读到了史蒂文斯、约翰·阿什伯利、W.S.默温、狄兰·托马斯、泰德·休斯等等,还有诗歌中的博尔赫斯。他们使我听见了神秘而清晰的诗歌声音。一年多后,此书被人有借无还。直至二〇一三年六月,才于旧书网重购。一九九六年,我在一个小书店跟《世界文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不期而遇,小说有“纳博科夫短篇小说两篇”(于晓丹译)、“夏多雷诺短篇小说四篇”(徐家顺译)、《跳房子》(胡·科塔萨尔作,孙家孟选译),还有余中先选译的《理想藏书》(后来我购得此书,由此买了不少好书)。那是我首次读纳博科夫,之后读了惊世骇俗的《洛丽塔》《爱达或爱欲》等。他热衷于文体实验,叙事繁复,含意深刻。作者宣称只考虑艺术,而对道德说教嗤之以鼻。许多公认的作家对他来说简直不存在,例如泰戈尔、高尔基和罗曼·罗兰。他认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文学石膏像,必须用锤子来砸碎;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则因形式平庸而像肥皂剧。该杂志太好了,遂每期必购。到一九九八年大学毕业后,订阅至今,成了我向文学青年推荐读物的首选。我还设法搜集了以往杂志及《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等系列图书。不少我热爱的作家都是在《世界文学》上首次接触,譬如科塔萨尔、萨拉马戈、伊·卡内蒂、凯·安·波特和麦克尤恩等等。选自《阅读简史》,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2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酷爱读书(读书是在他们的生活里插进一把刀),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读:童话,连环画(我收藏有许多连环画),康普顿百科全书,波布希双胞胎和其他斯特拉特梅尔丛书,关于天文学、化学和中国的书,科学家的传记,全套的理查德·哈利伯顿游记,还有相当数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作品。四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图森市中区的一家卖文具和贺卡的商店闲逛,在商店的后堂,我就像一下子跌进了一口装满书籍的深井,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现代图书馆出版的书籍。这里有各种流行书刊,在每本书的封底有我的第一份书单。我只好买来读(小的九十五美分一本,大的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一本),每本书都像木匠的尺子一般,让我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到达洛杉矶后的一个月之内,我找到了一家真正的书店,这是我沉醉于书店的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家:好莱坞大道上的“匹克威克”书店。我每隔几天就要在放学以后到那里去,站着阅读更多的世界文学作品。有钱的时候就买,胆大的时候就偷。每次偷了书,我都要责骂自己好几个星期,害怕将会因此受到惩罚而带来屈辱。但我只有那么一点点零花钱,我又能怎么办呢?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到图书馆去读书,我一定要得到那些书,看到它们整整齐齐一排排地摆在我那小小的房间的一面墙前。它们是我的守护神。我的宇宙飞船。选自《朝圣》,原载于《世界文学》2005年第1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到处疯狂地买书,春季秋季书市,中山公园,地坛,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出版社门市部和降价书店,有时不仅把吃饭钱用来买书了,还把公共汽车票钱也买书了。脸皮厚的时候逃票蹭车,脸皮薄的时候走路。从长安街或者朝内大街走回北太平庄是家常便饭。这时的外国书,不仅有文学的,还有哲学的、电影的,比如英格玛·伯格曼的剧本《夏夜的微笑》,而再次见到他的《冬日之光》则是几年之后了……当然文学是核心的核心。我开始买《世界文学》了。虽然穷得要命,但是书不能不看。不可能期期都买。即使买,有时买了《世界文学》,就不能买《外国文艺》了。还是老办法,用笔抄。何况湖南和广西出了一大堆外国书,都是要钱的。有一回,我写的一篇什么文章得了一个什么奖,奖金不是现钱,而是三联书店四十块钱的购书券,发了一笔横财,换回一大堆想买而买不起的书。我曾在新街口书店多次恳求营业员拿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看一看,因为当时还不流行开架售书,读者和书之间隔着台湾海峡一样宽的柜台,我只看不买,营业员终于忍不住对我发火了,你到底想不想买?我仓皇逃窜。所以我一直和聂鲁达没缘分。现在一看到聂鲁达的名字就心酸,就想起当年的窘状。选自《我的门,我的窗》,原载于《世界文学》2012年第4期,此处标题为责编自拟。
编辑:张露 天艾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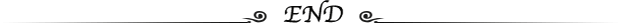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