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言说 | 寒烟:荒野之蕴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寒 烟

一首本真的诗,就是一片大口呼吸的荒野。
虽然她展现的形态,也许是一枝简短的幽兰,一束青翠的灌木,一柱高耸的云杉,或是一方理性的苔藓,一卧历史的玄武岩……但她的源头,她的根系,她的氤氲,她的创作冲动,她灵感爆发的隐秘故乡,她在时间里的鲜活与生命力的久远,无不与亘古莽莽的荒野同神同质。天高地旷,狂风歌吟着万物的自由与野性,深涧与湿地独守着静谧与鲜冽,若有若无的精灵鬼魅似的飘忽,弥漫……天——地——人,荒野本就是诞生人类的时空母床。谁若听从这神秘气息的召唤和原质力量的牵引,谁便会挣离俗世锈迹斑斑的因袭之链,不屑于闹市鼠目寸光的追逐,向着人迹罕至的僻远和空旷远行——那是一个生命竭尽一生,向那遥不可及的“终极雪山”虔诚匍匐的朝圣之路……
感谢这样的生命与诗歌。感谢她们深长不息的召唤和牵引,感谢那些在我蹒跚前行的途中,给予我及时搀扶的珍贵书籍——精神的“天火”,从来就只有荒野的气质而无地域的阻隔。




在我珍藏的书籍中,有两本书页已微微泛黄的薄薄的“小册子”,铭刻着早年对我具有“颠覆或重生”意义的启蒙。
她们是:《悲剧的诞生》(尼采著,刘崎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尼采》(乔治·勃兰兑斯著,安延明译,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三十多年来,她们跟随我历尽辗转流徙和世事变迁。有些书在颠簸的途中不知不觉与我走散了,下落不明,而她们却因为我“另眼相看”的珍视、呵护,一直须臾未离地相伴在左右。我常常摩挲着她们那朴素到极致的质地(装帧设计干净、简约,没有“附加”的装饰,没有“抓人眼球”的“推荐语”),深深怀念那尚未被商业化、消费主义绑架的年代严肃纯正的氛围,怀念她们赐予一个懵懂生命的那些身心震颤、坼裂的日夜……
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鲁中小城沉闷的气压下,与她们不期而遇,对于我,是怎样及时而幸运的“从天而降”的搭救。那来不及仔细辨认的陌生、辽远,携着高海拔的思想呼啸的寒冽,让我在透彻肺腑的深呼吸和激奋的寒战里,用来自血液的饥渴,贪婪地吸收、汲取着——《悲剧的诞生》,对于当时没有任何“接受储备”素质的我来说,这部学术著作太过高深、艰涩了,虽然在囫囵吞枣的阅读里,我能凭直觉领悟尼采所讲的悲剧和艺术的本质并对狄奥尼索斯精神情有独钟,但如果没有乔治·勃兰兑斯这位引路人领我进入尼采思想和命运的古堡,我也无法想象,尼采是否还会成为我灵魂的扳道工,给我的命运带来决定性的改变。
勃兰兑斯是尼采在世时,就很欣赏、推崇尼采的极稀有的同时代知音,这使他在《尼采》一书中拥有“近距离”的视角和一手资料(书中附有他和尼采的二十余封通信),让我能更真切、鲜活地触摸、感受尼采及其生活的时代氛围:那先知般的孤独,那对一切价值毫不留情的质疑和重估,那燃烧一生的对“深渊”探索的勇气和激情——直至最终被“深渊”吞没……在被尼采悲剧、悲壮的命运灼伤的日夜,一种对自我从未有过的审视,也在羞愧交加中拉开了序幕,我忍不住质疑自己二十来年的生命历程,回顾从小到大,不绝于耳的调教与灌输,以及被“传统”的家庭和社会像压制砖坯一样,柔软或粗暴地“顺理成章”安排的每一步人生……一阵阵颠覆前的惊恐与焦虑,往往比身在地狱更折磨人,以至于许多年后,我才能这样询问自己:如果能早一点读到这样的书,你还会那么驯顺地配合“命运”吗?
那是一种对“根基”的唤醒和摇撼,就像尼采肖像上那逼视的目光,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洞穿力一样,我在诘问的旋转中,终于感受到了生命板块在冰河里的碰撞和断裂,感受到了从那儿涌来的热血,携着朔风凌厉的尖啸,亢奋地撞破了苦闷的躯壳——终于,在一九九〇年代初的那个冬天,在整个社会基本还是“大一统”的生存条件的背景下,我从那个让世人羡慕的工作单位,从家庭很满意的生活保障里,莽撞地辞离了束缚,一无所有,踏上了颠簸动荡的未知之路。从此开始命定的、一去不回的追寻与认领……
在海边那个四面透风的出租屋内,没有书桌和椅子,我趴在床上抄写从图书馆借来的诗集——《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著,苏杭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茨维塔耶娃诗歌在国内最早的“单行本”)。冥冥中,在深夜的山路上,尼采朦胧的身影若隐若现,在他飘逝的瞬息,白发沧桑的茨维塔耶娃从一棵老树后面大步走来,她那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不妥协的决绝与激昂,挽着我彻骨的寒冷和饥饿,无时无刻不相濡以沫,噬心入髓……
在那样谋生无着却酣畅呼吸的日夜,在大海向一个生命彻底敞开的自由而荒凉的轰鸣中,我写下了属于我的最初的诗行。
然而,我却需要许久才能意识到,我的世俗的挣脱,是生命潜在的荒野原态对我的召唤与期许,而激荡我的、牵引我的尼采和茨维塔耶娃,他们之所以“脱颖而出”,之所以词锋如炬,个性卓立,正是他们的生命深处,蛮荒莽莽,暴风骤雨,火山喷涌,神性蓬勃——而我皈依得有些晚了,因此而悔恨,而走得很慢,很吃力、很艰难……




《瓦尔登湖》(梭罗著,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版)。一部让我沉寂、自省的安静之书。
一百五十年了。一八四五年三月底的一天,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上那个告别尘嚣,走向森林、湖畔的孑然背影,拉远了时空崇敬的眺望,也悄然拂落了我初次捧读《瓦尔登湖》的那个夏末,空气中仅余的最后一丝燥热和我生命中莫名的焦灼。
“我到森林里生活,是因为我想要清醒地生活,抛开各种细枝末节的事情,看看我是否能够少走点弯路,以免等到临死才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
梭罗“异数”的清醒,沁透了林雾湖岚那未沾尘埃的清冽潮润,凛凛叩击着我那尚未扎牢“主根”,仍在张望中彷徨的灵魂。那时,我已结束了困顿的漂泊,在一家杂志社谋得了文字校对的临时工作。虽然收入微薄,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但有充裕的时间用来读书、写作。身边的朋友一致认为我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便不时撺掇、张罗着为我物色新的工作。优厚的薪酬和待遇确实曾让我憧憬心动,但那些“为稻粱谋”而忙碌的紧张节奏,却令我望而却步——我已经看见,自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拧入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在晕头转向中迷失了心魂,就像那些如蚁群般在都市霓虹和高楼豪厦间疲于奔命的身影,也许永远都无法停下来,想一想——生命是否已沦为生存的奴才?
“简朴、简朴、再简朴”——梭罗那自我苛求的短暂、简朴的一生,蕴涵着多么深邃、意味深长的启示。这是一个已秘密啜饮过天地甘霖和自然神谕的灵魂来自源头的明澈洞察:“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变成一个农夫,树荫下歇力的人已变成一个管家……”他为人类被工业文明驱赶、被物欲役使的积重难返的沉疴顽疾开出了一剂根治的良方——“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
梭罗苛责的质问,使我在砭骨拷问的澄定后,终于将笃定之根,扎向了诗歌凝望、期冀的深处:只有在安贫乐道的坦然中,把对物质的需求降至最低限度,不为奢望所累,不为繁琐羁绊,我才能腾出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纯粹的空间,让诗歌不羁的血肉和魂魄,最大限度地涌入我祈祷般专注、凝聚的身心。
“给我一片文明无法容忍的荒野”——梭罗忧惧如焚的啼血呼告,成了后来美国兴起的荒野保护运动和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思想基础。一如他那孑然远去的孤绝背影,在人类工业化进程一路高歌的狂奔中,在环境破坏、资源匮乏、物种灭绝的恶性循环里,竦峙着愈来愈冷峻、峭厉的警醒——这时,我终于明了了,所有热爱荒野的人,是因为他们生命的荒野,还没有被所谓文明的“成就”层层覆没,他们的身心拥有大自然一样的生态;而且,不仅他们,人类历史上诸多像爱因斯坦、达尔文一样不朽的人,他们的想象、发现与创造,不也是源于生命深处的远古状态吗?只不过爆发的坐标点不同而已吧。




“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的生命之根……”深深浸没于《哲学走向荒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的那个深秋,我有幸跟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这位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智慧长者和杰出向导,如有神助般地走进了时空深处那片“灵启的荒野”。
这是一位难得一遇并值得由衷信赖的珍稀向导。因为他始终遵从生命、灵魂深处的真实。一九三三年,罗尔斯顿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著名风景区——谢南多厄峡谷的一个村庄里。从家门口流过的莫里河、抬头便可望见的贾姆坡山和霍格贝克山,使他从小就领受了家乡壮美山川“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和启迪。他最初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去认识并改造世界。但在获得物理学学士后,他却在星空和力学的世界中迷失了。为了走出迷误,他进入神学院,专攻神学。而万能的上帝也未能解答他心底的困惑。这位神学博士在苦思冥想中探寻着,在后来将近十年的牧师生涯中,他每周给自己放两天假,一天用来在野外山林漫步游荡,另一天则在附近的大学旁听生物学课。继学习植物学与动物学后又学习了地质学、矿物学和古生物学……而目睹周围环境不可遏制的恶化,使他“对自然的奇异感变成了一种恐怖感”,他一边积极投身保护荒野的运动,一边思考关于生命和自然的问题,在当时科学哲学对自然哲学的轻视之风中,他奋力为自然的价值辩护,开始深入思考荒野的价值问题——这些一波三折却又曲径通幽的求索历程,最终成就了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
成名后的罗尔斯顿仍是一个不改初衷的“背包客”。也许,正是一次次独自深入荒野山林的“净化之旅”,才能使他穿过岁月的风化,穿过荣耀桂冠和威望光环那不易察觉的腐蚀,罕见地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他在林间空地上,偶然发现一株轮生朱兰花或一朵紫色的凤仙花,毫无顾忌地欢呼雀跃时,当他在偏僻一隅出其不意地发现很多自己不认识的苔藓而高兴得忘乎所以时,当他为了调查一只狐狸的行踪,接连走了一整夜和一个上午时……他仿佛仍是谢南多厄峡谷莫里河畔那个用亮晶晶的好奇追问世界的孩童。
他充满敬畏的深沉步履深谙“自然之道就是十字架之道”,深谙“山月桂与泥炭藓也需要孤独”,深谙蚂蚁“似乎也有灵魂,值得人们尊崇”——在林中宿营因布置炉灶而惊扰了石块下的蚂蚁时,他也会本能地想要向它们道歉……
而他在物理学、神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领域的广博涉猎,又使他在探索造化之谜时,能比常人更专业、内行地探入内部肌理,并将多学科瞬间交融、打通,因而,由此窥见的世界也必然更本原,更古老——
“从崩塌的页岩中,我挖出了这些腕足动物的化石,它们已在这里沉睡了五亿年……它们是微小的,但却无容置疑地是寒武纪动物留下的遗骸,代表着我们家乡深邃的过去。那时这些山峰还孕育在海水的子宫中,后来才在形成阿巴拉契亚山的造山运动的阵痛中产生出来。”
一束从容回溯的深邃目光,把我整个生命牵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幽寂与深远。周遭的人、事以及日常生活那永无止歇的嚣闹与聒噪,也仿佛被某种神奇的装置隔离了,不再真切刺耳。真切的只有我与她——我心目中的“荒野”那脉脉的对视与耳语。这使我整个人仿若充了电一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勤勉地往守立于城郊的那座山上跑去——仿佛那儿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在以一种隐秘的语言讲述着我的起源。一次次,我踏着漫无规则的野径,伴着厚厚的落叶在脚下的深情絮语,下意识地察看着一棵棵早已熟记于心的刺柏、黄栌、酸枣树又有了哪些细微的变化……一天下午,我在一个岩石突出的岬角处停下脚步,也许是为了缓解一下僵硬颈椎的不适,我将两只手臂在头顶交叉,竭力向上拉伸、高举着……突然,不经意间的一瞥,让我如遭电击般震骇了:午后的阳光将我竭力拉伸的肢体的造型放大、变形后,投映到对面灰白的岩石上——一个在粗砺岩石上劲舞的剪影,像一道闪电,瞬间犁开了孕蓄在我生命内部的亘古洪荒——
“你是附体还是原生/是毁灭还是造物/我的体内蛮荒无垠……”
在“驱迫我的激素逆流而上的”的强劲旋流中,我的长诗《极舞》诞生了。
后来我才深悟:那个剪影,是上帝仅此一次的绝版。那个下午过后,我曾无数次面对那块岩石重复同样的动作,却再也唤不回那瞬间被击中的电流了。
每一次与上帝的狭路相逢,每一回神性的颤栗,都不可预期,不能复制。




劳伦斯是近年来我反复阅读、揣摩,恨不得对其作品“敲骨吸髓”的作家,也是一位以灵与肉的幽微,反复点拨,让我隐隐开窍的恩师。
“他把橡树蓬松的幼嫩枝条环绕在她胸前,插上一些风信子和剪秋萝;在她肚脐上,他放了一朵粉红色的剪秋萝,在阴毛丛中,是一些勿忘我和车叶草。”
我用洗去世俗泥垢和陋见的双手,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著,杨恒达、杨婷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11月版)这座芬芳馥郁的情爱幽谷,小心翼翼地采撷了这束“野花”——这极尽克制的白描,与小说中劳伦斯用排山倒海的笔触描写康妮和梅勒斯在大雨的森林中畅快淋漓地裸奔、交合的画面相比,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反差和张力。固然,那样惊世骇俗的“绽放”,确实撼人魂魄,但这束“含苞欲放”的野花那敛藏在蕊中的绝美,却在月夜星辉的无眠里,一次次为我喷薄、绽放……恣意葳蕤的狂想,埋葬了白昼发酵的衣冠、世俗佝偻的纷杂以及一切由来已久、无处不在的禁锢,盎然舒展的蓬勃和无忌无惮的昂扬,在喜极而泣的泪水中,将彻底还原的通透身心送回了亚当和夏娃的原夜……
只有返回这样的“原夜”,才能像劳伦斯笔下的康妮和梅勒斯那样,用野性的呼喊,用灵与肉的忘我,震裂所谓道德的镣链,赎回伊甸园那未被玷污的初曙晨岚。
“整个世界都被奸污了。”这是小说中康妮的内心独白,更是令劳伦斯痛心疾首、坐卧不宁的“肉中刺”。他用自我放逐、四海为家的一生,向着心目中的荒野朝圣,不仅为自己的肺病“寻找一个能吸入清新空气的地方”,更是到那未被工业文明践踏和戕害的原始自然中去体悟和汲取仍保留着造物主原意的蛮荒的气息和力量:无论是“没有历史、没有年代、没有种族”的撒丁岛那仿佛被尘世遗忘的孤寂荒凉,还是塔希提岛梦幻般的原始丛林;无论是阿尔卑斯山南麓似仙似幻的加尔达湖,还是墨西哥高原上蒙着圣洁、缥缈面纱的查帕拉湖,都让他忍不住赞叹“一种美的神秘性,仿佛那些神就在这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他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峡谷驻留期间,深入体验印第安土著人的生活,窥见他们身上那蒙昧浑茫、原始神秘的知识较之欧洲人那所谓“开化”的头脑更接近生命的本源和实质。这一体悟集中呈现在《印第安与娱乐》《玉米催芽舞》《霍皮人蛇舞》等散文篇章中;而《伊特鲁利亚游记》一书则是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劳伦斯对意大利中部众多的伊特鲁利亚古墓和遗迹进行考古和探索后,从远古文化和史前艺术中“掘回”的一脉“带有自发性的、从未被标准化框住”的“生命之流”,这大胆、活泼的生命之流与“今天我们虚浅的生命之流大不一样,似乎他们是从更深的地方吸取到生命能源的,我们在那里却遭到了排斥”。
人类正是从远古荒野一路蹒跚而来,从树栖、穴居时代与天地风雨相依的家园,到钢筋水泥的摩天丛林,从钻木取火到火箭飞船……人类是进步了,但何以一步步扯断了与自然一脉相连的脐带,原始生命力在不可避免地萎缩、退化?如何让“自然之子”回归自然母亲的怀抱,重新找回未被文明阉割的血性和天性,几乎是劳伦斯所有作品的主题,也是他倾尽四十五年的生命加倍燃烧的“焰芯”。在劳伦斯夫人回忆录——《不是我,是风》(弗里达·劳伦斯著,姚暨荣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一书中,弗里达披露了劳伦斯与自然之间那种血肉相融的“交感”:当劳伦斯第一次看到一棵龙胆(一种大的蓝色单瓣植物)时,“他似乎和龙胆在进行一种奇异的交流,似乎那棵龙胆把它的蓝色和它的精髓奉献给了他”;劳伦斯经常去树林间写作,“他倚靠在一棵大松树上,仿佛那树把浆液注入了他的体内,在帮助他写作”,当他在入定般的专注中驰骋于想象、创造的王国时,蜥蜴悠闲地爬到他肩头上玩耍,鸟儿在他身旁自在嬉戏、歌唱,仿佛他已化身为一棵树、一块石头或一片草叶,彻底融入了他渴望大写的“自然(NATURE)”……这使我不由想起惠特曼曾在散文中坦露他定期到罕有人迹的荒郊野外进行“裸身日光浴”的一些私密细节,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独门秘笈,不禁让我恍然醒悟:只有身心完全赤裸地向天地敞开,才能采集吸收到来自万物根源处的气息和能量,才能使他们作品中那“带电的肉体”充溢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沛然勃发的元气和活力。
大自然,灵与肉不竭的创造源泉。谁把生命内在的自然写得更透彻,谁的作品就会被注入天地不朽的活力和荒野未驯的气息。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丰饶磅礴的造化之母,在世间每个生命身上都留下了她那鬼斧神工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杰作”:天赋的海洋深不可测,性格的山峰怪石嶙峋,灵性的森林勃发着长得高、放得开的灵动葱茏……这是一片鸿蒙着神性雾岚的原生荒野,是一个生命区别于另一个生命,有如DNA密码一样的只有造物主才能破译的被加密的“唯一性”……
但人世的成长与存在,却似乎不得不必经身不由己的“驯化”之路——参差丰富的“原生态”在劫难逃,被不断地砍斫、磨削,不断地被“同质化”,直至自身也参与其中还自鸣得意。一个生命,从咿呀学语开始,就在“鹦鹉学舌”的模具里,学着怎样将“我”浇铸成“我们”了。流经每个生命的语言早已不是源头或上游的语言,不仅失去了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那与天地万物呼应的初始鲜活,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些语言因为难逃被利用的工具化命运而必然覆上了教化的菌丝和陈腐的锈斑……被这样的语言养育的生命和灵魂,再加上家庭、学校、社会齐心合力的“塑造”,怎能不在重重淤阻中扭曲、变形和异化?在循规蹈矩、行将就木的窒息中,在适者生存、实用至上的贫瘠沙漠里,我庆幸自己还能与尼采、茨维塔耶娃、梭罗等一颗颗蓊郁、辽远的灵魂及时相遇并深情相守,在他们还给我的亚马逊雨林的呼吸里,夜以继日地开掘、还原着生命本然、葱郁的初衷——这是艰难的辨认、甄别:哪些是自己生命原有的,哪些是被世俗强加的或不知不觉沾染的;这是残忍的自我手术,是剜骨剃髓的自我救治……我深知,在如今没有什么不被贪欲的黑洞裹挟、吞没的无形漩吸里,在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生态交互恶化的雪崩里,我必须比一百五十年前的梭罗更清醒、更孑然弃绝、更自我苛求,才有可能像黔南古镇上那棵独木也能成林的千年老榕树那样,在沉霾压顶、物欲攒动的市声里,气定神闲地守住那片与天地元初同在的静谧与蓊郁。
只有那样的静谧,才有可能聆听到诗歌来自源头的本真的声音;只有那样的蓊郁,才有可能为古老的语言注入野性的思想、情感与想象力,使每一个词,都如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恢复她那原始的处女般的清新”。
2018年1—2月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4期,责任编辑: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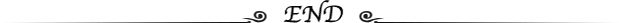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