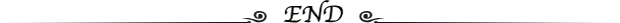众家言说 | 李森:孤立的人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孤立的人,既然是一个“类”,那就是概念化的人。或者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是共相的人,而非殊相的人。一个思想堕落的时代,是孤立的人行走江湖的时代。
李森
在爱尔兰的民间传说里,有一个吝啬鬼叫杰克。此人由于吝啬,死后不能进入天堂。不能进入天堂也没有关系,毕竟还有地狱可去。但可怜的是,他又因捉弄、取笑魔鬼撒旦同志,被魔鬼挡在地狱门外。又有一说,他进入地狱后,又被逐出,回到人间。
无论什么因由,无路可逃的鬼魂杰克只能混迹于人世间,成为人世间的游魂。这个鬼与其他鬼的不同之处,是他四处游荡时必须提着灯笼,见到人类,就躲藏在人类之中,变为人类的一员,或干脆进入人体,化为人性中的一部分。看来,杰克不但害怕黑暗,而且对人类充满了眷恋。
杰克提着灯笼游荡的一个潜在隐喻,是他并没有放弃追求光明。自古以来,任何一个版本的地狱和天堂,都需要“光”显现“明”的照耀,否则,连魔鬼也看不清自己和他们的同类。
不知从何时开始,提着灯笼游荡的杰克成了一个可怜甚至可爱的形象。在万圣节,提着萝卜灯或南瓜灯夜游的人们,都从防范魔鬼杰克者变成了杰克。所以,杰克事实上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何尝不潜藏着一个魔鬼游魂。
杰克,作为“人”这个复杂内涵中的一个象征,又是谁创作的呢?是我们所有人。在每年的万圣节上,每个人都参与了杰克的创作,年复一年地创作。人们之所以从厌恶、恐惧杰克,进而到游戏杰克,正是杰克身上有一种普遍的人性。
想到杰克附体于人这个事实,我要假想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孤立的人”。他看不见个别的、栩栩如生的事物,听不见单个心灵滋生的声音,他只属于某个自闭的系统,没有具体个人的人格。显然,这个人是个非人,非人也可以姑且称为人,因为他有一个人的形象,这个形象还会走路,甚至混迹于各种江湖,消耗自然和社会财富。一言以蔽之,他在我们中间,跨越了时空,混迹于人世。
那么,这个“形象”何以存在呢?一个没有个人的直观视觉、没有个人独立的听觉、没有个人的触觉、没有言语的“形象”,有行动着的精神性吗?
我想起了美国当代小说家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中的第一个孤独《南瓜灯博士》。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转学到新学校的小学生文森特·萨贝拉的故事。尽管班主任普赖斯小姐对他付出了巨大的爱,想尽各种方法,让他融入新的班集体,结识新的朋友,但文森特还是无法冰释由于贫穷、自卑和从小缺乏家庭之爱而产生的自闭的灵魂壁垒。
读者能体会到,在小学生文森特的心灵中,没有一扇窗户向普适性的人间情怀敞开,那看似冷静的外表下面,却沸腾着焦虑、颤栗、恐惧、敌视与撒谎的惴惴不安。为了表现自己,他不停地撒谎。比如,他说也像其他同学一样,看过正在放映的恐怖片《杰凯尔博士和海德先生》,误把片名说成是《南瓜灯博士和海德先生》,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他因而得了个南瓜灯博士的绰号。
普赖斯小姐对他的爱仍然温润而耐心,不过,那种爱的人性教化对他却毫无价值。他以恶行来报复这种温蔼之爱,在学校的墙壁上偷偷地画了一个裸体的女人——“大大的乳房,硬而小的乳头,线条简洁的腰部,中间一点是肚脐,宽宽的臀部、大腿,中间是三角地带,狂乱地画了阴毛。在画的下面,他写上标题:‘普赖斯小姐’。”画完后,他看了一会儿,回家了。这是故事的结尾。
耶茨在此将“杰克”(Jack)、“杰凯尔”(Jekyll)和“南瓜灯”(Jack-o-lantern)的音与义巧妙互喻,把读者引向万圣节上人们游戏的那个人间幽灵。
文森特即杰克。具体地说,文森特或杰克,已经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类”人,一个“孤立的人”。一个“类”,随时都在借助一个又一个个体,行走于世间。说到底,像杰克或文森特这样的人,只是一个“人形”。多少次,我想听这个“人形”的声音,我的听觉失败了。但我并不是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我总是自以为听见了一个黑暗的固体黏糊在一个黑透的深渊之中。一个像实心球一样的黑色固体,又没有重量,它会是个什么球呢?
孤立“人形”的存在,对于精神性的人来说,是个巨大的障碍。可是,孤立“人形”自身没有障碍。障碍不知道自己是个障碍。“行尸走肉”这个说法,是对孤立人的形象描述。
孤立的人,既然是一个“类”,那就是概念化的人。或者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是共相的人,而非殊相的人。一个思想堕落的时代,是孤立的人行走江湖的时代。比如体制中的多数人,即是共相的人,他们在体制的层面上,没有具体人的性质,也就没有鲜活的人性。
共相的人,是善的对立面——恶的一个形式。对于鲜活的人性而言,最大的恶不是单一的、个别的恶,而是“整体”的恶,即共相的恶,“类”的恶。“整体”的声音和形象,仿佛铁锤的重、刀锋的寒冷、不可阻挡的滚滚车轮。
在共相的人即“孤立的人”控制人世的体制中,由于没有个人言语,也就没有文明的创造。对于这种人而言,本真的善没有意义,因为本真的善即是个人的行动。
“整体”的恶,并不知道自身是恶。“整体”的恶如果知道自身是恶,那么善的反省已经发生。只有鲜活的个体,才有善和恶的反省。杰克、文森特等等,都没有反省的能力,因为没有自我。
善与恶的评判是最不确定的。善以恶行,恶以善行,随时都在发生。
在正义的恶面前,我,作为个人,是失聪的。正义的恶,是孤立人的恶,共相的恶。
我们既然听不见孤立的人发自人性的声音,因此对这种共相人的倾听也是无效的。
然而,作家和读者都在试图倾听,或者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创作一个个可以倾听的角色。鬼魂杰克的创作者在努力,文森特·萨贝拉的创作者理查德·耶茨也在努力。对上帝和诸神的创作,是作家这种努力的一个个极端的例证。
上帝和诸神的创作,是孤立的人即共相人的创作。尽管表现的角色从古到今一直在转化,并赋予时代的特征,但这种“类”人、“整体人”、共相人、孤立人的创作努力,一直没有改变。
孤立人的创作超越了任何艺术流派。在任何艺术流派中,都有典型的孤立人的存在。孤立人的创作,是任何一种创作隐喻形式的一个象征。人们往往记住的是孤立的人,而非单个的人。
这是语言的概括性特质决定吗?是的,语言,这个陌生的尤物。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奥楚蔑洛夫这个被喻为“变色龙”的警官和将军家的劣等狗,即是一个“类”的“人”和“类”的“狗”。奥楚蔑洛夫是一个“打狗要看主人”的警官,而将军家的狗,是因“狗”以“主”贵,两者都是恶的象征。警官与狗,在此的隐喻内涵可以互换,是“类”的隐喻的交叉。
作为“整体”的恶是可怕的,它无处不在,它与本真的人进行对抗,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抗。说到底,“整体”的恶,是世间行动之善的敌人。


不过,这个敌人(中性的)看来不可或缺。我们都有表现敌人的渴望,哪怕是个假想的敌人。
写作之所以喜欢对“类”人的表现,就是因为这个敌人的存在让本真之个人受到威胁。孤立人的威胁永远存在着。因为天才的作家,是个创造敌人的动物。
人类最天才的角色创造,即是上帝和诸神的创作。
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剧《等待戈多》中的“戈多”(Godot),可喻为上帝这个“类”人的共相,(Godot的前三个字母即英文的“上帝”)也创作了“等待”这个行为的事态“共相”。“等待”和“戈多”,都是“整体”的概括。
我们需要概括者。我们的语言这个恶魔需要概括,于是有了上帝和神的类人格。从上帝到耶稣,是“普遍性”的、“整体”的神向具体的神的亲近;从耶稣到上帝,是具体的神向“整体”之神的仰望。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神)三位一体(Three Persons in One)。我们总得要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来承受苦难,以表达存在的神秘性与我们有关。
在《等待戈多》中,戈多是上帝,永远也等不到,正所谓“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等待”是“神”,是一种基于人之行为的精神状态;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即“耶稣”,是上帝、神和人的具象符号。如果没有上帝和神这两个位格,人这个位格就只有个躯壳。因此,人既要等待,又要到远方去。而可怕的是,人既到达不了远方,也不能等来什么。《等待戈多》直到剧终,两个流浪汉也走不出等待的那个人间“地狱”:

弗拉季米尔:嗯?咱们走不走?
爱斯特拉冈:好的,咱们走吧。
他们站着不动。

我们又来看看第一幕中两个流浪汉的对答:

弗拉季米尔:你读过《圣经》没有?
爱斯特拉冈:《圣经》……(他想了想)我想必看过一两眼。
弗拉季米尔:你还记得《福音书》吗?
爱斯特拉冈:我只记得圣地的地图。都是彩色图。非常好看。死海是青灰色的。我一看到那图,心里就直痒痒。这是咱们俩该去的地方,我老这么说,这是咱们该去度蜜月的地方。咱们可以游泳。咱们可以得到幸福。
弗拉季米尔:你真该当诗人的。
爱斯特拉冈:我当过诗人。(指了指身上的破衣服)这还不明显?(沉默)

《等待戈多》是荒诞派的经典。批评家之所以命名这个戏剧为荒诞派,是以某种存在之不荒诞为前提的。可事实是,不荒诞即荒诞,荒诞即是真实。《红楼梦》也是个荒诞剧,其中有副对联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贾代善、贾政、贾宝玉、贾雨村、甄士隐,人世间的荒唐事,都是一把辛酸泪。可荒诞者并不知荒诞,因此,荒诞是没有“辛酸泪”的。泪流,是人文主义的荒诞;无泪可流,是荒诞之荒诞。


塞缪尔·贝克特创作荒诞“类”人的功夫当然了得,然而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个创作语境中,他也并非独立的一个孤证。作家创作孤立的人的这种功夫,是彼此熏染的。古往今来的艺术书写都不例外。神话中诸神谱系的创作,衍生为柏拉图各级理念的创作,柏拉图洞穴隐喻中被缚者的创作,衍生为耶稣所象征的人之苦难的创作,耶稣复活升天的创作,又回到了神的共相隐喻的创作。神不死,即孤立的人不死。玉皇大帝、世俗皇帝和他们的神性或神性附体的创作,都是一码事情,都为了寻找抽象的共相人而乐此不疲。
英国著名戏剧批评家阿诺德·P·欣奇利夫在其《论荒诞派》一书中说:“批评家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从文学上而不是从哲学上追溯了贝克特的承继渊源,并且发现他的主人公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那儿发展而来的——例如,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萨姆莎真的缩变为一只虫子,成了他担心自己所是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变成了卡夫卡的虫子,最后,又变成了贝克特的反主人公……贝克特拒斥学问,并且把语言看作是我们不能了解自己身在何处或者身为何物的原因之一,看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每一部杰出的作品,都试图塑造不同类型的孤立者,以此来展现作者自己破解人世荒诞迷梦的能力。不同角色类型塑造的尝试,是一个个重要的方式,在小说和戏剧中尤其如此。法国新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曾写下他曾经看到《等待戈多》主人公时的惊讶(转引自阿诺德·P·欣奇利夫《论荒诞派》):


戏剧中的人物通常不过是扮演一个角色而已,就像我们周围所有那些正试图逃避自己生活的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在贝克特的剧中,那两个流浪汉好像就是呆在舞台上,没有角色可扮演。
他们在那儿;所以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存在做出解释。但他们似乎并不依靠事先准备好的并熟记在心的台词。他们必须即兴发挥。他们是自由的。
当然,他们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能运用这种自由的。正如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要背诵一样,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即兴发挥。他们的谈话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因而变成了荒诞无稽的只言片语:无意识的交谈、俏皮话、全都有点甫起即伏的虚张声势的争论。他们漫无目的地东扯西拉,无所不谈。他们唯一不能想做就做的事情是离开舞台,不再呆在那儿:他们必须呆在那儿,因为他们在等待戈多。



人们对这个戏剧的论述汗牛充栋,“反主人公”的两个流浪汉角色,实际上也并没有摆脱创作者创作孤立人的叙述圈套。贝克特的“等待”既是“类”人的行为,也就是主人公之“典型”。在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历程中,我们极力消解了巴尔扎克式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而我们又创作了新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转换了种种叙述方式,极力消解典型环境,抹平典型人物,但我们消解或抹平的是小说或戏剧的情节或人物性格,却又孤注一掷地创作了新的“类”人,也即新的典型人。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创作的主人公布鲁姆的名气,并不比巴尔扎克创作的欧也妮·葛朗台、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创作的列文之类逊色。乔伊斯的崇拜者们,已经把每年的六月十六日变成了“布鲁姆日”。崇拜者在“布鲁姆日”狂欢的时刻,他们就是布鲁姆,同时也是乔伊斯和“布鲁姆”对他们的再创作。


葛朗台、列文、布鲁姆和贝克特的流浪汉,都是一个孤立的人即“类”人或共相人的象征。在此,文学流派和文学史“取消”了,只留下孤立人的时间书写。
作品中所有孤立的人,同时也是作者这个孤立的人的创作者。正如鲁迅的阿Q、孔乙己创作了鲁迅,翠翠创作了沈从文,华威先生创作了张天翼,信徒们创作了耶稣、乔达摩·悉达多。写作者最大的雄心,就是渴望被读者创作,不管是渴望被一个心仪的人创作,还是被芸芸众生创作。
自古以来的创作家,在冥冥之中总想被孤立,而成象征,而成英雄,而成“王”。
可是,除了孤立者的创作或被创作,艺术还有什么样的磁性可以撼动世人的铁石心肠?
二〇一二年五月六日昆明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2年第6期,责任编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