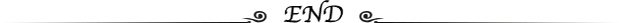新书快照 | 现代社会的噩梦、残缺人生与写作梦想——《卡夫卡传》出版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
[德]莱纳·施塔赫 / 黄雪媛 程卫平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 / 2022年04月
布拉格犹太人、保险局公务员以及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博士活了四十岁零十一个月,三十九岁办理了退休手续,最后因喉结核死于维也纳附近一家疗养院。
身为作家的弗朗茨·卡夫卡给后人留下了《城堡》《诉讼》《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第一场痛苦》《小妇人》《饥饿艺术家》及《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2022年是卡夫卡《城堡》诞生的一百周年,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即将推出广受赞誉的《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卡夫卡传:关键岁月》)。作者施塔赫吸纳诸多至今尚未发布的最新的卡夫卡研究成果,以颇富画面感的生动叙述手法展现卡夫卡的内心与外在世界,包括大量聚焦日常生活的近景镜头,令人身临其境。



卡夫卡的文字夸张、残酷、晦暗、不够幽默。他的世界不宜居住。但是他的语句渗入肌肤,发人深思,让人再也抖落不掉。卡夫卡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梦境逻辑”与现代社会的噩梦完全一致:对个体生活的剥夺似乎在我们所有人背后悄然发生。每个人看似自由,可无论你如何选择,你永远都只是一个“案例”,与之相应的规则、措施和制度存在已久,早已准备就绪,即便是你某些完全自发的举动、快乐的冲动都跳不脱那个彻头彻尾被管理、被规划好了的世界的樊笼。
阅读这样的文本,读者面前会浮现出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另一个是,“这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如果读者追随前一声召唤,会陷入作品诠释的密林;倘若循后一声而去,则会踏入一片生平传记的字谜方阵,费多少力也解不完。而在这套《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将带你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这是迄今为止内容最详实、体量最浩繁的一套卡夫卡传记。已译为英语、西班牙语等多国文字,斩获莱比锡书展奖、海米托·冯·多德勒奖等奖项。
如果我们搬用现今流行的那套幸福参数来衡量卡夫卡的人生,在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卡夫卡都是残缺的:健康、性、家庭生活、消遣、冒险、独立、事业有成。诚然,卡夫卡并没有生活在社会边缘,他有自己的社交生活,还升到部门副主任,能领退休金;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有限的安全感却是过于漫长而辛苦的求学生涯换来的,也可以说是用一生光阴换得的。
当今的年轻人已觉理所当然的决定权,广泛的选择自由,对于那个年代的卡夫卡而言都遥不可及。他三十岁的时候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只有几个月时间是搬出去住的(同在一座城市);他的朋友圈很小,而且非常稳定,几乎没什么变化。他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财产被疾病和恶性通货膨胀所吞噬。这个“世界”,他没有看到多少,看到的那一点也是匆匆一瞥,因为旅行时间受到严格的度假规定所限。作为补偿旅行不足的消遣活动也少得可怜:游泳,划船,做操,疗养,郊游,打理园圃,在布拉格酒馆喝个半醉。然而最叫人震惊的,还是卡夫卡为满足性与情欲的需求穷其一生付出多少无望的努力,弗朗茨·卡夫卡一生三度订婚,但却终生未娶,没有子嗣。而这种努力与那所得无多的幸福形成巨大落差,即使那微薄的一点幸福感,得来也总费尽周章,从来不曾自由畅快地抵达。
伴随着生活中如此种种限制和缺失,卡夫卡在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作行为在他眼里是生存之核心,写作让他内心平静,情绪稳定,写得成功令他感到快乐和自信。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聚焦1910到1915年那决定卡夫卡一生创作与生活的关键年月。这是卡夫卡一生中记录最详细的时期,无疑也是他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在这段岁月里,卡夫卡接二连三地作出了重要决定,从而定义和限制了他未来十年的生活。曾经无拘无束、易受外界影响的青年卡夫卡转变为敬业的公务员,成长为“卡夫卡式幽默”的大师。他经历了一些痛苦的事情,这些事件塑造了他的自我形象,被他作为典型事件而铭记一生,尤其是战争爆发前几周发生的解除婚约事件。在1912年至1914年间卡夫卡经历了两个极富成效的创作阶段,“爆发式”写出《判决》《变形记》《失踪者》《诉讼》等突破之作,就此铺平那条他将一直走到底的艺术之路。
此部传记集施塔赫十八年研究之所得,施塔赫查阅了大量马克斯·布罗德的笔记和日记等一手资料。有如全景电影般呈现了犹太人身份、布拉格社会环境、禁欲主义、战争、与菲莉丝之恋等每一要素与经历在卡夫卡身上烙下的印迹。这六年,构成卡夫卡生存的中心。或许在这本传记中,我们能找到破解卡夫卡这一阶段创作之谜的钥匙。





卡夫卡家的一天是从清晨六点开始的:清理厨房炉灰,准备早餐,给起居室供暖,准备洗漱用的热水——这一连串让人讨厌又嘈杂的活计,自然都是女佣分内的事。但是卡夫卡最小的妹妹奥提莉艾,小名奥特拉,差不多也在这个时辰起床。几年来,她承担了一项任务:每天匆匆吃完早餐,带上一串钥匙,赶往近一公里外近老城区的策尔特纳街,打开“赫尔曼·卡夫卡妇女时尚用品商店”的大门。七点一刻,店员们就已在店门口等候了。
奥特拉一出门,她哥哥差不多也要起床了。他那间狭小的没有暖气的卧室很不幸地连着父母卧室和起居室,墙这边早餐盘叮当作响时,另一边就会传来母亲的窃窃私语,父亲毫无顾忌地打着哈欠,在嘎嘎作响的双人床上重重地翻身。对着走廊的一扇门镶着不透明装饰玻璃,只要外面一开灯,他的房间也会亮起来。
卡夫卡家里十分局促:屋子里到处能听见父亲的大嗓门。如果有客来访,全家都会出面接待。要是不甘心于只能和客人打暗号,就得事先和家人说好,才能单独会客。从卡夫卡的文字描述里,我们倒不能看出有哪位家庭成员对缺乏私密性的家庭环境感到不适——除了卡夫卡自己。每逢星期天早上,卡夫卡只要瞥见几步开外父母双人床上一团乱的被褥,就会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当然他不会直接写下这种感受)。
不过,他没法抱怨,毕竟,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拥有自己房间的人,三个妹妹——艾莉、瓦莉和奥特拉长年挤在一间“女孩房”。大妹艾莉1910年秋天结的婚,婚后离家另住,但卡夫卡还得和另外五位(还包括一位女佣)同住一个屋檐下。清晨的家庭气氛令他感到不适,他愈发想摆脱这种居住环境。
睡眠也是一种姿态,能激起保护欲和母性关怀,而且这样的关怀不会去眷顾那个从容旅行的菲莉丝形象。她的弱点暴露之时,卡夫卡吃惊不小,但他并没有去修正她的理想形象,而是迷恋上了第二个形象。在这个形象中,她所有的柔弱都被浓缩成一个意象:一个睡眠中的女孩。
……如果我知道,你还醒着,而且是因为我的缘故,我就无法安心写作。但如果我知道,你已睡下,我就会勇气倍增地写下去,因为在我看来,好像你已经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了我。酣睡中的你是多么无助,多么需要人看顾啊,就好像我是为了你和你的安好而写作。
有了这样的想法,写作怎么还可能停顿呢?睡吧,睡吧,白天你的工作比我多多了。无论如何,你要快点去睡,明天请不要坐在床上给我写信了,也许今晚也不要写了,如果我的愿望足够有力的话。而且在你睡觉之前,你可以把阿司匹林药片先扔到窗外。
两种想象,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保护者,另一个是被保护者。两者相互矛盾,只要卡夫卡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包含两个菲莉丝形象,矛盾就无法消除。他感受着矛盾造成的压力,何时转向哪个形象,取决于恋爱曲线发烧般的起伏。他轻而易举就能逃避:从一个幻影转移到另一个幻影,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阻碍了他去兑现曾再三强调的亲密关系。
有一回强大的菲莉丝和弱小的菲莉丝相遇了。她给他寄了一张童年照,大概是她十岁时拍的,卡夫卡几乎感动到流泪。“肩膀这么窄!她真是弱不禁风啊!”他随即意识到,这个女孩就是那个“还未曾解释为何会在酒店房间里担惊受怕的女人”。菲莉丝于是又给他寄了一张照片———出于一种微妙的、有点矛盾的妒意,谁知道呢。这回她寄来的照片上是一位从容笃定的成年女性。卡夫卡忽然间就不确定了:
新寄来的照片给我的感觉有点奇怪。我觉得自己和小女孩的距离更近,我可以对她说任何话,而我对照片上的女士却怀有敬意。我想,即使她的确是菲莉丝,她也是长大成人的菲莉丝,俨然是位需要认真对待的女士。小女孩很有趣,她并不悲伤,但神情却非常严肃,面颊饱满(这也许只是晚上灯光的作用),脸色有些苍白。如果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虽然我决不会不假思索直接跑向小女孩,我不会这么说的,但我也会朝着小女孩走去,虽然会走得很慢,而且一边走,一边会四处寻找女士,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最好的情形是,由小女孩带着我去找女士,并把我介绍给她。
卡夫卡手里拿着两张照片,女孩和女士,两人都在看着他。他的目光从其中一个游移到另一个,他试图重合这两个形象。但他无法做到,总有一天,他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卡夫卡的《诉讼》是个庞然怪物。里面没任何东西是“正常”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简单的,无论你是研究它的诞生史,它的原稿,还是分析其形式、题材、内容,或者着力于阐释这部作品本身,探究的结果都一样。无论朝哪里看,都是幽暗一团。
这一点,布罗德最先感觉到了,因为卡夫卡经常会给他读上几页。最终,布罗德把手稿拿回家去了,他可不想让卡夫卡把书稿销毁掉。他深信《诉讼》是部重要作品,足以让好友成为超新星,光耀文坛。可他最终拿到手的却是松散的一百六十一张活页,大部分正反两面都写了字,从几个本子上扯下来的。卡夫卡给这堆稿纸草草归了类,给每一“捆”(可以理解为一个章节)加了一页封面,上面写有临时性的标题。但是有几“捆”里面仅存一页,而另几“捆”则让人怀疑包含了不止一个章节的内容。其中哪些章节已经写完,卡夫卡在生前从未透露,也从未给这些章节编过号。所以摆在布罗德面前的仿佛一个大杂烩,里面有已经完成的章节,快要写好的,才写一半的,以及刚刚才写了个开头的章节。而且如果要做成书,布罗德还得自己给这些章节排序。当然,他还有大把时间、大把机会直接询问作者本人。只是对此他很谨慎,不轻易开口。布罗德很高兴把这个珍宝锁在自己抽屉里保护起来。他以一贯的方式给卡夫卡施压,比如公开谈到卡夫卡“完成了”一部长篇,有一回甚至威胁说,他要独自将《诉讼》“缝合成衣”。倘若卡夫卡曾经疑心布罗德说的可能并非玩笑,那么肯定会找布罗德要回《诉讼》书稿。
布罗德是老道的文学评论家,但并非以研究文本见长的文献学家,他不具备这方面的技巧,也没有这类专家应有的顾虑。他把卡夫卡以速记体写下的段落整个划掉,然后在同一页上整整齐齐誊写了一遍。他觉得这么做并无不妥,他竭力要让那些为卡夫卡的文学天才所倾倒的读者读到完整的作品,用尽一切办法掩盖作品支离破碎的原形。他给小说添了标点符号,统一了人名,为了让没写完的一章显得完整,甚至调整了句子顺序。过于零碎的段落,他干脆拿掉,或者像在后来的版本中出现的那样,将其归入“附录”,其余则凭个人感觉来整理。就像“启示录”一样,这部令数代文本鉴赏家驻足评赏的文本最终以这样世俗的方式诞生了。


程卫平
1913年9月2日,布拉格。弗朗茨·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女友菲莉丝·鲍尔修书一封,卡夫卡在信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尔帕策、克莱斯特和福楼拜列为他的“真正血亲”(Blutsverwandte),以此解释他对婚姻极度矛盾、摇摆的心理。他在信里写道,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三人都是单身汉(卡夫卡自然也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段婚姻很失败),而对他自己来说,“为了写作而放弃人类最大幸福的欲望,不停地切割着我全身所有肌肉,我无法让自己脱身”。卡夫卡通过“血亲”的群体合理化他“不结婚”的心理暗示,反过来,也可以说他借助“单身汉”这条“身份”之索,找到一种特殊的“认同”。
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Reiner Stach)自1985年完成有关卡夫卡的博士论文起,三十多年来一直专事卡夫卡研究。在皇皇巨著“卡夫卡传记”三部曲之首卷——《关键岁月》(Die Jahre der Entscheidungen)里,施塔赫以全景电影式的叙述手法细致还原了对卡夫卡产生“关键”影响的爱情经历,展现囊括布罗德、韦尔弗、魏斯、拉斯克-许勒等人的布拉格(也轻触了维也纳和柏林)德语-犹太文学圈,更是逐月逐日勾画了卡夫卡灵感迸发、才思飞扬的“关键”创作期图景。其中也写到对卡夫卡文学试验的突破发挥隐形作用的“血亲”,这一点施塔赫虽未深入解读,但对于读者理解卡夫卡却颇为要紧。

卡夫卡爱读传记,尤其着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陀氏早年与暴躁专横的父亲间的紧张关系、在绘图科“像土豆一样乏味”的工作一定都让卡夫卡感同身受。而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纯粹文学上的相似之处也显而易见:两人都将目光聚焦于“负罪感”心理、理性主义之失败、传统家庭的消解、有着“冷硬钢铁外壳”的都市工业社会里个人的内心撕裂与孤独。
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夫卡最鲜明的影响体现在后者对“害虫”(Ungeziefer)的人格化和隐喻化,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体现为四处可见的酒色之欲、堕落场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嘉告诉阿辽沙,“……我便是一只虫子……咱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都是这样,你虽然是天使,可是在你身上也潜伏着这虫子,它会在你的血液中兴风作浪”(摘自荣如德译本);在《地下室手记》中,叙述者将那位过度敏感的“地下室人”描述为“受伤害、受侮辱的老鼠” 。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变形记》中的存在困境不免让读者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开场的“变形”暗示,但更让人联想到果戈理《鼻子》的开篇——主人公一觉醒来即已变形,变形是“既成事实”。不过,要确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夫卡的“直接”影响并非易事,说卡夫卡“效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有失公允,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两人都欣赏且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19 世纪那些幻奇文学和志异小说的创作大师。两人作品里既有狄更斯的回声(《关键岁月》里讨论到卡夫卡的《司炉》时尤其强调了这一点),也都有果戈理和E.T.A.霍夫曼的回声。莱纳·施塔赫在卡夫卡传记中认为卡夫卡视这些前贤为血亲,而非“榜样”;他是其“后裔”,而非效仿者。卡夫卡力图“接通历史的血液循环系统”,一切围绕着“认同”两字。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提到卡夫卡还喜读海因里希·劳贝(Heinrich Laube)所著的格里尔帕策传记,他在维也纳开会期间错过近在咫尺的格里尔帕策“书房复制品”,事后懊恼不已。也难怪:格里尔帕策学的是法律,卡夫卡则是法学博士;格氏在奥地利官僚机构中担任小公务员,也跟卡夫卡一样;格里尔帕策沉醉于写作,心思完全不在法律领域,这一点两人也像得惊人;各自都订过婚,却终身未娶。这些人生经历上的相似之处(他们俩甚至连名都一样)可能正如“穷乐师”故事本身那样既强烈吸引卡夫卡(“几乎能背下来”),也让他心生排斥:卡夫卡对这篇小说的喜爱和憎恨反映了他典型的矛盾心理。后来在给恋人密伦娜·耶森斯卡的一封信中,他谈及《穷乐师》,一开始说这篇小说对他“毫无意义”,后来又承认 “仅仅出于谨慎才这么说的”,因为他“为这个故事感到羞愧,就好像是自己写的一样”。这一告白无疑暗示了这位二十世纪现代派作家对远在他一个世纪之前的“血亲”的深刻情感认同。《关键岁月》里写到卡夫卡在众人面前朗诵自己的突破之作——《判决》时,终于体验到朗读《穷乐师》时的那种“美学爆发力”。

对福楼拜,卡夫卡更是推崇备至(又是一个学法律的),认为他完全投入文学艺术,几乎与其艺术融为一体(虽然福楼拜一样也在生活与创作之间撕裂),在单身汉-艺术家中堪称典范。卡夫卡在日记和书信中,七次提及福楼拜。在他的“关键岁月”里,卡夫卡在1912年6月6日的日记里抄录了福楼拜的一段话,借以表达他自己对写作的执着。“我的小说是山崖,我悬在上面,并对世界上正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同年12月,卡夫卡在致菲莉丝的情书中写道:“我曾梦想着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当然以有甚于我现在的精气神整日整夜无休无止地朗读整部《情感教育》。”
1881年,福楼拜生前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出版。两个抄写员离奇而不无喜感的故事无疑启发了卡夫卡,他在关键年月1915年写《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似乎在模仿《布瓦尔和佩库歇》,这种模仿不仅体现在两个难以对付的乒乓球(以及后来《城堡》里的两个助手)与布瓦尔和佩库歇在意象隐喻上的呼应,更体现在小说语言风格上——一方面追求精准而简洁的语句(le mot juste),另一方面都喜欢不动声色地讲述看似严肃沉重实则荒诞不经的故事(即所谓kafkaesque),虽然卡夫卡常常被视为沉郁、文场悲观的作家,但他很多作品恰恰证明了他作为幽默作家的一面。透过那些令人费解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背后卡夫卡那捉摸不透的微笑。
卡夫卡被诊出结核病后,一直自问:“结核病人可以结婚吗?”而这竟也让他对福楼拜的尊崇多了一个理由——《情感教育》的作者是结核病人的儿子。在1917年9月25日的日记中,卡夫卡语带嘲讽,父母患有结核病,其孩子“要么肺部废掉,要么成为福楼拜”。由此也可见卡夫卡的“血亲认同”绝不仅源自文学作品本身的吸引,也在于生平和心理上的相通相印。否则,恐怕连歌德也要列入他的“血亲”了。
191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德文译本面世,德语读者开始关注这位俄国文坛巨匠。后人发现卡夫卡的私人藏书室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短篇小说集、《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而卡夫卡也曾激动地给好友布罗德朗读《少年》。根据他的书信和日记所录,除了个人藏书室里的书,他还读过许多其他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包括尼娜·霍夫曼(Nina Hoffmann)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集撰写的介绍性长文。可以想象,倘若卡夫卡在中文世界复活,他应该会喜欢聚合了陀氏多种评注、传记作品的“文学纪念碑”。而我们作为卡夫卡和《卡夫卡传》的读者,或许也像爱读传记的卡夫卡那样,潜意识里正暗自寻觅精神上的“血亲”与生平上的“回声”,以追求自己的“内在真实”,抵抗生之孤独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