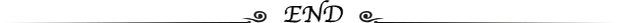第一读者 | 约翰•兰切斯特【英国】:克里斯蒂的作品背后是她对形式主义有意识的迷恋……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官方网站称她为“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家”。这一点很难证实,官网也未曾费心求证,但如果想到她所写的六十六部长篇小说和十四部短篇小说集仍在以上百种语言、各式开本出版,就会明白为何她的作品的英文版总销量高达十亿,译本销量也有十亿开外。别忘了,她还撰写了世界历史上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即克里斯蒂的剧作《捕鼠器》】。故而关于她的作品是否古往今来销量最高一事,纵使仍心存怀疑,也还是鸣锣收兵,转而探究更有趣的问题为好:是何缘故?我不敢以首位发问者自居。在以撰写经济评论文章为主业的时期,我开始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那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是我唯一能读下去的与主业无关的读物。她更是唯一能令我拜读其五十余部作品的作家。凡此种种,原因何在?



参看两位曾被视为克里斯蒂劲敌的作家,或许可以窥得部分答案。她们是玛格丽·艾林翰和多萝西·塞耶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两位代表人物。下面是艾林翰的名作《烟中之虎》中的一段:

她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忍着心痛锐利地瞥了她一眼。她真美。像个一身迪奥的埃及女王。服饰与人仿佛已融为一体。长外套是玫紫色的,夸张的衣领状如船帆,凸显出她苗条的身段。她遵从时下的风尚,整个人看起来柔若无骨,肌骨像猫一样柔软灵动。软毡帽下露出一绺亚麻白的卷发,下面那张面孔美得几乎不真实。骨格清纤的脸上薄施脂粉,妆容的每一抹色彩都含蓄地呼应并烘托出那双大眼睛——浅于斯堪的纳维亚蓝,而又深于撒克逊灰。她的鼻子小巧精致,丰满的双唇涂着淡淡的口红,直到她开口,才能相信她是个真实的人。她的声音沙哑,这一点也很时髦,但语气透着活泼灵巧。还没听到她说什么,听者就会惊讶地意识到她是个真诚的人,而且并不太老。
再来看一段塞耶斯的文字,选自《俗丽之夜》:


显而易见,艾林翰和塞耶斯的作品中文艺成分要大得多。艾林翰善写,她笔下的段落多多少少都有着引人入胜的力量、势能和细腻。塞耶斯的情形则要特殊一些,她的文字有力,但文风略显怪异:自带虚假的味道,读者要么勉强接受,只当看看老派文风找乐子,要么全然读不下去。即使你嘲笑的未必是她本人,至少也是她那一路数。这两位作家无疑都有文学才能。不过,正因为如此,强烈的风格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东西会过时,极易变得造作或陈腐。这么说吧,有可能“过期变质”的因素更多。以类型小说而言,文艺品质的分量越重,失败的风险越大。
三位作家的思想态度有相似之处。艾林翰和塞耶斯都认为自己是比克里斯蒂更为进步的思想者。艾林翰笔下的主角艾伯特·坎皮恩是个纨绔子弟,但她的女性角色都有像样的工作:最后嫁给坎皮恩的阿曼达·菲顿小姐是飞机设计师,坎皮恩的姐姐瓦尔在时尚界工作,这是《裹尸布中的时尚》(多好的书名)告诉我们的。瓦尔嫁了个名叫艾伦·戴尔的好人,条件是:戴尔对她“负有全部的责任”,而作为回报,他要得到“你的独立、你对事业的热情、你的时间和你的思想”。瓦尔愉快地接受了。这在如今着实难以入目,就连不服膺政治正确的菲·多·詹姆斯【菲·多·詹姆斯(1920—2014),英国当代著名推理小说家】也声言,这里的“厌女症触目惊心”。《裹尸布中的时尚》本可以成为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典范,却被这一点毁掉了。塞耶斯在写未婚同居的哈莉雅特·维恩时也陷入同样的困境,她热情卖力地宣扬其中的现代性,如今反而显得很老派,就像她称赞出身贵族的男主人公“双肩的剪裁完美得令人神魂颠倒”一样老派。



我在亚瑟·阿普费尔德的作品里看到了另一个打破边界的例子。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写了一系列以澳大利亚土著侦探邦尼为主角的小说。其中的名作《温迪之沙》是一部真实生动的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澳洲内陆的大量情况:去附近农场主家参加舞会须得开车,一众车辆开上一条沙土路时,女士乘坐的车要停下来等五分钟,让别的车开远,以免扬起的尘土毁了她们的连衣裙。只有曾身临其境、参与其中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场景。(阿普费尔德调研之“彻底”是众所周知的。一九二九年,一个名为斯诺伊·罗尔斯的畜牧工偶然听到阿普费尔德与他人讨论《温迪之沙》的写作计划,他模仿计划里的尸体处理技术实施了三起谋杀。此案的审判轰动一时。罗尔斯的失误是没能将一位受害者的戒指彻底熔化,仍能看出从前修理时留下的独特的焊接印记。阿普费尔德曾应法院传唤出庭作证。)阿普费尔德显然把塑造一位土著版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看作种族观念进步的标志,但邦尼系列作品对种族的思考(略举一例:书中常常提及“混血儿”邦尼陷于土著血统的返祖遗传和白人祖先的文明本能的交战之中)不只是引人反感,而是到了令人反胃的边缘。克里斯蒂偶尔也会流露出反映她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典型态度和偏见,但她似乎对性别和种族都无甚兴趣,不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多费心思。这是她的作品留在自己的跑道上、没有出界的原因之一。



不在场——即不被言说,甚至不在不被言说之列——对克里斯蒂来说极为重要。她的自传性写作殊乏内省,你会对她心理空白的性质深感诧异,你以为她在心中自我对答,却发现那里空无一物,唯有静默。她记录与第二任丈夫、考古学家马克斯·麦洛温共同生活的回忆录《告诉我,你怎样生活》堪称史上披露信息最少的自传性著作,与她的《自传》不相上下,后者至少还记载了些许童年往事的细节。克里斯蒂生平最著名的事迹是她曾离家出走并失踪了几天,最后发现她用化名住在哈罗盖特镇的旅馆里,像一例典型的失忆症,正与她的心理模式相符。或许她的整个存在,她的内心生活,都是某种空白、某种失忆。
她对个性、人格、复杂心理学(而非类型心理学)均兴趣缺缺,取而代之的是对形式的兴趣。英年早逝的作曲家迈克尔·弗里德曼【迈·弗里德曼(1975—2017),美国著名作曲家与作词人】身后留下一系列专栏话题,其中之一便是“我认为《罗杰疑案》的确是一部出色的现代主义小说”。鉴于克里斯蒂的技巧在多个方面全无实验性可言,此处“现代主义”一词的具体所指或可商榷,但若将其替换为“形式主义”,则不会再有争议。克里斯蒂的写作生涯可以归结为对形式手法和叙事结构的系统性探索,她探索的体裁有严格界定的规则和明确的角色清单:必须发生谋杀,必须由侦探破案,配备凶手、受害者、一组皆有嫌疑而又终将洗脱嫌疑的角色,提供几种可能成立的杀人动机(其中大多数都在误导读者),所有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另外,场景必须是封闭的,嫌疑人名单是确定的,真实动机和关键证据必须披露给读者,但最好是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还有,小说必须在五万字左右,这并非此类体裁的通行法则,只是克里斯蒂心目中谋杀故事的理想长度。


克里斯蒂在这个逼仄的框架内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实验,很难想出还有什么点子她没试过——只差让波洛【克里斯蒂多部作品中的比利时裔侦探】到巫师学校探案了。她的作品总会在某个节点提及侦探小说体裁、舞台布景或戏剧角色来暗示自身的着意设计,如罗杰·亚克洛伊【克里斯蒂小说《罗杰疑案》中的受害者】被描述为“老式音乐喜剧里总在第一幕早早登场的那种满面红光、热衷运动的人”。《罗杰疑案》是克里斯蒂具有突破性的长篇小说,不仅可跻身她的最佳作品之列,无疑也是侦探小说中的精品。这个故事里叙述者扮演凶手的角色,堪称类型文学或通俗小说中最大胆也最成功的形式实验之一。另一部几乎同样出色的作品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其中的谋杀并非由一个嫌疑人独自实施,而是由所有嫌疑人共同谋划。这也是个激进的实验,因为所有人物要协同作案,关键是如何防止侦探把证据拼成完整的画面。证据要刻意设计得自相矛盾且不能自圆其说:就像用点彩手法绘制肖像,要令那些斑斑点点无法组成一幅画。
有的小说,侦探其实是凶手。有的小说,整个故事架构来源于突然浮现在克里斯蒂脑海里的标题:“他们为何不问埃文斯?”有的小说,受害者按字母表顺序被逐个杀害。有的小说,所有人物都被杀死,最后才发现其中一位是凶手。(克里斯蒂称《无人生还》一书为“技术秀场”,难得透露出一丝她对自身技巧的真实想法。书中强烈的幽闭、恶意和阴暗氛围着实令人恐惧。这也是唯一一部我曾读过三次,而每次书名都不同的作品。【《无人生还》1939年发行时书名为《十个小黑人》,后来改为《十个小印第安人》】)有的小说,关键证人在案子被破以及凶手被定罪正法很久之后突然现身,带来凶手无辜的证据,导致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嫌疑,谜底依然未解。(《无妄之灾》是另一本心理氛围格外压抑的长篇小说。)有的小说,情节完全根据桥牌游戏设计,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打牌细节,甚至分析了积分表,而关键证据就藏在一位玩家某一手牌的打法之中。有的小说,谋杀是从火车车窗里瞥见的。有的小说,谋杀发生在一架小飞机上,文中还附上了座位表。有的小说,谋杀的时间地点预先刊登在报纸广告栏中。
克里斯蒂的作品背后是她对形式主义有意识的迷恋,这可以解答有关她的作品的一大谜题:史上最受欢迎的侦探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为何是公认最糟糕的侦探?这里“最糟糕”的意思是这个人物最不讨人喜欢、最脱离现实、最招人厌烦、最虚荣,他的个性塑造最依赖那些无助于体现其心理洞察力的鸡毛蒜皮——一言以蔽之,即大侦探波洛。侦探形象大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十有八九——都是招人厌烦又脱离现实的,但无人比波洛更甚。克里斯蒂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自问道:“有人会去‘请教’他吗?”她自答道:“我可不想。”她还曾说:“也许局外人比这个人物的创造者更喜爱他。”她告诫刚开始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创造核心人物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他可能会伴随你很久很久!”在同一篇文章中,克里斯蒂还明确指出她的读者早已看清的一点:用作家自己的话说,马普尔“这个老小姐住在小村庄里,爱打听家长里短,不管事情与己有无关系,都要往里掺和,多年来深谙人性,据此经验进行推理”,她的形象比克里斯蒂笔下另外几位大侦探都要现实可信。尽管如此,马普尔系列只有十二部长篇和二十个短篇;对比一下,波洛系列有三十三部长篇、五十一个短篇和一部戏剧。塑造得最不可信的侦探却在数量的扩展上最为成功。可见对于克里斯蒂的小说设计刻意、套路固定的属性,读者能够理解并产生共鸣;波洛作为一种形式主义工具也得到了理解和接受,甚至深受喜爱,他的存在对读者的提醒几乎是布莱希特式的:你们受邀加入了作者刻意布下的局。他之所以成为最受欢迎的侦探,恰恰正是因为他最脱离现实。


克里斯蒂的形式主义是她所处时代的产物,她的实践多多少少与现代主义同步并有共同的兴趣,只不过她的作品面向普罗大众。她的主题、场景、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也完美地反映了它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波洛的形象确实滑稽可笑。不过,我们不妨看看他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初次登场的时间点。《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一战期间而出版于一九二○年,当时比利时难民充斥新闻,却往往不甚受欢迎,由此背景来看,波洛这个比利时难民是与时事相关的人物。克里斯蒂小说的常见要素都已就位:一座乡间别墅;一份有限长的嫌疑人名单;一个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地方,先是被犯罪扰乱,又被侦探这个外来者闯入。克里斯蒂书中的世界犹如一幅世人的心理图景:有序的家庭象征着整个社会,即人人共享的意义宇宙,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经过编码的价值观和社会角色——可就在此时,闯入了一位凶犯,一位试图破案的侦探。由此揭开的真相便是:有些事物的深意与我们所想的不同;有些人的内在与他们的表象不同;有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与人们口中所说的不同。
克里斯蒂笔下的罪案大多是谋杀,这一点也很重要。若你有些日子没读柯南·道尔了,或是你对他作品的记忆完全来自无数竞争激烈的影视版本,你很可能会认为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典型的现代侦探人物,抓捕对象主要是杀人凶手。大谬不然。福尔摩斯解决的案件除了抓捕凶手外,还包括盗窃、造假、冒名顶替和种种鸡零狗碎。就连柯南·道尔最出色也最出名的作品《巴斯克维尔猎犬》也只是“近似谋杀”,书中的主要受害人是吓死的,并未被直接动手杀死。休·格林【休·格林(1910—1987),英国电视制作人、记者,曾任英国广播公司总裁】选编的侦探故事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对手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小偷小摸和狡猾罪徒的世界,书中的氛围与现代侦探体裁相去甚远,更接近达蒙·鲁尼恩【达·鲁尼恩(1880—1946),美国新闻记者、短篇小说作家】笔下那些机智小人物的故事:几乎没有人被杀害,而叙事视角也绝非始终站在法律与秩序一边。作者津津乐道于偷奸耍滑、鬼鬼祟祟、投机取巧钻空子等,对此大肆渲染;叙事基调是现实的,且故事往往以城市为背景。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侦探小说的整体基调发生了改变,克里斯蒂的风格就是这种变化的具体体现:谋杀发生在大别墅里,受害者横尸于地毯上……人们需要借探案和破案重新确立秩序。侦探小说迷有时称这类作品为“舒心侦探小说”,这一描述既有合理之处,也不无偏颇,毕竟,这种封闭的社交环境确实能给人的想象带来舒适感,但别忘了,那也是发生谋杀的地方。


若非如此,克里斯蒂的作品就会失去已有的优点。不可否认,克里斯蒂的小说是令人舒心的:场景是熟悉的,世界是封闭而有序的,侦探每次都是能成功破案、捉到真凶的;但除此以外,她的作品还有一股令人清醒甚至凛然的寒意。塞耶斯对上述问题的伦理认知较克里斯蒂更为复杂。在她最好的作品《俗丽之夜》中恶意与邪恶无处不在,却没有谋杀。谋杀类小说中总有凶手被捉拿归案,而之后的明正典刑则大多发生在叙事框架之外。塞耶斯对侦探小说耽于探案而不表处决之事颇感兴味。谋杀案告破的现实后果不在此种体裁的套路之内。个中原因不难想见:处决罪犯本身就是个复杂、紧张、自带激烈氛围的主题。从体裁角度来看,避而不谈是最好的方案,侦探小说确实十有八九都避开了这个问题。塞耶斯是个例外,她在温西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巴士司机的蜜月》中饶有兴致地探讨了这一点。新婚的彼得勋爵在赫特福德郡的乡村侦破了一起谋杀案,而在处决犯人的那天夜里,他受疑虑困扰,彻夜难眠,哈莉雅特不知他是否会向自己寻求安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爱情也难逃厄运……这是对侦破谋杀案引发的现实伦理问题的沉郁思考,意味深长,却很难在侦探小说中奏效。克里斯蒂从不犯此类错误,对犯此类错误也毫无兴趣。她对世界的认知是行恶事者终尝恶果,而她从中提取了份量恰到好处的真相,足以赋予她的小说现实感,又绝不至于令读者不安或扰乱体裁框架。倘若她不曾转行,一定会成为出色的药剂师。精准测定剂量是药剂师必备的基本功夫。
克里斯蒂对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运用也体现了这种将比例和份量掌握得恰到好处的功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不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之列,但二十世纪是她书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她在这个世纪的头一年刚满十岁,处于有利位置,可以观察到在接下来五十五年写作生涯中礼仪、风俗和生活方式将发生的诸多变化。从她作品中的建筑变化也可窥一斑:《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于一九二〇年问世,里头那座“美丽的古老邸宅”有两厢、一道长廊,还有单独的仆人住所;一九三四年的作品中则出现了“上乘的现代平房”;一九三九年,她书中的百万富翁建起了“奢华的现代别墅”;一九四二年,故事里的小屋则是“各种现代设施应有尽有,都藏在半木质、仿都铎风的丑陋外壳里”;到了一九六一年,读者身处的世界已然是拥有咖啡机、“冰箱、高压锅和噪音不断的吸尘器”的租赁公寓了,在这里“年轻姑娘们看起来脏兮兮的(如今的姑娘们在我看来总是脏兮兮的)”。此类社会经济变迁并非克里斯蒂直接描写的对象,但她总能准确地观察和记录,就像她笔下的马普尔小姐一样,很少会遗漏什么。


克里斯蒂的作品分三个层级,她的几部杰作位于顶端,中规中矩的侦探类型作品属于中等,最下层则是粗制滥造的速成品。失败的作品往往涉及政治阴谋,如《褐衣男子》《他们来到巴格达》《天涯过客》。描写夫妻冒险家打击犯罪的汤米和塔彭丝系列对我而言难以下咽,但想必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持不同意见。克里斯蒂的大多数作品都属于中等水准。公认的佳作有《罗杰疑案》《无人生还》和《东方快车谋杀案》,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可能还想加上《美索不达米亚奇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命案目睹记》,或许还有后期那部集其作品大成的奇特长篇小说《伯特伦旅馆之谜》。而最后要提及的是她的另一部杰作《谋杀启事》:这部作品将她对社会变迁的敏感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从中或可找到她的创作魅力为何深远而长久的终极线索。
这部出版于一九五〇年的小说以绝妙的一幕开场:奇平-克莱格霍恩的本地报纸上登出一则广告:“一桩谋杀将于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晚六点三十分在‘小帕多克斯屋’发生,望周知。诸友务必应邀前来,恕不另行通知。”书中人物按时登场,有趣的是,其中有几位的身份是通过各自爱读的晨报揭晓的:新近退休的伊斯特布鲁克上校订阅《泰晤士报》;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埃德蒙·斯韦特纳姆读《工人日报》。典型的克里斯蒂式大跨度人物群像:从牢骚满腹的上校、“小帕多克斯屋”的女主人利蒂希亚·布莱克洛克,到典型的战后女性伴侣欣奇克里夫小姐与穆加特罗伊德小姐【这两人很可能是一对女同性恋伴侣】;从难民女仆米琪、温泉饭店的瑞士籍前台鲁迪和他做服务员的女友莫娜,到布莱克洛克小姐的老朋友多拉。布莱克洛克小姐和多拉小时候一起上过学,当年多拉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有点傻傻的”。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书中对这些年多拉是如何度过的语焉不详,对上校在印度作何营生也同样未作交代,事实上,每一个人物是否表里如一都可存疑。即使布莱克洛克小姐自身的出场介绍也有种微妙的错位感和怪异感:“布莱克洛克小姐是宅邸的主人,六十开外,此刻正坐在餐桌主位。她身着乡村风格的粗花呢套装,戴着一串由硕大的假珍珠串成的贴颈短项链,和衣服搭配起来略显突兀。”为何要在早餐时戴珍珠——假珍珠呢?为何要在此处设置这个令人略起疑心的切分音呢?
这正是战后英国错位、混乱的社会的写照:生活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在地理和社会空间里四处迁徙,社会角色也比从前更复杂。“小帕多克斯屋”是一个封闭而舒心的谋杀场景,但《谋杀启事》却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反映了社会是怎样变化的,战后英国是怎样一个不同于以往、变动更频繁剧烈的国家。谋杀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有些人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但我们究竟以为他们是哪样的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或不是他们看起来的那样?书中人物又从何得知呢?侦探小说的本质就是一道谜题:一群人物中究竟哪个人并非自己所说的那样?以我愚见,这是克里斯蒂能够吸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众多读者的关键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这是根本原因。尽管克里斯蒂的创作属于形式主义而非现代主义,她对身份的思索却是现代主义的,触及性格与社会的建构本质,并通过刻意设计以吸引大众且易读的介质表达出来。她的作品像一杯鸡尾酒,混合了有序的场景与深藏的恶意、阅读的舒适与清醒的凛然,而它的核心是现代性反复求索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是谁?

约翰·兰切斯特(John Lanchester,1962—),英国新闻记者、评论员、作家,曾担任《伦敦书评》副主编。评论文章常见于《纽约客》《纽约书评》《格兰塔》《卫报》《每日电讯》等英美报刊。目前已出版6部长篇小说和3部非虚构作品,获得过诸多英国文学奖项。《阿加莎·克里斯蒂现象谈》(The Case of Agatha Christie)刊载于2018年12月下半月的《伦敦书评》。该文聚焦于虚构犯罪叙事的一大体裁:侦探小说。兰切斯特以资深“粉丝”兼批评者的身份探讨了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何会被奉为“侦探女王”,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英国作家之一。作者指出,克里斯蒂将侦探小说的形式探索到极致,放弃了对语言水准、人物塑造、思想关怀的追求,不去过多地介入重大的社会思潮,使自己的作品永远处于读者的阅读舒适区,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侦探小说领域的王者地位,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文学成就。兰切斯特最后还是承认克里斯蒂的作品里有一点与快速流动的现代生活紧密相关,即诉诸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你是谁?真实身份是什么?如何才能认识你?阅读兰切斯特对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创作的分析,我们或许能在鉴别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类型小说与“文艺小说”(literary fiction)方面找到一点启示。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4期,责任编辑:叶丽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