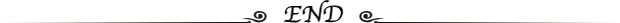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读者来稿 | 谭茜禧:在科幻的迷梦中,原初之情何去何从?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在这些科幻小说家们的笔下,科技的发展终究会一点一点侵蚀人自己的生存领域。如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便是融合;可是若任由其发展,机器、科技是没有温度的,那么造成的后果,到底是人发展了科技,还是科技框住了人类呢?这便是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了。时光在不断地流逝,科学技术的的水平也在不断地发展提高。诚然,科技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给予人们更加便捷的生活,但在沉浸于科技带来的便利之时,人们是否会忘记最原始最本真的美好情感呢?在读罢这三篇科幻小说《总裁太空人》《我们不是人类吗?》和《转调》(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1期)后,我思考起了这样的问题。虽然这三篇科幻小说分别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但其三篇都有共通之处。与一般描写幻想中的未来世界、述说未来世界科技的科幻小说不同,这三篇或多或少地在引导人们思考关于人的本身,人的原初的情感的问题。第一篇是托马斯·皮尔斯的《总裁太空人》。虽为科幻,但其着重描写之处却是主人公杜姆在启程去往外星球之前所遇见的人和事,去往太空又被遣返的过程只用了寥寥几笔,占全文很短的篇幅。杜姆在告别会上遇见了他人的不解,与前妻诺娜的幽会甚至使得他有放弃太空移民的冲动,虽然他马上就反应过来是不可能的。他想要前往家中与父母道别,结果父母先他一步不告而别,只是将能表明他在家中生活过的痕迹的物什放在家门口。在启程的前一晚住在杰罗姆家中,杰罗姆的妻子雷切尔却只是想找他要钱,再三确认他真的没有钱了之后气呼呼地抢走了他最后的现金。在爱情上失意,被亲情抛弃,剩下的人只是盯着他的钱,或唏嘘于他全部捐献给了教会的钱财。但是鲜少有人关注他本身。他爱着前妻,前妻却另有新欢;他思念父母,父母却在得知不可能挽回他的想法之后离开;他到了最后对雷切尔稍有改观,雷切尔却只想着要他的钱。他捐赠出了所有的钱财想要去往另一个星球重新开始,最后却被遣返回到地球。到头来,他什么都不剩,只有白发苍苍的诺娜收到通知,拄着拐杖来把他接走。他的经历就像最悲惨的戏剧一般,他失去了所有。但他却也是幸运的。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太空沉睡后,他回来仍然是年轻的。虽然不复当年总裁的风光,但他还有时间和机会。就像结局所说的:“光秃秃的头,油腻没有胡须的脸,眼睛肿胀,仿佛才第一次见到亮光——一个难看的婴儿。”婴儿是新的生命,而此刻的杜姆虽然一无所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获得了新生。第二篇是托·科·博伊尔的《我们不是人类吗?》。在一个绝大多数生物都是由基因编辑的年代,罗伊和邻居艾莉森有了私情,艾莉森自然受孕怀上孩子,女孩得知后却十分震惊。在那样的时代,每一个人的数据都是在出生前都被决定好了的,就像游戏中给角色捏脸一样可以决定孩子的外观,像分配技能点那样决定孩子的才能。路过的女孩就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孩子:智商有一百六十二,眼睛是自然界不存在的泛着虹彩的紫罗兰色。罗伊和妻子康妮的孩子也是经过了基因选择而怀上的,父母为孩子挑选了好的、所喜爱的基因。这样的孩子因其基因决定大概率会是某些方面的奇才,不过弊端则在于孩子本身,如此经过基因编辑下来的孩子,擅长的事物都是被固定好了的,失去了探索自己的可能性,孩子将会囿于基因编辑技术带给他们的牢笼。对于家长而言,孩子对于他们只不过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基因编辑的产物,孩子未来的发展已然握在了他们手中——父母双方所挑中的基因编辑的手中。对于新生命的到来,那一份本应有的期待的感觉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像看电影被剧透了一样的索然无味。在基因编辑的世界中,正常受孕的孩子显得十分难能可贵。虽然有风险,但有更多人或为了猎奇或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如果这一项技术真的发展下去,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是有钱的人能拥有更好的基因编辑而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还是技术的失误带来的毁灭?谁也不知道。人为干涉的基因,看上去是更加地实用了,但缺少的未知,对于可能性的期待,已经大大减少了。第三篇是理查德·鲍尔斯的《转调》,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老音乐家觉得现在已经没有真正伟大的音乐,年轻的孙子制作音乐却总是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女记者在战地采访却发现聒噪难听的音乐成为了士兵们战斗的武器。在电子音乐横行的年代,一种叫“耳虫”的病毒悄然出现,控制了所有的播放器,甚至人脑。人们的大脑被这一段旋律折磨,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一段音乐也会自动在全球的每一个播放器播放出来。“病毒”这个词汇,对于人们来说,是可恶的,是罪恶的。可是在这篇文章的高潮之处,每个人听到这一段音乐过后,却没有人表现出厌恶的情绪。对于人们来说,这一段没有任何修饰、不浮华不浮躁的音乐,反而比熙熙攘攘的电子音乐更加深入人心。音乐被创作出来,是为了给人们以真挚的情感。像文中所说的,“那是梦幻般委曲婉转的唱和,那种移民保姆为哄你发笑而哼唱的曲子,仿佛一根唱针不经意间落在崭新的 《佩柏军士》的唱片上,那是对大漠里的铸告者发出的召唤,是古老的福布尔东,是你高中所在的车库乐队渴望创作出的录音曲,是听起来异常美妙、之后却难以辨识的电台音乐的最后四小节,是高地寺院里的钟声,是傍晚的齐唱,是你和着祖母的自动钢琴奋力挤出的调门,是星球另一侧传来的、杂音阵阵的短波版《生日快乐》,是你的第一首慢舞曲,是你踏上意识之旅那一刻响起的圣歌,深沉而激荡,像谜一样,悸动着无限可能,又像耀眼的只言片语,将所有听者带入无限的永恒”。音乐本该如此美妙,应当蕴含了创作者本身的情感,创作者想要表达的那一份或欢乐或悲伤的情感。通过不同的音符所组成的旋律,本该传达出来的是最为纯朴的事物。而在文中的世界里,音乐是武器,是使人们获得胜利的事物,不再单单给人们带来美好。因此这所谓的“耳虫”病毒拥有着的美妙旋律自然使人们获得了美的享受。不受到任何的功利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是单纯一段美好的旋律,使人如沐春风。纵观这三篇科幻小说,虽然所讲的的确是不同的故事,但是究其根本,都是在探讨一个问题,关于人类本身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的问题。科技的发展当然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科技继续发展下去,却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恐惧。在科幻小说家的想象世界中,可以进行太空航行,可以进行基因编辑,更是可以编辑电子乐,病毒可以进入人类的大脑,控制人们的神经。但是在太空航行之前,杜姆所拥有的只是淡薄的人际关系,就连父母也将他的东西丢出门外;基因编辑出现的并不全是好东西,有失控的狗猫,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失去了一份牵绊;音乐不再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的方式,而是功利性的——或者,攻击性的。在科幻小说中,关于未来的想象当然远远不止这三种。但是关于人类本身情感的讨论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人最本真的情感是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忽视了人文关怀?这三篇小说给出的答案虽然不能说十分消极,但是至少是不那么乐观的。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正是因为人有着独特的情感:友情,爱情,亲情……或愉悦,或悲伤,或平静……各种各样的情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证明。如果没有情感,那么社会便没有温度。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失去了“人情味”。没有人情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目前并不知道。但是在这些科幻小说家们的笔下,科技的发展终究会一点一点侵蚀人自己的生存领域。如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便是融合;可是若任由其发展,机器、科技是没有温度的,那么造成的后果,到底是人发展了科技,还是科技框住了人类呢?这便是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了。科幻小说是对未来的幻想,但是科幻不是玄幻,未必不能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可以表达对未来的美好畅想,也能像这三篇小说一样表达出淡淡的悲观的情绪。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最重要的,都是身为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作为一个人可以去探寻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保持最本真、最简单的情感,而非将自己置于科技的牢笼之中,反而失去了人本应拥有的珍贵的宝物——最原初的本我。谭茜禧,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生。有较为丰富的文学阅读经验,热爱小说阅读。
编辑:言叶
配图:言叶
版式:宥平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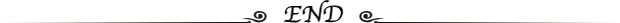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