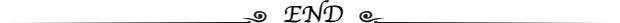散文品读 | 伊利亚•科切尔金【俄罗斯】:绿眼睛的、智慧的莫斯科环抱着这里的一切……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伊利亚·科切尔金作 郑晓婷译
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应该在一起。我父母和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不光是“认为”,而是从未怀疑过这一点——这有什么好想的呢。如果真的如此幸运,一般人是不会拒绝这份幸福的,除非,还期待着更大的幸福。
我们一起成长。七岁前我都住在她东南方向的郊区。早些时候,透过我们家的窗户能望见土豆田,但是,城郊分界线逐年远移,很快就难以辨认了——高楼挡住了视线。幸而我的大森林和那条通向森林的大道穿越其间的田地还在,但不久之后田地消失了,森林也变得不像森林。渐渐地,不远处覆盖着云杉和白桦的郊区也不见了,那里以前总长着很多蘑菇。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让人不舒服的大环外【莫斯科环城公路以外的地方,远离莫斯科市中心】。
后来我家搬走了,我进入市中心的一所小学就读,那里有保证幸福童年的一切条件。克里姆林宫对面是安静的、有些许外省特点的莫斯科河南岸区,聚集有大量垃圾堆和无数门洞,还有红色和绿色屋顶的二三层小楼,放学后,我们常常从一个屋顶翻到另一个屋顶,研究布满灰尘但无比安适的旧阁楼,就这样,我们从一条街道“游览”到另外一条街道。当时我们觉得自己就是没有螺旋桨的卡尔松【卡尔松,住在房顶,背上有螺旋桨。形象源自瑞典女作家阿斯特里特·林格伦的儿童文学作品《小男孩和住在屋顶的卡尔松》(1955),苏联时期该作品被翻拍成动画片】,不怕高,在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屋顶上打滚,幻想更多的惊险情节。
秋天,我们去采破土而出的香菇,摘苹果和山楂;春天,在鱼产卵的时候,我们用网在脏臭的小河里捕鱼,然后把鱼片风干,带到课堂上嚼。那时候,吸一口莫斯科的空气,就能闻到河面上飘来的“红色十月”巧克力厂的浓香。工厂院落里常常挤满了孩子。
城市就是城市,我们循规蹈矩地生活着。我长大了一些,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征服这座城市,仿佛这城市就是我的。只有别人的、陌生的东西才能激起征服和占有欲。比方说,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土地上,在乌拉尔山脉后面,肯定埋藏着什么好东西,我能感觉到。


驻足在辽阔大地上,望着前方的拉尔维尼瓦亚姆【拉尔维尼瓦亚姆河,位于俄罗斯勘察加边疆区的西北,注入奎维瓦亚姆河,最终流入鄂霍茨克海】大河谷和后面的空旷地带,你会长舒一口气,感觉自己年轻、健康、强壮,甚至无所不能,欢欣地盘算起回到莫斯科之后要做什么,甚至会由于激动而精神抖擞。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那儿,站起身来,仰起头。对,就是站着、望着、思考着——我在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了!真叫人不敢相信。我对自己说:‘就算现在快死了,我也一定要留在这儿。’”在品仁纳湾,安德留沙一边用地质勘探锤敲打岩石样本,一边这样对我说。
不知是距离的缘故,还是被灌输了太多这样的思想,回到莫斯科之后,我就进入国立莫斯科大学学习,走进那座备受瞩目的主楼,仰起头,站着,望着,努力追溯在勘察加时的心境。我只在大学待了一年,没什么长进。随后去了贝加尔湖,当了一名消防员。
谁都知道,贝加尔湖特别美。正如大家所说,贝加尔湖是西伯利亚的明珠。我读了多少关于它的书啊,早已做好去征服它的准备!沿岸的村镇我几乎都能叫上名来,对那里的历史和动植物知识也了解颇多。
贝加尔湖要比鄂霍茨克海或太平洋离莫斯科近多了。即使当你皮肤被晒得黝黑,在汽艇的铁皮甲板上懒洋洋地打滚,或者从世界上最清澈、最寒冷的水里跃出,体内血液的流动比任何普通人活跃九倍的时候,你还是会心甘情愿地被这个星光闪耀的贝加尔女郎所俘获,她的魅力在五千里以外的远处更能凸显出来。
九十年代的莫斯科我还是很喜欢的——苏联时期未曾见过的绚烂装扮和广告涌现在这座城市。当时的莫斯科饥饿、疯狂而又紧张。没错,我的确喜欢这样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仿佛都能无忧无虑、随遇而安地生活,在狭小的赫鲁晓夫公寓厨房里安心地做针线活。如果不是因为莫斯科的自私和顽固不化的傲慢,我会继续爱她并和她一起生活。说实话,一切都让我感到疲惫。


一九九三年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愈加冷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站在阳台上抽烟,在这座城市之间,听到从白宫【指俄联邦政府大楼】门口传来的机枪扫射和坦克炮轰声【指的是“炮打白宫”事件,又称“十月事件”,1993年10月叶利钦下令军队包围俄罗斯杜马所在的议会大楼,随后进行了炮轰,以武力强行解散杜马】。这是怎样一种傲慢,傲慢!
要建首都,要建你们的人造华盛顿,可以去楚赫纳沼泽或荒无人烟的奥伦堡草原啊,你们先搞清楚状况好吗,不要用射击、政府军和其他手段破坏这座充满生命力的城市。假如失去首都地位,有谁会知道莫斯科呢,她也就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了。
过了几年,我们再次分别。阿尔泰山距莫斯科三千多公里,这让我开始想念她,但我不想再回到那混乱关系中。她有她的生活,我过我的日子。在太阳落下的那个方向,她是一颗闪耀的明星。我甚至对于每时每刻和她同呼吸的那群人也不再嫉妒。没有我,她还是好好的,没有任何不幸发生。
当然,莫斯科就像一块磁铁,永不休止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而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美好新世界,我热爱的地方、我的习惯、我的众多朋友,还有我的工作和生活理想,统统都在那里,我还曾在那里放牧牛羊。就这样,我建立了一个可以与莫斯科抗衡的理想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我征服、体验、建造了又一个亲切的、永远吸引我的地方。
我为此感到骄傲,觉得自己心境平和,终于找到了归宿。可后来,我突然离开理想之地,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一待就是整整十年。其实我一心想要回去,回到那些我倍感亲近的地方。
这样很蠢,我甚至羞于承认。
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指望的。
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现在似乎已经妥协。我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她太远,便在三百公里之外定居下来,最终在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子。
三百公里——五六个小时的车程。整整半天时间我会待在莫斯科,然后剩下的半天——我就在自己的小房子里生炉子,房子位于梁赞农村一条空无人烟的街道尽头。触手可及。


当然,在拉尔维尼瓦亚姆河谷感受到的激动不安不复存在——早已不是那个年纪了,但我还是需要去乡下躲一躲,越来越频繁地朝夏日里太阳落下去的那扇门望去。
终于,连征服和占有的想法都没有了,仅仅按照旧习惯生活下去,不是吗?莫斯科也完全变了模样——她发福了,由于一点小事就暴躁不安,为自己的安危忧心忡忡,好像迫切想要得到什么。无论如何,在最近的二十五年里,很多年轻人、有趣的人都离开——去了西方更舒适、更简单的城市。莫斯科城里有很多要价不菲的美容师和整形外科医生,但是拥堵的交通、恶劣的生态环境没有丝毫改变,最主要的——那些头脑中的狂妄自大和不合时宜的激情让一切辛苦付之东流。
总而言之,你刚积蓄起一点力量,风就从那个方向吹来——为保持同样的速度,你须得鼓起鼻翼驾车行驶一段时间,于是你就开始厌恶自己,并感到莫名的疲惫,在回来的路上不停地咒骂“这该死的莫斯科”,因为升起的太阳又刺痛了眼睛。
也许,这已经融入到血液和记忆基因里了。我的祖辈来自不同的角落,他们远离自己的土地,朝着某个地方赶啊赶,寻找理想栖身之地的愿望一直吸引着他们。
那些追求浪漫、神经脆弱但富有想象力的人在读了各种各样翔实的《旅行者手记》和其他旅行笔记之后,开始走向东方。《从莫斯科到喀山【俄罗斯城市,鞑靼自治共和国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经叶卡捷琳堡【俄罗斯城市,地处乌拉尔山脉东麓】、秋明【俄罗斯城市,位于乌拉尔以东、西西伯利亚的中北部】、巴尔瑙尔【俄罗斯城市,阿尔泰边疆区首府,位于西西伯利亚南部】,穿过高山、沿着卡通河【位于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鄂毕河支流】……》,这是我前往阿尔泰山时用作参考的准确指南,在那里我度过了最好的几个年头,按照诗人让·拉罗沙【让·拉罗沙,(1930—2010),原名让·菲拉,法国作曲家、诗人】的说法,我找到了“黎明屋檐下的家,迎着我少年时期的风”。确实如旅行指南中所说,花上四十天(算上休息时间),你就能到达那里,一个被赐福的国度,那是自古以来农民的梦想——七十个岛屿组成的白水国【17—19世纪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自由国】,那里的人们幸福地生活着。他们不同于俄罗斯人,抢劫和盗窃从未有过,也没同谁发生过战争。那里草木葱茏,遍地栽种着葡萄、索罗钦斯基黍米【即稻米,彼得一世时期,稻米刚传入俄国时的一种叫法】和甜菜。正因为如此,他们来到了这里。


该怎样慢慢适应这一切呢?祖母讲了她的故事:
“当时给我分了一间‘大红门’【俄罗斯第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凯旋门,彼得一世时期为纪念1709年俄瑞北方战争胜利而建】附近的屋子,我去那儿时只随身带了一个小箱子。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柴禾,什么都没有。爹过来了,四下看过后,竟给我做了一个餐柜。他是一个手多巧的木工啊!在外头看到被扔掉的木板——他一块一块地捡回来,就是用这些木板给我做了个小餐柜。这是我第一件像样的家具,那时候我可真高兴啊!”
这个餐柜(被我修理过,已经刷了十遍漆)立在我乡下的房子里,凹凸起伏的气泡玻璃闪闪发光。有时候在半夜,橱柜的门会因为内部压力而自动打开。
“过了两年娜斯佳从乡下来看我,”祖母继续说道,“我打开门,当时身上穿的是一件大花长袍,娜斯佳激动地大叫起来。吃饭时我还开了一瓶甜露酒……”
为了准确地记录历史,还有必要讲一讲我的一位长辈。二十世纪初期,他害怕被这个残酷时代的金属履带碾压,出人意料地突然离开了阿斯特拉罕,去了北美洲,从此杳无音信。这位长辈开了一个先河,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在我们的家族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神经元联系。大约又过了三代人,我的哥哥巩固了这一联系,在地球的另一边,他颇为成功地抚育着自己的三个孩子,然而,这一切对我没产生什么影响。我想要的——无非是莫斯科,或者乡下的小木屋,最好能把这两样东西结合到一起。
有一天,一位心理师在听了我这些混乱的叙述后,提议给我做一个测试。
“把你的手放到桌子上,胳膊肘伸直。”他指挥着,“好,现在我的两只手会握住你的手,你要尽全力弯曲你的胳膊。目标是——碰到自己的肩膀。”
我警觉起来:“他想考验我的力气。”
我猛地一抬胳膊,他也攥得紧紧的。一开始还可以不费劲地抬起一半,接着就怎么都动不了了。
“快,抬起来!”他喊道。
而我的胳膊抖个不停,却无法移动。我咬紧牙关,脸也憋得通红,但再也抬不动胳膊了。
“看,我根本就没怎么用力。”心理医生一边说,一边用他的两根手指抵住我的手。
“一开始你的力气很大,抬到一半的时候,你的胳膊只是在徒劳无功地来回晃动。是你自己把自己绊住了——你往一个方向施加多少力,从另一个方向就有这么多力制约你。还想用左手试试吗?”
“现在我明白里面的诀窍了,这次你不会再赢我了。”我答道。
然而,左手也重复了刚才的结果。不要再骗自己了。


我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地摇摆——时而回到莫斯科,时而又离开莫斯科。买摩托、建澡堂、送儿子去莫斯科最好的学校。早上头脑清醒地选择一样东西,晚上又疲惫地换成了另一样。
只消往太阳升起的那个地方看一眼,那儿更纯净,更明亮,周围的世界在声音和感觉中显得真实而丰富,山杨树在风中的呼啸声不同于松树的;那儿有你种的土豆和苹果,你可以观察它们如何昼夜不停地生长;春天和秋天,大雁排成一排在天空中鸣叫;那儿的田间小路无限延伸到远方,相约在日思夜想的白水国聚首,那儿的熊和鹿也与人亲近友好。这个时候,快乐和力量会不知不觉地流遍全身,好像从身后为你点亮万盏灯。
转过身来,你会看到无数科学文化殿堂氤氲在温热、浓重的空气中;那里的书和奶酪都很好;教堂顶端,是一团团火一样燃烧着的黄色和天蓝色;在一条街道的这头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另一头则呈现出红色的轮廓;我的妻子应当会穿着高跟鞋;那里有流光溢彩的咖啡馆和神秘缥缈的指向标。在人们眼前,烟囱里升腾着春药一般的烟气,慵懒舒适地飘到半空,克里姆林宫塔楼上的五角星犹如燃烧着的降落指示灯,那里完全是一种现代化的节奏:高薪、安逸和灯火。绿眼睛的、智慧的莫斯科,还是有一点不真实,她就站在那儿,环抱着这里的一切,她微笑着。我觉得她是在冲我笑,她一直都在等我。怎么才能在这里扎下根来呢?


伊利亚·科切尔金(1970—),俄罗斯当代作家。生于莫斯科,曾在莫斯科化工学院、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后转入亚非国家学院学习东方语言。2003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同年凭借“阿尔泰小说系列”(《阿尔泰》《狼》)、中篇小说《中国人的帮手》获得莫斯科州政府文学艺术奖。代表作还有小说《说再见》《我是你的孙子》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1期,责任编辑:孔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