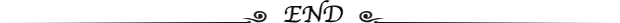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胡•爱•苏尼加【西班牙】:夜与欲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西班牙】胡安·爱德华多·苏尼加
童亚星译
“你这会儿要出门?大晚上的,别撞上什么倒霉事。”是父亲的声音,从屋子尽头传来,力道已经减弱了许多,与收音机的杂音还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混在一起。
她没有回答,心不在焉地想着别的事,凝神听着有什么奇怪的响动,听得并不真切。她朝窗户走近了一步,远处传来一个声音,是一个女人在院子里唱歌,歌声在这寒冷而危险重重的黄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歌词几不可辨,激情丰沛的音调却穿透了玻璃,偶尔停顿一下,但总会像拨个不停的电话一般再度响起。
天光暗淡下来,她凝神听着歌声,走出了家门。栋栋房屋上空,天际线的暗红渐渐隐去,换上蓝紫的色调,于是,街上的每个角落都笼罩在阴影之中,四下很快漆黑一片。
她觉得那首歌是为她这个恋爱中的女人而唱的。一个陌生女人为她而唱,笃信可以被她听到,可以为她注入坚定的勇气。


阿黛拉并不害怕,她在初降的夜幕中穿行,朝皇宫酒店走去,那里如今已经变成血淋淋的医院,从前却经常在下午茶时分举办舞会,提供茶点服务的餐桌围成一圈,一对对舞伴在舞池中伴着舒缓的音乐翩然而动,身体彼此厮磨。男人们留意着怀中女人婀娜的身姿,而那些尚未经历肌肤之亲的姑娘感觉到拥着她们的男人兴奋的下腹,无不羞色赧赧。最后一次去那儿的时候,阿黛拉打算不再拒绝邀请,被带去哪儿都行,她已经准备好经历早就渴望的一切。
渐浓的夜色总是不免流露出对爱的纵容,悄无声息地把每个潜在的动作都变成盲目而奋不顾身的冲动。阿黛拉穿过一条条路面高低不平的街道,把孤独的脚步声留在身后,嘴里默念着那位诗人的句子:“在夜里啊,每个爱人的歌声都已苏醒,我的灵魂也是其中一曲。”【本句和下文“当下……”一句均为尼采的诗句。】
有两次,阿黛拉都差点在坑坑洼洼的路面跌倒。尽管走得左腿撞右腿,她依然心怀憧憬,心想,自己穿成这样,要是在以前,怕是会被拦下,不可能穿过那金碧辉煌的厅堂或是进入舞池,现在倒是可以了。
走出普拉多大道时,阿黛拉定睛看着煤油灯的光线和几名工人的剪影。有两枚炸弹落在海神喷泉附近,工人们正在弹坑四周放置围板。阿黛拉看着这些有如鬼魅般干活的身影移来动去,不去理会自己路过时他们的起哄,而是望向酒店高耸的大楼,屋顶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浮现。激动人心又万分热烈的见面近在咫尺,她不得不用手捂住激动得怦怦直跳的心脏。她对自己念道:“当下,喷泉水声嘈杂,我的灵魂亦如此欢腾。”


可是大楼正面一丝灯光都没有,窗户黑漆漆的,一向把大门照得亮如白昼的路灯,也一盏都没有开。阿黛拉眼前一片黑暗,她摸到手感粗糙的麻布,明白过来,那是用于防御的沙袋。商店前,门廊下,地铁入口或是步道的喷泉边,到处都是这种沙袋。
成堆的沙袋当中,几块星星点点的光斑指引着入口。阿黛拉沿着一条倾斜的通道走进曾经如此熟悉的前厅,如今,这里只剩两个微弱的灯泡将将照着宽敞的空间,有几个人穿梭其中:都是穿着深色制服的男人,相互交谈着,消失在前厅的尽头。
曾几何时的奢侈华贵消失得了无痕迹,只剩层层堆叠的纸箱和沙袋,地毯早被抽走,当初舒心怡人的味道也被冷冷空气中的消毒水气味取代。
右手边,一名看守倚在柱子上打盹,阿黛拉向他打听安塞尔莫·萨韦德拉,得到的回答是此处不能通行,但阿黛拉言辞闪烁地声称自己是他的表妹,还提到什么伤员。最后,看守让她去二楼的贮藏室找找。
阿黛拉沿着中厅的楼梯向上,来到一条宽阔的走廊,灯光微弱,一扇扇房门在两侧一字排开。据她所知,这里的客房当初是全马德里最奢侈舒适的,大床,羽毛枕头,梳妆台上大大小小的镜子和各式香水瓶,还摆放着庄重的台灯。有一扇房门虚掩着,阿黛拉满怀好奇,大着胆子把手放上门闩,轻轻推了一下。她看到床上露出一个男人的头部,蓝色的毯子一直盖到他的下巴。男人闭着眼,呼吸吃力,头发贴在额头上,和胡须一样是金色的。床头柜上一盏小台灯发着光,照亮这个房间,旁边还有个杯子。
阿黛拉静静地站住,盯着那个男人看,随后又走近了一些,手指抚过他的面颊,男人没有动,他的脖子上缠着绷带。阿黛拉把毯子往下拉了几公分,看到男人的肩膀和胸部也全是绷带。她继续往下拉毯子,发现男人一丝不挂。她端赏着他的苍白,小腹上金色的毛发,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他的两腿之间。


阿黛拉哆嗦着把毯子盖回去,往后退去,又忍不住再次上前,有一股冲动想要碰碰对方一动不动的身体,想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瘦骨嶙峋的双腿上……她克制住了,离开了房间。在走廊上,阿黛拉寻找着贮藏室,最后,涂在墙上的指示告诉她到了。门是开着的,她看到男友弯着腰在一堆盒子前面忙着什么。
阿黛拉抓紧他的手,用气声说:“亲爱的。”她也不听男友回应什么,一门心思体味着他的亲吻,从嘴唇一路亲到没有戴围巾的脖子——“我是来爱你的。”
她凑得很近,一边说着话一边用嘴唇摩挲着男友长满胡茬的粗糙脸颊。男友避开了。他不能丢下工作,也没法休息或分神:氯仿所剩无几,绷带也快用光了,外科手术刀数量不足,而田园之家的前线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伤员。
“可我就是来找你的,为了让你亲亲我。”
“这会儿我顾不上你。明天我想办法跟你见面。你快走吧,我得去手术室了。”
去年,阿黛拉参加了美术中心的假面舞会,和朋友们一样喝了很多酒,好几个男人的胳膊都缠着她,抚摸她的后背,其中一个还低下头,吻了她的耳朵。阿黛拉打了个激灵,发现那人还咬了一下她的耳朵,用舌头把它舔湿。她慌了神,却没有逃开,也没有抗议。
阿黛拉一边下楼一边想起当时那一幕。到了前厅,她竖起大衣领子,整理头巾的时候搓了搓耳朵。到了街上,冷冰冰的空气扑面而来,她四下张望,看到酒店附近一个人都没有。前方有一辆像是被扔下了的救护车。
她朝圣安娜广场走去。天空像一顶黑色的穹伞,房子里一丝光线都没有,街道犹如无尽的围墙延伸下去,两侧的阳台几不可见。偶尔会有一辆汽车呼啸而去,或是听到行人匆匆而过的声音。远处传来防空警报。阿黛拉走到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旁边的时候,看到拉响警笛的摩托车朝阿托查火车站驶去,声音震耳欲聋。
阿黛拉跑进教堂的前院,一路冲进地下室的入口,期间不断有人加入,互相推搡着朝地下室的深处涌去。一只蓝幽幽的灯泡照着“避难”的标牌,所有人都嚷嚷着冲下来,神情紧张,左呼右叫,议论着可能发生的险况。很快又进来更多的人,打听着一个走失的孩子。
阿黛拉感到旁边有人挤她,是一个男人,正望着台阶的方向。没过一会儿,他开口谈论起前一天阿圭列斯住宅区的轰炸。阿黛拉反应过来男子是在对她讲话,于是点点头以示回应。那一刻,又一波尖厉的警笛声响了起来,愈发刺激着躲避的人群,众人发出一阵阵尖叫,不断挪动。男子移到了阿黛拉的另一侧,紧贴着她,问她是否孤身一人,是否就住在附近,因为如果要在黑夜里走远路回家可就太危险了。阿黛拉“嗯”“啊”地敷衍着,快速瞥了一眼,看到男子样貌年轻,戴着遮住耳朵的帽子,正对她微笑。阿黛拉没过脑子就回答道:“我不回家。”


男子凑得更近了,压低声音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和刚才一样,阿黛拉没细想就回答道:“没有。”她感到男子的身体紧贴着自己,嘴也几乎贴上了她的脸庞。
“我说,要不跟我走吧?去我家,你也不会冻着,有个火炉,暖和着呢,我还有没开封的肉罐头和红酒,我们可以一起吃。”
又有些人挤进了地下室,跟已经在里面的人发生了争执,里面的人不让新的人进来。众人推来挤去间,阿黛拉发现男子的手已经揽上自己的腰,但她没有躲避也没有抗拒,只是等待着,想知道男子究竟意欲何为。在周遭的一片嘈杂中,她专注地听着那一个声音:“我会吻你的肩,再慢慢往下,舔湿你胸前的小花蕾。我会让你很舒服的。”
阿黛拉已经要拔腿走掉了,却突然转身,朝向男子,微笑着,低声应道:“好啊。”
阿黛拉推开她前方的人群,奋力地穿行,但太过吃力,她只得用手肘撞开众人,在昏暗中她看到大伙儿带着惊讶和愤怒的表情转向自己,抱怨纷纷。大家警告她现在不能出去,劝她冷静,要她等到警报过去。可阿黛拉还是奋力移动到阶梯处,往上走去。她穿过小花园,来到街上,在黑暗中撞上一大群人,匆匆忙忙,高喊着“快去避难所,快去避难所”。她被挤出了人行道,差点跌倒。她穿过街道,沿着教堂的墙壁往前,直到那时才发现男子并没有跟她一起出来。自己真该留在避难所。
男人刚才的话勾起了她的好奇。阿黛拉原本会接受他提出的一切,毕竟她已经体验过那极致的欢愉。她想起在酒店床上看到的那个身体,走在自己熟知的街上,步子却变得愈发飘忽。
她走到一扇看上去是关着的大门前,推了一把,门开的瞬间,她闻到门廊里强烈的水汽。她摸索着墙壁在门廊中往前,走到楼梯口,一级级数着阶梯慢慢往上爬。老旧的木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她终于爬到顶楼,门缝里透出的微弱灯光指引她走到唯一的一扇门前。
阿黛拉敲了敲门,一个男人应声而出。他颇有些年纪了,留着长发,穿着罩衣,脖子上系着一条毛巾。在他身后,电炉亮着,为这小阁楼带来一丝暖意。
阿黛拉进门后与男人贴面吻了一下,问候道:“叔叔好!”随后在凳子上坐下,双手伸向电炉取暖,同时打量了一下四周:两张桌子上,一支支画笔伸出笔筒,一幅幅油画靠在墙上,有的只画了一半,是些风景画;画架上撑着一幅涂满褐色背景的画布。
叔叔嘴里叼着烟,站在电炉前,看着阿黛拉把头巾向后收拢,缚住凌乱的头发。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都快八点了。”
“我在家太无聊了,这么冷,真是烦死人了。”
叔叔流露出疑惑的表情,问道:“今天发补给了吗?”
“发了,我妈去领的。应该是大米。”
叔叔的目光投向房间的一角。
“跟你爸爸说,我又领到一个给市政府画宣传画的活儿,标语也是定好的——‘马德里必将成为法西斯的坟墓’。我真不知道怎么弄。”他走了几步,盯着地板,几乎是背对着阿黛拉,继续说:“我是个画家,又不是画海报的,现在却要画这些七七八八的。”
阿黛拉发现,叔叔的背似乎佝偻得更厉害了。
“你想想,我们可是在打仗,什么事都不能用常理要求,我们什么都得忍着。谁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画家。”
阿黛拉看到叔叔靠近桌子,撑在上面,伸出手去好像要拿什么东西,最后却握紧拳头砸向桌面。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想着好好提高绘画技巧,想要得奖,想要办画展,到头来却只能画这些蠢得要死的宣传画。”
叔叔骂骂咧咧起来。阿黛拉打断了他:
“你那位邻居来看你了吗?你还是那么爱她?”
“你说谁?卡梅拉?嗯,她几天前来过。”
叔叔走到窗边,停下脚步,拉开窗帘,望向外面。阿黛拉明白,他的目光是在搜寻自己渴望的东西,那里有他的憧憬,或许是在这暗夜中遥不可见的云层之上吧。
“她每次来这里,我都觉得她更美了。”
“你就从没对她说过什么?”
“我能对她说什么?我都这把年纪了,也太荒唐了。我请她允许我为她画一幅肖像画,她兴许会同意。”
叔叔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眼睛依然盯着窗外早已降临的黑夜。
“叔叔,不好意思,我得说,你要跟她表白才行啊。我们女人都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唤起男人的欲望。”
“她哪里会在乎我怎么想呢?她周围有大把年轻男人,处处献殷勤。”


叔叔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从一块搁板上取下一小包瓜子,递给阿黛拉,她嗑了起来。叔叔再次走向桌子,小心翼翼地把松节油和颜料管摆放得整整齐齐。
“说真的,她太美了,头发扎起来,配上画了眼线的大大的黑眼睛,笑起来就像有一道光在她脸上化开。她很懂得晃动耳环,来衬托自己的耳朵、脸庞和脖子。今年夏天她穿了一条低领的无袖长裙,我着了魔一样盯着她看。”
叔叔不说话了,没有什么再来打破屋内的寂静,只剩阿黛拉噼噼啪啪嗑瓜子的声音和叔叔的脚步声,可这脚步声反倒让阿黛拉愈发感到无力。叔叔举起手,伸向柜子。有几本书散落在一堆颜料罐中。他拾起一本,翻到用一张小卡片标记的那一页,腰比走路时弓得更低,慢慢念道:

时光消褪
爱愈发温柔,愈发不安
它散发着——是啊——它散发着余辉
那是残存的爱,是黄昏的霞光
血管中的热血已经平缓
可最后的爱的温柔还活在心头
那是祝福,也是绝望
叔叔读得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似乎每个字都充满激情的呼唤。他合上书,放回柜子,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和双眼,还有道道皱纹间没剃的胡茬,以及那被烟草熏黑的双唇。他的双手青筋突出,关节都有些变形了。阿黛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是鲁文·达里奥的诗吧?我觉得不错。”
叔叔说这是另一位诗人的作品。他在咳嗽,捂着嘴的手颤抖了好一阵。随后,二人听到警笛响起,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面露不快。阿黛拉停下了嗑瓜子。
“你什么时候也给我画幅肖像画?我想躺着画一张裸体的。”
叔叔闷哼一声,拉上了窗帘。
“有天晚上我梦到她了,”叔叔又开始说,“跟我在这里看到的她一模一样。我盯着她的嘴,她的下巴,她笑起来时嘴边的皱纹,还有她的脸颊。她太美了,让我害怕,因为我真的被她征服了,成了她的奴隶。总之吧,最后的爱【此处原文为法语。】啊!”叔叔弹了下舌头,“我也不知道说这些干嘛。”
阿黛拉看到叔叔慢慢闭上眼,双手垂下,僵硬地站在窗边。
“我走了,回家去。”
“太晚了,孩子,我送你吧,你一个人走,你爸妈会担心的。”
等待他们的,是黑漆漆的街,走起来很艰难。叔侄二人挽着胳膊,互相支撑着,摸索着每一步。很快,他们又听到了移动警报的声响,不得不跌跌撞撞地加快步子。还没到梅迪纳塞利耶稣圣殿,飞机的轰鸣已然在头顶响起,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几乎要把周围的房子震碎了。
二人找到一处虚掩的门廊躲了进去,跟另外一群人挤在一起,大家都默不作声,警惕着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危险。不过爆炸声没有再度响起,阿黛拉和叔叔决定离开那儿,踉踉跄跄地又走了起来。黑暗中,他们遇上一群人,听到大伙儿惊呼:“炸到博物馆了!房顶烧起来了!”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点,看到路中央有两团火还在烧着,那是飞机投下的燃烧弹。在他们对面,博物馆顶部的高度,一片红光。
右手边,莫拉廷街道拐角处的大楼也被燃烧弹击中,大火熊熊。有人说,阿拉尔孔大街也起火了。
阿黛拉和叔叔惊恐地看着远处的火光,叔叔不断重复着:“所有的画都要烧没了,所有的画!”阿黛拉搀着他的胳膊,感到他激动得发抖。他们头上,不时有防空探照灯快速地划过夜空,亮光照透云层,映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又很快消散殆尽,被更多从黑暗中涌出的新的云朵取代。有一瞬间,亮光持续掠过天空,云朵的白色和苍穹黑洞洞的深渊,交替闪现。

——路易斯·贝尔特朗·阿尔梅里亚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5期,责任编辑:汪天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