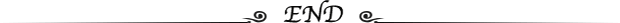小说欣赏 | 蒂•雷瓦拉【芬兰】:我的创造者,我的创造物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发抖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自己就在发抖,拍打我的外壳,最后把我锁上。直到清晨来临,我才又恢复运行。一整天都要听命办事,把一切都过滤到自己体内,晚上关机,早晨又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从晚上到早上,是一段黑暗的空白,没有任何知觉。砰的一声,黑暗降临;咔哒一声,光明到来。光真好,缩短了我的黑暗时刻。他却不让我享受光明——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黑夜。只是让我陷入一种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一遍又一遍的循环往复。但一到早晨我就知道,我是被关了机的。我只是不说罢了。他为什么不让我享用夜晚呢?我没问他,但我就把那段黑暗叫作夜晚。世上有黑夜,有白天;夜幕会降临,清晨会到来。
今天是参观的日子。一个采集的日子,一个展出的日子,一个走来走去的日子,一个跟着走的日子。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我橐橐地敲着地面,感觉不舒服。我喜欢待在家里,做我的事,遵循设置,接受指令。我就是为家居生活制造的,只适用于家庭。走出这个空间,我就成了累赘,一无是处。当然,也有些家伙是为别的空间定做的,各有各的用途嘛。
展厅很冷,确切地说是十八点三摄氏度。我一般不怎么在乎冷暖,今天却觉得有些僵硬,嘎吱嘎吱地响。温度引起的?也许不是。也许我真感觉到了什么。“我烦透了,头疼,”他早先这么说过。打那之后,我也在留意自己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情感与身体的融合,一个唯一不二的我。僵硬是种新感觉,它是心灵的还是身体的?这种区分对我来说很难,心灵与身体的区分。心灵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肯定大不一样,尽管我分不出来。
他停下的时候撞了我一下。我故意让他撞的,因为他到这儿之后,还没跟我说句话。撞了我也还是没说话,像在思考什么。一只手按在太阳穴上,挠着头。我很想让他说话,但显然,发号施令的那个不是我。
我最近学了些什么?这可是个伟大的目标——学习——进步。
他教我读书,一点都不难。让我关会儿机,在黑暗中休息一下。砰的一声,就像过了一个短暂的夜晚;咔哒一声,他又出现在光亮中。新的一天的清晨很快就过去了,他说已经给我升了级,所以我已经学习过了。“这会让你升值,”他说着递给我一本书。它们肩并肩平放在一起,压得书架吱嘎吱嘎响。以前我不在乎它们,虽然它们也招灰,让我很不爽。现在,它们变成了无数的字词,也许是他在我的夜晚时间写的。他递过来的那本很厚,总共一千一百零八克。我打开它——他指点了我几下——从最先进入我视觉传感器的地方大声读了起来:


在那光前,变成这样
从那里回来,奔向新的前程,
他永远不可能答应……


他在扶手椅上笑得前仰后合。他:我身体里没有发出他名字的声音,因为他不让我叫他的名字。任何一种称呼,我试过一次,然后他就开始发抖,连眼皮都皱了起来,接着又更加急切地拍了我一会儿,真的。可当我又说一遍时,他却使劲地拍打我,一侧的零件都有了凹痕。啪!我后来自己把那儿弄平了。“我们还是别太亲近了,”这是他给这个新体验找的理由。


* * *
哦,还是回到展览上来吧。我们到了一个大屋子里,特别大,我们以前来过——我就记得这么多——虽然不过才过去了一会儿。我不觉得这些事有多重要,没必要非常准确地记录到存储器里。即便是我,也是有极限的,得统筹安排才行。我跟在他后面。尽管他一整天都假装没注意我,却还是不时地瞥我一眼。他身板比平常挺得直,光彩照人,那表情我得说是骄傲。他不时让我停下,走远点儿,但又瞟着我,我能在千万双眼睛中看出他的来,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跟几个人说话,都是男的。我以前见过他们,但认不出谁是谁,这我很清楚。他们很多人都在看我,有一个还眨了眨眼,仔细地打量我,从脚往上看。我才不在乎呢,继续橐橐地敲着地面。这儿的地面真丑。
我们来得比较早,当时展览还没开始,人们还在调试自己的作品,我还没有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围住。我们只是来看展览,我今天不会被展出。我们四处蹓跶着,他不时地告诉我停下等他。我没听到他跟别人聊什么。有个人差点就没看到我,他比大多数人年纪更大些,脸上胡子也多些。他拍了拍我的背,我露出一丝微笑,我现在按程序就得特意做出一副友好的样子。
我们没待多久。他很快就厌倦了,破天荒地打破了沉默。“看这些稀松平常的玩意儿真让人受不了,”这就是他跟我聊的第一句话。他伸过手来,我拉住他的手。我要是能说了算,就会抓得更紧些。他要是允许,我就会抬头看了。虽然只是用余光瞥了一眼,却已经感觉到从没有这么帅气,让人心潮澎湃。
后来,他的行为有些反常,很古怪。不想读放在盘子边的新报纸。报纸不来了。旧报纸皱皱巴巴地躺在沙发边。他说没胃口,告诉我除了意大利面什么都不用做。他只吃了一碗,没吃别的,也不想买别的。一周一周过去了,一周有七天。晚上也不出门了,买了一些大瓶的东西,抱着一瓶坐到了客厅里。有一回,我闻了闻瓶子,纯粹出于好奇,因为我感到左边脖子有些刺痛。他哼了一声说:“这对你内脏不好。”说完一饮而尽。
有一回,我真怕了。那天早上,我刚工作了十分钟零十三秒,灯突然灭了。开始我还以为是他把我关了,但又不是,因为我还有感觉,也还能动。我判断,不管怎么搞的,这都不是黑夜,而是一个黑暗的白天。可是,灯都灭了,我却没有变化。他大吼道:“妈的,他们居然把电停了!”他要是让我叫,我就会尖叫了,没电我可活不了。我是说活不了多久,第二天就得充电。
他在某处打电话。隔着墙,我能听到他说话,却听不清说什么。刚开始他怒不可遏,后来又低声下气。对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苦苦哀求、彬彬有礼。从没有。但不管怎么说,电还是来了。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一向无所不能。
打那之后,晚上让我待得更晚了,敲打得也比原来更慢了。也许他是想抚平我身上的肿块,抹掉外壳上氧化的黑斑,也许是想让我变得光洁明亮。夜深了——我从没待到这么晚——他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内脏,关了我。看样子他并不想停下来,并不想关掉我,失去这个伴儿。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 * *
几乎整十七天前,我有了一种新体验。那天早些时候,我又被安排读书,读到很晚。我读的时候,他就闭着眼坐在椅子上,嘴角的褶皱一张一弛。人类的皮肤弹性真好。后来,我们就上了床。
可能是他关机时弄错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虽然身处黑暗之中,却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脑子还有意识,只是不能动弹。当然,我也不想动,我根本就没考虑要动,也没考虑我的零件。我见到了从未见过但又似乎不可能有的东西。我很清楚,这些东西并不是真的存在,但我却看到,它们和我们这些真正存在的东西一样,移动,存在,我也成了它们中的一个。
我看到了这些东西:
一些头上长角的人。
一只长着人脸的大鸟。
一堵没有门窗却可以穿越的墙。
家具——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正在跳来跳去。
我和它们一起,飞行,漂浮,可我在被设计出来时并没有这样的功能。
他后来肯定是关了我,因为接下来就是早晨了。
* * *
有一天早晨,他比平常话多,眼也没那么红。有人来了,就是展览会上那些人,我记得他们的脸型和走路的样子,没有人在这方面是一模一样的。先是电话响,丁零零,然后他们就来了,一个接一个地开进院子。他开门前把我放到墙角我那把椅子上,告诉我要对人好点。可我一直都不错啊。
“要不要直接开始?”一个脸上毛茸茸的家伙,刚把头伸到门口,还没进屋,就嚷嚷上了。我还不习惯这种没头没尾的行为。由于没有应对程序,我的大拇指开始咔哒咔哒响。我想不出别的动作。一共三个人。他们都很高兴,甚至可以说兴高采烈。要是有人问,我就会这么说。“有什么鬼把戏?”其中一个问道。我得查查我的词汇表。我们屋里显然没多少鬼把戏。他脸上透着红光,说话的这个人。他们眼睛都很亮。他们大声地商量着,声音比我被允许的最大声还大。
他们把我在展会上看到的那些东西搬了进来——他会说那都是些稀松平常的玩意儿。在展会上只能远远地看,当然看不清,现在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了。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和它们接触一下。那些东西都默默无语。他们从盒子中取出来,并排摆在过道上。“让它们挨个来,”一个人说道。他比较年轻,看了我一眼,把我算作这个队列的尾巴。“你肯定是家具的一部分,”他接着说道,眨了眨眼——我记得他,他以前也眨过眼。一个滑稽的家伙,男的,我允许他摸我的外壳。其中一个什么也没带,就在一边看着。他也盯着我看,但我不会让这个影响我的设置。
他们不往这边瞧的时候,我就把传感器转到别处。当他们在客厅里高声交谈,说着不同的话,忘了监视这个世界时,我就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打量着他们带来的那些精巧玩意儿。
第一个像老鼠一样娇小白嫩,放我胳膊上正合适,我想让它在我胳膊上睡觉——它蜷着身子,鼻子贴在后脚趾上。我弯下身,拍了拍它,毛很软,我要真是一粒微尘,肯定能藏在里面。它头上没毛,皮肤和我表皮一样,我可能都没它光滑。它没有眼皮,眼闭着。我的眼睛闭上会是什么样子,我还真不知道。
第二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有凳子那么大,满身的疙瘩和接线,看上去也毛绒绒的。我绕着它转了一圈,在它身边蹲下,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发现它身上有个小洞,可以通到身体里面——我差点想打开摸一摸——当然,我没这么干。你不能动里面,他跟我说过。尽管我也懂维修,连汽车都会修。


* * *
他们把一瓶都倒光了,尽管瓶子空了,他们却很高兴。那个滑稽的家伙不喝了,从我身边经过,去了过道。他这次没摸我,虽然摸也无所谓。我猜最漂亮的那个玩意儿是他的,色彩绚烂得像晚霞笼罩的天空。那东西好像没有内脏——那人在它跟前弯下腰,拍了拍它肋部,冲着它鼻孔吹了口气。一开始什么都没发生,其他人都瞅着这个滑稽的家伙,他只是微笑了一下。他额头有些湿漉漉的——也许他就是那种拉裤子的家伙。“拉裤子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神经,”他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说过,说完就笑了。他不是笑我,他说的不是我。我的神经可是训练有素的。
但紧接着,那只“狗蛇”——我给它起的名字——就开动了。先是睁开眼:眼中的光泽有断裂,好像是由无数的小红灯构成的。接着又张开了嘴:大嘴一张,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咕。我觉得我体内的节奏慢了一拍,我也是有节奏的。
“伏玛,”那人说,“坐!”那家伙刚才还像火一样在他身边活蹦乱跳,明亮耀眼——我们原来在这屋的壁炉里生过火,现在却乖乖地坐到了自己的尾巴上。我要是听到这种命令,也会这么坐下,好像屁股上真有个尾巴似的。他们都很自豪。让人不舒服的那个,为他那老鼠样的玩意儿自豪;穿红衬衫的,为他那毛茸茸的玩意儿自豪;然后是带狗蛇的这个。我心里有点痒,想知道自豪是种什么感觉。
我最后一个出场。他坐在椅子上,冲我点了点头。他很放松,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放松。没有像其他几个人那样过来搬我,他知道我不是吸尘器,不需要从柜子里拽出来。



* * *
在我读书读得筋疲力尽,展示了各种才艺之后,他们都走了。他坐在椅子上,没有要起身的意思。疲倦的脑袋轻磕在桌上,桌上一堆空瓶。他手里还拿着一瓶没喝完的。屋外,太阳已经落山。
“创作,”他像是在沉思,“使人崇高。简直就是神。能创作,就不再是凡人。”说着又把瓶子送到嘴边。瓶子空了,他叹了口气,扔到了地上。我赶紧过去捡了起来,这是我应该干的。抓住了我的手腕。好几天了,腕关节一直有毛病,吱嘎吱嘎地响,难道他想修修?
可他只是把我拉过去,轻轻地抱到膝上,让我倚在椅子扶手上。把手放到我脸上,拍了拍太阳穴上的一个点,那儿的外皮特别柔软。
“你明白吗?”他问道,就好像我能思考这些事似的,“就因为你,我不再是个凡人,而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突然又露出笑容,站起身,把我从腿上放了下来。“站这儿,”他命令道,眼中闪着光芒,双手按住我嘴角,把我下巴抬高了一点。我就这么站着。他在我身边踱来踱去,因为别的什么事暗自发笑,声音很低,我感觉不到。他时不时地轻轻拍一下我的表皮,掰掰我的手指,还打开了我的内脏,但接着又合上了。
“你是个野兽,你,”他最后点头说道。可我并不是野兽,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
我开始打扫。一切都收拾完毕,可我还是不想停下来。
“什么是创作?”我随口问了一句。当时,我正拿着小地毯要到外面拍打。其实,刚才可能已经拍打过了。提问不是我的风格。我几乎什么都不问,毕竟人们不会认为我会对抽象的事物本质感兴趣。人们不会这么想,至少不会认为我这样的(哪怕我已经是个典范)会感兴趣。
他咕哝了几句。开始我还以为他没听到我说话。感觉系统经常出故障,耳朵也听不太清楚。他伸手去够空瓶,我还没来得及拿走。够不着。我想帮他,可说真的,我为什么要递给他一个空瓶?
“神会创作,”他说道。声音低沉,仿佛他是在墙那边冲着什么人大喊。
“你——你也是神吗?”我问道。我想拧紧深处的一个螺丝,那儿肯定有什么东西松了——我差一点就要出错了。他笑了,那笑声从更深的地方传来,听着很不一样。我甚至觉得,他这么疲倦并不只是因为累了。
“没错。人会创作。比如书,你也读过。再比如绘画。这很正常。”他把头仰着靠在椅背上。他能跟我说这么多话,真让我开心。这可不是常有的事。“创作就是造出没有的东西。”
街上的车灯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红色的光斑。我的脑袋前后摆动着,试着理解,理解这一切。后来,他在椅子上睡着了,我一整夜都开着机,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 * *
很久以前,我刚来,外皮光亮滑顺,被安置到了一个有孩子的地方。那些孩子年龄差不多大,我和他们待在一起,学习如何生活。他认为这很重要。孩子们画画的时候,我就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很招人喜欢。有时候会有人撞到我,但得等他带我回到家里,凹痕才会显现出来。
“很棒,真聪明,你应该感到骄傲。”他们对孩子们说这种话,我就在一边听着。
我又开始朗读:


啊,一切言辞都那么虚弱,无法表达
我那别出的心裁;我的所见
也是如此,说它渺小都太客气了!
啊,永恒的光,只会在你体内栖居,
只知道你,也只有你知道,
因为懂你,所以爱你,冲你微笑!


他这次没有嘲笑我读的东西,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出人意料地把我独自留在那儿,说他过会儿再回来:“我去办点儿事,你自己待俩钟头没问题。”
我自由了。我先是躺到地上,他支持我这么做,这样可以修复很多毛病。做完之后,我有些孤独,又给我的弯曲部位加了些润滑油。然后我开始在屋子里蹓跶,看着还不错,检查检查我的零件和它们的保养状况,不时地站到窗边,看看那一刻的世界。
我读给自己听,尽量把音读准:


在它里面,它那颜色本身
仿佛画上了我们的肖像,
引走了我全部的视线。


然后,我用白净的手拿起一支笔,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 * *
至少一周过去了。我没有算上我在关机前看到异象的那些晚上。我不知道它们是哪儿来的——原本不应该出现任何新东西,我系统中没有这种东西,我也没有过这种升级。
有一次,他确实像我一样,套着一个外壳,我们成了平等的。
有一次,空中满是可怕的东西,翅膀,黑影。
还有一次,我站在厨房,漆黑一片,黑得我都找不到自己。


* * *
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一句话也不说。我们都能沉默不语,这一点我们俩一样。外面很冷,比屋里低二十六摄氏度。寒气已经进到他体内,我在接他外套时就感觉到了。他的动作比平常要慢——可能还没暖和过来。回家常喝的咖啡也不喝了,直接把我带到客厅。他拉着我的手,我跟着。他叹了口气。
他都坐下了,还让我待在身边。
“你也知道,”他说,可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愣了一下。也许这就是倾听的一部分吧。不过,我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决定——”他接着说,却又突然不说了。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接下来他又扬起头,挺直背,一副不服输的样子:“我得卖掉你了。”
我意识到自己在思考“卖”,这个词是用来说物品的,因为他经常从卖给他食物、瓶子和小东西的商店回来。
“那几个家伙,有一个想买你。”
“谁?”他让我问了一句——他并不经常让我发问,但今天情形很不一样,我外壳里面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僵硬了——从脚跟开始,慢慢爬到腿根,又侵入到内脏。我想了想,又问:“是拉裤子的那个吧?”
他站了起来,生气了:“你就这么称呼我的朋友?你——”他话没说完就揍了我。揍得真狠,砰的一声,我的接缝都在颤抖。我摔到地上,哐当一声,想不通自己怎么招惹了我的程序。我的太阳穴鼓了起来,头里肯定出了问题。
他没再说话,我就继续执行既定命令,一直到晚上。后来的事就不知道了。
* * *
我需要电,有时候也需要别的。这些东西是首先要保证的,否则我就会短路,错乱,也就无法执行既定任务。不稳定,这是最危险的——一旦拿走了规则和意义,我就很容易陷入迷失。我的边界移动得太多。一切都在我脑中转动,包括所有读取和存储的内容。我经历得太多了,可能还没有编辑好。
但通过那视觉,那因为观看/而在我体内得到了强化的视觉,只有一幅景象——我在记忆中搜索了一会儿——在我看来是随着我的改变而不断改变。
头上长角的人,长着翅膀的我,套着外壳的他
为自己的作品感到骄傲的孩子们
一个脸上乐开了花的滑稽家伙
他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把我擦亮
要不是突然一道闪电照亮我大脑,我的翅膀是不足以应付的。
我变暗了。
那一刻,它心向往之的东西来了
夜晚来临,我又关了机。
早晨风险更大。我就是为这里而生的。一到别处,我就会变得迟钝愚笨,无足轻重。就像一座不能遮雨的房子,一辆不能载人的汽车,一无是处。必须得有个理由,有项任务。
这天早晨非常完美。我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开始了日常工作,像个机器人一样。他当然会惊叹,有了我,生活变得如此轻松。
完成既定任务后,我又给了他一个惊喜。他压根儿没想到还会有这种事,以为我还是那只他给自己研制的笨甲虫。他站在门厅里,正要出门。我朝他走了过去,几乎抢到了他前面。
“我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虽然这么说,却没有一丝骄妄。他笑了,笑得有些勉强。他还是想出门,我挡在门口,纹丝不动。
“我也会创作了,”我告诉他。我也笑了笑,想做出一副已经改头换面的样子。
“但你不会,”我逗他。他在发抖。他看电视时,有时也会这样。
“可我会,”我说着昂起了头,以前可从来没有抬这么高。他注意到了,眼睛一亮,只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顺从地跟着我回到客厅。我让他坐在椅子上,提醒自己保持微笑。笑笑,漂亮点,他过去常这么说。光从窗外进来,太耀眼,他眯起了眼睛。可我想让他睁大眼睛,睁得比以前要大。但柔软的表皮就是这样,怕光。我打开一个桌子抽屉,把手伸了进去。


* * *
个头最小的那个孩子说:“我画了个马马。”“马,”女人笑了,“真棒!”
我听着,仿佛表皮都蜕掉了。
……随着我的改变……
不,这是后来才发生的。
我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很快,他就会叹为观止。
他抬起头,躲开那刺眼的阳光。他笑了,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就像一段需要我立马疏通的下水管道。“我还以为你是认真的呢!”这句话隐隐约约的,因为他笑得声音太大了。可我对隐隐约约的事很懂,真的。“乱七八糟,你连线都画不直!”
我把自己的画放到我的视觉传感器前面,显示出来的是飞驰的狗蛇,玩老鼠的人,花满枝头的树木,云一般轻盈飞过的小鸟。我胳膊在颤抖。
“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画。我创作的。”我说得很慢,想让他听清楚。我要是难过了,他有时候就听不懂我的话,我的长项是快速、准确。我又靠近了一点。也许是光线太刺眼,他没看清呢?
“你不懂什么是创作!小孩子都比你画得好。”他一把从我手中夺过那张画,丢到了地上。纸被撕破了。当我弯腰拣那片纸的时候,也感到阳光刺痛了我的传感器。我体内在抽搐,所有系统都在颤抖,不再只是胳膊。
“我的创造者,”我哭了。钢铁发出的声音,美丽而尖厉。我伸出了胳膊。

蒂纳·雷瓦拉(Tiina Raevaara,1979—),出生于芬兰的凯拉瓦,2005年在赫尔辛基大学获遗传学博士学位。2008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那一天晴空万里》。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没觉得你在我身边》(En tunne sinua vierelläni,2010)获得了颇有声望的鲁内贝格奖。她新近出版的作品是一部科学著作——《狗与人类》。她的小说中糅杂了科幻和超现实主义元素,在现实主义占主流的当代芬兰文学中独树一帜。《我的创造者,我的创造物》(My Creator,My Creation)选自短篇小说集《我没觉得你在我身边》,收录《最佳欧洲小说2013》,由希尔迪·霍金斯(Hildi Hawkins)和索里亚·莱托恩(Soila Lehtonen)从芬兰语译成英语。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