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余纨:一首献给普通人的安魂曲——读《尊严、纸条与遗忘》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对这些普通人来说,纸条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方法,更是抵抗遗忘的手段,是对战争中无数无名死者的菲薄却也是厚重的纪念。面对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或许一切精神慰藉都不过是无效用的自欺欺人,人们抵抗命运的唯一姿态或许只有存在主义式的悲壮,以一种直面惨淡人生的沉毅应对历史与命运的无情捉弄。
余纨
余纨
在《世界文学》2022年第5期刊登的西班牙作家苏尼加的作品小辑中,我最偏爱《尊严、纸条与遗忘》。这篇小说聚焦西班牙内战中参加共和派军队的两兄弟在战后的情感心理与人生抉择,以交织的叙事和迤逦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在精神创伤中奋力挣扎的普通家庭。“围观人群的背景是一栋栋平房,矗立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里面住着一个个与命运抗争的家庭”,小说正是献给战后西班牙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安魂曲,虽然他们被那些“统治着国家、扭曲了历史的强大力量”不断改变着人生轨迹,但在他们与命运的抗争中,我们看到这些无名小卒才是马德里的真正主人:“这座城市的命运与他紧密相连,渗透进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中。”或许他们不懂艺术,也没有什么高雅的生活品味,但他们内心的思想斗争却展现出更厚重的精神气质;或许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对生活惟命是从,但他们总是热切地把握住改变命运轨迹的契机;或许他们的生与死都如纸条般轻薄而微不足道,但纸条正是他们尊严的承载与记忆的象征。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呼吸与脉搏,是这座城市的精神缩影。





在小说描写的这个普通家庭中,两兄弟的父亲和姐姐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形象。衰老的父亲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命令只会逆来顺受,他无法理解两个儿子的行动,怪罪他们一事无成,这位老人已经被时代抛弃,和儿子之间有着巨大的精神疏离。在这里,作者或许并不是想要批评父亲这一形象的保守、迂腐。毕竟,麻木是普通人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时难以避免的精神样态。可悲之处在于,虽然业已参加战斗、力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两兄弟已经脱离他们父亲的麻木状态,但是觉醒的这代人却面临着战斗的失败,非但没有过上更好的生活,反而陷入更大的精神困境。在小说灰暗压抑的氛围中,女性形象带来了一抹亮色。姐姐胡丽娅承担着劳累的家务,并时刻关心、同情着两兄弟,调和他们和父亲间的矛盾。在战争中,像胡丽娅这样的女性与参加战斗、承担危险任务的男人们一样,肩负着生活的重担和精神的压力:“她们的手或是因为擦擦洗洗而总是湿漉漉的;或是纤细修长,指尖被针头戳破过无数次,又或是因漂白剂和繁重的家务而皮肤开裂。”此外,胡丽娅与那位送纸条的朋友还未来得及开口就已经结束的爱情,更是令读者陷入悠长的伤怀之中。
送纸条的朋友和两兄弟一样是个无名之卒,在小说中他似乎只是一个边缘人物,但却和两兄弟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在传递纸条前,他和兄弟两人的父亲一样处在辛苦而麻木的生活之中。但是自从他承担起传送纸条的使命后,他从自己疲惫的人生中超拔出来:“这力量为他渺小的人生增添了光彩。”他可能因为这份危险的工作失去生命,却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使命,因为这是他获得人生尊严的唯一机会。两兄弟选择投身战斗的背后动因或许同样在于此——“分发纸条能让他与所有重要人物和英雄志士相媲美”,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哥哥会再次接下传送情报的任务。


小说结尾,作者运用了蒙太奇式的音画拼接,在弟弟调弄的收音机的“一阵欢快的方丹戈舞曲和布雷利亚斯”中,哥哥最后的牺牲使小说达到情绪上的高潮。对这些普通人来说,纸条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方法,更是抵抗遗忘的手段,是对战争中无数无名死者的菲薄却也是厚重的纪念。面对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或许一切精神慰藉都不过是无效用的自欺欺人,人们抵抗命运的唯一姿态或许只有存在主义式的悲壮,以一种直面惨淡人生的沉毅应对历史与命运的无情捉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余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热爱阅读,热衷于在文学作品中体认世界、寻找情感的互动与经验的共鸣。


第一读者 | 胡•爱•苏尼加【西班牙】:夜与欲


读者来稿 | 徐阳:围城中的爱欲生死——读苏尼加《夜与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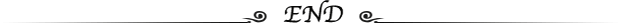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