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读 | 艾•温伯格【美国】:战后的美国诗歌或多或少就是“王红公的时代”……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要听到王红公的诗音就需要参照他阅读的方式:以爵士乐(或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以古琴)伴奏。直白的声音与回旋的音乐平行交叉:仿佛是对诗歌本身的模仿,仿佛是一个人走在仍在他身边徘徊的世界里。

艾略特·温伯格作 李栋译
*【王红公,即肯内斯·雷克斯罗斯(1905—1982),美国诗人和翻译家。曾翻译过大量中国和日本古典诗和现代诗。】
故事很典型:在我自己的提议下,美国《民族》杂志邀我为王红公写悼词。王红公曾是驻旧金山通讯员,为该杂志工作了十五年。悼词在他去世那周完成,但月刊马上退了稿,说是“过度吹捧一个小作家”(还讽刺他是“性别歧视的猪”)。后来在王红公遗孀卡珞尔·亭克的建议下,悼词寄给了《美国诗歌评论》杂志。两个月后,杂志说愿意第二年刊登并叫我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考虑到他们的闲暇和我不合时宜的咖啡杯,文章撤了回来。后来,刚开始发行的《硫磺》杂志愿意加页刊登——只有在那里,在那些名不见经传但时而还让人尊敬的小杂志上,我的小文缩水版才最终付梓。
故事很典型:我们甚至都不能发表献给一位美国诗人的悼词,因为他们中最杰出的死时比生时还凄惨。尽管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出现了所谓的“诗歌热”,每年数千本诗集得以出版,但大多数重要的美国诗人死的时候多数作品都还未发表或是没有再版,比如说路易斯·朱科夫斯基、H.D.、兰斯顿·休斯、保罗·布莱克本、查尔斯·奥尔森、玛丽安·穆尔、米娜·罗伊、弗兰克·奥哈拉、查尔斯·列兹尼科夫、杰克·斯派塞、罗缨·尼德格等。一小撮死的时候诗作仍在发表发行的诗人要么是在活着的时候得到大学英语系的赞同批准(如弗罗斯特、艾略特、洛威尔等),要么是得到青少年的追捧(如卡明斯),要么是新方向出版社发表并继续发行他们的作品(如庞德、威廉斯,和现在的王红公)。
除几个例外,美国诗人的死是可以扭转他们声名的。那些生时屡获加冕的诗人在坟墓里声名就消失得毫无踪迹了(如泰特、兰塞姆、蒂斯黛尔、麦克勒什、范多伦、施瓦茨、瓦依利、博根、宾纳、贾雷尔、艾肯、温特斯、希利尔,还有其他很多诗人)。相反,那些生时不被赏识而被遗忘的诗人,死成了他们翻身成不朽的重要条件。大学英语系去葬礼时通常是会迟到的,但掘起坟来倒是热情十足,他们的批判装置到那时终于开始运转。通常要等到很多年后,经由注释,有原创性的作品才终见天日,经典化终告完成,而我们则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孤岛总是出现在文学地图上的。(我们已经忘记威廉斯是死后才得了他唯一的一次普利策奖的,即使在他生前的最后岁月,院士们还认为他是诗界的祖母摩西;庞德最后一卷《诗章》被认为哪儿都不值得评论;H.D.死时,人们只记住了她几首早期的诗,《合集》的出版等了二十多年;玛丽安·穆尔的《合集》十七年没有再版,直到最近才重见天日;路易斯·朱科夫斯基写了三十三年才收到唯一一篇对他作品的评论。)


王红公诗集
今天,随着《圣传》杂志(由缅因州立奥罗诺大学发行的关注庞德—威廉斯—H.D.诗歌传统的杂志)特辑的出版,象牙塔才接纳了王红公先生。人们可以靠阐释他的作品来谋生了,那些渺小如中国山水画中人物的好奇探险者、学究、探听丑闻者、别有用心者都会蜂拥而至,在他生活、作品的山水间穿梭。不难想象王红公会对他们说什么——但他们又会怎样看待王红公呢?他们会怎样接受这位美国二十世纪最易读的诗人并把他变得晦涩难懂呢?换句话讲,让注释点评成为解读他作品所必须的,或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更“好教”呢?
我面前堆了一叠剪报:有《诗》杂志评论王红公第一本诗集,把它和犯罪分子做的汽车牌照做比较,并建议他尽早改行别做诗人了。作家、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说他是“老式的美国落魄鬼”。《纽约客》杂志以它惯有的略带困惑的居高临下式的口吻,戏称他是“老哥们”。《纽约时报》的约翰·伦纳德说:“他住在加州圣芭芭拉并在那里修佛冥想。冥想?(我)心都往下掉。如果王红公在冥想,那他就不是那过去美好记忆的倔老头了……就不是那些光怪陆离涂黑色指甲油的花花公子的老大了。”
至于他的讣告:在纽约是“嬉皮诗人领袖”;在洛杉矶是“艺术家和哲人”。几天后,篇幅长一些的吊文:《华盛顿邮报》的科尔曼·麦卡锡惊讶于报纸上的吊文都“没有几英寸长”,但他觉得“王红公工作过的《民族》《公益》《星期六评论》《诗》理所应当地会发长文来纪念他”。(但这些杂志都没有这么做。)《纽约时报》的赫波特·密特冈不无讽刺地说:“他或许会被作为公众人物而被大家记住,(在某些圈子里)会被认为是给人带来了灵感,而不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诗人、评论家或画家。”
出生在另一个国家,王红公或许会是公共知识分子、民族的良心:另一个帕斯、聂鲁达、麦克代尔米德、希克梅特。但在这个国家,就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在美国社会,诗人没有容身之处。根本没有任何地方会接纳任何诗人。”所以无论生前死后,他都被看成是个怪人,一个行为古怪却生命富有色彩、时而给杂志加料又写了三本影射小说的人。
让人郁闷的是,一提到王红公的名字,他宏大多变一生里的几个画面就被反复瓶装无限使用。一想到他死时在美国人眼中只是个上了年纪的披头族就让人伤心。又有什么比垮掉一代更遥远的呢?今天来读《达摩流浪者》(王红公在此书中以一个“披头散发戴蝴蝶领结的无政府主义老鬼”形象出现,而这又远早于亨利·米勒)就可以看到垮掉一代主要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另类消费选择——红酒、用筷子吃中国菜、没有婚姻束缚的异性性行为、搭便车、对非表象绘画的体味、对爵士乐的欣赏、休闲装、偶尔对同性恋的容忍、对冥想和东方哲学及神秘主义的涉猎、面部毛发、大麻——所有这些都很快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周末稀松平常的消费品,不无讽刺的是,垮掉一代还继续保留着他们“狂野波西米亚一族”的形象。


王红公译诗集
王红公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接受了垮掉一代(尽管他曾有过这样著名的声明:“一位昆虫学家不是一只昆虫。”)就如他接受并参与了很多运动一样:世界劳工、约翰·里德俱乐部、无政府主义、共产党(并未接受他的会员申请)、人权、嬉皮士、女权——所有这些运动都比垮掉一代对美国国家机器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作为政治思想家和评论家,他在本质上属于“革命无望一代”。与别的诗人相比,王红公的作品记录了时代幻灭的历史:克伦斯塔水手大屠杀、萨科和万泽提、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公审、希特勒-斯大林契约、广岛原子弹爆炸。他在一九五七年写道:
我们曾以为自己是
这些年巨变的领导者,
是人类正常生活的
先行者。
我们曾以为所有的事物很快
都会改变,不仅是经济
和社会关系,还有
绘画、诗歌、音乐、舞蹈、
建筑,甚至我们吃的食物、
穿的衣服都会更为让人尊重。
这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
尽管如此,他还是怀抱着自己撰写美国乌托邦历史里所折射的兄弟情谊的理想。他一九六〇年题为“学生接管”一文被学术评论家斥之为“疯狂”地“扯着海内外廉政的幌子宣扬国内革命”。但到了一九六九年,《民族》杂志却说:“不管此运动有没有肯定他们,所谓新左翼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红公和保罗·古德曼。”王红公的生活中不乏此例,最初的印象被记住了,但当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时候却无人为他平反:“当先知拒绝发狂,那他就成了个麻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道主义的美国是同样复杂的。”
王红公的敌人是国家机器(美国和苏维埃政府、大公司机构、大学、教堂)以及它们的产物:性压抑、学院艺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资产阶级的无趣、社会进步的神话、自然被夷为平地。他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最早拥护者,他写美国黑人生活的散文是为数不多的还有现实效应的文章。他是第一个对部落文化抱有极大热情的诗人,但他的热情并非来自弗雷泽、弗罗贝纽斯或是人类博物馆,而是来源于长期和美国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经历。他几乎是白人安格鲁-萨克逊新教徒中唯一一位不反犹太教的人,而且还是虔敬派和卡巴拉专家。最重要的是,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基督教诗人——此处所指的基督教极少出现在这个半球:世界兄弟大融合。他是美国的——不然还能怎么说呢?——他是伟大的美国诗人。王红公在本世纪的诗人中独树一帜,其作品囊括了这个国家所有能够让人去爱的事物:贫民窟里的街头小聪明、旷野、民粹主义反资本、爵士乐和摇滚、乌托邦社区、各种先锋艺术的小团体、美国英语以及所有在大熔炉里仍未熔化的块状物。



左为王红公肖像 右为王红公与爵士专辑
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第一部作品名为《一座叫作大马士革的宅第》——一组哲学对话,一首唯一值得美国青少年阅读的诗——然后的十来年,他脱离轨道,做了“立体主义”的实验。如果他停留在“立体主义”的实验中——比如说,像沃尔特·康拉德·阿兰思伯格——那人们顶多会记得他是现代派的非重要诗人,既不如米娜·罗伊有意思,更不如他的法国前辈勒韦尔迪和阿波利奈尔。随着一九四一年他的第一本书《在何时辰》的出版,王红公已放弃了立体主义片段式语言——但保留了立体主义在历史上同时性、在空间上连贯性的理念——他所用的语言是鲜有修饰的美国口语语言。(“我一辈子都想能做到我写的跟说话方式一样。”)这是一种任何读者都能欣赏的直接沟通的诗歌,也是他社群主义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他个人坚持的是基督教神秘传统(融合的宗教),而不是东方的宗教(解放式的宗教)。
王红公的诗歌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情色、祭奠;宣扬自然,谴责资本主义。他内心和身体力行的长诗是本世纪英语世界里最耐读的。尽管他写的高度色情的诗作是英语诗歌里三百年来闻所未闻的——值得入选《帕拉丁选》或是《魏迪亚卡拉典藏》——他基本上还是归属于颂诗而非抒情歌谣的传统。对某些评论家而言,他的诗在音乐性上平淡匮乏,但威廉斯觉得“他是我所认识人中乐感最好的”。要听到王红公的诗音就需要参照他阅读的方式:以爵士乐(或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以古琴)伴奏。直白的声音与回旋的音乐平行交叉:仿佛是对诗歌本身的模仿,仿佛是一个人走在仍在他身边徘徊的世界里。
奇怪的是,王红公对诗歌的影响不在于他作为诗人本身的贡献而是作为自由职业教育家以及诗歌的不懈推动者。他的活力与涉猎可同庞德一比高下:诗歌讨论、朗诵会和电台节目的组织者;是他把莱维托芙、斯奈德、罗森堡、邓肯、塔恩、安汀、弗林盖蒂和其他诗人介绍给新方向出版社的;他还是倡导者、记者、编辑和文选专家。尽管很难想象没有王红公的加里·斯奈德或是没有以《不可杀戮》一诗为榜样的金斯堡的《嚎叫》;尽管所有人都读过他的中文和日语翻译;但即使在诗人中间也很少有人读过他的《凤凰与乌龟》《龙与独角兽》《心之花园,花园之心》《花环山上》或是散落各处的诸多短诗。
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王红公死时成了最为著名但最少人阅读的美国诗人。此种情形很耐人寻味,而不无巧合的是,他的境遇和与他诗风最近的诗人休·麦克德米德不无相似。(我说的是麦克德米德在苏格兰以外的口碑。)除了麦克德米德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而王红公信奉异端基督教(此两者并无交集),但两位诗人都写短诗和复沓多变的长诗,都学富五车,两者都融会贯通了二十世纪科学、东方哲学、激进政治、异性情色以及对自然世界的细心观察。(奇怪的是,这种相似已经超越了知性上的亲和性:王红公自称在爱丁堡的街道上人们常把他误认为是麦克德米德。)
我怀疑对于王红公和麦克德米德的忽视,最核心的,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在“庞德—威廉斯—H.D.的传统”之外。尽管他们对此传统抱有不同程度上的同情,他们精神上的共同导师是华兹华斯和惠特曼:也就是说,精神生活在开阔的大路上。[附:汉语中的“道”字就是“首(头)”在“路(走字底)”上。]麦克德米德或许被自己星河系般广阔的词汇量所累,但王红公呢?一种猜测就是他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他写的诗任何人都能看懂,他颠覆了文学系统,特别是战后的大学文学情结。战后,诗人,特别是先锋前卫诗人,被迫走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发明发展了一种异教式的语言:他们私下里都坚持信奉(自己)是“世上未被承认的立法者”(雪莱)的神话,同时他们更趋向于圈内相互尊重但不能共同分享的个人式的封闭语言。对于大学教授们来说,他们享受于这种深挖文本来源与内涵的工作,他们是文本钥匙和译码器的持有者,就像是情报员乔治·史迈利和诗人中的卡拉一角演对手戏。王红公简单的语言承载了复杂的思绪从而颠覆了系统。英语系不需要“简单”的诗人,而创意写作班则不需要复杂的思绪。他成了一只未被钉成标本的蝴蝶。

左为麦克德米德肖像 右为麦克德米德诗集
不管怎样,有了王红公,美国文学史就将被重写。战后的美国诗歌或多或少就是“王红公的时代”,就如之前的几十年是“庞德的时代”一样。当然,我们也必须把震撼美国文坛的一个演变考虑在内:这位歌颂异性恋的诗人(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性别歧视的猪”)在人生的最后岁月致力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女诗人。
王红公翻译了两卷中国和日本女诗人选集;翻译编辑了日本当代女诗人白石嘉寿子;他最上乘的翻译是宋代女诗人李清照;他还杜撰了一位住在东京名叫摩利支子的日本年轻女诗人,这位女诗人同时用日语和英语写诗。摩利支子的诗特别出彩,一系列时间顺序排列的短诗描述了主人公的渴望,她时而梦见情人、与其相遇又失散,最终自己慢慢变老。尽管主人公被看成是一位“当代女性”,诗中却只出现了两件现代社会的物品(杀虫剂和弹珠机);诗中多为田园意象而脱下的衣裤则多为传统服饰。主人公以她情人来定位自己,而对她的情人,我们却一无所知,甚至连性别都无从知晓。留在文本里的只有激情:
你的舌摩挲曼妙
入我身,而我
渐成空,晕火
光旋,如体内
一巨珠放大。
这是在美国第一次出现的康乐可诗歌:激情使然,世界化解(诗里是主人公及其情人的身份以及所有外部条件;诗外则是摩利支子的身份),最后激情消散:
终有一天,六寸
长灰将是我们
脑海中激情所留存,
是世上所有爱的
创造和起源
而这一切将永逝。摩利支子的诗作连同王译李清照都是激情的杰作,在美国诗歌里,唯有H.D.晚年的作品《密封的定义》和《冬恋》与其不相伯仲——诗成时,H.D.和王红公都已近晚年,一个是女人,另一个是成了女人的男人。男人成了女人:身份的放弃,自我的超越。当庞德收回《诗章》陷入沉寂;当朱科夫斯基的《A》以放弃作者身份而结尾;王红公则成了另一性。

白 石
嘉寿子


庞德在诗章120中留给我们天堂的理想和不能入天堂的绝望。朱科夫斯基留给我们一个黑洞——“八十朵花”,其诗细密深奥程度非常人能参透。而现在是戴着李清照面具的王红公,他把激情和忧郁留给我们一个女人(男人)在世界永远频临绝灭关头的狂喜:
红藕香残
玉簟秋,
轻解罗裳,
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
锦书来?
雁字回时,
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
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
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1949— ),美国当代作家、散文家、编辑和翻译,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温伯格最先以翻译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而成名,其译作有《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印度之光》和《太阳石》。其他译作还包括维多夫罗的《阿尔塔佐》、比利亚乌鲁塔的《死亡的怀念》、博尔赫斯的《七夜》。他编辑的博尔赫斯《非小说选集》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评论奖。他深谙中国古典诗歌,是《十九种方式读王维》的作者,还是诗人北岛的英译者。他编辑的《新方向中国古典诗歌集萃》被《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选为国际年度最佳图书。
温伯格的政治杂文一针见血、犀利痛快,收录在《9/12》《我所听闻的伊拉克》以及《那里发生了什么:布什编年史》,后者入围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评论奖并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选为国际年度最佳图书。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纸上书》《局外事》《命运痕迹》《星星》《穆罕默德》以及《基本元素》等其散文包罗万象、笔力雄奇、渊博而精微,开创了英语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温伯格还是英国《伦敦书评》、德国《国际文学》和美国《纽约书评》资深评论员,耶鲁大学玛格罗斯世界文学共同体、纽约墨西哥文化院以及新方向出版社顾问。1992年,鉴于他对西语文学在美国传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温伯格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笔会克罗瓦库司大奖的作家。2000年,他获得由墨西哥政府颁发给国际友人的最高荣誉–阿兹特克雄鹰勋章,他是获此殊荣的仅有的一位美国作家。温伯格现居美国纽约市。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4期,责任编辑: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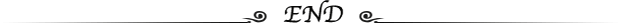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