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读 | 琳•莱【法国】:卡利班的情结(外一篇)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琳达·莱作 李焰明译
未被教化的卡利班像雨蛙一样说话,像风一样自由。博学者、善于利用书籍的普洛斯彼罗教他学语言。“我看你可怜,”普洛斯彼罗说,“才不辞辛苦地教你说话,每时每刻教你认识各种事物;你这个蛮人那时连自己想什么都不知道!你像个野兽一样乱叫,是我教你用话语表达自己的想法。”


普洛斯彼罗掌握着语言的秘密。他传播文化的种种益处。但其传播文化的使命对卡利班是致命的一击,因为这个“蠢物”很清楚掠夺是怎么回事,他自己就是受害者。所以他才会这样指控普洛斯彼罗:“这岛属于我,是你从我手里夺了去。你刚来的时候抚摸我,对我非常友好,给我有浆果的水喝,告诉我白天亮着的大的光的名字和夜里亮着的小的光的名字;我因此对你有了好感,将岛上所有财富都指点给你看……让你知道这一切,我真该死!……现在我成了你唯一的臣民,而不久前我自称为王……”
在普洛斯彼罗及搁浅在岛上的那不勒斯皇室看来,卡利班只是个“魔鬼”。但这个在沼泽地无所事事的牛首人身怪物也表现出普洛斯彼罗的阴暗面。他以梦想反对言说之欲,他与此欲抗争,因为学会说话使他远离了感受性。整部戏里只有一次,当他没有直面普洛斯彼罗而情不自禁吐露心声时,这野蛮人发出了另一种声音,童真的声音:“这岛充满各种回声、音符和悦耳的歌曲,令人愉悦,与人无害。我的耳边时而是成千上万的乐器在震响,时而是一些妙音,刚从酣睡中醒来的我便又沉沉睡去。于是,梦中,我仿佛看见云之门开启,露出无数财宝,就要落在我身上。梦是如此的美,我醒来后哭着还想再做一遍。”这番心声是不是讲给两个有犯罪意图的醉汉听的无关紧要,它以近乎孩童般的词语表达了一种怀旧之情。更擅长操纵词语的普洛斯彼罗带着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机警的智慧对此进行了概括:“就本质而言我们同梦想是一致的,我们平凡的生活,一个小睡就能使其趋于完美。”
普洛斯彼罗,上帝的使者,有两个仆人:一个是热情的爱丽儿,另一个是顽抗的卡利班。爱丽儿是空中精灵。卡利班是地道里的人。爱丽儿象征着光明。卡利班象征着黑暗。魔法师的法术需要爱丽儿的辅助,但也少不了卡利班,后者是他获取知识的源头。普洛斯彼罗接替西考拉克斯的王位,他的一部分延续着这巫婆的事业。化为卡利班的这个危险部分于他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对任何一个创造者那样。他试图教化卡利班,也想控制他。这是他内心的魔鬼,也是他的守护神,融入其心性的精灵。忒修斯不迎战米诺陶洛斯就不可能发现迷宫的秘密。普洛斯彼罗若在卡利班身上看不到自己就不可能击败巫婆的妖术,那巫婆竭尽毁灭和憎恶之事。普洛斯彼罗使爱丽儿获得自由,但也声明“魔鬼”就是他自己。普洛斯彼罗的语言不仅归功于召之即来的爱丽儿,也得益于岛之子卡利班,该岛被认为是一个“痛苦、焦虑、神奇和惊愕之地”。卡利班不需要词语。这个卑微的人,未定型的马尔多罗,从所学的语言里得到的全部益处,就是知道怎样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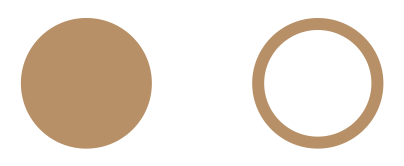

上帝用话语创造了世界。普洛斯彼罗即是话语的产物。普洛斯彼罗教卡利班说话。卡利班于是学着用一种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作家选择非自己生长环境的语言创作,他看待自己与这另一种语言的关系就如同卡利班看待他对普洛斯彼罗的屈从。他被主人的语言所吸引,想成为像普洛斯彼罗那样到达艺术顶峰的卡利班,但他对所获得的这种语言和这种文化的迷恋带有论战的意图。选择用法语创作的流亡作家深受卡利班的情结之苦。他对语言的忠诚掺杂着反叛。
他体内的那个卡利班反对他的选择,想制造分歧。无论他做什么,设想哪种计策来掩饰原初的悲伤、填补空虚,他总是听见其影子对他说他已无处立足。他在出生地没有自己的位置,因为他失去了卡夫卡所称的“祖国有声的气息”。接待国的土地上也没有他的位置。他在此感觉是个可疑的宾客,一个入侵者。但他可以说实现了所有作家的梦,因为他挣脱了个人为稳固其创作而定居一方的束缚。但他经常会被问到如何界定其身份。法国作家?用法语创作的越南作家?越南裔法国作家?每当此时,他就感觉自己像伊索寓言里那个面对敌手随机应变的蝙蝠。当蝙蝠受到憎恨禽鸟的黄鼠狼攻击时,就声称自己不属于鸟类。而如果追击它的是个不喜欢哺乳动物的黄鼠狼,它便说自己不属于哺乳动物,而是鸟类。这个计谋使得两栖作家避免一切身份界定,不被两个阵营的黄鼠狼吞食。但他总是因为要在两者中作抉择而处于一种不真实的境地,因为他未在此地又不在他处,他还无法界定自己。
他难以接受内心的矛盾,他只有把自己的抉择不视为背叛而是当做选择一种命运,才能克服这个障碍。那么,他的语言就不再是从普洛斯彼罗那里学来并且像卡利班那样只用来骂人的语言。

卡利班只有与爱丽儿结为一体,变成爱丽儿,那个“自由地回到空中”的人时,他的语言才成为自己的。爱丽儿对普洛斯彼罗如影随风,自然不会与他抗争。
爱丽儿不是奴隶,他不想成为主人,但他所向无敌并且像风一样自由。“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命运的使者”,爱丽儿说。他实现了文学的双重梦想:他救起落水者并引导普洛斯彼罗放弃“狂暴的魔术”,懂得“做善事比复仇好”。
爱丽儿为普洛斯彼罗效劳,同时与某个至高无上的神作战。不是为权而战,而是同死作战(即普洛斯彼罗制造的海难者的死),是为了让岛屿主人兑现还他自由,那“空气般的自由”之诺言而进行的一场战斗。
卡利班这个魔鬼、怪物、怀有梦想的孩子,便是那黑暗部分,作家与其缔结了一份共存契约。是线团把他与未表达的东西、与文字前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爱丽儿便是纺线的织女。卡利班策划阴谋,复仇之意愿在其中为自己寻找新主人。爱丽儿使用法术在岛上发动革命。他的想象力是知识和记忆。他显现的智慧及其古典主义是武器,没有这些武器,卡利班的语言只是同词语发明者作对的普洛斯彼罗的语言。
卡利班竭尽破坏之能事,普洛斯彼罗只想着复仇,爱丽儿践行道德。尽管爱丽儿忠实地履行助手的职责,实际上他就是革命的发动者,这场革命结束了西考拉克斯的继任者普洛斯彼罗十二年的统治。西考拉克斯代表毁灭,黑暗时代。普洛斯彼罗体现文明的力量,爱丽儿象征着奔向自由的激情。作为乌有之地之子,爱丽儿也是卡利班的兄弟。他将卡利班的语言译成真理之语言。但他的手段与普洛斯彼罗不同:普洛斯彼罗采取迫害、监禁的方式,爱丽儿则是释放。爱丽儿属于神话。那个将光明带给人类的盗火者的神话。他那似空气般轻盈的法术使普洛斯彼罗的魔法(一种威力无边的魔法)化为乌有。被征服的普洛斯彼罗变得有人情味了:“我已将我的魔法全部抛弃,只剩下属于我自己的微弱力量!”
普洛斯彼罗的结语是作家的起点。他仅拥有自身的力量,这力量具有双重性,一半是卡利班,一半是爱丽儿。两个兄弟不再互相仇视。写作,就是把一个人的语言翻译成另一个人的语言。不再是归属某个国家就得放弃另一个国家,而是从深渊升向自由的天空。那个只在即将被吞食时才知道自己是哺乳动物或鸟类的蝙蝠,从此可以展开它变化不定的翅膀。以为自己的翅膀已折断、不知道飞往哪片天空的作家牢记松尾芭蕉对弟子的忠告。弟子造了个俳句:“一只红蜻蜓/拔去它的翅膀/一个辣椒。”松尾芭蕉也以俳句回应他:“一个辣椒/给它安上翅膀/一只红蜻蜓。”
琳达·莱作 李焰明译
我是什么?英格博格·巴赫曼自忖。一万颗粒子还是乌有?乌拉圭作家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在《厚颜无耻的人之日记》里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一天夜里他发现他的身体,即“厚颜无耻的人”不属于他,他的头即“她”单独活着。米修更有狂言,称人的体内不止一个人。曾经的我同现在的我说话。我可能成为的那个人同我想成为的那个人说话。是人,就是让自己有可能成为混杂在一起的无数亲密影子。布朗肖总结道:创造一个人物,用“他”替代“我”,就是任自己被带出身体以便死后继续活着,就是消除固有的分歧。一切文学都是自我放逐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旨在消灭自我。作家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戈利亚德金先生一同冒险,看见四周出现大量跟他一样的人。西班牙诗人何塞·安赫尔·巴伦特表达了一切创造者的愿望:“让我在一次新生中死去吧。”对此,博尔赫斯以诗回应道“布朗宁决定做个诗人”。布朗宁断然离开自己的身体。他便是那无我之我,其命运处于濒死和复活的循环往复中。



艾米莉·狄金森擅长写短诗,这些诗对她来说是“日常喝的上等酒”。她在一首短诗中写道:“我不可能独处/因无数人造访我。”她在阿莫斯特小镇过着隐居的生活,与逝去的家人为伴,他们不是幽灵,是在者。绝对的在者,活在献身于诗歌、视其为写给世人的一封信的生活中。她没有公开这些信,她无比珍视自己的使命,因而拒绝诗人之身份。孤独的艾米莉既是缺席者(遁世,逃避自我),又是呈现者,当她体内的诗人成为她理解其痛苦的每个在者时。而做个诗人,成为象征肉身的语词,也就是形成血肉,对死有深刻的认识,从而赞美生之辉煌。
无数人造访我,艾米莉·狄金森说。这位美国女诗人死后半个世纪,丹麦一位喜欢使用假名、玩变脸游戏的女小说家在其《哥特故事七篇》里坦言道:“我可以是无数女人。她们是否快乐,是疯子还是有理智的人,这无关紧要。(……)我愿成为好多人,我的情感和生活不再仅与一个女人关联。”无与伦比的凯伦·布里克森【凯·布里克森(1885—1962),丹麦女作家。作品大多描写没落贵族的生活,著有短篇小说集《哥特故事七篇》《冬天的故事》等】希望自己是个魔鬼般的但诚实的讲故事者,她在书中安置陷阱和魔镜,读者无法捕捉其隐秘部分。布里克森的作品似乎是对女哲学家玛利亚·桑布拉诺留给我们的那句教导的回应:“一切知识都是同某怪物的一场战斗。”
玛利亚·桑布拉诺从奥尔特加·加塞特【奥·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曾在马德里大学任形而上学教授,提出自称为“生命理性的形而上学”,著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群众的反抗》】那里继承了“思考,即将我们的个性置于真实事物面前”之观念。但她身上潜伏着一个诗人,自称是个个性很强的人,被无数人造访并且同佩索阿一样认为自己最大独特性在于:大多数人凭感觉思想,而她则用思想去感受。思想和原初感受都源自同怪物的这场战斗。即先同他的自我作斗争,引起分裂。


艾米莉·狄金森、凯伦·布里克森和玛利亚·桑布拉诺。三个与生活分离的女人。三个不愿受自我束缚和时代局限的孤独女人。三个致力于搅乱定义、打开边界(地理的和精神的边界),对男性和女性以及文学体裁的种种模式提出质疑而不可征服的女人。
因此,将这三个形象按某个体裁归类是最保险的,如果不特别在意表象的话。布里克森的辛辣讽刺充满哲理,她富有同情心的散文洋溢着浓浓诗意,同样,桑布拉诺的作品处处是隐秘的忏悔。狄金森的诗讲述的是炽热的灵魂,也可当做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来读,孤独变奏曲由此产下忧伤的思想。
三位女作家只从自我出发写作。但她们的自我是只候鸟,写作于是成为总是重新开始的一次次企图逃离。“我想写一本可以自由幻想的书”,达雷尔【劳伦斯·达雷尔(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曾任英国驻埃及大使馆新闻官员,著有长篇小说《亚历山大四部曲》,诗作《城市、平原和人民》等】在《亚历山大四部曲》中说,这是一部逃避定性的小说,一部发出尖叫声、寻求和谐、向卡瓦菲【康斯坦丁·卡瓦菲(1863—1933),希腊诗人,一生写短诗约二百首,多取材于古希腊历史神话,其文风和格调是现实主义的】的诗致敬、在一个如亚历山大的城市周边遐想的小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亚历山大城(因其居民总是具有双重人格),四部曲的每个人物都有慌乱、令人不安的一面(这与城市一致),他们既是女性又是男性,显现又隐蔽,玩弄明暗对比就像摆弄一出情欲骚动的影子戏。


达雷尔的愿望,写一部可以自由幻想的书,也是狄金森、布里克森和玛利亚·桑布拉诺的愿望。是所有作家的愿望。分身,增多,是个人同时也是整个世界,构思一本自我逃离的书,一本摆脱一切束缚、可以行走的书,把诗人的问候带到他心爱的地方,即便他只是在梦里造访过这些地方。
我们不要受骗上当。玛利亚·桑布拉诺说的这场同怪物的战斗也是一场与魔鬼的激战。如果写作可以是这样的许诺——同怪物天使的一夜鏖战后黎明将升起,那么与另一个我相遇就是威胁,死亡的征兆。浪漫主义作家将此变成他们最喜爱的主题。爱伦·坡在《威廉·威尔逊》里描述了主宰那场与其相像的人即与“同一性中的绝对存在者”较量的必然结果。当威廉·威尔逊一剑刺向那个与其相像的人的胸膛杀死他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声音(仿佛是自己的声音)对他轻声说:“你已获胜,我倒下了。但从此以后你也死了,与世界断绝,与上帝和希望断绝!你存在于我之中,你从我死亡的影子中(其实也是你的死亡)看到,你是多么彻底地杀死了你自己!”这非同一般的感觉,这预先体验死亡的滋味,身上有另一个我且作为威胁出现的这一发现,博尔赫斯的文本再现了由此带来的恐惧感以及精神的超现实。
一个文本可能源自某种恐惧感,源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极度紧张而生发的精神短路。“失去另一个我,焦虑便出现了,”玛利亚·桑布拉诺在《林中空地》写道。“存在与生命分离。生命丧失了存在,存在便停驻,毫无生气却也不死。”然而,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产生于某个纯粹的恐惧时刻。真正的文学是炼金术,从疯狂中提取元素制造黑钻石,恐惧的凝练。从此,威胁变成机遇,恐惧成为对一个反世界的系统探索。文学的奇迹属于数学解法而非神秘灵感。
或许自我的秘密有待在以下种种可能性中被发现:当威胁变成机遇,焦虑因升华作用而消除,自我超越变成道德需求从而排除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这时,潜伏在体内的另一个人,直面他的另一个人呈现了,不再是作为“伟大的我是什么诸多未写完的信息”(此语出自西尔维娅·普拉特),而是作为在世界奔跑的无数人呈现的,这个世界已从仅仅是自己的诅咒中解脱出来。另一个人像哨兵那样出现了,在他巡视的那片领土上,对“自我”的各区域探索使得自传被抬到神话的高度。
乔治·斯坦纳在《真正的在场》里说作家是自己的读者,他颠覆的是自己。对自身革命始于想成为二元论者,成为综合之敌。一切生命都具有双重性,对自我的追寻同样是在召唤神话里存在两面性的生灵中获得认知的。写作,就是抓住机遇成为斯芬克斯、半人马、美人鱼、独角兽,如此多的混合形象。因为写作的需要不是产生于快乐的盈满,而是来自无法弥补的空虚感。人们发现自己是个瘸子、跛脚魔鬼、“落到地面遭众人嘲笑”的信天翁。人们知道自己是可怜的、无能的、软弱的。文学能使这些不足变成种种可能性,朝向未知的通道。人类历史“是一场失望与希望、可能的现实与不可能的梦想、节制和狂热之间的战斗”,玛利亚·桑布拉诺说。艺术作品就处于左右为难状态并进行超越。这是在隐秘的裂口与魔力中间的摇摆不定,因这魔力裂缝里突然冒出一颗跳舞的星星。两难的困境要求人们推倒人类心胸狭隘的隔墙、最终消灭自我。
东方哲学没有把内心迁移定义为我们沿循的路,而是引导我们前进的道。苏格拉底式的思想把生命描述为从未知走向未知。艺术作品也许只是一种迁移,我们不知去往哪里也不知起点在何处。伟大文学触及到了非理性。纳博科夫说《哈姆雷特》是一个患神经症的博学者之谵妄性幻觉,说果戈理的《外套》是个怪诞的噩梦,在看不清的生命道路上挖了无数暗坑。纳博科夫论文学的随笔尽是这类突发奇想。但这些不恭的断言也道出了一个创造者与其先辈的亲密关系。纳博科夫尊果戈理为骗术大师,吸血鬼果戈理,会说腹语的果戈理,疯子果戈理,神秘主义者果戈理。果戈理笔下的所有人物都痴迷于骗术,他摘掉这些人的假面具,并把他自己个性中最阴暗的部分暴露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清他的真面目,向人类昭示自我。残酷的纳博科夫在向我们传达果戈理的结论:人类自我只是个幽灵,它试图掩饰地狱可恶的臭气,它浑身都是这臭味,夹杂着玫瑰水的芳香。



博尔赫斯所设计的迷宫旨在让自我这只猎犬迷失在其复杂的诡辩里。调查转向审讯,审讯者我对焦虑不安的我所要求的,就是承认其幽灵身份。一个苛求知识的幽灵在镜子迷宫里游荡。他在寻找生命的真理,而作为最后真理出现的是死亡,这死亡甚至不是亨利·詹姆斯弥留之际欢呼其显现的那件“崇高的事情”。最后真理只有几个词,不合时宜、残缺不全的词,从别人那儿借来的词,提醒人们一切知识都是模糊记忆,任何所谓新事物都只是一种遗忘。
迷宫是自我同忧虑的显影,即牛首人身怪物作战时游荡的表现形式之一。那个潜入迷宫杀死怪物(他的自我怪物)的是被复仇女神分尸的奥菲斯的影子。但被撕成碎块的奥菲斯唱着他最美的歌。玛利亚·桑布拉诺在她的散文《黎明》中提及寻找一门语言,这语言如同初生的火,一种标志,它来源于忧虑的夜晚,因而将是“肺腑之音,血之光”。要找的就是这种语言,一门如同一次试图存在的语言,一个乌托邦,一门变成热情的语言,即创造一种在恐惧门前跳的舞蹈。

作者简介

琳达·莱(Linda Lê,1963—),越南裔法国女作家。出生于越南大叻,六岁时跟随家人逃亡到胡志明市以躲避越南战争。十四岁时远赴法国学习并定居,至今已出版作品十余本,包括《温柔的吸血鬼》《逃亡》《独奏》《罪恶福音书》等等。由于她的低调,琳达被媒体形容为“藏在洞中的熊”,评论称她“悄无声息”地跻身于文学界。而她的作品风格却大气磅礴,带有“继承于十七世纪文学的剖析力和雄辩力”的印记。
琳达·莱童年时期接受法语教育,因此从小就感受到了自己和越南孩子的文化差异,这种深深的孤独感促使她将自己埋藏在书本和阅读中。她从童年时期起就着迷于那些离自己遥远的巨著,对雨果和巴尔扎克情有独钟。然而来到法国之后,她依然面临着身份认同的焦虑:“我依然感觉在流浪。即便在法国生活多年,我也从未对自己说‘这是我的祖国’。但我也不觉得越南是我的祖国。”
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法国作家?用法语创作的越南作家?越南裔法国作家?琳达在《卡利班的情结》一文中,借着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一系列隐喻,对于“身份”提出终极拷问。而在另一篇《自我的栖移》中,作家描述了三位“从自我出发写作”的女作家:艾米莉·狄金森、凯伦·布里克森和玛利亚·桑布拉诺——三个“与生活分离的,不愿受自我束缚和时代局限的孤独女人……写作于是成为总是重新开始的一次次企图逃离”——似乎是通过她们来影射自己的写作历程。本期收录的这两篇只是随笔集《卡利班的情结》(le complexe de Caliban,2005)一书中的一小部分,该书实则是琳达阅读雨果、艾米尔、维吉尔、莎士比亚等作家著作时的读书笔记,也是她童年记忆的一瞥。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3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