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宝生(1942-2023)| 《英国女人》(黄宝生译,载于《世界文学》1988年第4期)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世界文学》前主编黄宝生先生于2023年3月23日在北京仙逝,享年80岁。黄先生毕生致力于印度学和佛教学,笔耕不辍,出版相关领域的专著及译著四十余部。此外,黄先生还曾翻译过英、美、印度等国的现当代英语文学作品。英国小说家、剧作家露丝·普罗尔·贾布瓦拉的作品就是通过黄先生的译笔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1988年第4期《世界文学》刊登了贾布瓦拉的三篇短篇小说,译文皆是出自黄先生之手。今天我们重刊其中的《英国女人》,以此纪念这位为文明传承、文化传播、文学传译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


露丝·普罗尔·贾布瓦拉作 黄宝生译
这个英国女人,她的名字叫萨迪,决定离开印度时,已经五十二岁。她几乎连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她感到年轻和自由,在五十二岁这把年纪上!她的手提包已经装好,她就要逃脱,就要出奔,撇下一切——丈夫、儿女、孙儿孙女和三十年的婚姻生活。她的心情轻松,她的行李轻便。她要带走的东西少得出乎意外。她的大多数衣服都不值得带走。最近这些年,她几乎只穿由一个戴头巾的小裁缝缝制的老式棉布上衣,她还有些纱丽,但不准备带走。她甚至不想再穿这些纱丽。
面对她即将出走,哭得最伤心的是安纳布尔纳——她丈夫的情妇。安纳布尔纳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她看看已经装好的手提包,也像萨迪一样,为里面东西之少而感到意外。她问道:“你就带这些吗?”萨迪回答道:“就带这些。”安纳布尔纳又涌出一阵热泪。
“这样很好,”萨迪劝说道,“少带东西,轻装旅行,这不很好吗?”
“哦!你是这样圣洁,”安纳布尔纳用萨迪的袖子擦拭眼泪,对她说道,“真的,你远比我更像印度人。”
“胡说,”萨迪说道。她真是那么想的。十足的胡说。
然而,这倒是真的:如果像许多人喜欢相信的那样,印度人意味“圣洁的人”,那么,安纳布尔纳是个例外。她是个非常非常世俗的人。她体格粗壮,皮肤绷紧而有光泽,眼睛和牙齿明亮,头发用黑染料抹得光滑油亮。她喜爱衣服、珠宝和油腻食物。虽然她和这个英国女人年纪不相上下,但精力远为充沛。她走动时,纱丽瑟瑟有声,手镯叮咚作响。
“你真的要走?”
安纳布尔纳总是问这个问题。而萨迪也总是扪心自问这个问题。但她们以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问这个问题。安纳布尔纳感到惊诧和悲哀(是的,悲哀——她爱这个英国女人)。而萨迪快乐得自己都不相信了。这难道是真的吗?她反复问自己。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印度了?她的心欢快地跳跃,她难以抑制自己脸上的微笑。她不想让任何人猜疑到她的感情。她为自己的无情而羞愧。但她还是微笑,越来越抑制不住,心中的快乐像一汪泉水在突涌。
上星期,她去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告别。他们两个现在在孟买有各自的家庭。她的儿子德维已经结婚两年,刚生了个女儿;她的女儿莫尼卡有三个男孩。德维在一家广告公司有份好差事;莫尼卡也工作,因为她精力太充沛,在家呆不住。她称自已是活跃的女性。正是这样,她满城里转,为她给一家妇女杂志撰写的文章进行采访;她用孟买流行的最新俚语谈话;她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在里面充任主角。莫尼卡长得很像印度人——她的眼珠乌黑,皮肤有光泽。比起这个憔悴苍白的英国女人,她实在更像安纳布尔纳。
莫尼卡虽然是个欢快的人,但也愿意进行严肃的讨论。她试图与她的母亲进行一次这样的讨论。她说道:“可是,妈妈,为什么你要走?”她用一种在严肃时刻特有的严肃表情望着她。


萨迪不知道怎样回答。她能说什么呢?但是,她必须说点什么,否则莫尼卡的感情会受到伤害。于是,她也变得庄重起来。她对自己的女儿解释说,人到老年,会得怀乡病,思念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这种怀乡病越来越严重,最终生活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莫尼卡理解她说的话,表示同情。她计划好了他们所有人怎样到英国去探望她。她答应等男孩长大后,会送他们到老太太那里去度假。她现在完全同意母亲离开,因此萨迪为自己向她作出的这番解释感到高兴。如果德维问她这个问题,她也准备这样解释,可是他没问。他和他的妻子在那些天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公寓里突然蔓延水痘,他们怕自己的婴儿传染上。但他们也答应经常去英国探望她。
只有安纳布尔纳还在哭泣。她望着萨迪的小提箱哭泣,而后望着萨迪哭泣。她总是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萨迪试图用说服莫尼卡的那些话来说服她,但安纳布尔纳置若罔闻。在她听来,这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她是对的,萨迪自己也明白。她问萨迪难道不会怀念他们所有人,怀念他们对她的爱?难道不会怀念她度过的岁月,生活过的地方,过去三十年中经历的一切?整整三十年啊!她感到震惊,一次又一次地哭泣。萨迪也感到震惊,多么长的时间啊!安纳布尔纳说,印度媳妇也想念自己的娘家,在刚结婚的时候,总是盼着回娘家探望。但天长日久,她越来越与婆家融为一体,那些早年的回忆渐渐消褪,最后成为隐埋在心底的一种甜蜜感。萨迪知道安纳布尔纳说的是对的,但也知道这完全不适合她的情况,因为她现在的感情并不是柔和的怀乡感情。
这个英国女人不愿意回忆她当初来到这里生活的那些岁月。这仿佛是她想要否认那时有过的快乐。那时她多么喜爱这里的一切!那时她从不怀念老家或英国。她丈夫全家赞赏并鼓励她努力成为印度人。他们所有人——婆婆、姑姨、堂姐妹和朋友,会全体出动,挤进他们家的小汽车(蓝色的绸布窗帘小心地拉上,挡住外来的视线),开到市场,为萨迪买纱丽。至于选购什么样的纱丽,他们从不充分征求她的意见。一旦他们买回家来,便把她拖来拽去,互相争论怎样裹住她最合适。他们帮她穿戴完毕,便往后靠靠,以便表示赞赏,只是他们没有发出赞赏,而常常是望着她的模样忍俊不禁。她却不在乎。是的,她知道自己的身材太高,太瘦,太英国化,不适宜穿纱丽,但她还是喜欢穿,喜欢感到自己是印度人。她也试图学会印地语。这也使大家感到有趣。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反复念一些词汇,然后由于她的发音而爆发一阵阵欢笑。这个家庭里的所有妇女,人人都有许多趣事。她们健康、富裕和欢快。这个家庭决不是因循守旧的。尽管她们在家里的生活有点深闺制度封闭、沉闷的味道,但她们开放的思想充满活力和好奇。婆婆本人那时早过了六十岁,她用大量时间阅读方言小说,还尝试写一些自传性素描,描绘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高级种姓家庭的生活。她在晚年学会抽烟,抽上了瘾,结果成为一个一支接一支抽烟的人。萨迪现在一想起她,眼前就呈现她斜躺在席地而铺的绣花垫子上,一只胳膊撑在长枕上,背后塞了些靠垫,透过她的眼镜在阅读一本破旧发黄的小册子,全身笼罩在缭绕的香烟烟雾中。


安纳布尔纳常常谈起那些日子。安纳布尔纳是这家的一个表亲。她逃离她的丈夫(她的丈夫酗酒,人们还私下传说他沉湎于同性恋),来到这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安纳布尔纳谈起那些遥远的往事时,仿佛人人都还活着,人人都像当年那样年轻和欢快。她常常说:“如果希利罗多(或者罗蒂迦,或者罗克莎,或者钱德罗莱卡)现在还在,她会笑成什么样!”但是,希利罗多已经在二十年前死于伤寒;罗克莎已经嫁给一个尼泊尔将军,住在加德满都;钱德罗莱卡因爱情受挫而服毒自尽。然而,对于安纳布尔纳来说,仿佛人人都还在。她回想起某件往事,活灵活现描述每个细节,以致萨迪也仿佛能听到那些日子的声音。最后,安纳布尔纳回到现实。她的一只手臂伸展着,丰满的手掌向上朝向天国,她承认她们都已离去,其中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她转过身子,望着这个英国女人,说道:“现在,你也要走了。”她的眼神里充满责备。
情妇会责备夫人,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安纳布尔纳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么多年来,是她代替这个英国女人尽到一个妻子的全部职责。在她俩之间从来没有怨恨或妒忌。相反,萨迪始终感激她。她知道她丈夫在与安纳布尔纳相好以前,总是去找别的女人。他必须这样;他的精力如此旺盛,他需要像他一样健壮的女人。这些女人常常是年轻的妓女。但很久以来,他已经满足于安纳布尔纳。近些年来,他体重大增。这是安纳布尔纳的过错。她把他喂得太好,怂恿他贪恋美食。他进餐次数频繁,又难以消化,以致在两餐间隔时间里都无法挪动身子。他躺在阳台上为他特设的一张躺椅上,沉重地呼吸着。有时他噗哧噗哧抽水烟。这水烟筒就放在他伸手能够到的地方。他一连几个钟头躺在那里,而安纳布尔纳坐在躺椅另一头,与他神聊,让他开开心。他喜欢这样,但如果她没有时间陪他,他也一点都不在乎。一旦他感到需要谈话,便召唤一个仆人来坐在他躺椅旁边的地毯上。
萨迪最初认识他时,他是牛津大学学生。那时候,他是个身材细长的小伙子,眼神火热,浓密的头发覆盖前额。他总是面带微笑,总是忙碌不停。他喜欢当学生,虽然他从不设法毕业,但还是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他举办早餐聚会,有自己的酒商和一辆红色小汽车。他每星期要驾车去伦敦好几次。他常常发现新的乐趣,譬如福特农和梅森公司的船具,船上香槟酒会。萨迪是在十分严格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的家庭经济上还算宽裕,但奉行高度的自我克制原则,推崇高尚的思想,不赞成奢华的生活,萨迪本人是个严肃的姑娘,是个节俭、严格、有教养的英国美人。她也认为自己奉行同样的原则。但是,这个印度青年使她看到自己本性的另一面。当他返回印度时,她无法与他挥手诀别。她随他而去,嫁给他,甚至比在英国的时候更爱他。他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回来后如鱼得水。有时萨迪一连几天看不到他——他和朋友结伴狩猎或探险去了——但她并不介意。她和其他妇女一起呆在家里,像他一样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在夏天的夜晚,他们全都坐在花园的喷泉旁。钱德罗莱卡用甜美的歌喉唱着忧伤的山歌,罗蒂迦用琵琶那样的弦琴为她伴奏。月儿明亮,安纳布尔纳为大家切芒果。这些芒果的味儿与盛开的灌木丛逸出的花香混合,如此强烈,如此令人陶醉,以致这个英国女人今天回想起那些夜晚,历历在目的情景也总是由这种香味而引发。


安纳布尔纳和萨迪的丈夫每天晚上玩牌。他们赌钱,安纳布尔纳经常输,输了就耍赖。她总是拒绝付钱。而第二天晚上,他们很容易忘记她的赌债,又从零开始。但是,一旦他输了,那她就坚持要立即付钱。她得意洋洋地笑着,伸出她的手,手掌贪婪地忽开忽合,叫喊着:“快,付钱!”她也叫萨迪和仆人们来证实他输了。那些晚上经常是欢快的。或迟或早,常常在玩牌中间,她睡着了。一次,安纳布尔纳睡着了,周围一切十分宁静。仆人们已经关了灯,回自己的住处去了。萨迪的丈夫坐在他的躺椅上,朝花园里凝望,抽上几口水烟。萨迪在楼上自己的卧室。毫无动静,没有声响,直到萨迪的丈夫笨重地抬起身子时,大声地叹了一口气。他唤醒安纳布尔纳,他们互相搀扶着上楼,进入他们的卧室,躺在他们柔软的大床上,顷刻之间酣然入睡,直到天明。而萨迪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入睡。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反复进行自我争辩。她思绪起伏,犹如暴风雨中的大海。周围一切安然入睡,这反而加剧她的烦躁。她渴望某种响应,渴望自身之外某种东西或某人感受到她的内心活动。但是,只有静谧和沉睡。她走出房间,来到阳台。花园里昏沉朦胧,在月光映照下忽明忽暗。偶然,非常非常偶然,一只鸟儿醒来,在树上沙沙作响。
正是在这个孤寂的时刻,她作出了离开的决定。对于别人——而在正式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刹那,甚至对于她自己——这似乎是个突然的决定。但事实上,她回想起来,她的这个决定已经酝酿了二十年。她甚至能确切指出二十年前的哪一天,她第一次发觉自己不想继续在这里生活。那时,她的儿子得了一种印度儿童常得的神秘的突发性疾病。他躺在一张大床上发着高烧,两眼火红。他十分安静,只是偶尔发出呻吟。家里所有的女人全都围在他的床边,七嘴八舌,提供不同的疗法。她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板上。婆婆盘腿坐在他的床头,眼镜架在鼻梁上,抽着香烟,一页一页读着小说。她一次又一次发出安抚德维的哄声,捏他的脚踝。安纳布尔纳坐在他的身边,用冰块擦他的额头。每次德维呻吟时,她们异口同声:“哦,可怜的宝宝,可怜的宝宝。”仆人走进走出,他们也说道:“哦,可怜的宝宝,”怜悯地望着他。这个英国女人记得自己童年时代生病卧床的情景:她一连几个钟头舒服地躺着,闲得发慌,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树,望着饱满的、湿漉漉的雨点拍击窗玻璃,而后流下。她的母亲是唯一进入房间的人,那是在她服药的时间。可是,德维不喜欢那样。他要每个人都陪着他。如果哪个姑姑离开房间的时间长了些,他就会用微弱的声音问起她,别人就得去找回她。
萨迪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但是,那里也好不了多少。这天的天气照例昏黄阴沉,太阳淹没在尘雾中。她充满恐惧,为德维,也为自己,仿佛他俩要被什么吞噬。被什么呢?暑热?里面这些可爱的妇女?像滋生热病的沼泽那样混浊的空气?她渴望在一个凉爽的地方独自陪伴她的病孩。但她知道这不可能,因为他俩属于这里的这座住宅,里面挤满亲属,在昏黄的天空下闷热窒息。她永远也不能忘却此时此刻的绝望,尽管在以后的岁月曾多次遇到类似情况。但这是第一次。


她站在阳台上的这会儿,看到她的丈夫回家来了。他是这个阴沉天气中的唯一亮点。他身穿上浆的印度白衬衫,缀有小宝石纽扣。因为她站在阳台上,他仰脸望着她,朝她微笑。他已不再是她最初见到的身材细长的小伙子,但也不像现在这样肥胖。是的,他那时正当盛年,多么健壮!他从外面的楼梯奔跑上来,问她道:“他怎样了?”
“他还能怎样?”她回答道,“家里所有人都呆在那儿。”
他对她的语调感到惊讶,停止微笑,忧虑地望着她。她现在的气儿不打一处来,不光是暑热和挤满人的房间,还因为看到他如此年富力强,春风满面,而她——哦,她感到筋疲力尽,痛苦失望,她知道自己看上去就是这副模样。她想象他去寻找的那些妓女。她似乎能看到和闻到她们的年轻的肉体,它们扭动着,丰满,黝黑,涂抹了芳香的油膏,滑腻腻的。
她以颤抖的声音说道:“那个可怜的孩子快给他们闷死了——他们不让他呼吸。看来没有一个人懂得起码的卫生常识。”
他知道她话里有话,继续忧虑地望着她。“你病了?”他问道,伸手摸她的额头。而她把身子往后缩,他充满同情地问道:“怎么了?”
他们刚才一直是低声谈话的,但安纳布尔纳在挤满人的房间里照样觉察到出了问题。她离开床边,走出来到他们这儿来。她以探询的目光望着萨迪的丈夫。他俩那时还不是情人。但他俩之间有一种那个家庭中所有成员之间都有的直觉的理解。
“她不舒服了。”他说道。
“我好好的!我压根儿好好的!”萨迪涌出了泪水。她控制不住泪水。她忿怒地擦去脸上这些可笑的泪水。
他俩顿时充满柔情。安纳布尔纳张臂抱住她;她的丈夫抚摩她的背。她努力挣脱身子,他俩以为她又要发泄一次怨忿,加倍关心起来。最后,她哭喊道:“真热啊!”确实,她几乎透不过气来,她的身子在肥胖的安纳布尔纳的挤压下汗流如注。于是,安纳布尔纳放开她。他俩站在那里,忧心忡忡地望着她。这两张容光焕发的圆脸望着她,怀着爱意,怀着怜悯,她感到无法忍受。她怕自己涌出泪水。她蔑视这些泪水,但她知道他俩不仅等待,甚至盼望这些泪水。于是,她转过身子,沿着阳台匆匆离开。这阳台围绕整座住宅,像是回廊。她躲进自己的卧室,锁上门。他俩跟随而来,急切地敲门,恳求她让他俩进去。她拒绝开门。她能听到他俩在门外谈论她。他俩是通情达理的,懂得人们有时确实会这样心烦意乱的,这时别人就有责任去安慰和帮助。
她过去一直受到安慰和帮助。她现在仍然受到安慰和帮助。安纳布尔纳取出她的手提箱里的所有东西,按照她认为更好的方式重新整理。她特意缝制了一些鞋袋。事实上,她愿意给她定做整套全新的衣装。她说,如果萨迪的小提箱里只装着那几件破旧衣服,让人看到了像什么样子?萨迪心中暗想:让谁看到?她在那里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了。有几个远房亲戚,一个老同学。她已经离开那里三十年,没有来往,没有通信,然而她就要回家!回家!喜悦的浪潮再次涌上她的心头,为了能承受它,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连一件珠宝首饰也没有。”安纳布尔纳埋怨道。
萨迪笑了。她早已把所有的珠宝首饰给了莫尼卡和德维的妻子,并为自己摆脱这些沉甸甸的、价值昂贵的金首饰而高兴。这些首饰是她在这个家庭中享有的一份,但她从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她肯定无法佩戴这些首饰——她始终过于瘦削,过于苍白,不能佩戴这些适合原始部落皇后佩戴的首饰。这样,她把这些首饰搁在一个小橱里,闲置多年,后来才由安纳布尔纳取走,锁在一个保险箱里。
“至少你当时可以让我为你保留一件,”安纳布尔纳现在说道,“那么,你就可以给他们看点东西。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谁会想什么?”萨迪问道。一想到远房亲戚和她的可怜的老同学(克莱尔,至今没有结婚,还在教书)居然会考虑她从印度带回什么财产,她再次笑了起来。她的笑声里含有一种相违已久的轻松愉快。安纳布尔纳听了,感情受到了伤害。
他俩都被她的态度刺伤了。萨迪已有多年没看到她的丈夫如此心烦意乱了。不过说来也已有多年没有什么事能真正使他心烦意乱的了。他近来过着一种非常平静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他的生活不总是平静和舒坦的,而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像家庭里的其他任何人一样,也有过感情爆发。她特别记得他和他的妹妹钱德罗莱卡发生冲突的那一次。说真的,那一次,全家闹翻了天。钱德罗莱卡不幸迷上了一个全家反对的男子。他们不是那种古板的家庭,家里已有好几对相爱结婚的夫妇,但似乎钱德罗莱卡的选择完全不合适。萨迪见过那个男子,给她的印象是头脑聪明,颇有个性。事实上,她认为钱德罗莱卡很有眼力。但是,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的丈夫时,他却不以为然,说她不懂。确确实实,她不懂。在那些日子,这个家庭里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不可思议。哦,她模模糊糊懂得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男子是低级种姓,他的所有优秀品质和自我造就的地位都不能抹去那个污点。但是,由此引发的种种激情,被看作生死攸关的种种问题,对她来说实在无法理解。然而,她能看到他们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钱德罗莱卡忍受着内心冲突的折磨(确实,她后来自杀了)。
一天,钱德罗菜卡端着她自己制作的甜饭进来,说道:“你尝尝再作评论!”她亲热地舀了满满一勺,放在她哥哥的盘子里。他开始还津津有味地吃着,但骤然间,他推开盘子,大声哭叫起来。当然,谁都立刻知道是为什么。唯一惊诧不已的是萨迪,既由于这种发作的突然,也由于这种发作的剧烈程度。他往墙上碰撞自己的脑袋,扑倒在钱德罗菜卡的脚下,刹那间,他抓起一把刀子,举向自己的喉咙,围在他四周的所有妇女不得不从他手中夺下刀子。他始终哭叫着,“孩子啊,孩子啊!”萨迪起初以为他指的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莫尼卡和德维,不明白他们遇到了什么危险。但是,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他指的是钱德罗莱卡的尚未出生但终究会出生的孩子。如果她嫁给这个男子,她的孩子的血统就会受到玷污。萨迪不知道这一幕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她当时离开了,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愿听到透过房屋回响着的喧闹声和哭叫声。


这是她在印度的最后一夜。像往常一样,她的丈夫和安纳布尔纳在一起玩牌。当她走到他们那里时,他们热情地望着她,待她像个客人。安纳布尔纳端给她茶、果子露和柠檬水,但她都不想要。这使安纳布尔纳感到苦恼。她经常为萨迪的食量比她少而感到苦恼。她说道:“你怎么能那样生活?”想了一想,她又说道:“你在那里怎么生活?谁来照料你,留心着不让你饿死自己?”萨迪望着她时,仿佛情况就会像她害怕的那样:安纳布尔纳的眼泪再次流下双颊。紧接着,一阵抽泣进出她的胸膛。这阵抽泣引起另一个人的一阵抽泣,萨迪抬头望见一滴滴眼泪也从她丈夫的脸上淌下。他俩都不说话,而实际上,他俩继续在玩牌。这个英国女人垂下眼睑,不看他俩。她坐在那里,安详,端庄,不露感情。她希望他俩认为她没有感情。她竭力隐藏自己的感情——快乐的感情,这是甚至见到他俩流泪也无法抑制的。
安纳布尔纳已经玩够。她扔下牌(她一直在输)。她像孩子那样用手臂擦去眼泪,打着呵欠,叹着气,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啦,到睡觉时间了。”他也同样叹着气,同样无可奈何地说道:“是啊,到时间了。”他俩已经认可这个英国女人离去;这使他俩感到悲哀,但他俩屈从这个事实,因为人类必须屈从一切,诸如老年、疾病和各种损失。他俩互相依偎着,缓步上楼。
而萨迪回自己卧室时,几乎是激动地奔跑上楼的。她望着镜子,惊讶地发现镜中望着她的是张枯萎的脸。她根本没有感觉到会像那样——不,她的感觉仍像往常一样,因此现在她希望她那明亮的眼睛复原,她那粉红的面颊复原。她转身离开镜子,为自己犯傻而发笑。她能听到自己的笑声,这笑声正像往常一样。她知道她今夜不会入睡。她不想入睡。她喜爱这种青春时代的、激动的感情。她在房间里踱步,心儿跳跃,思潮澎湃。仆人们已经关掉楼下的灯,睡觉去了。她的丈夫和安纳布尔纳的房间外面的灯也关掉了;他俩肯定已经并排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这个英国女人看不到月亮,但花园被一种朦胧的银色光芒照亮。她能辨出矗立着雕像的喷泉,柠檬树,大片盛开的夜皇后树丛;还有长板凳,他们经常在晚上坐在那里,钱德罗莱卡用甜美的嗓音唱歌。但她望着望着,月光下的景物越来越明亮,最后它们不再是银色的花园,而是英国的丘陵草原。这些丘陵草原极目延伸,一边是黄色的,另一边是绿色的。绿色的一边下着雨,轻柔的细雨像徐徐而降的纱帘;而黄色的一边是晴天,阳光像细雨一样轻柔。在前方隆起的一个土丘上,有棵橡树,长满叶子和橡子。她正站在这棵树旁。她站在这个俯瞰草原的高地时,一阵阵强劲的大风正对着她吹过来。它们凉爽清新,犹如山中湍急的洪水。它们险些把她吹倒,她必须使劲站稳脚跟,伸手扶住树干(她能感觉到树皮的粗糙质地)。她昂起她的脸,她的头发——不是她的头发,而是她的青春时代的、发光的头发——在大风中狂放地、自由地飞舞。


露丝·普罗尔·贾布瓦拉( Ruth Prawer Jhabvala,1927-2013),生于德国,父母是波兰裔犹太人,二十世纪30年代末全家移居英国。贾布瓦拉自幼在英国读书,50年代后长期生活在印度。她是当代最有成就的描写印度生活的小说家。
《英国女人》译自贾布瓦拉的短篇集《我怎么变为一个圣母及其他》(1972)。
黄宝生,上海人,1942年7月25日出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上海虹桥中学,1960-196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65 年毕业,入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1977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自此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南亚西亚非洲文学研究室主任、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世界文学》主编、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会员等职。
黄宝生先生一生致力于印度学和佛教学,笔耕不辍,出版专著及译著四十余部,涉及印度文学、诗学、哲学和宗教经典等,主要著作有《印度古典诗学》《梵汉诗学比较》《印度古代文学》《〈摩诃婆罗多〉导读》等,以及《巴汉对勘〈法句经〉》《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入楞伽经〉》《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等佛典对勘系列11部,主要译著有《十王子传》等“梵语文学译丛”系列16部、《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下册)、《摩诃婆罗多》(合译)、《薄伽梵歌》《瑜伽经》《奥义书》《印度哲学》(合译)、《印度佛教史》等,并撰《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巴利语读本》《罗怙世系》等梵巴语系列教材。
因在印度学和佛教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黄宝生先生曾获首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2012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印度总统奖和莲花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两个奖项的中国学者;2019年获得第22届师利旃陀罗塞迦罗因陀罗·娑罗私婆底国民杰出成就国际学者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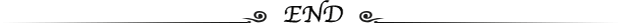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