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鬼鬼:孤独的人需要一只鼻虫吗?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在“我”和鼻虫的关系里,通常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颠倒。“我”是鼻虫的生存环境,因此“我”将自己视为客体,鼻虫则是主体,在“我”身上自在地生存、玩耍。在社会活动里,“我”亦被机械异化为客体。在“我”看来,机械有时带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怪诞,它发出嘈杂声响,就像是空气中有巨大的怪物在呼吸。它在向“我”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而“我”却无法理解。
鬼鬼


鬼鬼
多和田叶子的短篇小说《鼻虫》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6期。故事中的“我”意识到鼻虫的存在,是在学生时代参观“身体中的异物”博物馆的时候。那是一种半透明的虫子,小到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它栖息在人类的鼻毛里,从鼻涕和鼻屎中吸收营养,不需要外出觅食,似乎生活得怡然自得。
与之相反,“我”的工作乏善可陈。手机厂里,人是流水线上的一环,似乎可以被拆分为某些功能,成为为机械打工的必要零件。“我”制造着沟通感情的手机,现实中却没有信赖的好友,这无疑是一处精妙的反讽。“我”只有想象着自己鼻孔中住着鼻虫来慰藉孤独:“我”的鼻毛是潮湿的树木,鼻孔作为洞窟,鼻息是吹来的疾风。玩累了,鼻虫就在鼻毛上沉沉睡去。“我”生活在枯萎的现实国度,而那个看不见的同伴——鼻虫——却过着一种自然、舒缓、无忧的生活。活动于方寸之间,却宛如在自然中自由生长。
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而僵硬。侥幸逃过公司的大裁员后,主人公从一个普通女工升职为课长。可刚刚离开工人的岗位,她却产生了“想要欺负她们、让她们痛苦”的念头。曾经她坐在传送带前,从未想过这些。隔着玻璃远远盯着别人的后背看,是否就会自然地变成这样?系统的冷漠让人也变得冰凉,如果说人能将他人视为非人的工具,那如何能保证他或她不这样看待自己、要求自己?越来越低落的食欲和对工作与日俱增的厌倦是她的自我惩罚。


她在“身体中的异物”博物馆得知鼻虫的存在,但鼻虫真的是异物吗?主人公这样理解:胆结石由体内渗出的液体凝结而成,按理不是异物。但是它会给人带来困扰,又应当是异物。可以想象,她身上的鼻虫也一样。它从体外进入体内,应该属于异物。但它与主人公之间浑然一体,又给她带来愉悦的想象能力,这让它说不上是异物。这样一种观察视角也让主人公与鼻虫构成了一个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小小乌托邦。
在“我”和鼻虫的关系里,通常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颠倒。“我”是鼻虫的生存环境,因此“我”将自己视为客体,鼻虫则是主体,在“我”身上自在地生存、玩耍。在社会活动里,“我”亦被机械异化为客体。在“我”看来,机械有时带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怪诞,它发出的嘈杂声音,就像是空气中有巨大的怪物在呼吸。它在向“我”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而“我”却无法理解。
《鼻虫》的故事有一个令人振奋的结局:一天清晨,驶向工厂的巴士像往昔一样从雾中开来,“我”却没有从后门上车,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步行离开。小说的结局好像告诉我们,主人公终于从空虚的生活中出逃。但美丽的幻影刺痛人、追问人,逃离后会有新的生活吗?在结构性的异化劳动体系中,主人公的新生活又会在哪里?


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的小说充满着对现代社会危机的忧虑,不论谈论的是核污染、城市拆迁,还是被异化的劳动和人际关系,她似乎总是以文字敲响警钟。除《鼻虫》外,也推荐大家阅读多和田的其他作品。她的忧思充满洞见,却又轻盈可触。她的作品中既有绮丽的幻觉和不可思议之物,又具备现实的质感,让人联想起自己的真实生活。她常常以第一人称视角落笔,关注迷失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们,描绘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自我成长。起初他们也许内心焦虑、空洞,但趋向美的天性与奋力生活的愿望仍在闪闪发光,引领他们走向新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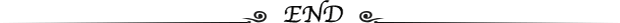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