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欣赏 | 凯•巴利【爱尔兰】:公牛山的死亡之歌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布朗警长沿着海边的小路,朝家里驶去。他知道,公牛山上的每一点灯火,都可能用来照亮卡纳文家族的孩子,根本用不了多久,这孩子就会穿上长裤,根本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得精强力壮,而那时,警长早已长眠于斯莱戈郡的泥土中,冰冷而无酒气。或者,至多不过是待在心脏监护室里,而最终留给他的,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
公牛山的死亡之歌

凯文·巴利作 刘洋译
自十七岁起,他便在公牛山一带四处“留种”。这也难怪,他生着如此这般的毛发,咧嘴笑起来像只雪貂,在斯莱戈郡与梅奥郡的交界地带,鲜有哪个女人能在他的一瞥之间,逃过那对淡褐色眸子的扫描,或是躲过他粗鄙言语的挑逗,不论是在酒吧的黑暗角落,涌动着男性荷尔蒙的乡村迪厅,还是在逃税的黑车里——停在僻静的小路上,映着那痴痴傻傻的月光。他有着女孩一样柔软的睫毛,猪一样粗莽的肩膀——性感得令人垂涎,这是他的自我评价,太多的蠢女孩和笨女人抱有同样的看法。任何时候,他都是脚踏多只船,一旦她们怀孕,便断然抛弃。
如今有些人,一辈子也离不开一个女人——鼓不起勇气,或迈不过感情这道坎——而卡纳文却每天都与女人作别。
布朗警长第一次遇到卡纳文——他来自一个长久以来臭名昭著的家族,是这个家族最近一代的成员——是在派出所里,当时男孩十四岁,罪名是在巴利莫特路上销毁一辆偷来的赛利卡。警长的第一个举动,是拿起电话簿,照着他的后脑抽了一记。
“这下不把你的雪貂脸打下来才怪。”他说。当然,此举并没奏效,卡纳文只是得意地笑了笑,性感而迷人。
淡褐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女巫的魅惑,得意的笑容中透着地狱般的邪恶——种种迹象让警长意识到,年轻的卡纳文终有一天会做下命案。
他拿起电话簿,又给了对方一记。
“你他娘的严肃点!”警长喝道,“屁都算不上一个,至多是公牛山来的烂人一个!”
器宇轩昂的年轻人即便感到了疼痛,也没有表现在脸上。他只是捋了一下金色的刘海,啐了口唾沫,用已然变得低沉且颇具成年男子气概的嗓音说道:
“你也不过是个牢骚鬼而已。”


转眼来到六月末,一个潮湿的星期天——与以往那些阴沉压抑的星期日一样,这日的天气给人一种不详的预感——空气中发酵着恶兆的气息——基拉拉海湾飘来阵阵迷雾,公牛山耸着脊背,仿佛一头匍匐着的野兽,水雾中透出乌蓝色的身躯,神情阴郁,时刻警戒着。
那位警探,布朗警长——警长汤姆·布朗,穿着一袭便装——驾驶着一辆霹雳马“便装警车”,带着满身紧张的汗水和满腔的怨忿,行驶在海边的小路上。
“狗杂种。”他嘴里骂道。
他正试图锁定卡纳文的行踪,却空费了一番气力——这狗娘养的像水一样难以抓握。最令警长困扰的是,对方患了蕈状肿瘤。用不了多久,卡纳文家族的这名成员就会告别这个世界,或是这个世界里的女人。
眼下,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布朗警长来自一个警察世家。他的父亲曾任奥格里斯镇的警长,后因纵酒过度,长眠于当地的泥土之中。他父亲的父亲,当时仍隶属皇家爱尔兰警队,曾任巴里纳卡罗村的警长,后因纵酒过度,长眠于当地的泥土之中。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当人们还在路边嚼青草、吐绿水儿时,就已经是伊斯基村的警长,而他同样因为纵酒过度,长眠于当地的泥土之中。
汤姆·布朗警长从不饮酒,却嗜甜如命。甜食成了他的管教。汗水涔涔的警长身上微微冒着热气。坐在阴暗潮湿的车子里,在这N59国道的艾莫村服务站旁,在这公牛山可憎的山阴处,他吃了一根瑞士卷。
他望了望后视镜中的自己——镜子里是一张孩童般肥嘟嘟的大脸。“这一天下来,又他娘的长胖了。”他自言自语道。
如今,他连爬个楼梯都会气喘吁吁,下楼时喘得同样厉害。自八十年代末以来,他还从没欣赏过镜子里的自己。现在,他已经六十五岁,再过三周便要退休——他立下的决心是,要在退休前把卡纳文给安顿好。
地区医院的肿瘤病会诊医师与警长相识已久,久到两人曾一起训练跳远。他是警长相识最长、且对他帮助最大的知己。卡纳文的肿瘤,医师解释说,正从他的青春和活力中得到滋养。
“换做一个老家伙,可能会有所延缓,”他说,“年轻人不行。”
肿瘤正加紧步伐,朝全身扩散,眼下已经蔓延到了淋巴。卡纳文二十九岁,正当盛年,得知会因治疗变成性无能、头发会掉光,他断然拒绝了治疗。
“他看不到圣诞节的彩灯了,汤姆。”医师说道。
两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眼下,卡纳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仍在公牛山一带的乡间活动。这点,警长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在公牛山附近,他的本事便接上了超自然力量——纵使你把他逼入邮票般丁点大的一块区域,他依然能挣脱,并且还有足够的时间扭过头,妥妥地瞥你一眼,露出一副迷人的表情。



沼泽附近的小路、灌丛、柏树林、乔木林,他一清二楚。山坡上的每一片洼地,每一处可以藏身的水塘,他全都知晓。他知道海岸附近有哪些隐蔽的角落,知道哪里是新修的住宅区,就连面貌日新的小村里那些连成片的平房、镇子里的后巷、牧师的花园,以及高墙环绕的私人老宅,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同样,他也知道那些熟透了的寡妇们在何处栖身,熟悉海风中那股潮湿的、海滨公寓里的厕所味。他熟悉那些用铅皮做屋顶的窝棚,那些仓房和洞穴,知道锡安山,知道联合森林【联合森林自然保护区,位于爱尔兰西北部的斯莱戈郡,由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服务处与科伊尔特林业公司共同管理。】,了解乡间的一道道车辙、一条条隧道,公牛山的乡间地带——后冰川时期形成的地貌,并且了解山区的变化,了解人工开凿的裂隙和开口——他对公牛山的乡间地带了如指掌,知道这里有上千个藏身之处。
卡纳文家族的成员还知道,对于男人而言,最大的慰藉在于——女孩能被哄得开怀大笑,屁股蛋像苹果一样的女孩。大西洋沿岸那些青灰色的日子,只有借助性爱和斗殴——在那些暴力熏烧的时刻——才能获得生气。卡纳文家族的神奇之处在于凭借星点琐事,便能擦燃暴力的火花。上一代的每位成员,都会对下一代构成挑衅:挑唆着后辈去超越前人、更进一步。所有的一切都被继承下去,就连姿势也不例外。嘴唇的曲线,肩膀的轮廓,还有那些古怪的本领。例如,凭借天生的机警,卡纳文家族的人可以嗅到空气中警察的气味——对于他们而言,这就像是茴芹籽的味道。
一年又一年,来了复又去,发生改变的只有裤子——粗麻布的马裤被浸满雨水的华达呢裤取代,后者又被带有烟草味的、斜纹布料的裤子取代,随后又换成丁尼布料的各种牛仔裤(靴型裤;直筒裤;展现魅力时穿的喇叭裤),接下来换做尼龙料的运动裤,继而是纯棉运动裤。但一直以来,卡纳文家族成员的标志性姿势从未改变:拇指猛地插进裤腰,向上提提裤子。
卡纳文家族——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始终为公牛山贡献着时而复杂时而简单的元素:神秘主义的知性以及鲜活的精液。
在乡间出没时,卡纳文已然做好了准备——恰如肉已做熟,只待撒盐——只待嘴唇上鲜血带来的那份咸意。
警长汤姆·布朗驾驶着那辆霹雳马,任凭两只肥厚的手掌导引着行驶方向——称之为感觉也好,卜算也罢,近半个世纪的从警生涯,让他凭借直觉就能读出罪犯的活动规律。他能感觉到,沉寂良久的犯罪活动,何时会骤然来袭,他知道几番得手之后,人会变得更加顽固大胆,他还知道,侥幸得手的几率会突然增加。最重要的是,他能察觉到暴力来临前的气息:每逢此时,他的皮肤会变得汗湿而冰冷,胃肠会翻搅起来。
在这个弥漫着浓雾与恐惧的星期天,当他沿着海边的小路行驶时,这种感觉出现了。他的感官里充斥着对卡纳文家族成员——特别是这一位、这一类成员——的仇恨。一切都变得异样起来——他的视线模糊得厉害,路标上的字迹变成了扭曲的阿拉伯文;他的听觉出现了错乱,如同遭受过惊雷的震撼——直到那个混蛋被捕、直到他完蛋,一切才会正常起来。
“他就在不远处。”警长说着,一边开车,一边吮着软瓶中的蜂蜜。
有一位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太太,生活在大山另一侧梅奥郡的一处旧农场里——凄凉得可以想象——上周四,她半夜里听到一阵沙沙的响动,打着院里的灯后,突然发现卡纳文手里举着把钩刀,一根手指竖在玫瑰色的双唇前。
他抢走了四百欧元,一个手机充电器,并且出于造孽的天性,戳伤了她两侧的腰眼。
他一定就潜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布朗警长担心的是卡纳文此时的潜伏状态,他可能像雪貂一样躲在洞里,身旁放着杀死的兔子,舌尖舔舐着兔子颈部的血液,锋利的牙齿撕裂着肌腱和骨头,两只爪子小心翼翼地拨开皮肉——动作是如此的轻柔,几乎带着几分爱意——让丰盛的内脏暴露出来,这顿大餐足够吃上几天,再没有什么办法能将雪貂赶出洞穴,除非有伸缩杆或炸药。
然而,真正需要的不过是耐心而已——卡纳文家族的人不可能永远龟缩着脑袋,他们往往会忍不住暴露行迹。那张垂死的帅气面孔,会再次出来寻找光亮,走向舞池,走向酒吧里的高脚凳,会趁着潮湿的季节,搜寻那些忘记关闭的窗子,或是在高尔夫俱乐部的停车场,尝试着拉开车门的把手。布朗警长——特别是这一位,这一类警长——需要做的,不过是耐心地等待,严格地听从手掌的指引。
从恩尼斯克朗的一位酒吧侍者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关于那个寡妇的消息——据悉,她在伊斯基村外新修的那栋带有天窗的房屋,是卡纳文最近一次的藏身之处。
警长赶到那里时——恰好是星期天的午茶时间——她正一个人待在家里,身上已然带着淤伤。脖子和两肩带现出山莓色的拇指印。她穿着一件太阳裙,衣着显得过于年轻,皮肤上带着许多明显的斑点,两眼呆滞无神,流露出磕过药一般的神情,一对令人眩晕的乳房荡来荡去。
“啊,太蠢了,”她说,“太蠢了!”
她至多不过五十岁出头,坐在对面的警长更加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发现她的嘴巴最近也被打伤过。如同被蜜蜂蛰过的嘴唇肿胀着,看起来倒有几分粗暴的性感。脸上的美黑妆并没有掩盖住颧骨处的淤伤。
“啊,都是我自找的。”她说。
真是个蠢得掉渣的女人,警长心想。
“你跟他交往多久了,希拉?”
她在皮沙发上出溜起了身子,太阳裙被蹭得向上卷起,露出了后侧的大腿,窗外的大海卷起刺耳的声响,她翻了翻白眼。
“有一阵了。”她自豪地说着,一股威士忌的味道传了过来。咖啡桌上放着一瓶几乎喝空的高司令。
调和威士忌,一闻酒臭就知道。警长心想。
“现在他在哪里,希拉?”
“我他娘的也不知道,不是么?”
“我可不这么想,希拉。”
“你他妈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他在这里留了什么东西么?”
她承认,对方的确留了东西——放在了一间弥漫着麝香味的卧室里。警长检视着卡纳文的旅行袋——锐步牌的,拉锁已经损坏。袋子里装着一个手机充电器,一包诺洛芬牌止痛药,一条换洗用的运动裤,还有几条三角裤。这个手提袋令人心碎,它所引发的伤感促使警长回过神来。


他走回到希拉跟前,对方正从瓶里倒出最后一点酒来。他仔细地望着她,这个女人和那个命不久矣的男人让他有些触动——两人的生命都散发着余晖。
“他在哪儿?”
“我说了,不知道。”
接着,警长在她身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只手轻轻搂住她的肩膀,胳膊猛一用力,将她狠狠箍在怀里,悄声对她解释为何她最好老实交代。
“现在治疗的话,对他还是有帮助的。”他说。
女人像条蛇一样望着他。
“可能是在基什丘,”她说,“上面的那些山洞里。”
汤姆·布朗肉墩墩地喘了口气,站起身,准备离开这栋明亮而冷漠的房子——四周的墙壁薄得像蛋壳——窗子遭到了破坏,砸得不成样子。他早就知道,现在更是深信不疑——在公牛山投下的暗影里,一场杀戮即将展开,就在乡间黑夜未尽、黎明将来之际。
女人破损的嘴唇散发着青紫色的诱惑,他怔了怔。
“那里要缝几针才行。”他说。
离开时,女人投来一道恨恨的目光。
“滚蛋。”她骂道。
基什丘的那些山洞距离公牛山不到五十分钟的路程,那里零零散散地隐没着几头麋鹿,几匹狼,还有一头熊。自从山岭出现裂隙并被凿穿——以及康诺特省的设立——走投无路的哺乳动物便躲到基什丘栖身。连绵不断的页岩和欧洲蕨,有时会给那个地方增添几分阴森和恐怖;这黑暗的气息并非来自山上,而是自地下缓缓渗出。
布朗警长把车停在一条小路上,然后沿着一级级岩架向上攀去——他一只手掌捂着胸口,生怕心脏会随时停摆。
爬得越高,岩架就越发险峻,那条小径堪堪只容得下一个胖子的宽度。焦糖色的粗皮靴内,他那两只紧张的小脚,开始在汗津津、滑腻腻的袜子里游来荡去。天色已经半黑,最后一抹光亮笼罩着这个漫长的周日;灰蒙蒙的天空更加阴沉;一道道飞机云映着渐渐淡去的天光,微微颤动着。薄暮是亡灵的国度。杀戮将选定它降临的时刻,而此时,这一时刻已然铸定。在最高、也是最后一个山洞外面,警长发现了卡纳文——他正愉快地吮着烟卷,两腿交叠着坐在地上。他完全清楚,杀戮的时刻已然铸定,且这一次,他再也无法挣脱。
“站起来。”警长说道。
他站起身,一对俊美的眸子火辣辣地烙在警长身上。汤姆·布朗想要捆住他,甚至想要吻他。
警长不需要做任何选择。抓住他们中的一个,拯救我们中的一个——此举是为了实现他对警察这份职业许下的诺言。押着俘虏下山时,他仅仅伸出一只手的手掌,按住了后背的一小块部位——迅猛而突然地一推,便让卡纳文跌下岩架,一路坠落下去。下方的岩石默默地、迅速地终结了一切:淡褐色的眸子,懒散的神情,身体里的癌症。


此间毫无胜利可言。布朗警长沿着海边的小路,朝家里驶去。他知道,公牛山上的每一点灯火,都可能用来照亮卡纳文家族的孩子,根本用不了多久,这孩子就会穿上长裤,根本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得精强力壮,而那时,警长早已长眠于斯莱戈郡的泥土中,冰冷而无酒气。或者,至多不过是待在心脏监护室里,而最终留给他的,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
如今,他对夏夜产生了恐惧,害怕那诡秘且融化着甜意的黑暗,他将夜里的微风想象成讥讽的曲调,仿佛那是公牛山对他发出的嘲笑。那一座座大山,坚守着它们的信条:想要逃走的,终归会逃走,致心追逐的,必定要去追逐,并且要等待——哦,不是一直都有——些躁动而无知的少女么?听——
清脆而悠扬的笑声在黑色的大山里回响,彼时,她正对着一只撩拨着她的手佯装嗔怒,嘘——再听——空气微颤,发出最轻的声响,那是她合上睫毛,拉下黑暗的幕布:那是一首“爱—情—又—重—来”。
END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1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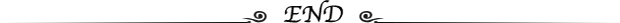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