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与岁月和解:老年文学小辑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瑞士〕贝尓纳·高芒作 唐飞戈译
泳池静悄悄的。她游着,没有烦闷,但也没感到多少乐趣。让她感到快乐的,是漂浮着的感觉。她不喜欢气喘吁吁的感觉。当她从一端游向另一端,到了半中央,她会喘得上不来气。二十二米,这个泳池的长度十分巧妙。泳池的一角被围栏围着,那里水更浅。每次她看向这栅栏和进入浅水区的三个台阶时,她内心深处的柔软都会被唤醒。孩子们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当他们长成少年后,还是从那里下水。茉德,她从不大笑,但时不时会有一弯微笑挂在她脸上。她的微笑美丽可人,她的双肩上下起伏,深褐色的头发卷卷的、长长的,而她的两条长腿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向前行进,如同在滑行,又像在漂浮——不是在水上,而是随时随地。今天,她依然漂浮着,是那么温柔可爱,但这是为了更好地掩盖内心的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只有母亲能够感知。有时候,当她们四目相对,这种不安便会产生。每次她都犹豫要不要说出来,最终还是放弃了——说出来又有什么用?男孩子们也许觉得自己更强,他们并不喜欢茉德,从未喜欢过。这是由本能驱动的。这里面有苦涩,也有嫉妒。他们也感受到了姐姐的优雅,不过把它看成一个问题,或当成一个谜。
一切皆浮,天空上添了几点云翳。她闭着眼睛游着。确实,在弥留之际,一切行将结束之时,只有三五个生命中的重要记忆会留存下来,而对她来说,其中的一个记忆她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它将随她一起被埋葬,没有踪迹,没有证明,只有一些迟疑短暂的存在,然后立刻被时间吞噬。那是一个如此冷的夜晚,没有一片雪花飘落。寒风呼啸,这是大城市特有的寒冷——在肮脏的城市中,那暗夜里刺骨的冷。然后,茉德出现了,带着仅属于她的优雅。男孩子们——这些过分自信的后生——神情有些凝重,心情有些沉闷。那时很冷很冷,冷到极点,而这份寒冷自此伴随了她一生。泳池的水在酷暑时节依然是热的,她很满意。在温热的池水上漂浮着,静静地一个人游着,感受水中身体无拘无束的轻盈,她很高兴。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幸福。
策划及责编:赵丹霞




〔法国〕努·夏特莱作 唐飞戈译
想知道炖肉的问题出在哪一步,为时已晚。是在放奶酪的时候吗?是胡萝卜或者韭葱没选好的缘故吗?是在把蛋黄打进奶油这一步吗?不管什么原因,饭桌上一家人的沉默清楚地表明:坏了,白汁羔羊肉搞砸了!
她几乎不能面对小孙子有些游移的目光。女儿把这道菜从桌上拿走,没问大家要不要再添。蕾蒙德也感到一丝尴尬,她正了正有些歪斜的发髻——这是她排解尴尬的小动作。她的女婿一直沉浸在报纸上的填字游戏之中。奶酪味、水果味和奶油味已经尽它们所能来掩盖白汁肉那持久又带有谴责意味的气味——一种又浓烈又难闻的气味。这味道似乎想要紧紧附着在饭厅的每一件物品上,它悄悄钻进挂钟里、窗帘里、放着干花花瓣的水晶酒杯里,从羊毛地毯一直渗透到落地灯灯罩里。这是一个菜肴做失败了的标志。最后,大家离开了饭桌。
蕾蒙德帮着把碗洗了。厨房里散发出阵阵咖啡的醇香,她的女儿哼哼唱唱地忙活着。女儿不是耿耿于怀的人,她哄着老太太开心,时不时还带着嘲弄的神气稍稍安慰下老妈,告诉她“这道菜的失误无足挂齿”或者“这道菜做得还可以,挺好吃!”
蕾蒙德觉得她的身体渐渐变冷了,每一句安慰都让她陷入到一种更加无可挽回的痛苦之中。
此时,她坐在床边,两手交叠着放在膝上。上半身僵直,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她在思考。
一只莽撞的苍蝇突然飞起,发出令人熟悉的嘤嘤嗡嗡的躁动声,似乎和老太太的安详格格不入。
公寓那头传来了电视机里体育评论员激情的声音,他在解说科隆布竞技队的比赛,声音时不时被一阵阵刺耳的口哨声盖住,那是她的外孙在炮轰他的铅制玩具兵,那声音带着一种让她心惊的残忍。不时有缝纫机的咝咝声传来,为外面的男人和男孩子发出的喧闹降降温。这是一个温柔的、令人心安的旋律,伴随着她从妻子、母亲到外祖母这一路的旅程。
她还能从衬衣的褶皱中闻到那搞砸了的白汁肉的味道。尽管这次搞砸了,她依然在脑海里急切地寻找着继续下去的理由。
没有找到。
她站了起来。
窗帘上的牧羊人不再跳舞,牧羊犬也似乎在花边床上睡着了。她用失去光泽的双手把裙子捋平,把椅子推到靠窗边的位置。窗外,马森纳大道上的栗子树高处的枝桠昂然耸立着。蕾蒙德用右腿跨过了窗栏,那条腿还像当姑娘时一样有力。
策划及责编:赵丹霞




〔加拿大〕凯·黛·米勒作 徐阳译
平日第一处歇脚点是缘水而建的小观景台,围有一圈长凳,他们到的时候,座位已经有人占了。一对年轻人。都在抽烟。在这个清冷灰暗的早晨都戴着墨镜。莱恩路过时,一边把“老妹”往他身边拉,一边望向下一处观景台,只听那年轻女人说:“还有别的。问题。此外。还有那个。”
是那种谈话,听起来是。还记得吧?琼连珠炮似的对他说个不停。他只能干等她说完。所有女人都这样吗?事态刚平定下来,就要重新搅乱?她们总是执拗地说,还有别的问题——这所谓的问题在他听来总是闻所未闻,却不知怎的偏偏要怪到他头上。
莱恩从不以牙还牙。本来可以的。本来可以指责她。为自己申辩几句。如果他说了,能改变些什么吗?或许琼有办法调转话头,照样把他指责一通?
“老妹”在他身边轻声呜咽,因为他不觉收紧了绳子。“对不起,‘老妹’。我们歇一会儿吧。”他们来到下一处观景台,没人,谢天谢地。莱恩僵直地在长凳上坐下,感到疼痛从双脚转移到膝盖。如今痛感从不离开身体,只是四处游走。
雾气消散。他眼前的木板道曲折迂回地伸进湿地,又绕回到坚实的大地。水面被雨珠打出了一个个水泡。一只麝鼠用鼻子拱开一条缝,接着又隐入水中。
往常这种时刻,此地简单的氛围——鸟儿和其他动物完全活在当下——正是莱恩平复心情、振奋精神的源泉。但今天早晨他有点郁郁寡欢。总想着最好深埋不提的往事。一定是受了知心专栏那封来信的影响。那个蠢透顶的女人想在丈夫怀中起死回生。总比在棺材里一个人睁开眼睛要好,莱恩猜想。得使劲推棺材板,顶起沉沉的泥土,才能爬到地表,以响应末日的号角声。只是他怀疑那女人是否当真这样想。可能她想象一切都将是美好、简单而神奇的。或许没有料到,丈夫睁眼再次看到妻子时——这回是永世都能相见了——他的反应恐怕算不上十分欢喜。
死后会怎样,莱恩毫无头绪,也说不好是否在乎。琼的葬礼过后,他有一年都远离教堂。不停地告诉自己,他绝不回去。但时过境迁,他回去了。现在莱恩差不多每礼拜日上午都要去那里。这是外出活动。见人的机会。
琼还在世的时候,莱恩去那里,仅仅是因为她与那里的关系紧密。她像管理艺术节组委会和图书馆理事会那样管理教会。每礼拜日早晨催莱恩打好领带出门,留出时间在教堂长椅前的跪凳上祈祷——眼睛闭着,浅笑的嘴唇翕动着。莱恩干坐在那里。他成长于长老会教徒的家庭,在琼坚持为两人婚礼举办的圣公会仪式上,他的父母显得如此渺小而迷茫。
琼知道该怎样坚持己见。这是她的天赋。她把事情办成的原因。两人从不讨论琼在主日礼拜仪式前祈祷的习惯——她为何祈祷,究竟相信什么。准确地说,除她自己之外。没错,琼·斯帕克斯绝对相信琼·斯帕克斯。
一对绿头鸭滑水而过。倒栽葱觅食,完美合拍。莱恩很好奇它们是否终身为伴。又有了可以搜查的话题。想想那该有多么安宁。这就是你的伴侣。不会有别的。只要蹬着蹼划水,什么都别想就好了。
但如果其中一只死去呢?警察来到家门口,告知琼横穿主街时被一辆小货车撞倒,莱恩的第一反应是,跟“老弟”一个样。第二反应是,我从没告诉过她。她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知道了。
这些年来,有时话已到嘴边。怪得很,刚发现的那一天,他情绪稳定。或许是怔住了。当晚,莱恩照样在闲聊工作中把晚饭时间打发了。有些部分顺利地略过去:那天午餐后头痛,请另一位老师代课,提前开溜。像往常那样走回家,心想,琼是在家里还是出门组织活动了。随后,半个街区开外,只见一辆银色本田从他们家门口开走。琼在门廊上凝望着。突然冲下台阶。车停住了。司机探出脑袋。琼俯身亲吻他。
莱恩似乎完全知道该怎么做——迅速退到一片高高的树篱后,看着那辆本田从身边驶过,司机的模样在反光的挡风玻璃后面看不分明。莱恩觉得自己置身于一出戏里,扮演他一辈子都在排练的角色。接下来,戏剧脚本指引他转身走向转角那家小咖啡馆。对着一杯逐渐冷却的咖啡,坐到正常下班时间。
那天夜里关灯后,他躺在琼身边,感到两人之间仅隔着几英寸。话语似乎堆挤在嗓子眼。为什么?有多久——?他是——?琼已经好几周都没要求他碰自己了。但她向来都是这样喜怒无常。而莱恩总是淡然面对这一切,既然琼回来了,他就要为此感到欣慰和感激。
他确实是这样做的。日后,当琼的确回心转意,最终滑过那几英寸贴在他身上时,莱恩感到的唯有素日里的感激和欣慰。尽管他从未停止找寻,那辆银色本田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策划及责编:叶丽贤



〔美国〕马克·贾克布森作 刘志刚译
真正的顿悟发生于今天早上。我照镜子时对自己说:包括耳毛在内,我的身体一点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那个婴儿照片里的我,那个在皇后区高中操场后面的树丛里初次体验性爱的我,那个在弗兰克·卢卡斯【弗·卢卡斯(1930—2019),活跃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毒枭】横行天下的日子里开出租车穿行于哈莱姆街区的我,那个子女眼中为人父的我,那个昨天的我——地球每多自转一圈,我每多活一日,都与昨天的我更多了一份相似。我再次处于起点,准备步入惠特曼式宇宙中的另一个空白区,如同即将远航的麦哲伦。
*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即便衰老并非什么新鲜事,但能避开交通拥堵时刻总是好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更多人正在步入老年,其数量之大可谓史无前例。我说的是我这代人,扬言要在衰老以前结束生命的一代人。这又是一句老掉牙的狂言浪语,除了凯斯·穆恩【凯·穆恩(1946—1978)在著名的“谁人乐队”中担任摇滚乐鼓手,死于过量服用镇定片】,没人会疯狂到想要去兑现它。每天有一万名美国同胞——要能回到大一那年的学生宿舍,他们都可能是我的大麻烟友——与我汇合,踏上了那一级级通往天堂和/或地狱的下坡阶道。所谓的“婴儿潮一代”如今已经在出纳员的窗口前排起了队伍,而我只是处于其中第一波。这次大潮将一直持续到二○二九年,总人数约七千万,足够让奥巴马的医改计划破产一百次。而且相信我,其他年代出生的人也许愿意在黑暗中悄然离场,但要把这个爱炫的“婴儿潮团伙”赶下台来,可就难多了。
那是因为这代人很特别。我们总是不停地自我指涉,凸显自身的特别之处。在我们发明性、毒品和摇滚乐这三件所向无敌的法宝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青春。同样,一旦考虑生儿育女,我们下的崽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受宠爱、被写得最多、装备最齐全的婴儿。这也难怪,即使人类的始祖亚当公认活到了九百岁,在我们眼里,还是没有人真正老去,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老去。
等着瞧吧,大量书籍、博客和暖心的演讲将会纷纷涌现,汇成一整套夕阳红文献,当然,这一“末日”论述会有一部分隐藏在所谓的《启示录》和其他热播的有线电视节目中。关于这个话题的某些言论难免会比较烦人。前不久,我在《赫芬顿邮报》网站的“年过五十”栏目看到曾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安娜·昆德兰【安·昆德兰(1952— ),美国专栏作家,曾获1992年普利策新闻评论奖】的一段视频。她说有那么一刻,她突然觉得年老要比年轻好。“当我终于完成一次头手倒立的时候。”她说。她没上年纪时凭借“身体的敏捷”也许能完成这个动作,但之所以到晚年才实现这一壮举,正是因为老当益壮的“信心”,昆德兰如是说道。
以下是不证自明的假设:我们是不凡的一代人,只要想做任何事,就一定能做到。就像戴安娜·奈雅德【戴·奈雅德(1949— ),美国长距离游泳健将,记者,励志演讲人】历经一百零三英里从古巴游到美国,每天都有老年人在创造辉煌成就。毕竟,二十来岁的时候,谁都可以很酷、很厉害。但过了六十岁还能很酷、很厉害——那才是真正意想不到的惊喜。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婴儿潮一代”的博主就会宣称死亡比生命更酷炫。
策划及责编:叶丽贤




〔澳大利亚·英国〕琳恩·西格尔作 陈龙译
我们应该知道,衰老的面孔,衰老的身体,千形万态,难以尽数。一旦我们选择凝目细看,就会发现其中很多都颇为优雅,富于表现力——专注的眼神绝不会失去自有的光彩。然而,在本书里,我打算蜻蜓点水地掠过肉体遭受的岁月摧残及其更新的潜能,更仔细地考察衰老心理学与衰老政治学。我主要关注那些不受我们的年龄影响,维持和阻碍我们生命活力的因素。由此我首先想到了衰老的时间悖论,以及保持对外界开放、与外界相通的持久方式。
随着逐年衰老、蜕变,我们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保留了曾经所有的自我痕迹,这造就了一种“时间眩晕感”,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的心理跨越了所有年龄,又没有年龄。“所有年龄与没有年龄”一语出自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唐·温尼科特(1896—1971),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客体关系理论大师】,曾用于描述心理生活的特点:它的时间性是任意多变的。依据温尼科特的记述,病人们来到他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的诊所接受精神治疗时,他能察觉他们身上存在多重年龄。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年长,就越是通过层层积叠的错综身份来直面世界,努力协调变动不居的当下,同时应对那些无比唐突地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令人不安的老者形象。北美诗人斯坦利·库尼茨在七十多岁时创作了一首优美诗歌,其中有一句是:“生活在叠层中,/而非在垃圾上。”
许多人可能会怀念他们年轻时激情四溢的行乐和冒险活动,害怕再也无法重拾他们失去的东西。然而,无论如何,不管好坏,总有一些曲折迂回的手段,使我们不论年岁几何,始终能带着过去的那些激情,生活在当下充满奇特变幻的精神生活里。我们不必成为普鲁斯特,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重拾过去激情的留痕,当然,要找到恰切的语词——或者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日常时间旅行,肯定并不容易。
因此,一方面,自我似乎可以变得永远不会衰老;另一方面,我们被迫在持久的转变中,尤其是通过对他人的影响,标识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弗吉尼亚·伍尔夫始终关注时间、记忆和性别差异问题,一九三一年,她年近四十,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觉得自己已经活了二百五十年,有时又觉得自己仍然是公共汽车上最年轻的人。”我对此深有同感。
“我不觉得自己老。”年长的受访者反复告诉口述史家保罗·汤普森【保·汤普森(1935— ),英国社会学家,现代口述史先驱】。他们的心声呼应了汤普森在深入自传出版物和采访档案时读到的言论。与之相似,在作家罗纳德·布莱斯【罗·布莱斯(1922— ),英国小说家、散文家、编辑,代表作为《阿肯菲尔德》】收集的口述史中,一位八十四岁的前校长反映:“我倾向于将其他老人视为老人,但我本人除外……我的童年从未消逝,现在仍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对它的感受非常强烈——更甚于以往。”
研究发育生物学这门硬核科学的刘易斯·沃尔帕特【刘·沃尔帕特(1929—2021),南非裔英国发育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写过一本探讨老年的奇特属性、书名诙谐的著作《你的气色真不错》。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处问道:“我才十七岁,怎么突然变成了八十一岁呢?”这种对青春的深情眷恋再次有力地说明了伴随老年而来的羞耻感:我们永远不会说“你看起来很老”,除非旨在羞辱对方。一方面,我们在穿越时光的历程中,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持续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无论面临什么诱惑,我们都很难忽视自己衰老时所处的独特位置。然而,我发现,在审视了其他人关于衰老的言说或著作中的极端含混性之后——特别是当这些人思考这个话题既不是为了哀叹老年,也不是为了赞美老年,而只是为了确认它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我变得更容易直面自己对衰老的焦虑了。这催生了下文的内容:我集合了不同证人来带领我穿越那些曾令自己夜不能寐的想法,思考所有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并揣测衰老对我与它们的持续联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策划及责编:叶丽贤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二期,完整版可以点击本图文信息末尾的封面链接,进入微店购买纸刊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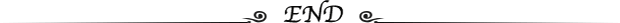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