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林子:观察是为了置身其中——读劳伦•格罗夫两个短篇有感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如果说《鬼与空》(杨博译)是一次漫长的夜跑,从滴水成冰的冬跑到潮湿闷热的春,那《眼壁》(逯璐译)就是一场现代的多萝西与绿野仙踪。这位可爱的女作家,总在以摇摆又亲和的姿态,传奇地叙述所居的城市。

读到第四遍,我才稍微领会了题目《鬼与空》的含义。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鬼故事,而实际上它几乎是一篇极具写实感的散文;再读,我以为“鬼”指的是文中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潜伏在夜间如鬼魅般的人;直到最后一遍,我意识到,或许“鬼”是正在凝视这一切的夜跑者本人,在穿过一个个街区,透过窗子,透过变化的月份观察周围的人与物时,她自身的边界正在逐渐消失,随之与她所生活的佛罗里达融为一体,宛如可以随意穿行的鬼魂。
这是一个从夜跑开始的故事。夜跑者从家中离开,在以散心为名的慢跑中充当城市观察员。作者刻意隐去了夜跑者走出家的原因,只用一句“我成了大喊大叫的女人”作为开头,但在后文中,又常常感觉跑步者身上隐隐流动的情绪:愤怒、焦虑、困惑,从绝望转向希望,又从希望回到绝望。时间在夜跑中流动,看似只有一次慢跑,实际上却描述了长达几个月的情形,其中不乏人、建筑、城市那些正在发生却隐入尘埃的变动:流浪者的聚居地被光明正大地烧掉,寓寄地板下的夫妇偶然出现又偶然消失,冷寂无人的街道逐渐迎来空调的嗡鸣,浓郁的栀子花香取代了烟味和汗味……夜跑者如同扛着摄像机,将几个月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没有品评,只有观察,气氛轻松愉快地如同一场真正的饭后散步。


小说开头的笔调是冷的,光线黯淡,行人稀少,气氛和一月佛罗里达的气温一样低。就连空气也不好闻,充斥着霉菌、樟脑和木屑的味道。夜跑者路过老街区,目击的尽是因疏于打理而腐朽、潮湿、颓败、锈迹斑斑的建筑。但随着对人的靠近和观察,文章的色调和感情明显温暖了起来。夜跑者通过透光的窗户观察着“邻居”,观察他们如同在鱼缸中的家庭生活,从气味、动作、神态来揣测他们的故事和关系。她遇到了许多人,有唱赞美诗的修女、健身的肥胖症男孩、遛狗的中年女士……也许是对“人的关系”太过入迷,她甚至把黑暗中的一棵枝叶下垂的木瓜树当成了一对依偎着的老年夫妇。佛罗里达的夜间生活,在夜跑者的叙述中如同夜昙般舒展开来。
到小说的结尾,夜跑者的心情已经好了许多,她逐渐不在意跑步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而是单纯享受这种奇妙的处境:置身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之外,置身于沿街的他人生活之中。她不再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他者上,不再误以为黑色的天鹅总会哀悼幼子丧命,漫画式弯弯的月亮或许在嘲笑自己——我们太渺小了,根本不值得月亮垂怜和嘲笑。与此同时,随着春天的抢跑和天气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夜晚的街道,夜跑者似乎失去了独享危险、神秘又充满奇遇的夜晚街道的特权。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她已经在一次一次的奔跑和观察中,逐渐消融了自我与他人的界限,真正成为了自由自在、游荡在夜色里的鬼魂,和所有人一起共享着这座城市或好或坏的空气与明天。
我尤其喜欢《鬼与空》的结尾,“重压在我身上的,是我不能为之大喊大叫的事物,是我的身体、影子和月亮一起游荡的时刻”。这多像古诗的那句劝诫,既然“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就“昼短苦夜长,悔不秉烛游”。

我是在一个和文中类似的大风天读到《眼壁》:在狂风大作的眼壁中,主人公陆续见到了鬼魂般的、已然逝去的丈夫、恋人和父亲。
这真的不是出自《精怪故事集》?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追风者的冒险罢了,谁会在台风的中心安静待着,而不是迅速立刻这个危险之地呢?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这是一次刻意为之的独处,一次对自我和自然,真实与记忆的检视。在故事中,主人公始终是平静的,甚至冷眼旁观周遭灾难般的变化,以及相继出现的心灵幻象。尤其是读到“雨水释放了自身”时,我突然想到了里尔克的诗句: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也许,作者和《眼壁》的主人公一起,在台风中释放了自身。



格罗夫曾在访谈中提及,她希望通过小说的方式来回归自然,进行“野生化”。正如《眼壁》中,主人公面对狂风下汹涌的湖面、哆嗦的花园和逃窜的鸡群,高喊着“放马过来吧!”,毫无畏惧,满是期待,荒诞又勇敢。同时,文中有不少笔触描写了风暴中的灾难场景:山丘式的白色扬尘、倒伏的蓝莓丛、呼啸而入的暴雨……如印象派的速写般,带读者领略这远离日常、难得一见的奇异景观。
靠近,观察,最后融入……这似乎体现了格罗夫一贯的文学观:观察是为了置身其中。在《鬼与空》中,她是一个从窗外窥探他人的夜跑者,而在《眼壁》中,她选择了居于风暴中心,亲自感受这一切。
无论是一月的佛罗里达,还是七八月的加州,人总是看似弱小、摇摆、无能为力,面对自然只能眼花缭乱或是逃离躲避。格罗夫称,这是因为她明白“我们强加的限制和标度未必能在自然中留下痕迹”,所以,与其选择争夺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不如将人视为自然的延伸,将人际关系视为一种自然塑造的结果,在一遍遍的惊奇、敬畏、观察与靠近中,与自然和解。
毕竟,自然无意于毁灭我们,它只是以某种原始的力量回归自身。正如在摧枯拉朽的风暴后,仍有破败不堪但一息尚存的房子,一颗稳稳当当立在台阶上的鸡蛋,和一位历经活见鬼但越发平心定气的女性。他们静默而庄严地立在大地上,再无过多的边界和隔绝,与自然本身一起保存着勇气、力量和执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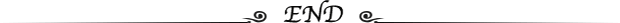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