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克•佩•罗西【乌拉圭】:我将抵抗化作文学,努力去做一位女堂吉诃德,惩恶除害,争取自由和正义……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曾经,我不得不流亡,逃离乌拉圭的独裁统治,因为我就像卡桑德拉一样宣布并揭露了独裁的来临,换来的惩罚是我所有的书、连带着我的名字都被禁止。我奇迹般地逃生,来到西班牙,当时,在西班牙也有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正在压迫人们的自由。正如许多流亡中的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样,我将抵抗化作文学,我并没有像玛尔塞拉一样避世,而是通过我的书,通过我的生活,努力去做一位女堂吉诃德,惩恶除害,争取自由和正义。
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
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作 黄韵颐译
我是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出生的,那是一九四一年,欧洲不幸仍深陷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我家左边住着一位老补鞋匠,是个波兰犹太人,此前奇迹般从大屠杀中逃生。我家右边住着一位德国音乐家,一只眼睛戴着黑色眼罩。我问母亲——她是一所免费提供世俗义务教育的男女混校的老师——那个犹太人和那个德国人为什么不跟对方打招呼,母亲回答道:“要是在欧洲,他们会杀死对方的。”在乡下出生,受到探戈里唱到的“中心之光”所吸引而移居首都的父亲则简洁地对我说:“欧洲并不存在。你在地图上见过哪个地方叫欧洲吗?”地图上确实没有。我问为什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向我解释道,二十年前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慢慢地,我在街区里认识了许多流亡的西班牙人,因为,除了一场我弄不清原因的战争【指的是西班牙内战(1936—1939)】之外,还有在西班牙建立的恐怖独裁政权,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又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蒙得维的亚之外的世界似乎危机四伏。但多亏了舅舅的藏书(我的舅舅是个公务员,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同时极端厌女),我明白了一切向来如此,从最开始,从圣经的时代,从古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时代起就是如此。战争总是起源于同样的动机:对权力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贪欲。典型的雄性动机。


我在很小的时候曾为三本书感动:《安妮日记》、高尔基的《母亲》,还有《堂吉诃德》——读最后这一本的时候,我手里得拿着词典。《堂吉诃德》是三本书里最难读的,也是最能激起矛盾心理的。我从没见过有哪本书的作者会在书里说自己的主角是疯子,但与此同时,我又为堂吉诃德惩恶除害、伸张正义的理想心潮澎湃,这理想是多么合情合理啊——既然世界是这个鬼样子。而且,在我住的街区里,有许多女邻居来向我的外婆(她抚养了失去父母的七个兄弟姐妹,又抚养了三个失去父亲的子女)诉苦,说她们的丈夫喝得醉醺醺的,有的殴打妻子,有的把所剩不多的钱拿去赌马,有的去嫖妓,还虐待自己的孩子。那时候我多么希望堂吉诃德骑着他那匹瘦马“驽骍难得”出现,从殴打和虐待中把她们拯救出来。而且,外婆也让我想起书中的女管家,她也觉得人读书太多就会丧失理智,发起疯来,不过,我并不觉得那些饱受虐待的女人们的丈夫读过很多书,他们施暴不可能是因为这个。
在读到堂吉诃德把风车误认成巨人那一节时,我大为光火,觉得塞万提斯把角色写得这么荒唐无稽,是为了向我们证明改变世界、伸张正义的事业不过是一种妄想。后来,我在第十二、十三、十四章里读到玛尔塞拉的故事与演说。玛尔塞拉美丽又富有,因此被男人们追求、纠缠不休。他们指责她要为格利索斯托莫的自杀负责,她否认了,接着发表了一段惊人的演说,拒绝男人、婚姻和性别权力关系:她要求自由,因此才远离社会,做一个牧羊女,在乡野中避世。“我生来自由自在,也想活得自由自在,所以才跑到这空荡荡的野地来。”她是这样说的。就像《伊利亚特》里的海伦诅咒自己出生的那一天,又或是欧里庇德斯笔下的海伦,反抗着那个将美貌视作女人唯一属性的社会。
塞万提斯以自己的方式去除了美貌作为女性特质的神圣光环,将玛尔塞拉塑造为一位悲剧女主角:面对想要占有她、支配她的男人们,她为了守护自己的自由,拒绝了社会生活,孤立于世界之外,从男人们身边逃离。当然,这位女主角未来将会被指为一个歇斯底里、冷淡、患神经症的女人,因为她没有扮演父权社会分配给她的角色。堂吉诃德对这样一位真实的女性角色表示同情,让我意识到疯狂可能是一个借口,用来排挤那些挥舞着可恶真相的人。当然了,为了学到这一课,我付出过极高的代价,但如果我的人生从头来过,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舅舅熟读塞万提斯,但从未跟我提起过这个段落,而且他也警告过我,女人不要写作,她们要是写作,就会自杀,就像萨福、弗吉尼亚·伍尔夫、阿方斯娜·斯托尔尼,等等等等。
我和玛尔塞拉一样,很明白在一个父权社会里,做独立女性是很奇怪、很惹人生疑的一件事。评委会【指的是塞万提斯文学奖的评委会。】(很感谢他们给予我这一殊荣)在列举颁奖理由时,不仅提到了坚定彻底的文学志向,更承认我为捍卫那些常常被政治权力和军事独裁损害的人性价值所作的斗争。曾经,我不得不流亡,逃离乌拉圭的独裁统治,因为我就像卡桑德拉一样宣布并揭露了独裁的来临,换来的惩罚是我所有的书、连带着我的名字都被禁止。我奇迹般地逃生,来到西班牙,当时,在西班牙也有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指的是1939年至1975年佛朗哥在西班牙的独裁统治。】正在压迫人们的自由。正如许多流亡中的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样,我将抵抗化作文学,我并没有像玛尔塞拉一样避世,而是通过我的书,通过我的生活,努力去做一位女堂吉诃德,惩恶除害,争取自由和正义。尽管我采取的并不是宣传口号式的、现实主义的笔法,而是通过寓言与想象的力量。我不想复制现实,而是想要讽刺现实、解读现实,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乔·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代表作有《格列佛游记》】所做的那样。让-保罗·萨特曾说过,文学即是介入。而介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从纪念那些遭到侵犯与折磨的华雷斯女人【华雷斯是位于美墨边境的一座墨西哥小城,从1993年开始,已有四百多名女性在此遇害,另有五千余人失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由此引发了当代拉丁美洲重要的女性主义运动“一个都不能再多了”(Ni una más)】,到科塔萨尔笔下的短篇小说,还有,对过度使用技术、电视摄影棚综合症以及狂热球迷庆祝仪式加以讽刺,难道不也是一种介入?写一首赞颂女女之间或男女之间欲望的抒情诗,这也是介入。想象可以是预言,也可以是介入。我不是记录现实的编年史家,许多时候我自认为像《埃涅阿斯纪》里的卡桑德拉,预言着鲜少有人洞见的未来与危险。但我创作的并不是高堂之上的文学。生活可以是悲剧,可以是正剧,但我们也可以去讽刺和批评生活的陈风烂俗,就像佩索阿写过的,“所有的情书都是荒谬的”。没错,而且,情书也可以是甜蜜的,残忍的,深情的,侮蔑的。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始于一场世界战争,终于一场国内战争(南斯拉夫内战)。保罗·瓦莱里为此写下了一针见血的定义:“战争是那些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的残杀,为的却是那些彼此相识却不彼此残杀的人们的利益。”
有时我的心头会笼上恐惧的阴影,害怕邪恶与暴力其实是人类存在的常量,而善恶之间的斗争会持续至永恒,或者变得荒谬,像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发生的那样。但当我聆听参孙与大利拉的咏叹调、洁西·诺曼的《你的声音开启我的心扉》、拉腊·法比安的《寡人有疾》、苏珊娜·里纳尔迪的《与你有关》时,我又恢复了一部分对善的信心。
有些人狂热地追求财富,追求对权力之源的支配,也有另一些人(我们这样的人)致力于表达人类的情感与幻想、梦想与欲望。


我在一首诗里写道:“古代的法老/命令书写员记载现在/预测未来。”我想,这仍旧是作家的责任,不过并不庄严,也换不到多少报酬。但作家要有幽默感,幽默感是文学的第六感。我在这首短诗里写道:“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如果诗句真的能解决问题。”而今夜,我能写出最感激的诗句,我也会完成我书写员的义务,尽管诗句无法拯救在文明的欧洲因炸弹和导弹失去生命的人们。
我读过的书(不管是路易斯·塞尔努达【路·塞尔努达(1902—1963),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还是塞萨尔·巴列霍【塞·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拉丁美洲现代诗歌的重要先驱者之一。】)都验证了母亲对我说的话:我们知道得越多,反而知道得越少,因此最基本的美德就是要保持谦逊。我的经历也证实了文学呼应了福音书中的教诲(“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也不明白”),而我用比喻写作,正如我在一首诗中写过:
词语是幽灵,石头,阿布拉卡达布拉咒语
剥落古老记忆的火漆。
诗人们庆祝语言的节日
在乞灵的重量之下。诗人们点燃篝火
照亮古老偶像永恒的面孔。
当火漆脱落,人会发现
他祖先留下的痕迹。
未来是火焰的赤红余烬里过去的阴影,这火自远方来,
来处不明。


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Cristina Peri Rossi,1941—),乌拉圭当代重要作家,2021年荣膺西班牙语文坛最高奖塞万提斯文学奖,是该奖项近半个世纪历史上第六位女性得主。佩里·罗西年轻时代即为左翼杂志《前进》撰稿,1972年因反抗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流亡西班牙,此后长期生活在巴塞罗那。至今她已出版《疯人船》等七部长篇小说,十余部短篇小说集,五部诗集和多部散文集。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3期,本小辑策划及责任编辑:汪天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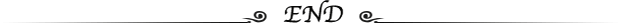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