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边界与纽带:身体书写专辑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身体是一种自然构造,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每个人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就卷入了由政治思想、宗教信条、道德观念、性别文化组成的巨大网络之中。每个人的身体并不全然属于自己,而是与其他个体和公共权力交错重叠,其间存在着一条模糊易变的界线,沿着这条线永远上演着一场沟通与对抗、联合与孤立、侵扰与自卫的拉锯战。女作家对人类身体之间的边界和纽带尤为敏感,本期的话题专辑将为读者朋友推荐一组出自女作家之手、以身体经验和关系为主题的作品。

〔俄罗斯〕克·布克莎作 孔俐颖译
这所小小的产院坐落在郊区荒无人烟的街角。旁边是一个废弃的巨大公园,里面鸟语啁啾,但四下没有灯火,只能看到点点星光。公园外面是一些破旧的房屋、棚库和停车场。野生苹果树上的果子还没成熟就已掉落。附近居民推着婴儿车、牵着小狗在公园里散步,坐在倒地的树上生火;孩子们在收集橡子。公园后面是繁忙的高速公路和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
这所小小的产院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窗框已经发黑,窗外长满了青苔,窗户里面的白漆已经褪色,夹杂着燃烧后留下的褐色痕迹。正是在这所小产院里,那些没有登记注册的孕妇被从全市各地送到此处分娩。在这里,只要付费,就能得到医生和助产士的关照,然后在双人间休息。也许产院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小。这里总共有三层楼:二楼是产房,三楼是待产室,一楼则是产后室和急救室。旁边还有个小配楼,但关于小配楼和里面的情况,我们就略去不谈了。
每天都有一些妇女在小产院里分娩。在这破旧斑驳却又温暖的产房里,门被刷成了白色,窗户上满是污迹,走廊的圆形玻璃灯散发着微弱的光亮。产科主任韦尔尼克和他的助手维尔萨维娅在这所产院的二楼为婴儿接生。从早上开始,就有很多人排着长队去找他们看诊。候诊室里的女医生对产妇发号施令,给每个人登记、灌肠、发干净的病号服,病号服上残留着未漂白的棕色污渍和常年洗洗涮涮留下的破洞。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韦尔尼克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在所有医学专业中,这个专业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不仅关乎病理学,还讲究规范。在产院里,无论韦尔尼克走到哪里,都被一群印度学生和俄罗斯学生簇拥着。他们需要实践,所以韦尔尼克有时会让他们代替自己接生。
…………
策划及责任编辑:孔霞蔚



〔俄罗斯〕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 孔俐颖译
…………
母亲走进房间,打开灯:女儿和孩子“一览无余”。母亲立时面色煞白,倚在门楣上。
“怎么,你到底还是生了孩子?我就知道!”
“是的。”奥莉娅回答。
母亲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谁的?”她终于问道。
“嗯,一个朋友的。但他后来结婚了。”
“他知道吗?”
“是的,我告诉他了。“
“我要杀了他。”
“不要,他有个女儿,比我的帕夫利克大五个月。”
“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母亲喃喃着,哭了起来,她不停跺脚,揪扯自己的头发。
之后她大声喊道:“我感觉到了,我给所有的医院和停尸房都打了电话,但就是没想到产科医院!你这个贱货,贱货,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把我们的生活全都毁了,我已经放弃你了,我心里找不到你的位置了,你这个放荡的贱货!”
母亲一屁股坐到地板上,然后躺倒在地,开始嚎啕大哭,似乎所有伤心事都涌上了心头。
婴儿哼唧起来,重重地喘着气。奥莉娅揉了揉他的鼻子,他又开始吸吮。
四周一片寂静。
最后,妈妈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
一大早她就跑出去工作了,而奥莉娅走进厨房,在冰箱里找到牛奶,给自己熬了点粥,吃完后陷入了沉思。妈妈很可能不会再给她钱了。妈妈恨她。日子过不下去了。她只能再把儿子送到育婴院。
她抱起小家伙,就这样和他一起坐着,直到天黑。
…………
策划及责任编辑:孔霞蔚





〔英国〕露·考德威尔作 柯子烨译
…………
舍友们出去了。她曾给那人发了两次短信,然后又发了一次。他没有回复。手机显示信息已经送达,有一次她甚至看到了那三个表示他正在回复的点号,但点号随即消失了,她再未收到回信。一周后,她在博塔尼克大街的克莱门兹咖啡馆见过他,他显然一脸尴尬,说自己丢了手机,刚买了新的。把你的号码给我们吧,别忘了,他说。她确实给了手机号,但知道他不会联系自己——他确实没联系。在那以后,她实在不好开口问他——可以问吗?——为什么一直是她在尝试联系。这也该是他的责任,可如今世道就是这样:这事与他无关。所以,他永远不会知道。甚至不会起疑心。奇怪的是,有那么一瞬间,她替他感到难过。这种感觉出现在半夜,倒是说得通。可她醒来时,这种感觉已经不见了。
她无法待在宿舍里。走到商业区,但离商店开门还早,接着开始下雨了,雨势大而沉闷。昨天那高远、轻盈的天空完全遮蔽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云层,阴冷潮湿的空气。这是五月的第一天。五月节,她思索着。她想起在女童子军时学到的:必须连说三次。五月节,五月节。【“五月节”的原文是Mayday,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无线电通话遇难求救信号。驾驶员求救时必须连呼Mayday三次,以防止噪音干扰、误听或混淆等情况。】她返回学生宿舍。两个舍友已经起床了,两人都是宿醉,在厨房里吸着烟。她泡了一杯茶,和她们坐了一会儿。闲聊;听自己闲聊。大笑。跟她们说说康洛赫的礼拜日,那顿圣餐。她们都觉得好笑。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十一点十一分,第二次服用药片:四片一起服下。在舌头底下,它们有着白垩的口感,带着苦味。十一点四十一分,几乎还没有融化。长时间用力保持嘴巴和舌头不动,下颚开始酸痛。坚持到十一点四十五分,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到了十一点五十分。应该够了。她大口地吞着瓶子里的水。现在不能再出去了。这些药片很可能在两个小时内起效,也许要等五个小时——有些时候会更长。打开笔记本电脑,再一次登录那个网站,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然后又一次删除浏览历史:清空历史记录,重置置顶网站,删去所有网站数据。
她等着罪恶感升起,等着感到后悔,但这种感觉并没出现。到底是什么感觉?她辨别着内心的感受。害怕,是的。绝对是害怕。她已经删除浏览记录十七次,十八次了。但他们有办法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在网上某个地方清楚地写着她的名字,她的住址,她的贝宝账号,她的所作所为。何时,何地以及具体的方式。她,或者任何帮助过她的人,都会被终身监禁。所以,那种感觉是害怕。
…………
策划及责任编辑:叶丽贤



〔美国〕海·玛·维瑞蒙迪斯作 秦贵兵译
…………
他躺在那里时,他的灵魂在闷燃,就像一团快被浇灭的火,嘶嘶作响。托马斯的妻子想到了崩塌中的塔楼,接着想到他喝那些刺激品,把隐藏在内心的激情解绑、释放了出来,这些激情灼穿灵魂,飘向一团闷燃的烟,让他大发了一通无名火。托马斯现在成了一团不可战胜的过往烟云,她想。一缕袅绕的烟魂。她跪坐在他身边,把她拼图小拼件般的心靠在他失去生机的心脏旁边。失去生机是因为她用力扣动了扳机,然后手指紧扣不放直到他胸膛炸开,溅出来的血四处渗,玷污了所有的明天。然而他却显得越发有生命力了。不。是比她身边的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更加真实。她用祈祷的口吻对他说话。“你呢?这是你的选择,托马斯。至于我,我没得选。为了你,我放弃了做真正的女人,就像你娶我时放弃了你的自尊自重。当然了,此时此刻,我感觉和你很近;同样是死了,但同样真实。”她怎么能向他解释自己被他、他的上帝和他说过的话搞得如此疲惫和憔悴,如此备受折磨呢?她曾经试图挑战成规,和另一个男人上了床,但那只是让她的处境变得更糟糕了。她离不开他,因为她不再拥有自我。他拥有她,她的孩子们拥有她,并且她需要他们所有人才能活下去。而她厌倦了需要。
该告诉警察什么呢,该说什么。托马斯的不忠。那就像他躺在沙发上的尸体一样真实。“托马斯是个可靠的男人,但是肉体就是肉体,男人就是男人……”
阵阵酸性雾气在她的五脏六腑猛烈地抓挠了一通后,怯懦地从她身上爬开了,与弥漫在医院病房里的尿味混合在一起。她的孩子们迟早会原谅她的。但是上帝呢?永远不会明白的;也是一个男人。不会。她会变成一只蟋蟀,夜夜哀鸣以祈求救赎。这挺适合她的;她会为了救赎而哀鸣。带着一种抗拒性的认命姿态,她像僵尸一样盯着印在腕带上的名字。
…………
策划及责任编辑:杨卫东



〔尼日利亚〕奇·恩·阿迪奇作 林红译
美国总统画着浓妆:她的巧克力色脸上扑的粉底太浅,睫毛膏在睫毛上结成了块儿,下嘴唇上的浆果色口红有点糊,像一个小伤口。她看起来准备得很仓促——编织接发【编织接发,原文为weave,一种接发方式,将人造发丝或真人发丝通过编织手法与接发者的头发接在一起,使其头发更长更厚】有些平直,需要卷一卷——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话时也不停地眨眼。若在以前,这种新闻发布会对奥比纳来说只是电视背景噪音,即使他在听,那也是漫不经心,敷衍了事。现在,他紧盯着电视,音量开得很大。对那些以观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为荣、了解美国国会远甚于尼日利亚参议院的拉各斯朋友,他一度觉得很傻,但是他,至少这一次,正做着与他们同样的事情。大约一个月前,老朋友伊兹打电话说他要回国看看,自那之后,他便开始疯狂地看美国新闻。《男性手淫法案》似乎就是新闻上讨论的全部内容,这个已有四十年历史的法规正受到挑战,专家们语速飞快地推测着最高法院的决议会是什么。就在今天,决议宣布:男性手淫仍然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十五年监禁。
美国总统在一个面部特写镜头中说道:“我为最高法院这一公正而道德的决定鼓掌。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有可能出世的小孩子给浪费掉了。”
她看起来过于戏剧化,但就算那样,也比尼日利亚总统好。她戴着不合适的假发和艳丽的珠宝,在镜头里总是以一种平板的语调磕磕巴巴地念演讲稿,就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些语句似的。电视屏幕中的背景是一群男人,有黑人白人,有亚裔西班牙裔,他们穿着西装,或连帽衫,或T恤衫,手里举着标语牌。尊重男性身体自主权。政府的手别碰我的精子。我们的身体我们做主。原小说里不少引语未加引号,在译文里皆以楷体标注。奥比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对一些本该秘而不宣的事情大惊小怪。严格来说,男性手淫在尼日利亚也属违法行为,但男人们一直在做这种事情。男人毕竟有需求,奥比纳自己也做过很多次,但大家都秘而不宣而已。挑战法律的美国人声称,自己要活在真实中,不用再隐瞒手淫的事实,那是他自己的身体,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奥比纳来说,活在真实中听起来就很傻,为什么美国人总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还有就是,他想对这一决议有一个更成熟的观点,好给伊兹留下深刻印象。他想知道,伊兹是否还喜欢修旧引擎和旧钟表,一切原先好使但后来坏掉了的东西。每当想起伊兹对机械的痴迷时——他尤其喜欢修理机器并让它们起死回生——奥比纳都会对过往的日子产生一种强烈的怀旧感。
在伊兹离开的这十一年里,他们只是偶尔联系,可仍然有些事情让奥比纳怀念在大学一起度过的时光,让他觉得,只有伊兹懂。他们是中学时的好友,到大学后更加亲密,大家甚至叫他们双胞胎,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像,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一起:伊兹,高大英俊的一团火,一路上碰着东西就烧,而奥比纳,内向、专注,总是走在边上。
…………
策划及责任编辑:余静远 杨卫东




〔阿根廷〕塞·阿尔玛达作 张雅惠译
…………
晚些时候,安德烈娅和爱德华多骑着摩托车去市中心闲逛。主广场周围车水马龙,汽车和摩托车混在一起,速度慢得像在游行一样。他们吃了冰激凌,就回安德烈娅家了。
父母和弟弟都回卧室了,法比安娜去跳舞了,房子里一片寂静,穿过薄薄的墙壁,大人卧室里的电视声隐约可闻。这对小情侣在厨房里亲吻,彼此爱抚了好一会儿。突然,他们听到院子里有动静。爱德华多出去看了一圈,没发现任何异常,不过,在大风中摇曳的树冠和邻居家晾衣绳上的衣服都在提醒着他:要变天了。回到屋里,他告诉女朋友要变天了,两人一致决定他最好现在就回家,以防在半路遇上暴风雨。他没有马上离开。两人继续亲吻,隔着衣服彼此爱抚。直到安德烈娅敦促他赶紧走。
她把他送到街上。狂风吹乱她金色的长发,她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两人又吻了一次,然后他骑着车迎风而去,她则小跑着回到屋里。
安德烈娅打开了朝向院子的窗户。这时候的气温虽然下降了一点,墙壁仍然是热的,床单也是温暖的,就像刚刚被熨过一样。她穿着背心和灯笼裤躺到床上,拿出笔记——划满重点的复印件,空白处还有手写的注释。
不过,安德烈娅应该是很快就睡着了。根据她母亲的证词,风越刮越大,母亲去她房间关窗户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安德烈娅的母亲刚看完《私人演出》节目中播放的电影。这是一档风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节目,由卡洛斯·莫雷利和罗穆洛·贝鲁蒂主持,节目流程是他们先介绍一部电影,看完之后,两位主持人边喝威士忌,边对电影进行评论。那天晚上播放的是一部快二十年前的电影,卢卡斯·德马雷执导的《大麻烟》。其实,安德烈娅的母亲对这部电影兴致寥寥,但因为毫无睡意,还是把它看完了,然后没有继续听莫雷利和贝鲁蒂的评论,就关掉电视睡着了。
过了一阵子,她醒了过来,下床,走到两个女儿的房间,打开灯。安德烈娅还躺在那里,但是鼻子上有血。母亲说自己看到这一幕后,整个人都瘫软了,钉在门口无法动弹,连着喊了丈夫两三声。
“快来!安德烈娅不对劲。”她喊道。
过来之前,丈夫还花时间套上了长裤和衬衫。他抬起安德烈娅的肩膀,她的胸口又涌出一点血。
旁边法比安娜的床还空着,床单铺得很平整。暴风雨来势汹汹,正是最猛烈的时候,阵风强劲,大雨滂沱。雨水打在铁皮屋顶上,听起来像连发的枪声。
要是安德烈娅在死前曾经醒来过,她一定会感到迷茫。她的眼睛猛然睁开,在氧气耗尽之前的两三分钟里,她肯定眨了几下眼睛想让大脑清醒过来。她会感觉迷迷糊糊的,被接连不停的雨声和院子里被风吹断的娇弱的树枝声搞得心慌不已,噩梦来袭,魂不守舍。
…………
策划及责任编辑:汪天艾



〔法国〕白·卡诺纳作 陈贝译
…………
*
我们唯有自己可怜的身体以供呈现。美丽或丑陋,年轻或衰老,均无关轻重:世人皆如此。陪伴我们的,仅有这具肉身、这张脸庞和这副骨骼。若想满足他人的欲望,我们能献出的,仅有这一个身体。时常,你瞧着路人来来往往,那景象让你揪心,难以描述: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悲怆与脆弱——无论上天有何赠予,凡人都是如此脆弱。而人人都操心着这样一个如此短暂易逝的外表,乐此不疲。
*
并不是说,我们应摒弃修饰。自古以来,人们就装扮自己的身体。因为外表是内心的表露,内心因外表而可见,外表能向外界宣扬自己的个性,同时,亦是向他人的致敬(我为你而容),向他人彰显他的存在。我们花心思打扮自己,盼望以这种方式,来昭示对他人的敬意。日日清晨,我们并非衣衫褴褛地踏进世界之中。或许,我们亦以这种方式,颂扬宇宙。
墙上贴了些海报,宣传的是一部关于失忆症与真爱的电影。你旋即浮想联翩,你寻思着,假若我们忘记了一切,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否还会记得?假若你突然失忆了(永久性的),那么,面对你曾热切渴望的那个人,你的身体是否仍会有所触动?然而,这依旧是同一个身体吗?你抛出有关记忆的假想之问,而记忆(兴许)仅与心灵相关,你想知道:纵使失去记忆,欲望之源(身心)自己是否还会记得?
有些失语症患者再也无法说话,但可以唱出长长的歌曲,且歌词毫无差错。他们唱出的词已不完全是一句言语,而是属于语言区域之外,大脑另一个区域控制之处。欲望亦如歌曲一样,寓居于我们的存在之中吗?
*
休憩。身体缠绕在穿透窗扉的旭日灿烂之中,永恒的夏日之光。你感觉已历经了上百次这一时刻,它淹没在你故事里的所有缠抱里,它不再是个人的体验:你觉得自己像是古典画作《日光下的相拥》里的人物——普桑【尼古拉斯·普桑(1594—1665),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画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的一幅感性之作。
*
你有时激动不已。因为,在肉欲和快感之外,贝洛伊佐【贝洛伊佐是作者的一个虚构人物。作者在《海洋报》2016年4月30日的采访中表示,随笔虚构化是自己的创作风格,这里的贝洛伊佐便是一处佐证】的姿势给你的感受仅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雄辩。你回想这一切,你无法解释这种感觉——然而,你确切地觉察出,他拥抱中的雄辩之力。
身体与文字一样,皆能清晰地传达意义。
…………
全文链接:第一读者 | 白•卡诺纳【法国】:握持
策划及责任编辑:赵丹霞




〔英国〕克·汉森作 方芳译
…………
随着产褥期精神病这一病种的出现,医学话语对母体不稳定性的强调在十九世纪势头更甚。这包括产前和产后的情绪紊乱,通常持续数月,每次怀孕都会复发。怀孕可能导致过度消沉或精神错乱的想法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产科医生提出的。例如,道格拉斯·福克斯在《孕期的迹象、疾病和管理》(1834)一书中写道,一旦被确定怀孕,身体“系统内会出现无数的交感反应……通常会引起最异常的精神刺激,表现为焦虑和抑郁”。同样,威·费·蒙哥马利【威·费·蒙哥马利(1797—1859),爱尔兰产科医师】在《论孕期的迹象和症状》(1837)一书中写道:“神经系统所受的刺激在某些人身上最显著的表现是精神气质的改变,使人变得抑郁和沮丧。”神经质发作、妄想和抑郁的案例屡见不鲜,两类主要病种应运而生:产后躁狂和产后抑郁,前者的症状是精神错乱和情绪激烈,后者的症状是情感淡漠、绝望及自杀念头。在这个时期,为人之母、善理家务被奉为女性最神圣、最崇高的使命,产后精神失常可以视为母性的怪怖分身;一些最常见的症状,如破坏家用物品、勾搭陌生人,可以解读成对母性意识形态的直接挑战。这种疾病的起因复杂,不过,它的流行,经证明,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母亲所经历的相对隔绝的社会状态有关,也与穷人长期健康欠佳以及家庭破裂之类的压力有关。
从伊丽莎白·布朗宁的诗作《奥罗拉·李》(1857)到艾伦·伍德【艾·伍德(1814—1887),英国作家,常被称作亨利·伍德夫人】的奇情小说《东林怨》(1861),大量文学文本都探讨产后精神失常问题,只不过很少有人讨论这个文本现象,也许是因为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母性总体上是一个探讨不够深入的话题。最引人注目的片段之一出现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中。凯瑟琳·林敦的怀孕串联起这个跨越数代人的小说情节。怀孕巩固了她从呼啸山庄的社会边缘地位到画眉田庄的高级资产阶级女性的转变。怀孕也确立了她传承林敦家族血脉和财产的角色,而她却试图维持与希斯克利夫的关系——这段关系可以追溯到童年,当时的她“泼辣,刁蛮,又无拘无束”——来抵抗这一角色。然而,凯瑟琳试图保持独立自我的努力被自身的母体挫败,她和林敦的一场激烈争吵引发了产后精神错乱。发病的过程与托马斯·格雷厄姆【托·格雷厄姆(1795—1876),英国医师】在《现代家庭医学》(1827)中的描述完全吻合。《现代家庭医学》是一本大众医学指南,勃朗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就曾拥有一本。第一阶段的典型症状是产后狂躁,比如,凯瑟琳用头撞击沙发,然后跳了起来,“头发披散在肩上,眼睛里闪烁着火光,脖子和手臂上的肌肉异乎寻常地鼓了出来”。耗尽气力后,她将自己锁在屋内,后因脑膜炎卧床两月。尽管身体恢复,但在纳莉·丁恩看来,她如今空有一副人的躯壳,表现出产后抑郁的所有症状。她无精打采,被病态的思绪折磨,林敦试图安慰她时,泪珠“顺着她的脸蛋淌下来,她都不理会”。她的外貌特征符合当时对产后抑郁患者的描述:
她那对本来炯炯闪亮的眸子,现在蒙上了一层迷梦般凄楚的温柔,你只觉得她不再注视身旁的事物,而似乎总是凝视着远方,那遥遥的远方——你也许会说,她的视线落到了人世之外呢。她脸上的肉长了回来,原先憔悴的模样儿已经消失了;可是,那苍白的脸色,那异常的神态——她内在心境的写照——让人痛心地想起背后的原因,同时又格外地惹人怜惜。
纳莉的描写强调了落在人世之外的凝视的目光,预示了她对凯瑟琳之死的反应。在她眼中,凯瑟琳已然脱胎换骨,她平静而安详的神态激发人们去思考“那无边无际、照彻光明的境界……在那里,生命之火永不熄灭”。这种对母体的神化源于纳莉对凯瑟琳的道德缺陷与其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读,其言外之意是凯瑟琳所受的苦难,对她的固执任性来说,是一种补救。
…………
策划及责任编辑:叶丽贤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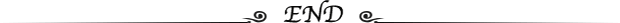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