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读|维•谢阁兰【法国】:一切江河命中注定了不认识其他江河,只知自己……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而这一切,大江的精魂实在也不知道。也不知要流几里路;也不知将有多广的流域;或许只知道支流的数量,而它只当作那是一个个搏斗的时刻;它无需十分确切地知道,它吞没的这条大水流的长度是第四还是第五;又或泥沙含量第二……一切江河命中注定了不认识其他江河,只知自己。
维克多·谢阁兰作 邵南译
我不确知它从何奔流而来。它自己也不知道,更不必说那贯穿它,鼓动它,为它的每一次跃动打上印记的江神了。那是因为,大江之精魂——但愿其存在从此确凿无疑——仅当大江完全意识到自我,确认了自身滔滔不绝的个性之时,方才存在,蕴藏其中。正因此故,虽然我唯图以此文向江神致敬,却无意花工夫分辨,那儿,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到底是这一茎细流,抑或极为相像的那一缕,才是它的正源。如同在一个巨大的婴儿身上一样,所有的细流,在那儿,包含着一切可能:只要向西或向东一百华里,这条溪流没准就会成为忧伤而面目模糊的黄河,半为北方的泥浆吸收,不然就成为湄公河或萨尔温江,在热带雨林中度过数不尽的日头,或者出于最荣幸的机遇,成为大江自己——扬子江,以意愿之弓洞穿这巨大的帝国,它像甘橙一样浑圆,如同行将腐烂时那样流香四溢。而这一切,大江的精魂实在也不知道。也不知要流几里路;也不知将有多广的流域;或许只知道支流的数量,而它只当作那是一个个搏斗的时刻;它无需十分确切地知道,它吞没的这条大水流的长度是第四还是第五;又或泥沙含量第二……一切江河命中注定了不认识其他江河,只知自己。


所有的大河命运相似,它们在世上独一无二,但凡一条河去接触同类,都只是去吞并它。相形之下,山的精魂友于兄弟,山头和山头可以自由相望,且经由地脉相联相通。河流,就算靠得再近,也一个同类都不认识。它脱离潜演的水网,只为立即开始孤独苦涩的生命之流,从此江神被再也翻越不了的屏障与外界隔离,而人们知道它将奔向海洋,溶解于怎样的虚无……两股水流,无论路径是否平行,无论水质是否相同,都只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犹如天上的两道星轨……即便是它的支流,它去接受,去认识,只是为了立即将它们吸纳为自己的一部分,那时便少不得一场搏斗,时而造成强大的涡流。所有的大河,都绝对唯一而无与匹敌。美丽的生命,苦涩而高傲,从不触类旁通,唯有一己的曼曼长波。
这一点,江神隐秘而强烈地猜到了。而仅仅当大江集聚力量,确认了自己的威力;当它凭着意愿而存在,正当此时,而非其他,当它,大江,达到自身顶点之时,江神才存在。这时它才拥有生命,它的急流,它的盈枯,它的愤怒,它的悔恨,枯水时节的湍濑,星辰引起的潮汐,另一些则无端而发,与日升月落无干;它的涡流,它的跳跃,它的泛滥,还有它翕动的皮肤上的寄生虫:载货的舟船和节庆的游艇;它两岸的蚤虱:拉船的纤夫、他们的女人、附生的村庄。也正是在这一刻,它以最强大的活力奔向最严酷的障碍。正当此时,它的个性爆发,这是它生命中异乎寻常的瞬间。此刻,大江包藏着江神,如同一个力量达到顶点的人。
那是险滩和山峡的时刻【谢阁兰笔下的“时刻”(Moment)一词有特殊含义,指的是极其相异的两个生命或世界相碰,神秘感和刺激感达到顶点的时刻——谢氏认为,这也正是生命力爆发、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机。此处乃将一系列的险滩与山峡视为江神生命中的关键点】。它久已兼并了嘉陵江,随后是涪陵江【原文“fleuve de Foû”所指不明。“fleuve”既为“江”,此似当为“涪江”,但涪江乃嘉陵江支流,并非直接进入长江,与此地所谓长江兼并“fleuve de Foû”不符。谢氏在笔记中还多次提到与此略似的“Fou-ho”,乃成都之府河,即岷江经都江堰分流而流经成都市区之一支。谢氏既是从府河登舟泛江,遂时常误将“岷江”与“府河”混称。既然“Fou-ho”实指岷江,则此“fleuve de Foû”亦岷江邪?然岷江乃先嘉陵江而入长江,非继其后为长江吞并,谢氏亲历二江且印象深刻,笔记颇多,似不致将顺序颠倒。另外,下文尚有表述相近的“rivière de Fou-tcheou”,按描述应是继嘉陵江之后入长江者。按“Fou-tcheou”是“涪州”(今涪陵)无疑,“rivière”为“河”,则“rivière de Fou-tcheou”应指涪陵江(今乌江)。至于何以称“涪州河”而不称““涪陵江”,则恐是涪州正当涪陵江口,而谢氏遂将城名涪州与河名混淆。则此所谓“fleuve de Foû”者,不知谢氏乃误以涪江为注入长江,还是误将岷江(所谓“府河”)与嘉陵江顺序颠倒,抑或将“涪陵江”(所谓“涪州河”)误省为“涪江”?我们姑且遵从地理事实而译为“涪陵江”】,势力得以壮大,于是丰盈,坚实,与群山的万般阴谋较劲,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他要向东去;那一回,他最终决定了前去投入东海,而非附庸国安南的海湾),它将要越过一道又一道槛,奔下一级级阶梯,投身于崎岖坎坷的幽谷……这一切,位处重庆和宜昌之间,在十八行省的中央、佛国明珠——四川的心脏,也适值它将要洞穿的甘橙中腹。那是它伟大的成熟岁月,充满暴力的年纪:险滩和山峡接踵而至的征途。



重庆的岬角是它新生活开启的标志。当它来到此地,已经拥有了它美丽的醇厚色彩。它打磨了如许的陡岸,它舔舐了如许赤红、赭色、灰色或是微蓝的黏土,而它的水一旦混和了所有这些尘土,便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色泽。不再是愚蠢的清澈,不再是它源泉的眼神里那种天真;而是变幻如虹影的乳色;不再如玻璃般透明,亦不再冷漠……河岸与水的长期磨合造就了这油润的水流,它阻断窥探隐私的目光,藏匿深渊,唯示人以变幻的光影,时而铁锈色,时而蓝绿色,取决于这是它那流动之身本来的颜色,还是蓝天的颜色投映在它不透明的表面上。
就是那儿,最底下,躺着江神不可捉摸的身体,他守着自己不可理喻的存在,就是那儿,那些奇谲的泥浆下面。而互相碰撞的每一颗微尘,每一颗悬粒,是大江的一星回忆,他由此得以历数自己绕过的弯,接纳过的支流,往昔的漩涡。正是在翻卷这些泥土,翻卷亿兆微尘的过程中,大江回味过往,继续前程。金属的颗粒缓缓锈烂,一点一点融化在奔腾的江涛之中,予它以自己的滋味,而渐渐失去自身的特点……有时,从河床的底部突然涌起一堆陈年旧物,一股诡异的洑流瞬间将它们托上水面。大江想起:这来自馥郁的云南;或者,它依稀记得这来自某次汇合,而今这属于别人的滋味令它不安。江神颤抖了,仿佛正迎向某种未知的危险事物。
重庆的岬角是它步入成年的标志,——大江雄风浩荡的岁月。正是在重庆,一场纷争让它展示了巨大的膂力。正是在那儿,突然,嘉陵江呼啸而来。起初,尖尖的山嘴将它们隔开;它们本已行将相遇,大山蛮横地插手将它们阻拦,在两边都造成了激荡。且看两个敌手先是猛然跳开,再重新扑向对方,厮打起来。它俩分歧显著,差异鲜明:水量、宽度、丰枯季节和水位尽皆不同(或许一个已迎来盛夏的大潮而另一个尚全无征兆)。这种反差时时造成剧烈的涡流。倘如它们势均力敌,流速缓慢,便兴不起波澜。然而,一旦嘉陵江猛涨,且看从它的右岸到左岸,以一种缓慢呼吸的匀速形成了螺角形的漩涡。水在其中像马戏一样打转,旋纹向中部收束,在漩涡中心生成一种无可抗拒的吸引力。那是江河翕动的大口,一张活跃的吮吸的大口,充满了强暴而胶状的水,一口咬定便不再松开。每当一个鲜活的猎物,一具人身,只要触及它的边缘,由于人生短暂,且他所属的领域(譬如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不同于“江河界”,他便注定了葬身水底。唯有这大江,这激流,这无孔不入的水,拥有随物赋形的流质生命,无止无休,长化长新,却又万变不离其宗。
那如同环行的水流,立刻就会团团打转。寄生其上的人类嗅到了严重的危险。且看小舟的细腿全都狂舞起来,舟上的八个小人儿使尽了气力,时在船头,时在船尾,然而一想后退,船却前进,想要前进,却趑趄容与,终不免原地打圈。少时它便滑向中心,逐步下沉,因为既已拢起的大口是空洞的,比冬天低潮时的水面更虚。于是小舟陷入坎穴,陀螺似的疯转起来。它的头被攫住,扎了下去,尾翘在半空,于是为大江所吸,所禁,所持,终于惨遭灭顶。霎时间,大口平静了,不再向其他猎物张开。它们本可轻易通过,但不知何故却紧跟着猛冲上前,或许正疯狂地期盼着相同的厄运,这对于生命短暂、形态具体的人类来说兴许是充满醉意的。有时,大江会把它宴席的残渣啐在他们脸上。因为它流动的肌肤并不能消化所有材质。另一些碎屑太轻,只是浮泛而去……


大江和嘉陵江搏斗一场,取得了胜利,立即将对手拽上了自己的道路。此时的大江,水量丰沛,仍然鼓胀,只不过是在涪陵江口的对岸。哪儿来的呀……这些清澈而甘美的水。这水融入大江的生命,它顿时春光焕然,步履轻盈。这水蹦蹦跳跳,透着一种天真朝气。可这水载来的小舟,还有它任人在其沙渚上拖动的那些舟船,是多么古怪呀……大江对这些两角的种族漠不关心,只管过去,水流既归平衡,它便奔向第一道山峡、第一重险滩。如此而已。大江与众不同,个性完满,就此率领全部浩荡洪流,冲进千岩万壑的险途。
迄至此时,它的骨骼表面上是柔软的:这暗示了底下的情形。那里的水仿佛连绵起伏的平缓山丘,下贴河床,河床稳稳地端着水。水在流动,却由于规模浩大而和普通的流水毫无共同之处。首先,江上的的确确长着一层皮肤;大江的皮肤。
他们是想触知这皮肤的颤动吗?这些水生的昆虫,三板的船夫们,时时驾着三块木板拼就的小舟奔赴江流,舟尾曳着一条长长的桨。兴许这是一种极好的用以触摸和感知的器官。江流黏稠的肌理、它的欲望或平静中极细微的变化,用眼睛需延滞许久才能看出,而多亏这尾部的触须,人们登时就能察觉。于是,根据情况,他们或者应以尾桨(他们称之为“艄”)的一击,或者让前端的条条细腿飞舞起来。而大江的皮肤尚有别种感觉:它时而内褶,时而皱缩,时而延展;它拉伸,凝滞或黏连,或者转瞬间直直地朝前流去。江风乍起,令它蹙迫,将它激怒,把它的皮肤逆向撸过;它便暴跳起来,扬起波涛(正如大海和它那些粗鲁而简单的运动),那波涛翻滚着,飞沫喷向北风。不过这些动作都是古怪的,与流水的生命格格不入。它们只是停留于表皮而已。那只是粗野的刺激行为。


这张波澜起伏的皮肤下,激流的生活何等惊人:这儿流水的运动在别处绝难见到。此地全无那种粗鄙而可怕的幻想故事,把一艘八十吨的轮船垂直吸进去之类,而是一系列漩涡的戏耍,不张扬,不停歇:这些螺旋的生命,倏然降生于两股速度不同的流水相触之时,有条不紊,生机勃勃地打旋,移动起来有一种喜剧性的威严,而如果可能,它会在路过的时候逮住另一只漩涡,制服它,吸收它。这是一系列永不停息的此消彼长,或者毋宁说体现了无穷无尽偶然事件的连缀:“原自无识……非也,吁,师尊……”大江想起自己来自高原佛国,那里的文献依旧保留着有关佛法与认知的纯洁篇章。
在这些漩涡周边,另一些运动更为粗鲁,有点可笑。那仿佛巨型的扁豆,流动的庞大水母,突然抬高水面,一时间展露出它们圆润、光滑、油亮的穹顶,随后周边开始流动,它们破裂,水花飞溅,伴随着环行的震颤。这如同钝器的一击,水中的羊角。它们强大起来,有时会造成破坏;三板的船夫们轻蔑地称之为“水炮”,对它们避之唯恐不及,因为那里边自下而上的冲顶相当猛烈。
他们有所不知,大江在底下并非蜿蜒蛇行,而是像海龙一般驰骋的:这是它同侧脚爪一齐拱进时的晃荡;这是它在斜坡上的腾跃,它腾跃而起和戛然留步时迸出的水泡。
视丘陵质地的不同,视路途本身的不同,还会有别的跌宕和变数。江流知道如何满满地舔一口河湾的沙土,又如何抛出腻烦的一切来把尖岬塑得圆润。然而,这中空而急速的湾流偏偏还得打上新的失衡的印记:哪怕在这安详无比的水隈,丛丛水草滋生繁衍,绿意葱茏,比起时而采食它们的人类恬静有加,这里尚且有倾仄的岸,还有迅捷突跳的潮水,时而漫过一块岩石,向四围泻下水幕。这里边还有“险角”,有点像陷阱,一旦进入便难以安然脱身。
最后,视河道与水流的形状,根据江面是散涣还是收束,它的速度——它的身外之物——增强或是减弱。有时却是反常的:三峡的河道,其高十倍于宽,江流在其中本应呼啸奔腾,却时时趋于平和,且信心十足,胜券在握,故而缓行阔步,静水深流。
这是一些各自为政的元素;各行其道的动作。所有这一切,湍濑、漩涡、急流,在大江生命中这可羡的危机时刻,也就是险滩,汇聚一处,登峰造极。那是江流的一个结,决定性的一刻,一出完整的悲剧,其情节的开展,危机时刻以及大结局尽皆演绎在唯一的布景之中,那挫锐解纷的过程真可谓酣畅淋漓,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胜利之狂喜。
正是在险滩的核心,大江所拥有的暴力品质、能量、对付大山的谋略,都达到了极致。险滩可谓强暴品质达到巅峰的时刻。它拥抱并包围的每一道障碍,每一次跌宕,都是一头活蹦乱跳的猎物。而大江似乎并不知道能否顺利过关。它遭遇的障碍可能和它自己一样历史悠久:一道长坂、一道埂,还有江神在出海口的踉跄摇曳之前,在激流趋于平缓之前,久已熟知的那些岩石。然而有时,比如所有险滩中最美丽、最纯粹的那一处,新龙滩【新龙滩在今万县和云阳之间,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一次大规模的山体滑坡造成。初名“新滩”,旋改“新龙滩”以区分于秭归新滩。后又讹音为“兴隆滩”】,“新近出现的龙之险滩”,那是一道新生的障碍,大江自己都没有浸蚀过。那是一整座小山丘的基部发生了松动,加之大雨的连日冲刷,翻倒在峡谷里。



大江,自它在那儿的廿余年以来,已经将它驯服了一些,然而还是犹豫了,因为在这关口之前两三华里的地方,我们看到它突然沉静下来,舒展肢体,流速减缓,仿佛陷入一种慵懒的状态。在此,大江肯定是自知即将进入险境,预作准备——不如此解释,哪怕从河床的深度和河岸的形貌来分析,我们都无法理解这种慵懒。它一定是知道的,无可置疑;因为这一伟大的流动之身,其生命的丰富性即在于此,它不是从源头到入海口单向流逝的,而是时常通过一些相当神秘的暗脉,自遥远的上游便获知了下游的情形。在这儿,显然,大江每分钟都在搏动。这是险滩激流的脉搏,决战在即的颤抖。
正是如此,收魄敛魂,屏气凝神,专心致志,水流非常缓慢,却已经因奔向障碍而激动得发抖。大江准备就绪,只等第一次飞跃。
周边的岩石不胜高峻。略无缝隙可通。大山拦在那里,扑灭了所有绕道的希望。大江开始加速,坚定无比地奋勇向前;它的脉搏总是维持同样的节奏,然而愈来愈喧嚣。柔滑的江波变成了狂野的惊涛,涡流和轻微的震颤已经显现。假如它能看,它现在应该看见路障了……可它已经在这儿了。
最底下,左右两侧突出的岩石像两道栈桥一样,收束着水流。所有奔腾的水正要从那里一泻而过。大江刹那间改变了性格,且看从最中央,一条三角形的水舌电射而出,光滑得犹如一把锃亮的利剑,那是因急速而坚硬无皱褶的水;凝成一股绳的不屈的江流。


然而在它岸边,下面,两旁,更深处,所有尚未过关的浩荡洪流在抗争,崖转石砯,争喧竞豗,相对于那股锐利的水舌,是为激荡着涡流的另一层水面。接着是所有它迄今未知的障碍、顽石、断壁。顺着两岸是长流的细水;其中一些随着中央的水舌下泻,另一些则冲上土岸,再不停地打着回旋落下。而就在此地,水舌连同涡流一齐注进坎底,此际,无名的纷乱之中,任何动作都有可能。铦利的舌尖旋转起来,几乎竖直向水深处捅去。一溜喧嚣的泡沫将它吸纳,吞没。一些漩涡往一侧打旋,另一些则反向旋转,将它们碰破。水中有瀑布,有水洞。有自下而上的涌射,向水面冲破一只只水泡。大江分散在努力之中,仿佛碎成齑粉,没有脉搏,没有江流,没有意识。唯独在下一道河湾,当它恢复了宁静,平息了暴怒,仅仅当速度重新变得均匀,归于平衡;——大江回忆起先前的搏斗,于是明白,那一刻已成过往。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是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1909年12月15日,谢阁兰从成都登舟,泛岷江,入长江,顺流而东,直至次年1月28日抵达上海。2月4日,继续从长江口出海,赴日本长崎。这次为期一月有余的长江之旅,对谢阁兰文学创作的影响至为深远,长江从此成为谢氏笔下的一个重要意象,在《砖与瓦》《一条大江》《画》《出征》《西藏》等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而散文《一条大江》(Un grand fleuve, 1910, 1912),作为唯一专门摹写长江的作品,可谓谢氏关于长江的众多体验、想象和思考的结晶。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9年第5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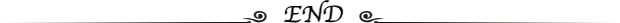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