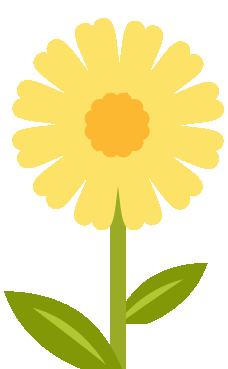散文品读 | 弗•马尔蒂诺夫【俄罗斯】:我命定要在莫斯科漫步,于是,我漫步在莫斯科的土地上……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莫斯科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像是一篇巨大文本中的一行,或许只不过是小学生练习本中字迹潦草的那一行。然而,我已经不再需要去写文章或者写诗,因为,当我漫步在莫斯科街头时,我本身已经成为这篇文章或这首诗的一部分,即便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词。
——对一个尚未形成的卦象的解析
弗拉基米尔·马尔蒂诺夫作 刘娜译
《漫步莫斯科》【《漫步莫斯科》,苏联影片,格奥尔基·达涅利亚(1930—)执导,尼基塔·米哈尔科夫(1945—)主演,1964年在丹麦首映】这部电影中有一个镜头——顺便说一句,我后来才知道,这正是达涅利亚本人最喜爱的镜头——瓢泼大雨中,一个浑身湿透的姑娘赤脚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中间,双手拎着鞋子,另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缓慢、笨拙地围着她绕行,极力用自己的伞为她挡雨,但那姑娘却躲开他,宁愿在雨中淋着。这个镜头大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莫斯科的象征。它让人感到异常幸福,一种只有在那个时代的莫斯科才能体会到的幸福。莫斯科夏天的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桩特别玄妙的事。电影《普柳希哈的三棵杨树》里,莫斯科出租车司机就是在雨天爱上了一位农村姑娘;胡兹耶夫的电影《七月雨》中,莫斯科的雨成为所有美好希望的化身。总之那个时代一切都很好。要是有人不相信这一点,说“不是这样”,肯定有人会回答说“就是这样”。想象一下,假如那个说“就是这样”的人是你即将爱上甚至已经深爱的女孩,你就不可能不赞同那的确是个美好时代,因为以后确实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时候了。我知道,《漫步莫斯科》影碟开始出租后,很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支持达涅利亚,他们指责他有意美化现实,赋予现实某种完美幻想。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谁能将幻想和现实完全分开呢?被我们当作幻想的事情,实际上却是千真万确的;而我们以为是现实的,只不过是可怜的幻想罢了。生活中此种情况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对于我,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的苏联的确非常美好,就像国库券花边上的图画一样完美。在这幅图画里,飞机在空中展翼疾飞,大型高炉和工厂里的烟囱拔地而起,瀑布从大坝上倾泻而下,电动拖拉机在一望无际的麦田上作业,而在远方,流线型的火车呼啸而过,雄奇伟岸的建筑物一尘不染。当我长到可以持有债券的年纪,我开始像新生儿一样观察这个世界,发现它比上面这幅图画还要美好。斯大林时代建造的气势恢弘的高楼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后来我的精神导师西捷利尼科夫称它们为“瘟疫时期的后古典主义建筑”,但童年时代的我却认为,它们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乃至整个人类精神的伟大胜利。莫斯科地铁给我带来同样的震撼。环线地铁站甫一开通,妈妈就带我去参观,我被各式各样的风格和工艺彻底征服了。壁画、镶嵌画、彩色玻璃拼贴画、马约利卡彩陶工艺、大理石雕塑,应有尽有。对于我来说,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妙不可言的、史诗一般的传说,它在歌颂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民族团结。国民经济成就展的展馆和喷泉也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于我而言,整个建筑群的和谐统一,那里的每一块石、每一片铜、每一滴水都是各民族友谊的化身。在这里,所有事物都以整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连我自己好像也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感觉在我看到克里姆林宫后愈加强烈起来。那个年代,克里姆林宫对普通游人并不开放,因此只能从外围观看,但这已经足够了,因为若是站在石桥或者别尔谢涅夫临河街上看克里姆林宫,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里蕴含着一切事物的实质,这里是友谊、团结和爱的源泉。一九五二年,母亲带我参加了五一游行后,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走过列宁墓的时候,她用手把我举起来,好让我能看到斯大林。我朝斯大林挥舞我的小旗子,他微笑地看着我。不对,他并不只是看着我,他看着所有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他看着我们,我们看着他,这恰是团结的要义。因为只有看着他,我才能看见我自己,以及我们所有团结、相爱的人。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庄重感,沉浸在这种情感中,“总统”“首相”“总理”,甚至“总书记”等概念都显得不合时宜且无法想象。斯大林是我们的首领,俄语中“首领”这个词,就像德语词“领袖”一样,满足了我童年时代对古老神话的所有幻想。这个词不仅关乎尚且健在的人,还关乎我那时念念不忘的所有人物: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传说中的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和古莉娅·卡拉寥娃。当我向斯大林挥舞手中的小旗子时,我明显感觉到,这些人物就在那里,与我同在。我执着地认为,莫斯科是五海之港。


然而,现实慢慢向我展示了它的另一面。当然,从大人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中,我开始慢慢了解到当局的一些事情。从一九五五年起,我的同龄人之间也出现了类似话题,有时这种话题还带有某种幻想色彩。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姓卡明斯基的奇怪男孩,不知是本来就疯疯癫癫还是故意恶作剧,他曾言之凿凿地说,如果夜里去红场,当那里“空无一人”的时候,双脚可以感觉到地上的条石颤动。他说,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地下有一个巨大的齿轮在转动,这个齿轮“控制着我们所有人”。升五年级的时候,卡明斯基留级了,从此我便与他失去了联系,但他的话深深刻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其实这种说法包含某种建设性的思想。事实上,当我们白天随着游行队伍穿过红场,向斯大林挥舞小旗子时,很难弄明白苏联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作为个体的“我”,还是由成千上万个群体构成的“我们”,抑或向我们微笑致意的斯大林,所有这一切都汇聚成对庄严的统一国家的狂热。这种时候已经无法辨别“我”在哪里,国家在哪里,更进一步说,什么是“我”,什么是国家,都已经分不清了。但是如果夜晚去红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一个人去的时候,因为我和国家是直接面对面的,也就是说,我将有更多机会认清二者。我仿佛在偷窥某个不该知道的秘密。我发现,高空中一些血红的星星发出不祥的光;我看到自己面前有一座金字塔,里面是那个未被埋葬的逝者,以及一群不知是死是活的、纹丝不动的哨兵;最后,我开始感觉到那微弱的、依稀可辨的嘈杂声。或许这只是我的错觉?不会的,我确实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勉强听得清楚的声响。这是什么声音?是白天游行人群发出的喧嚣,还是科雷马劳改营里地狱般的嘈杂,抑或克里姆林宫地下那个“控制我们”的巨轮发出的隆隆声?我不知道,但我有种感觉,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甚至或许是致命的灾难。这种声音完全毁灭了我的个性,完全毁灭了作为个体的我。
这种感觉使我那遥远而纯洁的童年回忆蒙上一层灾难性的色彩。在兹韦尼哥罗德,我和小伙伴们把抓来的甲虫装进火柴盒里,耳朵凑上去,仔细倾听甲虫用小爪子挠盒子发出的哗哗声。我们还互相交换火柴盒,好比比看谁抓住的甲虫弄出的响声最大。如今回想起来,国家就好像一个庞然大物,把我们塞进不同的火柴盒,听我们如何在里面竭尽全力想要逃离却无济于事。我还记得,在兹韦尼哥罗德电影院附近的街心花园里有一座领袖雕像,坐落在茂密的丁香树丛深处,不太显眼,所以让人感觉好像是有人故意把它藏在那里的。雕像不大,形状很像父亲的打字机,白天看起来甚至有点滑稽,但一到晚上,我就开始发挥想象力,觉得一定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控制着这台“打字机”,用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发出指令,所以第二天我们的生活中才会遭遇种种不可挽回的事件。我们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因为白天一到,这台“打字机”就会变回最普通的领袖雕像,那座位于丁香树丛深处的不起眼的雕像。


到底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消灭了作为个体的“我”的事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独自一人走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开始对此产生强烈的怀疑。从前克里姆林宫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已经荡然无存。或许,这个事物的确存在,只是它已经无法让我遭受打击,也无法让我精神振奋了。从前的克里姆林宫去哪里了?那个令仇视俄罗斯的著名侯爵屈斯蒂纳【屈斯蒂纳(1790—1857),法国贵族,君主主义者,作家,旅行家。曾于1839年访问俄国之后写下了著名的随笔集《1839年的俄国》,在书中,他对俄国人的评价毫不留情,以致此书在沙皇时代成为禁书】异常害怕的克里姆林宫(不过,他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真的仇视俄罗斯呢?)在哪里?这个瘦削、敏锐的法国人曾这样写道:“克里姆林宫是一切城堡中的勃朗峰。假如这个被称为俄罗斯帝国的巨人有一颗心脏,我要说,这颗心脏正是克里姆林宫。在一座座宫殿、博物馆、城堡、教堂、监狱之间,蜿蜒曲折的小路让我害怕。隐秘的声响从地下传来,这种地方并不适合我们这样的生物……徐行于克里姆林宫,你会慢慢开始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塔楼:有圆的,也有四角甚至多角的;有矮的,也有其尖顶高耸如云的,有望塔、侦察塔、警戒塔,有大小、风格和颜色各异的钟楼、宫殿、教堂,有雉堞的城墙、炮眼、射孔、壁垒、加固路堤,有别出心裁、难以理解的一些地方,还有位于大教堂旁边的那些凉亭……”所有这些都去哪儿了?哎,令屈斯蒂纳恐惧的克里姆林宫已经消失。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十九世纪尼古拉对克里姆林宫的修葺中销声匿迹。但即使二十世纪初的克里姆林宫已经与屈斯蒂纳所看到的相去甚远,它还是充满魅力,令汉姆生、穆夏这样的知名外国游客叹服。如今克里姆林宫已如朽木枯株,如一具蜡像,一个塞满木屑的稻草人。对屈斯蒂纳侯爵来说,克里姆林宫是俄罗斯帝国这个巨人的心脏,而他唯一的疑惑在于,这颗心脏是否属于俄罗斯,他本人其实并不相信这个巨人的心脏的确存在。同样,如果我们说如今克里姆林宫还是俄罗斯的心脏,那也只不过是一颗装满酒精的心脏。无论如何,每当我有机会以各种理由行走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内,心中总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更确切地说,克里姆林宫的外观已经被强行简化而变得不完整了。假如人的视野会对自己产生影响,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长期处在如此外观的克里姆林宫之内的人的意识和状态,也就是说,那些按照工作性质应当在克里姆林宫上班的人,我指的是我们政府里的工作人员们。这个畸形的空间、被强行简化了外观的克里姆林宫是否有可能完全不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乃至政府决策的性质和质量呢?即便这些决策或许正确有效,那也肯定会是被削弱和有所缺憾的,不可能具有内在美。我所说的美是什么?政府决策的美——这是一个已经完全被遗忘的、不合时宜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可能与当代世界并存,就像屈斯蒂纳侯爵所看到的那座克里姆林宫也不可能与当代世界并存一样。



接下来事情变得更糟糕了:莫斯科开了家麦当劳,这几乎成为整个民族的大事件。报纸电视争相报道,大街小巷飞短流长。要想在麦当劳吃一顿,通常需要排五小时的队。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替人排队,一个位置能卖四五个汉堡包的好价钱。这种事就发生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诗人的雕塑前。连续几个月,广场被那些到这个美国餐厅排队用餐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普希金全程目睹。但是情况有些微妙,因为普希金雕像的所在地,以前曾经有座斯特拉斯修道院,而普希金雕像过去所在的位置,现在则是排队数小时等着吃麦当劳的人们。历史文献学和文化学都可以由此得出互相印证的结论,但现在我不想谈这些,我只想表达我每次看到普希金广场上冗长队伍时的感受。
当我看到这条长长的队伍时,除了无限的民族耻辱感,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在冷战中已经失败了。冷战的失败与真正的“热”战的失败不是一回事。在真正的战争中战败,要么会给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要么会被迫做出正确决定,走上一条可以使经济繁荣的道路,就像德国和日本一样。但在冷战中失败甚至算不上什么失败,只不过是“冷”失败,无需做出任何决定。更进一步说,这种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的是个人的胜利,因为原来无法做的事情现在却可以做了。以前人们不能去麦当劳吃饭,也不能将自己的画作拿到苏富比拍卖行去卖,但现在可以了。只是别忘了,无论麦当劳还是苏富比拍卖行,都是美国式西方文化的物质载体,它们更强大、更有吸引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淘汰掉俄罗斯文化的物质载体,进而取代俄罗斯文化。所以冷战其实是文化之战,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文化彻底失败了。我们自称第三罗马,到头来却成为第二迦太基。就像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倒下一样,我们的墙也应该被推倒。到底我们是纯粹被西方打败的,还是被我们自己——俄罗斯最凶猛残酷的敌人打败的?这个问题着实不简单。总之,我们不再想成为第三罗马,于是亲手拆毁了位于莫斯科正中心的斯特拉斯修道院和里面的钟楼,建造了普希金雕像取而代之,好建立起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基础。后来,在这座雕塑对面,我们又亲手建造了麦当劳,似乎就是为了让那些在普希金面前拼命想挤进麦当劳的人们证明,俄罗斯文学大势已去,俄罗斯的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


不过我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这种想法和心情中。回首往事,我突然明白,莫斯科,我的祖祖辈辈都赖以生存的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命运和归宿,是我所面对的现实对我的呼召。莫斯科那些街道的古老名称,像涅格林大街、彼得洛夫卡大街、特维尔大街、尼基塔大街、鲍瓦尔大街、阿尔巴特大街、普列奇斯坚卡大街、奥斯托仁卡大街,都是儿歌里常常出现的词汇。当你漫步在这些街道上时,就像在读这些词汇一样,你会听到现实对你的召唤,进而达到与现实的和解。或许还会发生更奇妙的事:当我一边沿着莫斯科的古老街道徐行,一边用小竹棍占卜,可能会出现某个未知的卦象。身为生活在莫斯科的莫斯科人,而不是世居圣彼得堡的彼得堡人,我深感幸运。圣彼得堡虽然美丽,但我不喜欢它那皇家所特有的富丽堂皇,以及象征世俗权力的亚历山大圆柱、有古战船船头形装饰的圆柱和旧俄海军部大厦的尖塔。我更爱莫斯科,尽管实质上莫斯科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充其量不过是一座大村庄,这座大村庄里有修道院、庄园、花园和菜园,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当然了,还有位于中心小山丘上的克里姆林宫。如今旧城所遗留下来的部分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莫斯科才给我带来更深的触动。因为它不仅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莫斯科,还是我的父母曾经看到的,后来又讲给我听的那座城市。他们说,他们曾亲眼目睹中国城的塔楼和城墙被推倒,从红场就可以看到当时被拆除的沃兹涅先斯克修道院和丘托娃修道院,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就要被摧毁前,妈妈和马尔克·科列文斯基还从教堂的长廊里走过,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组成我现在所看到、所生活的莫斯科的一部分。总的来说,当代的莫斯科保留了不少古代特征,比如建筑杂乱无章、居民楼胡建乱造,大片土地被闲置——我指的不是洋葱头式的建筑遗产,它们大概是最好最美的事物了。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正如俗语所说“歌词难改”,儿歌也不好改,而莫斯科就是我的儿歌,它是我的城市,是我的现实。
莫斯科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像是一篇巨大文本中的一行,或许只不过是小学生练习本中字迹潦草的那一行。然而,我已经不再需要去写文章或者写诗,因为,当我漫步在莫斯科街头时,我本身已经成为这篇文章或这首诗的一部分,即便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词。我甚至不奢求成为其中深奥的甚至只是正确的单词,只要是其中一个错别字,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因为即使是一个错别字,也是那被称为“莫斯科”的巨大文本中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在与西尼亚夫斯基的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说法。西尼亚夫斯基回忆说:“他好像把自己的全部诗歌都抛在了过去,他说,用脚而非用手书写的时代已经来临。”当然,我可以从消极的方面解读帕斯捷尔纳克这句话:“要明白,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人生的见闻和经历都已经结束,而不是还未开始。”当然,它的意思与我前面提到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即书写现实的时代已经结束,体验现实的时代已经来临。因为书写现实是创作文章的方式,需要我们用手、用钢笔、用电脑去完成,而体验现实只能用脚完成,只有漫步在莫斯科的街头巷尾和街心花园,才能体验现实。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莫斯科只代表我自己的理解和立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市、草原、森林、冻原、沙漠或者山川。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脚去完成对现实的书写。在命运召唤之地漫步的人是幸福的。我命定要在莫斯科漫步,于是,我漫步在莫斯科的土地上。

弗拉基米尔·马尔蒂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артынов,1946—),俄罗斯作家、作曲家。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次年毕业于该学院钢琴系。曾为六十多部电影和电视剧进行过音乐制作。2002年获得俄罗斯联邦政府奖。他的文学作品《阿丽萨的时间》《书籍之书》《自身考古学》等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