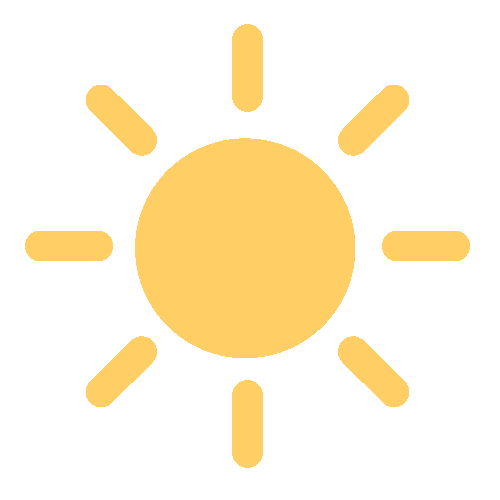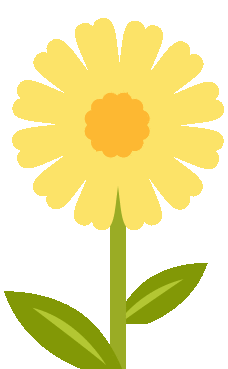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季•鲁宾娜【以色列】:好几夜辗转反侧,心里有如虫子在啃,不断啃噬……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坐进他的小巴。继续等乘客,没人来。十分钟,二十分钟。我跳下车,叫道:算了,我打出租,那边有辆空车。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喊道:“你要抛弃我?!你要抛弃我这个耶路撒冷人!!你想让那个臭特拉维夫人赚钱!”他把手指指向天空,激动地说道:“听我说!好几架飞机就在头顶上!很快人就都来了。全是人。都是我们的乘客。你听明白了吗?坐下等等!”
季娜·鲁宾娜作 刘早译
……我常常思考:为什么画室展台上赤身裸体的人会显得很可靠,似乎一旦有事——比方说保险盒跳闸时,就会一丝不挂地跳起来冲向走廊里的配电箱——你就不再是个模特,而只是个裸体女人……总之,赤身裸体之人——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而我在里面当人体女模特挣外快的那间画室,保险盒总是跳闸。艺术家——是个简单又光荣的群体,但他们的双手只会摸画笔。一有点什么事,就有人喊:拉雅,你去。更何况在前一段人生里,我还是个电气工程师。
如果灯灭了——我会从展台上消失,出现在走廊里,摸索着找到配电箱,眨眼间——电来了。这时候,阿维·科恩,画室负责人,一个待人亲切的秃头,就会伸出手来帮我爬上展台,说道:“那么,我们继续吧……”
一小时十五卢布——不对,是十五谢克尔【谢克尔,1980年以色列启用的货币单位。1985年被新谢克尔以1:1000的比率取代】——这可不是轻易就能遇到的。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你算算。在军士入伍之前,我和他就靠这个糊口——靠我的光屁股……当然,以色列女人拿得更多,每小时二十五。但阿维·科恩向我承诺,从逾越节开始涨一卢布——不对,是一谢克尔……
我也不是不懂——这些艺术家,我们的也好,他们的也好,都是穷光蛋。尤其是冬天,没有游客来,意味着画没人买。自然,他们也得找地方挣外快。
来我们这里画画的有位萨什卡·科尼亚金,来自沃罗涅日。他通过前妻来到以色列,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儿。他在米歇雷姆区的一家私人小厂磨面粉,做无酵饼用的面粉,每小时七谢克尔。最近手受了伤,还正好是右手——据他说,血流如注……旷了三次课。但他跟没事人一样,乐呵呵的,还笑着说:现在可以证明无酵饼里面没有添加基督教婴儿的血……
俄罗斯人在这里顽强地生活着,就像犹太人在俄罗斯一样。
我们这儿还有位法布里齐乌斯·冯·布劳威尔,非常讨人喜欢。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一头金发,是荷兰犹太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荷兰人,直到六年前他妈妈弥留之际,才得知自己是犹太人。那时她庄重地向儿子宣布,他是马兰家族的后裔,五百年前受基督教洗礼,但私底下仍旧坚守犹太生活方式,尽管宗教裁判所不会纵容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妈妈亮明了他的出身。又因为他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就像我和军士这样——妈妈让他发誓,她死后依照七日丧期【七日丧期,犹太教中,人死后其亲人需照犹太教的传统举丧七天】守灵,之后立刻前往以色列。一个人顷刻间遭受如此冲击!想想看,一个单纯的荷兰人要面对如此蛮荒的犹太生活环境……
他守完七日丧期,来到这里,还行——就住了下来。他挺喜欢这儿。唯独学不会希伯来语,而是说英语。一个高高大大的荷兰人,嘴里说着“我父亲是犹太人……”。
他在哭墙那边当保安。




再就是阿维·科恩,当地知名的前卫艺术家——总是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毛衣。前些日子,一位税务局的官员突然出现在他家。假装成买家,要买他们的东西……看看这看看那……等到谈妥价格时,那人掏出的却不是支票簿,而是工作证……我们的阿维毫不慌乱。他殷勤地搂住那个家伙的肩膀,把他带到冰箱前。空无一物的隔架,一个小盘子,里面搁着一块皱巴巴的奶酪。税务局的官员站在那儿,瞄了瞄缩水的奶酪,默不做声地离开了……正如阿维·科恩在这种情况下会说的那样:“那么,我们继续吧!”至于我——看上去总是一副衣食无忧的样子,当下也是这副模样,即便还要上展台工作。我的生活态度是——任何时候都不向任何人借钱。结果有一天在超市,一个男人——显然是摩洛哥人——帮我补齐了三十戈比。不对,是三十阿高洛【阿高洛,以色列辅币(硬币)单位名称】。百分之百的摩洛哥人,毫无疑问。
我挑了满满一篮子东西——有大瓶的洗发水,有我看中的蓝色斑点茶杯,有军士喜欢的番茄酱(正好他周六从部队回来了),还有这样那样的东西……到收银台才发现,我把支票簿落在家里了。现金又不够。收银台的女服务员很客气,说:没办法,非急需的东西就先拿出来吧。我心想,那好吧,茶杯——见鬼去,低热量小面包——见鬼去,洗发水和番茄酱——不要了。她说:嗯,你还差三十阿高洛。
此时那个男人,一看就知道是摩洛哥人的那位,正站在我身后,他从钱包里掏出零钱,说道:“这位女士差多少?”
我简直火冒三丈。“亲爱的,你干吗?”我说,“谢谢好意,不用了,我自己有钱。”他回答道:“别扯了,嗳哟,嘴真硬!……”便随手把零钱丢在收银台上……典型的、百分百的摩洛哥人,就像本地俄语报纸描绘的那样:脖子挂金项链,手腕挂金手链……
我当时心想:是什么驱使他这样做呢?想羞辱我?还是说他只是赶时间,而我占住了收银台。也许他就是个好人,倒是我喝牛奶烫了嘴,再喝凉水也要吹一吹……哦不,在那件事上我基本上是无所谓的……刺激我的东西,说起来甚至有些好笑——是一纸不会离开居住地的保证书!好像我现在打算潜逃似的。什么好东西我没见过!这是其一。其二,我和军士有钱,偶尔还大手大脚的……真是受刺激!好几夜辗转反侧,心里有如虫子在啃,不断啃噬……这算什么事啊,我心想,难道是迷失自我了?!转念一想——需要客观论证:警察局里根据什么办事?根据事实。有哪些事实?我给那个老太婆做过扫除没有?做过。她在报案书上申明丢了钻石,丢了没有?鬼知道。大概是丢了。
在审讯时,我对警察说,你瞧瞧我,我这副不愁吃穿的样子,拿她的钻石做什么?
那人十分和善地说,听着,你把东西交出来,然后爱去哪儿去哪儿。
我说,我受过高等教育,是电气工程师。你知道在厂里,我手底下有多少像你这样的男人吗?
他又说,我没有时间研究你的履历。把你从太太那里拿的东西交出来,你就自由了。如果抵赖,我们就让你过测谎仪。我哈哈大笑,说,把测谎仪拖过来吧,还想吓唬俄罗斯犹太人,只不过也得让那位知书达理的老太太过一遍。他在案件卷宗上记录道:对方同意用“真相检测机”检测。
能干小伙儿……
结果是,我那位老太太拒绝接受测谎仪检测。因为有高血压。这时我回想起我和她之间真诚的对话。经常是这样:我卖力地用抹布擦拭沙发和柜子底下,她跟在我身后悲痛欲绝,说我们,俄罗斯犹太人,背离了自己民族的伟大传统。她在我背后盯着,指指点点——哪里需要再擦一遍——然后接着劝说我回归传统。


当然,各种传统让人非常糟心。传统这事总让我与军士非常尴尬。刚到这边时,军士的邻居送来一条祈祷披巾。他们早上来敲门,进屋后庄重地将披巾搭在他肩膀上。军士深受感动。妈妈你看,他说,他们送了一条好漂亮的毛巾。要说这是传统——也很有道理。审讯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事发之前她一直试图在我面前炫耀那些钻石。你看啊,她说,我这些东西可值钱了!……但那天我着急赶去画室,已经快迟到了,根本顾不上什么钻石,何况还是别人的。
当我回忆起这情形时……简单来说,我恍然大悟。我只想当面问问她——我们民族的伟大传统该怎么说?只想问问。
于是我去找她……她在海法有栋小别墅。我按响门铃,就像平日里一样。她的孙子走出门廊,十六岁的小伙子,很帅气,一边耳朵戴着耳环。滚开,他喊道,俄罗斯小偷!对,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对这些,我并不在意,对口舌之快不敏感……我基本上不算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还松开了拴狗的绳子——蠢到家了:我不怕狗,谢天谢地不是本地狗,况且这狗还认得我。它跑到大门口,快活地直摇尾巴。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捡好了石头,够大够沉的一块……然后改变了主意。对,我是可以砸他们家的窗户,可之后自己还得赔玻璃。我便离开了……最主要的是——我对军士只字未提。我从来不拿自己的烦恼去打扰他。我的军士自幼起就是个好沉思的男孩。因为他好沉思,我一直都没有再嫁,免得让他又多出个借口去想东想西。事到如今,出嫁对我来说更是徒劳无益。见得太多了。同样的一杯水,早晚会端给你,但问题是要付出多大代价,以及你能不能活到这杯水端来的那天……
我认为抱怨是一种罪孽——军士从部队带回家的只有文书。前不久他竟然被奖励了一台收音机。我很感兴趣:“有没有给你一些物质上的奖励?”
他说:“给了。”
“什么东西?”
“在将军身边就坐进餐。”
“你没吧嗒嘴?”我问道。
“没,”他说,“将军吧嗒嘴了……”
就在最近,他接到命令去参加一些军官课程的测试。是他在信里说的。部队心理医师给他打来电话。知道吗,对方说,根据此次测试的结果,你的处事态度不仅不能参加军官课程,甚至不能继续留在部队……去吧,两个月后你重新参加测试。军士对他说:你认为,两个月的时间能让我有机会改变想法?……对方哈哈大笑道:提拔军官我不会选你,但当朋友会选你。我的军士是个下士。应该很快会晋升到上士。然而他不感兴趣,说是不想。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过是从肩章上撕下旧杠杠,贴上新杠杠……
……就这样,我不得离开居住地——我也不需要离开。只是每天早晨跑到邮筒看看,免得错过警方的通知书。
就在这期间,我们的画室遇到了一件事。我们的法布里齐乌斯·冯·布劳威尔与阿姆斯特丹一家画廊达成协议,为我们这帮人办一场画展。现在需要把画运过去,但没人手。萨什卡·科尼亚金在为做无酵饼磨面粉——逾越节即将到来,这是最忙碌的时节。而法布里齐乌斯在哭墙执勤,为女性发放头巾,也抽不开身。


于是他们找到我,说:你去不去,拉雅,把画运过去。我们凑齐路费,派你过去。
真是意料不到——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无所谓,我哪儿都不想去,然而只要闪现一丝微光,我便有了知觉——想去,死也要去阿姆斯特丹。自幼想去的就是阿姆斯特丹。
我对他们说:男子汉们,不管什么情况,我都非常愿意把肩膀借给你们依靠,但目前我因为一桩珠宝失窃案被警方登记在案。总之,把老太婆的事跟他们说了……
我的艺术家们惊呆了,斥责我,批评我——为什么闷不出声。我回答说,我的生活态度是——任何时候不找任何人借钱……这件事甚至让阿维·科恩眉头大皱,就像吃了酸涩之物。他用希伯来语说,什么离境不离境,都是胡扯!他带着我去了警察局,与负责人谈了很久,我不清楚——要么是签了担保书,要么还有其他,总之允许我暂时离境三日。我和阿维离开警察局,在雅法街上买了烤肉卷饼。阳光明媚,人来人往,如此美好。他对我说,没事的,拉雅,你看——在以色列就像在家里,最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在以色列总能找到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为你慷慨解囊……你知道,也许那老太太有妄想症?也许是她的孙子翻腾了她的珠宝盒,而她怪罪在你头上?要我说,去他的老太太和孙子,去他的珠宝盒和妄想症……
阿维吃完烤肉卷饼,说:“那么,让我们继续吧……”
……至于阿姆斯特丹——我是不是可以不说呢?那边没有什么好说的呢,唉……我在城里逛了三天,始终在思索法布里齐乌斯·冯·布劳威尔的事——本该如此,是命运把人引领到某个地方。我想象此刻,我们这位荷兰飞人正在哭墙边为女性分发头巾。美中不足的是——脑子里的英语消失得无影无踪。想要说两三个像样的句子,都是白费力气……这时候蹦出来的全是希伯来语。主要是,你会下意识地冒出一股针对对方的愤恨:你知道吗,他像傻子似的杵在那里,空有一副耳朵却听不懂,对古希伯来语更是一窍不通。
我干活抵了差旅费,还把大家的钱带了回来——画廊老板一口气买下三幅画,还有五幅放在那边寄卖。剩下四幅画需要带回去。我预订了去机场的出租车。来接的是个荷兰人——香水味扑鼻,绅士风度。我说,不好意思,我有几幅大尺寸的画,后备箱估计放不下。他说,噢,小姐别担心,都是小事!他拿起画,放进后备箱,箱盖关不上,他不知从何处掏出绳钩,钩住,绑紧,上车,出发。又快又准时,混蛋老外……




凌晨两点,我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拎着大包小包——行李,还有画。我冲到小巴跟前,问:“到耶路撒冷多少钱?”
一个大块头站在那儿,脖子上挂条金项链,嘴里嚼着口香糖,瞄着远处。
“一百谢克尔。”
“什么?”我问道,“小巴,一百谢克尔?!有这些钱我直接打出租回家!”
他停止咀嚼,板起脸,口香糖从口中飞射而出。
“什么?!”他叫道,“出租车到耶路撒冷,一百谢克尔?!来,你指给我看看,这点钱,谁会载你!如果有人说他载你,这一百谢克尔我来出!上车坐下,别糊弄人了!”
“二十。”我说。
“听着,你这俄罗斯疯女人!八十——上车!”
“二十。”我说道。
“你在戏弄我?以为这是俄罗斯呢?六十——外加一声谢谢!”
我坐进他的小巴。继续等乘客,没人来。十分钟,二十分钟。我跳下车,叫道:算了,我打出租,那边有辆空车。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喊道:“你要抛弃我?!你要抛弃我这个耶路撒冷人!!你想让那个臭特拉维夫人赚钱!”他把手指指向天空,激动地说道:“听我说!好几架飞机就在头顶上!很快人就都来了。全是人。都是我们的乘客。你听明白了吗?坐下等等!”
总之,我累瘫了,都没发觉自己是如何睡过去的。睁开双眼,已是破晓,我们在蜿蜒的山路上朝着耶路撒冷驶去。左侧,拉莫特社区层层发散开去,轻轻摇晃,就像从机翼上往下看。
我看看司机——天啊,我怎么没认出是他!对,当然是他——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就像俄语报纸上描绘的那样。到了我家门口,我从钱包里掏出六十谢克尔和一些零钱——三枚十阿高洛硬币——放进他手里。他很诧异,这多出来的是什么?!我说,你在超市为我垫付了三十阿高洛,记得吗?我是个不愁吃不愁穿的人,不爱欠别人钱。这是我的生活态度。
啊呀,他说,是你啊?!我没认出你来。
他帮我把画搬下车,扛上三楼,站在那里,看我掏钥匙开门。他说,你看,事已至此,你不请我喝口咖啡吗?
不了,我说,不想在你们本地口头文学中新添一个关于俄罗斯妓女的故事。
他只好下楼去,一步一挪……在下一层转角处停下,看着我把画搬进屋。
是的……站在转角处仰望。


我已经不记得上次有人这样看我是什么时候。我不过才三十九岁,身材似乎还没走样,但总感觉已经三百八十岁了——要知道我上学时还是使用吸墨纸的时代。不久前,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在街上拦住我。她说,我们正在按照年龄组对居民进行快速问卷调查。您属于哪个组别——五十至六十岁,还是六十至七十岁?
我说,属于一百至一百二十岁,我上学时还是吸墨纸时代。然而我却不由自主地盯着她丝绸般光滑的脸蛋……好吧,她甚至无法感受这个水平的幽默,说声“对不起”,就走开了。
所以说不要盯着我看——没用。我基本上不算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把画搬进屋,砰的一声关上门。
……晚上,军士从部队里回来,我俩坐下来喝茶,吃荷兰产的茶点。他一直问——快,讲讲,讲一讲阿姆斯特丹!
“怎么说呢,”我说,“各种房子……就像模型师喝醉后拿剪刀剪的,再粘起来……”
“你呢,”他问,“想在那边定居吗?”
我没说话,心想:明天得跑一趟警察局,告知我已经回国,否则就会坐牢,拜那该死的老太婆所赐……
军士像个孩子,追问道——那你想在哪儿定居?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已经发财了——发了大财!但我还有军士……他感兴趣……那么,让我们继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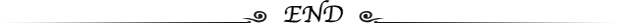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