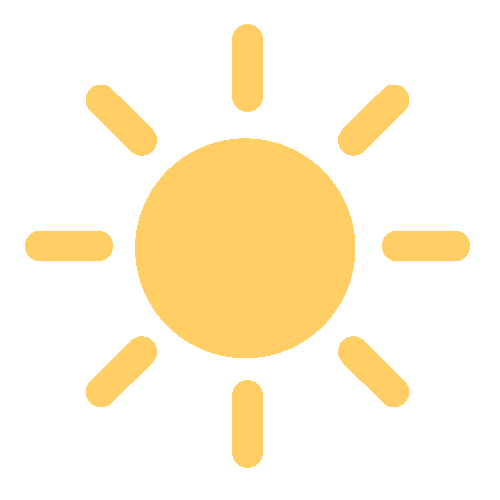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塔•托尔斯泰娅【俄罗斯】:大灰狼和小红帽从两侧走来,彼此相向而行,却没有机会相遇……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美国东海岸的春天疯狂至极。那些树木昨天还支棱着枯死的枝条,一夜之间就都复活了。小樱桃树伫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仿佛粉红色的喷泉,连翘丛中缀满了黄色的花朵,没有一片绿色的小叶子——它们稍晚一些才会长出来。梨树——我的天哪,美得令我难以承受!接着,木兰花绽放了,可是,这也太过分了吧,普通人的心脏怎么配得上如此的奢华。配得上的花朵应该是皱巴巴的,被撕碎了一般,乱蓬蓬的,比方说,像芍药这种。
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作 许力译
“您明白了吧,难道不是吗,从这一刻起,所有与这份财产相关的权利、义务和问题就都属于您了,”律师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道,“这些都已经不再是大卫和芭芭拉的责任了,而是您的。”
大卫和芭芭拉苦着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我手里握着一支黑色自来水笔,准备最后在购房合同上签字。大卫和芭芭拉离婚了,卖掉了他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房子,而我买了下来。我们坐在律师事务所里。窗外,滂沱的美国暴雨肆虐——天气大概就是这样,就像一八二四年的彼得堡,雨水从天上砸下来,疯狂、凶猛。在远处,十米开外的地方,除了浑浊的雨幕,什么都看不见,而那些能看见的东西却令人恐惧:地面上水流汹涌,水位已经升到了那辆停放在窗外的汽车轮子的中间位置,并且还在以秒针转动般的速度上涨。
“是啊,可能要被淹了,”律师心不在焉地说,随后盯着我的眼睛,“在新泽西,这样的大暴雨过后,一定会有几千辆汽车出售,二手车。我是不建议买的,都是破烂货。不过呢,这事终归要由您来决定。”
“那么房子呢?”我问,“房子有可能被淹吗?”
“房子在一座山丘上,”大卫坐立不安起来,“有几户邻居家被淹过,而我们还……”
“喂,您,彼先生!”律师严肃地提醒大卫。


律师禁止大卫和我说话,也不允许我和大卫说话。看来,大卫一定会说漏嘴,比方说,他会讲一讲自己的房子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缺点,而我只要惊叫一声,房价就会下跌一点,大卫也就要遭受损失了。或者就像现在这样——大卫用空头支票忽悠我,说那座山丘似乎能保证财产完好无损,而我也一定会信以为真;然后呢,我,比方说,走进那所小房子,却在里面的地下室听到了水声。这就意味着大卫骗了我,而且还是当着两位律师的面骗我的,这种情况下我一定得去法院告他,跟他打官司——所以,千万别肆意妄为。大卫应当按规矩行事,表现出漠然、回避、中立的态度,客客气气地在一边待着。
大卫就是这种人!他为有人想买他的房子而由衷地喜悦。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来说,那所房子糟糕极了:一座狭长、阴暗的烂尾棚屋,屋顶还漏水;棚屋隐藏在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偏僻荒凉的角落里:房子的地址说起来很体面——在普林斯顿,可实际上鬼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一片僻静的森林,一条损毁的道路,通到一所被废弃的、摇摇欲坠的房屋跟前:在那里,密林深处,道路尽头,有一所充其量只能算作小木屋的房子——我暗地里称之为“绝路”。小木屋被钉死了,玻璃也敲掉了,看上去灰扑扑的,破烂不堪。要是没有那二十根虽然纤细却很结实的木头支撑,整座房子立马就会倒塌。那些木头像长矛一样穿透了小木屋,刺向天空,它们发了芽,均匀、笔直地挺立在那儿,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大卫是个头脑简单的老实人,确实太老实、太简单了——他不愿意骗人,甚至就连不经意间愚弄别人也不愿意。他瞪圆了眼睛,指给我看他家小厨房里的地板已经腐烂到了何种程度:油毡早就磨出了窟窿,三十年来一直没换过!不过木地板还在。他建议我四肢着地、趴下来和他一起看看那个柜子下面——那里的木地板不完整了。他拉了拉窗框,上面的插销粘满了油漆,已经黏住了:真是太糟糕了!只能换掉!他仔细告诉我屋顶上漏水的位置,说应该把水桶放到下面接着。他还讲了他在建凉台这件事上所费的周折。大卫家没有凉台,或者说,有凉台,但仅仅存在于想象中。而实际上当然是没有凉台的。您自己看吧。他用大腿顶了顶门,门没有马上打开,而是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晃晃悠悠地开了。这扇用胶合板做的门立在这个简陋住所侧面的一堵墙上,黑乎乎的——而后面……后面,有一个神奇的房间。
您跨出一步——从地面上的这个幽暗、狭窄而又低矮的小盒子里钻出去,就来到一个半悬的露台上,露台比地面略微高出一点。左右两侧的墙壁——从地板到高高的天花板——全都是玻璃的,一直延伸到满眼绿色的花园,一只只红色的小鸟在花园里飞来飞去,绿植在轻轻地摇曳,盘绕在树上,绽放出花朵。
“我做了这些窗框。那个木匠特别棒,想找他干活,排队就得排几年,”大卫说道,语气中带着歉意,“我花了很多很多钱,大概两千,两千五。但要建凉台还是不够用。”


他开始拽那扇像蜻蜓翅膀一样的玻璃推拉门。墙移到了一旁。门槛外面有一个不大的、绿色的坎,一棵松树伫立在不远处。在阳光的照射下,松树下面有几株铃兰破土而出,颔首而立,把去年飘落在地上的松叶挤到了一边。我的心为之一动。
“没有凉台,”大卫遗憾地又说了一遍,“这里应该有个凉台的。”
大卫真是有病!他着手实现自己对天堂的梦想,却没有考虑到资金问题。这个荒唐而奇妙的建筑、这个悬在空中的透明盒子,原本有望成为通向浮华世界的出口,最终却搁浅在这个沉闷的处所。
“不过,要知道,还是可以把凉台建起来的,”他说,“你得写一份申请报给我们的市政局工程处基建科,他们会出具许可证。”
“那么,您为什么一定要卖房子呢?”我问。
“我想买一个牧场,策马奔驰。”大卫垂下眼皮。我们身后,芭芭拉在低声啜泣,她一直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们回到阴暗的房间里时,她已经完全控制住了情绪。
“我买了,”我说,“房子很称我的心意。”
这不,现在我在美国人的这张小纸片上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美国的一英亩土地就将转入我个人名下。这是一九九二年。更准确地说,这一年在惊涛骇浪中流逝,而我离开俄罗斯来到了这儿。那时候,在俄罗斯,一切都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一切都模糊不清,那里的所有东西都有了归属,但全部与你无关,在俄罗斯,你失去了脚下的土地——可是现在,在这里,在大洋彼岸,我要为自己买一块可靠的绿地,我将拥有它,就像我将拥有自己不曾拥有过的任何东西和任何人一样。假如有人胆敢擅自闯入我的房子,我就有权开枪。不过还是应当搞清楚小偷和强盗有哪些权利,因为宪法的效力也与他们相关。
这不,我和大卫就这样成交了,我现在就要买下他的房子,我们甚至为此坐下来一起喝了一杯。我们尽量不看芭芭拉,她时而去卧室痛哭,时而到花园里哭泣;大卫告诉我,这所房子最初的主人是一对没有子女的黑人夫妇。花园里已经一派秋意,花儿都凋谢了——这个花园是前男主人围起来的——所有这些花都是他的妻子亲手栽种的,而那位丈夫做了些什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在她这个园子里一切都长势惊人,等下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您就会看到的,您将会看到一切。



买房的事持续了整个夏天,其间学校确认接收我入职,银行认可我那还不见踪影的工资,并且已经算出了我的贷款利息,大卫的律师处理好了大卫与芭芭拉离婚和房款分配事宜以及一大堆需要走官方程序的麻烦事。夏天结束了,树叶失去了光泽,房子也变得黑、阴沉沉的。
我们谈妥了所有事项,而且甚至都快成为朋友了。芭芭拉已经不再伪装,弓着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满脸泪痕,眼睛红红的,双手像鞭子一样耷拉着,绝望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卫向我展示了存放在车库里的所有男人的宝贝:刨子、凿子、螺丝刀、钻孔器——男人们总是乐意向女人展示各种有趣的工具,而女人们也总是装模作样,仿佛这些工具确实棒得很。大卫甚至从墙上取下他祖父的雪橇——在二十年代,他的祖父曾经踩着这副雪橇从小山丘上滑下来,那时他才五岁,脸色绯红,面颊鼓鼓的;后来他上学了——在冰天雪地里要走一点五英里——天还没亮他的妈妈就得起床,烤两个土豆,让孩子揣到口袋里,在漫漫长路上暖手。大卫把这副雪橇送给了我,可我并不清楚如何才能让它们派上用场。他还把他现在已经不再需要的房屋改造平面图送给了我,那是一个画满图纸的本子,那些图纸证明他有着马尼洛夫【马尼洛夫,俄国作家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此人生性怠惰,崇尚空谈。后人常用“马尼洛夫”喻指耽于幻想之人】式的幻想:一栋废墟一样的房子;房屋左右两侧都插着翅膀;房顶上有个翘着的阁楼,上面有一扇半圆形窗户;房屋周围环绕着凉台,仿佛围着一圈皱边——简单说吧,大卫折磨、诱导、迷惑了我:他把自己的理想、美梦及飞船一起卖给了我,飞船上没有乘客,舵手不露形迹。
与此同时,我出高价租了一所目前我并不需要的住宅,用来存放自己的生活用品——我在美国生活三年期间积攒下来的物品。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添置了一些物件,虽说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全都是临时用的手提箱和餐具——但数量也很可观。我们甚至还有一张临时用的桌子和四把确确实实只是临时用的椅子。我问大卫,是否可以把这些家当统统运到房子里——运到我们的和他的房子里,比方说,塞进地下室?大卫没有反对。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咨询了自己的律师。律师担心得要命,跑来阻止我们这样做,他说,我的东西存放在我还没有完全买下的房子里,按照新泽西的法律,这就意味着有些潜在的权利受损——大卫受损,而我,既像是利用权力无偿占据了他的房子,又似乎是在奴役、强迫和掠夺业主。


因此把家当搬进那所房子是不可能的。我将惶恐地看着我最后的资金储备消耗殆尽——这也意味着今年我无法修补屋顶,也不能更换浴缸——换掉大卫的旧澡盆——我的钱不够。那点钱也买不起割草机——没有割草机,我已经知道,无论如何是不行的。那么更换新油毡呢——钱倒是够用,因为我可以自己来铺,而且一定不能买整块儿的,而是买便宜些的,正方形的,黑白相间的,就像画家们的格子画,比如沙皇彼得审问阿列克谢王子的那幅画【指的是19世纪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尼·尼·盖伊(1831—1894)所绘名画《彼得大帝审问阿列克谢王子》】上的那种。
我又看了看窗外。我看见雨水已经涌到我的汽车车门那里了,如果我现在不签字,一会儿想要离开这里的话,这么说吧,就没有交通工具可以乘坐了。于是我下定决心,签了字。房子变成我的了,而我也变成它的了。
这一过程的所有参与者都得到或是贡献了自己的金钱,体会到了复杂而矛盾的感觉,大家各自散去:大卫开着自己的小卡车消失在雨幕后面;芭芭拉也离开了,走进雨瀑中,谁都看不到她的泪水;而我们一家人直奔自己的房子,至于这所房子,不能保证它是否还矗立在那儿,或者他妈的已经被水冲走了。
这所房子年久失修,里面空荡荡、光秃秃的。地面已经发黑,被踩得污迹斑斑,窗户被屋子外面的云杉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我不喜欢云杉——这是给死人栽的树。浅蓝色——将军服颜色的云杉就更糟糕了,人们也把这种树种植在掩埋功成名就者的地方;一棵这样的小云杉在邻居家的地盘上显得甚是突兀,这就意味着我不得不看着它。
天花板下面的角落里,褐色蜘蛛网摇摇欲坠。动作麻利的美国蜘蛛一夜之间就能盘结出高质量的蛛网,可是,由于芭芭拉早就彻底放弃了打理房屋,蜘蛛网铺了一层又一层,假如有人莫名其妙地开始往上面放一些不太大的物品,这网子也能轻而易举地承受住这些东西的重量。我家的那几个男人沉着脸在这几间昏暗的小屋里走来走去,然后打开各自的电脑,盯着自己的显示器。
那个有魔力的房间同样令人感到凄凉和冰冷。几扇玻璃门随意敞开着,完全没有固定的方向。
只有我一个人喜欢这套房子。



美国东海岸的春天疯狂至极。那些树木昨天还支棱着枯死的枝条,一夜之间就都复活了。小樱桃树伫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仿佛粉红色的喷泉,连翘丛中缀满了黄色的花朵,没有一片绿色的小叶子——它们稍晚一些才会长出来。梨树——我的天哪,美得令我难以承受!接着,木兰花绽放了,可是,这也太过分了吧,普通人的心脏怎么配得上如此的奢华。配得上的花朵应该是皱巴巴的,被撕碎了一般,乱蓬蓬的,比方说,像芍药这种。
我这所小房子的首位女主人是个黑人,我一点也不了解她的情况,虽然她把鲜花种满了整个花园。在那条从街上通到房前的小路上,直到现在还能看见长长的一排鸢尾花。在一棵叫做梓树的树下,有一个小小的玫瑰花圃,这个花圃已经荒芜了,但是等我拔掉一簇巨大的美国莠草,砍光硕大的美国蒺藜(一种带刺的螺旋状植物,适合种植在需要提供特殊保护的区域周边)后,美丽的白玫瑰便完全显现出来,甚至还散发着芳香,尽管在美国花朵是没有香味的,蔬菜也没什么味道,总之,一般而言,气味在当地的文化中不受欢迎。
那位女主人在房前的小草中间种了一株日本槭树,树上长着巴掌形状的小红叶。这件事她干得漂亮!我经常想到她,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她总是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她从我和她的灰色房子里走出来,被太阳晒得眯起了双眼,她走向那片白玫瑰,走向那丛淡紫色的鸢尾花,鸢尾花的花朵看上去就像女人的生殖器。她伸出一只黝黑的手触碰红色的叶子,亲眼看见它有多么美丽。还有,她,据我所知,种过水仙,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水仙被人从这里挪到了南边,我也在南边和邻居家的交界处寻找过,在草丛里,在藤本植物中间,在无处落脚、只有双手勉强够得到的地方找到了这些花。当然,我把它们挖了出来,移回房子跟前,要知道,她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我似乎觉得她正从我旁边走过,还看了看我。
在这块土地上,我四处找寻她的足迹——可这块地太大了。我很快就知道她在南边种了什么,在东边种了什么,在松树下面藏了什么——就像那些铃兰,在紧靠台阶(我们那儿只有三级破台阶)的地方,她又想看到什么。当美国繁华的夏天到来之际,我最终对她的意图做出了判断:由灌木丛构筑的壁垒——沿着这块地的边缘栽种的灌木——长高了,完全遮挡住了我们,把我们与马路、汽车、废气、噪音、别人的目光统统隔离开来。我们看不到任何人,任何人也看不到我们,假如不知道我们的这所房子就在那儿、在这堵绿墙后面的话——这种事肯定是猜不到的。到了晚上,灌木丛的颜色与暮色融为一体,就连我自己从街上也看不到这所房子。
在小走廊里,一根绳子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这根绳子是做什么用的?我拉了一下,一个奇妙的折叠梯从天花板里伸出来。这是前往阁楼的通道。阁楼上摆着几个装着六十年代破烂衣裳的硬纸盒,衣裳已经绽了线,皱皱巴巴的——全是女式上衣和小围裙,这种衣服,即便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愿意穿,可是扔掉又有点可惜。实在太难看了。还有很多圣诞节、复活节贺卡,也都不漂亮,难看极了。圣诞节快乐,亲爱的比尔和诺拉。复活节快乐。也就是说,她叫诺拉。黑人的名字可真古怪。我一直觉得她叫萨莉。


她又从窗外悄然飘过,一只手抚摸着耷拉下来的枫树枝——这是一棵非常漂亮的树,树脂丰盈,带着日暮时分的颜色。比尔没有从这里走过,他不在花园里溜达。他一动不动,长到墙里去了,若隐若现,眼睛闪闪发亮。
不出所料,邻居们过来了,带着小馅饼作为礼物。我们也已经知道,当你乔迁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是否该做点什么答谢大伙儿。邻居们都有农场。
“您爱吃肉吗?”他们问。
“是的,当然。”我们贸然说道。
“那么来我们这儿吧,挑一只小羊羔。我们替您宰杀,您就省钱了。”邻居们继续说。
听了这话,我们这几个城里人有点愣住了。我们原本也没打算吃素,但是,想象一下,可以去农场,在那儿挑选一只可爱的、无辜的卷毛小羊羔,还有,还有……你们杀了它,这是我所希望的吗?……
我想,我们突然间这一愣神,一定被他们当成了外国人普遍的、特有的痴呆。
“那您来取蓝莓吧,我们免费送给您,只是您得自己采摘。我们的收成棒极了,已经没地方放了。”
我同意去取蓝莓。我是拎着篮子去的——绕道而行,在田野上走了很远。我们的房子之间距离不超过一百五十米,但这是从树林、灌木丛间穿行的距离。树丛把我家和邻居家全都隔开了,完全无法通行。大灰狼和小红帽从两侧走来,彼此相向而行,却没有机会相遇。
我用眼睛搜寻了一会儿蓝莓,却一无所获。女主人把我带到一个笼子跟前——莫斯科的动物园里就有这种笼子,关在里面的必定是一个支棱着羽毛、有着复杂的拉丁语名字的家伙。
“只能把蓝莓扣在网子下面,否则会被小鸟吃掉。”她抱怨道。


我踩到笼子上面。在我的头顶上,从灌木丛上方高高的树枝上耷拉下来的,其实不是蓝莓,而是野果——依我看,是越桔。你得踮起脚来、高举双手,这样才能够到这些野果。太阳格外刺眼。小鸟绝望地在网一样的树冠上飞来飞去,毫无办法。我没有坚持太久,摘了一小盒野果后就放弃了,然后独自离开了。女主人彻底看透了我这个弱智,脸上现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小心地掩饰着自己的想法。谢天谢地。我自由了!一个黑皮肤的小男孩站在遮阳棚下面的桌子旁边,他的小脸蛋上流露出惶恐不安的可怜神情。男主人用教训的口吻对小男孩说着什么。
“他是我们收养的,”女主人伸出一根手指朝他比划着,“打个招呼吧!”
小男孩慌忙欠了欠身,点了点头。
“没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过得很糟,可是现在,他在我们这儿多快活啊,”男主人说道,然后转身对着小男孩,结束了说教,“既有活儿干,又有饭吃。”
我从田里绕道回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觉得自己的心灵遭到了践踏。这些鸟儿也是一样……道路拐进了森林里,在这里,透过树木,可以看见一些空房子,犹如发芽的种子。
“诺拉,”我对着空无一人的森林里的一所空房子说,“诺拉,他原先过得不好,但是现在他在他们那儿很好!”
可是她望着远方,她原本就没有来过这里。
我在北部,在离家很远的一所很小的大学里教书。一周两天——星期一和星期三,我教学生们写小说。我们所有老师都对大学生说,不可能教会他们这项本领,但学生们只是嘲讽地微微一笑,觉得大人在撒谎:他们自己不是全都会写嘛。
这群学生当中很少有人特别努力,但我并没有为此恼火。更糟的是,他们完全不会阅读,也不想弄明白应该怎样做,就连文本里大概写了些什么也不明白。
我布置了作业,让他们读一个五页的短篇小说,海明威的,或是塞林格的。
“好的,史蒂文,请你讲一讲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它。”
“很好,你的想法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太重要了。那你给我们讲一下吧,你究竟不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小说的主人公背叛了妻子。这真的不好,不道德。我不喜欢读这样的东西。”
“那你告诉我,史蒂文,人们总是彼此背叛,对吗?”
“对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写这个话题的小说呢?”
“背叛——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你认为文学应该有教化作用?……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却有争议!论证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吧。”
我完全不在意史蒂文会说什么,我的任务就是不让这个滑头的乳臭小儿戏弄我,掩盖他没读过这个短篇小说的事实,这小子抽了一整夜的大麻(现在还有味儿呢),刚才还开着自己的保时捷跟我抢道,然后又占了我在停车场上的车位。他在走廊里向自己的妞儿打听:那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什么?那个女孩告诉他:一个人给自己的老婆戴了绿帽子,嗯,于是他准备承担责任。“你骗不了我,”我心想,“看我怎么折磨你,让你走投无路。”
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如果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揭穿这个学生,因为他没有准备功课而给他打两分,那么等到学期末他就会报复。结课当天,他们所有人都会收到系主任办公室下发的特制影格纸,上面罗列着各种提示性的问题。他们坐下来,兴奋地把不习惯拿笔的那只手弯起来,用印刷体写字,污蔑老师——“教授对我没有吸引力。”“他没有营造出能激发人产生兴趣的氛围。”“我不喜欢他的领带的配色。”“他打二分和三分,却不解释为什么。我很失望。”
所以老师有必要及时让学生明白一个事实,即他是一个懒惰的畜生(假如他想让这个事实——他是一个懒惰的畜生——尽人皆知的话),只有这样,他自己才会被迫承认这一点,同学们也才能承认这一点。任何真诚的想法、理想的模式、良心的呼唤、崇高的榜样,以及其他那些在我们祖国喜闻乐见、冠冕堂皇的废话,在这里全都不起作用。在这里,你得不停地哄所有人开心,让每一位大学生都觉得只有他才是最重要的,是我全心全意关怀的对象。但是你不能流露出任何亲昵的、粗俗谄媚的态度。假如教授想讨好学生,指望通过给他打高分获得好评,学生就会充满鄙夷,最终还要在自己写的最后几句评语里故意对老师使坏。
最好还是放弃理智行事的想法:理智使人生气。措辞也要更简单些,否则他们就会抱怨我使用了他们不懂的词汇。此外,当然,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及油腻的赫列斯塔科夫气质【赫列斯塔科夫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在俄语中,赫列斯塔科夫气质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人们撒谎吹嘘、庸俗市侩、厚颜无耻的习气】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不应教大学生学习,而是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学会的。
我本来就是个差劲的老师,这种心理骗术和本土化的滑稽戏对我来说太过遥远了。第一个学年结束后——我呆头呆脑、老老实实、费尽心力、使出浑身解数给那些学生上完了课——他们给我打了两分,还写了一大堆负面意见。几个和我要好的教授朋友为我感到难过。
“明白吗,你是外国人,塔季雅娜,你也不像我们一样有经验。我们单独给你补补课,做些训练,一起试着做些调整。”
“不用啦,我自己能行。”
“但是,如果下一学年你的评分还是这么糟糕,你会被解雇的。我们可不想和你分开!”
我也不想和自己的家分开,我想了想。我需要这份工作,也务必拥有这份工作。就算要我趴在地上汪汪叫,我也一定会趴下来汪汪叫的。因为我爱自己的家,它也爱我。
第二年,所有学生都给我打了最高分。朋友们看着我,就像看着尤里·盖勒【尤·盖勒(1946— ),以色列著名的魔术师】一样——他能把没有钟表构造的钟表鼓捣得滴答作响。
“你是怎么做到的?!就一个学期?校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你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撒谎了,厚颜无耻地看着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诚实的眼睛。我可不能承认自己为了博得学生的喜爱而趴在地上汪汪直叫。
…………
END

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Татьяна Толстая,1951— ),俄罗斯当代经典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文学评论家、电视节目主持人、政论家。托尔斯泰娅出身名门,是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与女诗人娜·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孙女。她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出版了二十余部作品集,其中短篇小说集《爱与不爱》《白墙》《坐在金色台阶上……》《葡萄干》多年来一直深受俄罗斯读者的喜爱,而以未来俄罗斯作为书写对象的反乌托邦小说《野猫精》,则是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在中篇小说创作上,托尔斯泰娅同样有所建树,本期译介的《浮华世界》(Легкие миры),就曾在2014年为她赢得了别尔金最佳中篇小说奖。
上文节选原文四分之一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入微店,购买纸刊阅读全文。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策划及责任编辑:孔霞蔚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