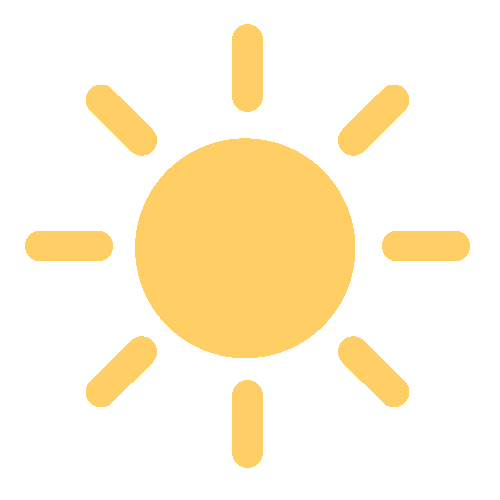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莉•特莱斯【巴西】:倘若我能这样一动不动地伫立着,轻轻地呼吸,没有恨也没有爱……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莉吉娅·特莱斯作 丁晓航译
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进了门,没有一点儿声响。他算不上敏捷,只不过走路小心翼翼,挺儒雅的。
“鲁道夫!你在哪儿?……在睡觉吗?”他问道,看见我穿上衬衣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又压低了嗓门:“是你一个人吗?”
他知道我是一个人,他很清楚我总是一个人待着。
“我在看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我合上书。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我想记住当中某个段落……可是天太热,这恐怕是入夏后最热的一天了。”
他把夹包放到椅子上,然后打开他带来的那袋紫葡萄。
“已经熟透了,看看多漂亮。”他说着,一边拿出一串葡萄,像钟摆似的在手里晃动着。“尝尝吧!鲜美得很。”


我装作不经意地把上衣抛到桌上,盖住我当天早上开始写的短篇小说手稿。“葡萄上市了吗?”我摘下一粒葡萄,问道。虽说甜得腻人,但只要咬开厚实的果肉,就能品尝到它的原汁原味。我的舌尖能感觉到硌舌的葡萄籽。我把果肉嚼碎,酸汁儿在嘴里蔓延。我把籽儿吐出来,心想写作也是如此:进入核心中的核心,直至找到像胎儿一样躲在最深处的种子。
“我还带来一样东西……过会儿拿给你看。”
我面朝他。他微笑时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眼睛像葡萄珠一样水灵。
“是什么?”
“我都说了是惊喜!还是等会儿再给你看吧。”
我不再坚持。从前每当他让我猜他口袋里或者枕头下藏着什么时就是这副表情,我太熟悉了。他总是神秘兮兮地围着我转悠好一阵,最后才把宝物献给我:苹果、香烟、色情杂志或是一包叹息饼【一种葡萄牙风味甜点】。
“我去煮咖啡。”我说道。
“给你自己煮吧,我刚才在街角喝过了。”
他在说谎。街角的咖啡店肮脏不堪,对他来说,喝咖啡是一种崇高体面的礼仪。他这么说是为了帮我省钱,他一向如此。
“在街角?”
“对,我买葡萄的时候……”
我的兄弟。金发,晒成黄褐色的皮肤,雕塑一般的双手和难以界定颜色的眼睛。
妈妈认为他的眼睛是紫色的。是紫色的吗?
她是对德博拉阿姨说的:我儿子爱德华多有一双紫色的眼睛……
他脱去上衣,松了松领带。“眼珠子怎么会是紫色的?紫色的。”我一边打开炉子,一边问自己。
他笑着,挨个儿摸着口袋,终于掏到香烟,神情很专注。
“天啊,从前咱家花园里种过紫丁香……不是紫丁香吗,鲁道夫?”
“是紫丁香。”
“还有一株葡萄藤,记得吗?咱们没从上面收获过一串熟葡萄。”他一边说一边深情地折着装葡萄的纸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葡萄甜不甜,甜吗?”


“我也不知道,你总是不等它们成熟……”他慢慢解开衬衣袖口的纽扣——衬衣上的图案很有特色,细心地卷起袖子,以免留下皱褶。他拥有游泳者的强健臂膀和金色的头发。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些父亲曾经用过的纽扣。
“奥菲利亚想请你星期天过去吃午饭。她重读了你的长篇小说,比之前还要喜欢,你得听听她饶有兴致地分析人物,谈论细节。”
“星期天我另有安排了。”我往水壶里灌着水。
“那就星期六?别跟我说星期六也不行。”
我靠近窗户。灼热的风迎面吹来,感觉就像待在烤箱中。此刻他看不见我,我可以张大嘴呼吸,可以皱眉头,就像他折纸袋一样。我用手绢擦着脸。有完没完,有完没完?!……这一切又把我带回童年,难道他不清楚这只会给我带来痛苦的记忆?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为什么?为什么非要到这儿来戳我的痛处?我不想回忆任何往事,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我闭上眼睛。黎明时分,朝霞从天边升起,微风吹过草地、瀑布。冰凉的露珠滑落到花冠上,细雨润湿我的头发,山峦和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空旷。静止和空旷。倘若我能这样一动不动地伫立着,轻轻地呼吸,没有恨也没有爱,倘若我能就这样待一会儿,没有形体,没有念想……
“星期六怎么样?她要做你最爱吃的核桃糕。”
“我戒糖了,爱德华多。”
“偶尔改变一下饮食习惯而已。你瘦了,对吧?”
“恰恰相反,我胖了,你没看出来?我胖得不行了。”
“不可能!从背后看我感觉你瘦多了,我正要问你减了多少公斤。”
我的衬衣紧贴着我的身体。我把黏乎乎的手在窗台上蹭了蹭,然后睁开炽热的眼睛。“这孩子真是的,我的天!刚换上干净衣裳就开始淌汗,看着像没洗过澡似的。够烦人的!……”我母亲从不用“流汗”这个词,因为在她看来这词太重了,她喜欢用典雅的词语,欣赏典雅的形象。她连谈论流汗都要很优雅,要给那些词穿上优雅的衣裳,就像给我们穿衣一样。问题是,爱德华多能始终保持洁净,就像待在玻璃罩里似的,手不沾灰,皮肤润泽。他可以满地打滚而不受污染,没有什么能真正让他变脏,就算身处污秽,他也能一尘不染。我就不同了。我轻而易举地被肥胖腐蚀了,汗水在脖子上、腋下和两腿之间流淌着。我不想出汗,不想,但可怕的汗水不停地流着,把衬衣染成黄色,再镶上一道绿边。那是一种诡异的、动物才会排出的毒汗。我急速擦着额头和脖颈,试图做最后的努力,至少要保住衬衣。可是,我的衬衣已经像一张皱巴巴的皮似的,和我的皮肤、气味以及颜色粘在了一起。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有一天,为了不再出汗,我想到了死。




“昨天夜里我梦见咱们从前的家。”他一边说一边走到炉灶旁边,打开水壶的盖子,看了一眼壶内,又盖上了。“我记不清了,房子好像已经废弃了,一场奇怪的梦。”
“我也梦见过从前的房子,但那是好久以前了。”我说道。他靠近了些。我往柜子那边退缩着,拿起杯子。
“妈在你的梦里出现了吗?”他问道。
“出现了。爸爸弹着钢琴,而妈妈……我们跳华尔兹转晕了头,我人很瘦,轻飘飘的,脚尖蹭着地面,甚至感觉浮了起来。我笑着挽住她在吊灯下面转圈,忽然之间,我开始出汗,不停地出汗。”
“她活着吗?”
“她雪白的连衣裙吮吸着我黄绿色的汗液,可是她仍然在跳。她渐渐离开,远去,越来越模糊。”
“她活着吗,鲁道夫?”
“不,是她死了以后跳的舞。”我说着,一边把一只完好无缺的杯子放到他面前,把另一只有缺口的留给自己。“你还记得这杯子吗?”
他抓着杯子的耳朵,仔细察看。彩绘玻璃在阳光照射下令人眼花缭乱,映衬着他的脸也发着光。


“啊!日本杯子。还剩很多吗?”茶具、刀具、水晶饰品以及地毯等等都已经归了他,还有那些刺绣床单。当初我强迫他接受所有那些物品。他拒绝接受,相当激动地说:“我不要,这不公平,我不能接受!除非你留下一半,否则我什么都不要!有一天你也会结婚……”“不会的!”我回答说,“我一个人过,我喜欢房子里什么摆设都没有,越简单越好。”他似乎一句都听不进去,把物品分成了两份,“好了,放在你房间的那些归你了……”我不得不来硬的:“如果你执意要把那些东西留给我,你前脚走,我后脚就把它们扔到大街上!”我抓起一个花瓶说:“扔到马路中间!”他脸色煞白,嘴角抖动起来。“别,千万别!鲁道夫,快请住嘴,瞧你都说了些什么。”我用手捂着灼热的脸。我母亲的声音从骨灰中弥散出来:
“鲁道夫,为什么非要让你弟弟伤心?你没看见他在受折磨吗?”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拥抱了他。“听着,爱德华多,我本来就是个怪人,你明明知道我近乎疯狂。我什么都不要,说不清为什么,就是不想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把东西都拿去给奥菲利亚,当作我的礼物。我不能送你们一件结婚礼物吗?我也不是什么都没留下,你看,这儿呢,我留下这些杯子!”
“像蛋壳一样细滑。”他说着,一边用指甲弹击着瓷杯。“以前它们被放在粉色柜子的格挡上,记得吗?柜子摆在咱们的客厅里。”
我把开水倒进杯子,咖啡粉极不情愿地溶解着。我的母亲。后来的奥菲利亚。难道不该留下那些床单?
“奥菲利亚好吗?孩子何时出生?”
他把手伸向那堆摞在地上的旧报纸,仔细地整理着它们。从他的表情来看,他想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存放它们。然而,如此杂乱的套房里还能容下这样一件多余物品吗?他把报纸塞进柜子的空格里,转过身对着我,目光伴随着我在水池下的橱柜里寻找糖罐。一只蟑螂惊慌地逃窜着,躲到一个锅盖儿下面。接着一只更大的不知从何处掉落下来,也试图躲到锅盖儿下,但那个缝隙太狭小了,它只能勉强把头藏在里面,啊,如同一个绝望之人在寻找藏身之所。我打开糖罐,等着他向我介绍一种灭蟑螂的新招儿:极为便捷,只消打个电话,就会有穿黄褐色制服、手提空吸泵的人出现,瞬间剿灭所有蟑螂。他家里有电话号码,可以给我,蟑螂和蚂蚁都不在话下。


“好像是下个月。她动作还是那么灵敏,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快要生了。”他一边说一边在我身后踱来踱去,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在眼里。“你猜猜谁会是教父。”
“什么教父?”
“当然是我儿子的教父!”
“我从没想过。”
“是你。”
我的手在颤抖,仿佛不是在舀糖,而是把勺子插进了砒霜罐里。我感觉自己越发肥胖,越发卑微了。我真想吐出来。
“这毫无意义,爱德华多。我不信上帝,什么都不信。”
“又有何妨?”他问道,一边给自己的杯里加了点糖。他几乎把我拽进了他的怀抱:“放心吧,上帝我替你信了。”我把苦咖啡一饮而尽,一滴汗水落到茶托上。我用一只手托住下巴。我当不上父亲,只能充当教父。我不够和蔼可亲吗?
这对夫妇真是有心人。我趁着给咖啡加热,转过身悄悄用抹布擦去脸上的汗水。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我问道,而他却一脸无辜地看着我。我又重复了一遍:“惊喜!刚进门的时候你说……”
“啊,不,不是!不是这个。”他喊着,眯着眼睛笑了起来,那双微笑的眼睛里透着一丝狡黠。“惊喜另有其事。”“如果,鲁道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总之,你自己去猜想,随你猜想。”
他那种神态同从前母亲的神态如出一辙。每当母亲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时,总是在我身边踱来踱去,一声不响地盯着我,咀嚼着秘密,直到实在忍不住的那一刻才讲出来,条件是一成不变的:“你得答应我一星期不吃糖果,就一星期!”
要是他能住得离这儿远一点?他可以移居到其他城市,或者去旅行。但是不会的,他必须待在附近,永远守在附近,盯着我。从儿时起,当他还在摇篮里时,他就这么看着我。我要求不高,并不需要他恨我,只需忽略我的存在便可,哪怕只是对我视而不见。他英俊,聪明,招人喜欢,无论做什么,总是做得比我好很多,比别人都好,再小的事情经他的手一做,都会变得有意义,让人眼前一亮。结果呢?那个肥胖、穿戴不整、体味不佳的兄弟自然会被冷落。作家,没错,但不是那种受邀出席庆典、在电视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成功作家,而是一个低微的、必须张开鹰爪为自己掘路的作家。哪怕他只……可是不会,当然不会,从儿时起,我就注定要领受他的关爱。有时候我躲进地下室,跑到花园里,爬上无花果树,一动不动,像只蜥蜴似的伏在墙头上——好了,这下你可找不到我了。但他总是打开门,查看柜子,扒开树叶,眼含泪水不停地笑。他总是趴在地上,像动物似的嗅寻着我的踪迹。“鲁道夫,别再惹你弟弟哭了,我不想让他伤心!”为了不让他伤心,只有我知道她即将死去。“你已经长大了,理应了解实情。”父亲直视我的眼睛说:“你母亲剩下的日子……”
他没有把话说完。他回到墙边,双臂交叉,拱着肩站在那儿。“只有我和你知道这件事。她太担心了,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弟弟知道实情,你明白吗?” 我明白。最后一次为她庆贺生日的时候,一家人围在她的床边。“劳拉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国王,”父亲说着,给她喝了一口葡萄酒。“不过她没有把一切都变成金子,而是把她碰过的东西都变成了美。”我的眼睛因为哭得太久肿得眯成了缝,我跪在她床边,假装为她整理枕头,把头靠在她的手能够着的地方,啊,哪怕她能怀着一丝母爱抚摸我一下。可她只顾看她的胸针,那枚茧子状的胸针是爱德华多用他在花园里捡到的一块玻璃缠上金属丝做的。“亲爱的妈咪,这是我给你做的!”她亲吻那枚胸针。铁丝变成了银子,碎玻璃瓶变成了翡翠。她用那枚胸针固定连衣裙的领子。向她告别时,我把她冰凉的手紧贴在我的嘴唇上,那我呢,妈妈,那我呢?……
“我忘了给你拿饼干,看呀,你喜欢吃的。”我说着,一边从柜子里取出饼干罐。
“是你的佣人做的吗?”
“不是,我的佣人每周只来一次,是我在街上买的。”我一边说,一边把目光投向他。现在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惊喜了吧?他让我自己猜,我怎么猜?到底是什么?我问他:“你藏着什么秘密,爱德华多?还不想说吗?”
他似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吹去了落在裤子上的灰,然后俯身看着那些饼干。“啊,甜面圈。奥菲利亚从咱妈的配方本上学会了做这个,但是还远没达标。”


我进屋的时候,他正在吃甜面圈。巧克力奶杯在一旁冒着热气。我喝过茶了。茶。我围着他转了一圈,告诉他,儒里奥已经在街边等着了,说必须现在做个了断。他站了起来,穿上凉鞋,摘下手表和小项链,步伐坚定地走向大门口。我很吃惊,仿佛看见他满身是血,衣服被撕成条。“你个头比他矮一截,爱德华多,你会被虐成狗的!” 他摊开双臂。“那又怎样?你想让全班人骂我胆小鬼吗?”我在之前他坐的椅子上坐下,蜷缩着身子,喝着他留下的巧克力奶,嚼着饼干。当我听见母亲喊 “鲁道夫,鲁道夫”的时候,嘴里塞得满满的。此时她正试图用眼泪拔出插进爱德华多胸口的匕首。
“我去过两家书店找你的长篇小说,都没找到,我想送几本给朋友。已经售罄了吗,鲁道夫?书店的人说卖得挺火。”
“太夸张了,可能只是一时缺货。”
我的嘴里全是甜面圈,汗水从所有的毛孔里渗出,渗出。耳边又响起母亲响亮的声音:“鲁道夫,你听见我说话了吗?爱德华多在哪儿?!”我走进她的房间。她斜倚在床上,正在绣什么。她一见到我就把绣品放下来,神情变得很沮丧,不停地摇着头,“儿子,又吃上了?!你想胖上加胖吗?”她叹口气,表情很痛苦。“你弟弟在哪儿?”我耸了耸肩说:“不知道,我又不是他的跟班儿。”她盯着我说:“你就这么回答我,鲁道夫?嗯?!”我一边下楼梯,一边吃着藏在口袋里的剩饼干。寂静伴随着我缓慢地走下台阶,沉重的身子像是粘在地上似的。我停止了咀嚼,猛地加快步伐向街上走去。得让他活着,不能动刀子!我看见他坐在排水沟上,衣服被扯破了,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抓痕。他苍白的脸微笑着,喘着粗气。儒里奥已经逃走。我盯着他的胸口。“他没用匕首吗?”我问。他的脚崴了,用手撑着树艰难地站了起来。“什么匕首?……”我垂下了头,心怦怦跳着。我弯下腰趴到地上。“你走不动道了,”我说着,把手撑在膝盖上。“来吧,骑到我背上。”他服从了。让我纳闷的是:他看起来那么瘦,却像铅锭一样沉重。烈日在头顶上照耀,风吹动着他被撕破的衬衣。我在墙上看见我们的影子,那些布条像翅膀似的扇动着。他抱紧了我,下巴倚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抽泣道:“你能来找我真好……”
“你的新书吗?”他异常激动地问道。他在桌上看见了那些草稿。“我能读一下吗?鲁道夫,能吗?”
我从他手里抽回稿纸,把它们放进抽屉里。写作,是我仅有的一点技能了。难不成他也……
“不,不行,爱德华多。”我试图用柔缓的语气说道。“刚开了个头,炎炎夏日,效率低得很。”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补充道。我望了望他放在椅子上的夹包,那个惊喜……蓦然间,我的心像一只贝壳似的合上了,痛苦仿佛看得见摸得着。我看着他说:“你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是吗?手稿就在夹包里,对吧?”
他打开了包。

莉吉娅·特莱斯(Lygia Fagundes Telles,1923— )出生于圣保罗市,写作生涯始于1938年,共出版《石人圈》等四部长篇小说和《绿色舞会之前》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集。2005年获卡蒙斯文学奖,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除了她擅长的魔幻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外,亦有不少作品被称为忧怨小说,透过描写市民生活,触及情感纠葛、家庭伦理和精神健康等主题。《绿黄色蜥蜴》即是运用时空转换、自由联想等手法描述兄弟间错杂的情感关系。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3期,责任编辑:汪天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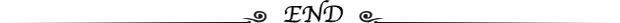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