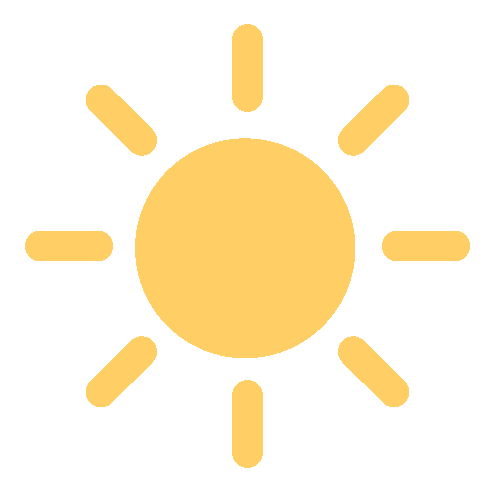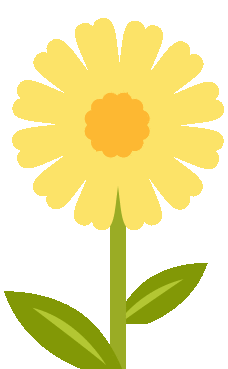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伊•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俄罗斯】:整个世界犹如那个密封的地窖,世人也无非是跟耗子一样在挠爪子……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作 万海松译
门闩生锈了,所以栅栏门无法打开。“往事一去不复返。”塔拉斯一边想,一边拆掉了栅栏上的几根木条。
房子年久失修,开始变得歪斜,地板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患病的关节。家具上蒙着殓衣一样的白床单,镜子里映照出一个穿着正装的四十岁男人的模样,现如今,这套衣服比他的命还值钱。
周围这一带的人们都管塔拉斯叫“莫斯科”。自打他中学毕业后,小村庄就像童年时代的衬衫,变得又紧又小,而在首都,他迅速地飞黄腾达起来。他换车换得比换女人还要频繁,每天早上都系好绳套般的领带,而世界在他眼中就是一间巨大的办公室。
花园里杂草丛生,一簇簇荨麻朝窗子里张望,犹如好奇的邻居。塔拉斯掀开床单,用衣袖拂去桌上的灰尘,抽起烟来。
他过夜却是在车里。
在街上,他偶遇卡佳。他早已知晓她有四个孩子,过着连衣裙一样褪色的生活。在边远地区,人们传播谣言就像嗑瓜子一样,一边嗑,还一边在院子里挂晒洗净的内衣。
“老公怎么样?”
“还好。他上吊死了。”
云朵宛若受惊的羊群,堆砌成厚厚的云层,太阳躲到了它们的后面。孩提时代,他常常和卡佳一起爬上屋顶,互掷苹果,还发誓永不分离。而如今,他们的眼神一接触,就觉得彼此形同路人。
房子附近有人守候着塔拉斯。庄稼汉们身上散发着酒味,就跟他童年时从父亲身上闻到的一个样。
“你要雇人干活吗?”一个人摘下便帽,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们都是现成的劳动力。”
他摇摇头,再次从木栅栏上掏出的洞里钻了进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他留下这么一句话。
塔拉斯躺在睡袋里,下面垫着铺好的被褥。“生活很漫长,但一张欠条就能概括。”他一边思忖,一边听着树梢拂动屋顶的声音。小时候,他曾在菜园子里发现一个军用头盔。夜深了,塔拉斯无法入睡,总觉得树梢像是从一个阵亡士兵身上长出的手臂,而他正在敲门,请求在此过夜。
接着,真的有人敲门了。
两个理着短发的孩子,活像一对双胞胎,狠揍倒在地板上不停抽搐的塔拉斯,而第三个孩子,则在抖搂那一包包从密室里拿出来的捆扎好的钞票。
“抛掷金钱有时,堆聚金钱有时。”【这句话化用自《旧约全书·传道书》第3章第5节:“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意指人生命定、各有其时】一个孩子藏起了车钥匙。他抓过手机,哈哈大笑起来:“还要手机干嘛,难道有谁可打吗?”
他们拖着塔拉斯穿过人群般稠密的杂草,来到了院子里,然后从油桶里倒了点油,一把火点燃房子。
他猛然间惊醒了,发现自己正在一个挂着花花绿绿窗帘的房间里,一些像《格列佛游记》里小人国侏儒的孩子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他公司的保安是直接死在岗位上的。他就躺在门口,双臂伸直,用早已凝滞的、泛白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当时正值早上,上班族犹豫不决地聚拢在办公楼前。塔拉斯看了看手表,熄灭烟头,跨过保安的尸体。其他人紧跟在上司身后,接二连三地跨过尸体,仿佛跨越施洗约翰节【东正教的施洗约翰节在每年新历的7月7日(俄历6月24日)】时的篝火。现在,当塔拉斯也这样躺着,死盯着天花板的时候,他不禁想起自己跨过尸体时,那死去的保安看他的眼神是何等狰狞。
卡佳身上散发出扑鼻的香水味,弄得塔拉斯的鼻子十分难受。她摸了摸他的脉搏,而他,在再次昏睡之前,感觉到她的双手在颤抖。
草地上反射出萤火虫般的点点星光。塔拉斯坐在门廊上,裹上厚毛围巾,抽起烟来。
“该死的世界,”卡佳叹息道,“有人变成了酒鬼,有人一走了之。”
塔拉斯没有听见她的话,因为他回想起那纤细的、少女的手指和酸涩的花香。他躺在草地上,衬衫浸透着露水。“我会等你!”那时卡佳弄得他耳朵直痒痒。
“那是怎样的日子啊,连鬼都求过。”卡佳的声音直达门廊,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你来并不是为了祈求施舍,你,通过女秘书转交了一封信,就像对叫花子一样。”
塔拉斯深深吸了口烟。
“你从莫斯科回来,就好像从另一个世界回来,开始喝酒了。有一次,你竟然拿上一根绳子,直接去了林子里。”
塔拉斯跳了起来,忘记身上还披着厚毛围巾——赤裸裸地站在那里。他骂了一句,随即用手遮住自己。卡佳哈哈大笑。但她立刻就哭了,还像小时候那样,用袖子擦拭眼泪。
“丈夫留下的东西……”
塔拉斯试了试卡佳亡夫已经穿破的衣服,也试了试他的人生。白天他送孩子们去上学,修理已经歪斜的木栅栏,晚上透过酒瓶的玻璃观察世界。现在,谣言像狗一样,正跑在他前面,而人们好奇的目光好似狗儿刺一样粘了上来。
卡佳变得越发漂亮了,她还能一眼就猜出他在想什么。她猜到他正在想莫斯科。
他的母亲还在莫斯科。“人应该死在出生之地啊,”离开村子的时候,她哭着说道。在莫斯科的院子里,她拆掉栅栏,坐在长凳上嗑瓜子,邻居们把孩子留给她带。儿子把她葬在市中心的一处墓地,竖起一个用巨大的石头做的十字架。可是,打那以后,她时常在夜里来找他,求他带她回老家。


篱笆门旁有人在等塔拉斯。
“你走吧,‘莫斯科人’,你在这儿就是个生人。”他的一个老同学正皱着眉瞅着他,此人折断的鼻子好像睡着了一样躺在脸上。
“把卡佳留下,”第二个人吐了口唾沫,手里在摆弄一把刀子,“给你三天时间准备。”
卡佳把饭锅弄得叮当作响,在他跟前哼唱小曲。
“让我走吧,”塔拉斯从门槛外甩出了一句,“我会回来的。”
“最好别回来!”她一头扑进他怀里,塔拉斯觉得自己的衬衫已经被露水湿透了。
窗外一闪而过的村庄还都沉浸在睡梦中,公共汽车宛如一匹未经驯服的马,在坑洼上蹦来跳去。塔拉斯心里在占卜:“如果前面的转弯处出现一片林子——我就永远留在莫斯科;如果是一片平地——我就还要回来。”可他又害怕起来,眯缝起眼睛。
前方是一片片低矮的新建筑,仿佛几百个闪耀着炯炯目光的巨人。“这么多窗户——却没有一扇属于我。”塔拉斯一边想,一边走近一栋房子。
“你要是再来,我就报警。”前妻透过门缝漫不经心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就住一晚。哪怕睡地板上也行。”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他下到地狱般的地铁里,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穿行,如同穿越一丛丛野蛮生长的荨麻。他躲进电气小火车一节车厢的角落里,像个大铁环一样滚来滚去,直到把自己弄得头晕目眩。
他在公园里过了一夜。在长椅上,伸直身子一躺下,他就想起小时候和卡佳玩躲猫猫游戏的情景,当时他藏在一个散发着霉味的地窖里。地窖的盖子砰地关上了,他死活都出不去。他蜷缩在装满土豆的袋子上,牙齿直打颤,耗子挠爪子发出的咯吱声都听得一清二楚。而如今,对他而言,整个世界犹如那个密封的地窖,世人也无非是跟耗子一样在挠爪子。
餐馆中人声嘈杂,飘荡着饭菜香味。一个朋友沉着脸,一头扎在盘子里大嚼着。
“现在的钱不好挣……”
“我不求施舍,只是求一份工作!”塔拉斯突然大发脾气,“我只要有事干就好。”
“那你晚上来一趟办公室吧。”有人拍拍他的肩。
商业中心很像停尸房里的冷柜,似乎从敞开的窗户里就能看见尸体的双足。在办公室前,塔拉斯捋了捋翘起来的头发,然后用落地窗帘擦净肮脏的皮鞋。但是,前台女秘书就像瞅一只被放大的蟑螂一样,瞥了他一眼,递给他一个信封。
卡佳用手指指着课本在教儿子识字,而儿子却一边跟着妈妈重复,一边打哈欠。塔拉斯把钱扔到桌子上,从怀里掏出一瓶酒。卡佳装作没看见,可她的胸脯起伏得厉害,仿佛马上就要从她躯壳里活生生地蹦出一个少女来,这少女就是从前的她。
“你别教他识字了,教他数数吧。”塔拉斯抓起酒瓶喝了一口。
学校里举办毕业周年纪念活动。到处摆放着两两拼在一起的课桌,就像在举办追悼宴。墙上的涂料已经脱皮,摆放在带玻璃门的橱柜内的地球仪已经破烂不堪,落满灰尘。胖得像吹了气的女同学喝葡萄酒喝得红光满面,惺忪的醉眼四下逡巡。



男人只有两个:塔拉斯和那个折断鼻梁的同学。
“有人拿刀子猛扎安托哈,长长的刀柄都没进去了,那个喝高了的黄毛小子,科斯佳,落下了终生的……”他弯折着手指头说道。
塔拉斯只哭过一次,就是他旷课的那次,当时他父亲朝手掌里吐了口唾沫,解下皮带来揍他。“要是大家都不上课的话,那就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那时他曾这么怂恿同学旷课。有些同学真就把课本塞进书包里,从课堂上溜之大吉了。
“大家都不上课,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他太阳穴的血管砰砰直跳。
那个老同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仿佛在问:“咱俩谁先溜?”
塔拉斯觉得自己的脖子上似乎紧紧地缠上了一根绳子,他惊讶地发现,眼睛里竟然涌出了泪水。以前在莫斯科的经历,就像那间办公室一样,是消过毒的,而现在的一切则模糊不清,仿佛他又躲进了黑暗的地窖。“你在哪儿啊?”传来一个小女孩清脆的嗓音,“你究竟在哪儿啊?”
瞅着卡佳圆鼓鼓的肚子,塔拉斯却看不见未来。
这个城市小得可怜,而且周边全是密密匝匝的、已经荒芜的村庄,犹如孩子们依偎着母亲。在河对岸,教堂圆顶闪耀着金光,牧群在吃草。一棵白桦树像扎在田地里的一根刺一样矗立着,空旷的田野中央停放着一节铁皮小车厢。从河边望去,能看到一个塔吉克女人正在和面,准备用篝火烤馕,而一个塔吉克男人一边抽烟,一边用手驱赶蚊虫。衣服穿在他身上就像戳在木棍上一样直晃荡,因此远远看去会让人误以为是个稻草人。塔吉克人被太阳晒得黝黑,却又穿得花花绿绿,跟四周单调的风景很不协调,仿佛他们是被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从色彩鲜艳的杂志上剪下来,贴在了一幅描绘俄罗斯森林的油画上。
从大清早到深夜,这些塔吉克人都在放牧集体农庄的牛群。一个孩童的嗓音如铃铛般响彻在田野之上。小男孩给母牛起了各种绰号,这些绰号都是他从大人的谈话和电视里学来的,当鞭子在牛背上呼啸时,他就大声呼喊美国“明星”和集体农庄女挤奶员的名字。
“你怎么区分它们呢?”母亲笑着问。
那些扎根在大地上的房子极像板棚,不过每个房子上方都耸立着卫星接收器,仿佛一只只竖起的耳朵。从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电视的声音,几个塔吉克人紧靠在栅栏上,出神地听着。
“在黑毛子【对高加索人的蔑称】那里,”一个秃顶的老头看着他们,咧嘴笑道,“连生活都是黑毛子式的。”
在俄罗斯,受洗的塔吉克人好像取了新的名字:斯维塔和科利亚。他们的人在称呼他们时都带着嘲笑,因为俄罗斯人是不会这么跟着叫他们的。但小男孩却保留了自己本来的名字。“扎法尔。”他含混不清地说道,眼睛盯在地上。可在农庄里大家都喊他扎哈尔,换成了他们习惯的叫法。农村人不喜欢新名词,所以农场的经营方式还是按以前的叫法,被大家称作集体农庄。


领工资那天,斯维塔双脚交替着站在会计室的门槛上,不时还露出金光闪闪的牙齿,笑容仿佛一只自由自在的猫,在她那疲惫不堪的脸上溜达。“喏,哪怕给——我一百卢——布,也没——什么。”她把一个词儿掰成两半说,好像在切烤馕。女会计不耐烦地挥挥手,连头也不抬。保安把她赶了出去。
“邪恶的城市。”鞑靼-蒙古人如此咒骂科泽利斯克【俄罗斯卡卢加州的一个城市】。“这儿的人都不善良。”塔吉克人直摇头。
他们把简单的零星用品装进包里,动身前往莫斯科。他们穿过一个村庄,一个脸长得跟烤苹果似的老太婆对着他们稍显驼背的身影不停地划十字。在车站上他们靠乞讨勉强凑够了路费。可是就在他们刚坐上公共汽车的时候,集体农庄的保安出现了,像扔几袋土豆似的把塔吉克人扔进了一辆小汽车。他们夺走护照,把塔吉克人拉到那个铁皮小车厢里,铁皮小车厢的门在风中摆来摆去,仿佛一只受伤的鸟儿。“下次打断你们的肋骨!”
雨下了一整天,雨点如不速之客,疯狂地敲打着铁皮屋顶。塔吉克人钻进了被窝,为了节省蜡烛,就让门敞着。他们沉默不语,眼睛瞪得溜圆,看着屋外的田野——实在是太累了,所以一言不发。
集体农庄所在的这个村庄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捷绍夫基”【与俄文“便宜货”一词发音相近】。
“因——为在这里,人——的生——活还算值——两——个——钱!”不知为什么,斯维塔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那在杜尚别【塔吉克斯坦的首都】呢?”女挤奶员尖刻地讽刺道。
“那就一——钱——不——值了。”
当地人远远地看见塔吉克人就会抱怨:“一边是黑毛子,一边是圣徒!”他们把莫斯科人称作“圣徒”,因为一些莫斯科人自奥普塔修道院【奥普塔修道院位于科泽利斯克市东北约两公里处,是从15世纪开始修建的一个小修道院,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曾拜访过这里。苏联成立后,该修道院一度关闭或挪作他用,二战时曾作为战俘营,1987年底返还给教会,恢复为宗教场所】重建时就定居于此。莫斯科人的孩子们光着脚,脏兮兮的,总是在附近吵吵嚷嚷地玩耍,完全一副农村人的模样。
从田野里归来,塔吉克人发现,有科泽利斯克人在铁皮小车厢旁堆放了一些东西。大包小包的直接打开来放在路边,人们忙着试衣服、往嘴里塞面包。扎法尔费劲地把女孩穿的花花绿绿的短上衣往自己身上套,而大人们瞧着他那样子,都不出声地笑着。斯维塔忧郁地摆弄着用不上的餐具,因为除了烤馕,她什么也没做。晚上,扎法尔一边撒欢奔跑,一边用煎锅敲击饭锅,老太婆们把敲击声当成了火警警报,轻轻地划着十字。
斯维塔每天都要放牛,而那些胖乎乎的、喝酒喝得浑身发热的女挤奶员却给她吃剩饭。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塔吉克女人有一天突然坦率得过了头,说道:
“我习——惯了科——利亚,舍不得把他——交还回去。”
“交还给谁?”女挤奶员不明所以。
“任—尼娅。”
接着,她就详细讲述了自己和科利亚在从塔吉克斯坦回来的路上相识的经过。在塔吉克斯坦相识是在火车上,而同居则是在俄罗斯,就和在战争中一样,一个人没法活。
茉莉花开了,空气因而像东方的甜点一样,甜腻腻的。有人在烤羊肉串,客人们围拢在长长的桌子旁,他们的谈话声仿佛火盆里不同的角落,有的地方突然烧得很旺,有的地方倏地熄灭了。
“我决定做些好事。”一个胖男人一边在裤子上擦手,一边高声说道。
桌前的人们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啦?”他生气了,“每天做一件好事——这难道还多吗?”
“你用闹钟代替了心跳,”男主人在屋子里嘿嘿暗笑,“一切都要按照时刻表来!”
胖子噘起了嘴。坐在他旁边的神父被葡萄酒弄湿了胡子,他高声咳嗽几声,清清嗓子说道:
“上帝会亲吻你的善愿的。”
孩子们像一群蚊子一样在边上跑来跑去。
“这四周是如此之大,”女主人双手一摊,“而我们过去在莫斯科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啊?”
“真让人羡慕!”几个莫斯科人纷纷点头,“我们回去的时候,会在所有的广告牌上看到这句话:‘欢迎光临地狱!’”
“在周围人的眼中也是这样的,”一个瘦瘦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便条本,“我已经开始记录那些进入我脑子里的思想了。瞧,你们听着:‘有的人活着,好像已经死了,只有在死后,他才能重生:在书本、谣言或悼词里复活。’”
他神经质地扶了扶眼镜。桌子后面一片沉默。每个人都埋首杯盏之间,想着各自的心事,连孩子们也安静下来,面面相觑,用眼神发问:“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了?”
神父疲惫地点点头:
“说得还真有点道理。”
夜幕很快降临了,就像有人突然关掉了灯,于是女主人端来了蜡烛。可以看见,在河对岸有人点起了篝火。
“他们那儿没有电。”有人低声说。
“中世纪,简直是中世纪!”


人们一边往高脚杯里挨个儿斟葡萄酒,一边回忆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回忆那些皮肤像黑土地一般的莫斯科看院人的卡拉库利湖【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一个淡水湖】之行,而且非常严厉地咒骂起农奴主般的农场主来。当所有的酒瓶都底朝天之后,他们决定为塔吉克人出头。
越野车呼啸着在科泽利斯克疾驰,一路上惊动了狗,引得它们狂吠不止。黑漆漆的夜晚,空中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因不认识路而绕来绕去的越野车终于驶进了牧场。摁了很长时间喇叭后,胖男人才去敲铁皮小车厢的门,那门仿佛因为害怕而晃动着。
塔吉克人手牵着手走了出来,刺眼的车灯晃得他们眯缝起眼睛。“你留在屋里吧。”胖子拍了拍扎法尔的小脸蛋。
斯维塔和科利亚被他们用车拉着去找农场主。路上还捎上了两个科泽利斯克本地农民以及一个来自军营的军官,那个军官一直像抱女朋友似的紧抱着一杆双筒猎枪。
科泽利斯克人把这条街叫做“贫民区”。几处独门独院的私宅高高在上地坐落于捷绍夫基,豪宅仿佛凌驾于那些板棚的上方,农场主家的宅院还建有几个带射击孔的炮楼,好像中世纪的城堡。高高的围墙上雕刻着一只耀眼夺目的雄鹰,长着两个公鸡般的脑袋。那位雕刻雄鹰的巧匠一辈子都在养鸡场工作,他甚至能像砍鸡脑袋一样横着劈木柴。
农场主不是单枪匹马来见他们的,从大门口出来一队警卫。几个莫斯科人瞬间清醒过来。农场主一脸冷笑,保安全都皱紧眉头盯着他们,几只看门狗发出低沉的咆哮,一个劲儿地想要挣脱锁链。不速之客们已经后悔来到这里了。黑夜正在逝去,而他们就这样站着,谁也不愿率先打破沉寂。静得都能听见一个酒醉的婆娘骂人的声音、一个塔吉克女人用鼻子大声吸气的声音,以及肥胖的农场主沉重的呼吸声。
“庄稼汉们的日子不好过,”最终还是军官开了口,“应该付钱给他们。他们可不是农奴。”
一个长着大头菜般结实后脑勺的保安狠狠地盯着他,仿佛要把他记在心里。
“我们都是俄罗斯人,我们来商量一下。”农场主朝脚下擤了把鼻涕。
塔吉克人互相拉紧了手。
“有什么可商量的!”胖男人尖叫道,“难道这还看不出来:他根本不是把他们当人,而是当畜生了?”
农场主做了个手势,消失在重重铸铁大门之后。保安从人群中拽住塔吉克人的头发,像从地里拔胡萝卜一样,拖着他们就往汽车里摁。军官还未来得及端起双筒猎枪,就挨了一记铁拳,扑倒在地。汽车很长时间都没有发动起来,斯维塔敲车窗的声音清晰可闻。
现场还剩下几个人,莫斯科人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军官吐了血。隔壁房子窗户上的窗帘微微动了几下,但没有人出来。
“瞧,就是这么一回事,”瘦男人双手抱胸,如捂住心脏一样捂住了胸前那个装有便条本的口袋。
大门猛然敞开,看门狗冲了出来。农场主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些不速之客惊慌地四散奔逃,看着恶狗把他们的衣服撕咬成条条缕缕,看着那个军官奋力挥舞枪托阻挡恶狗。那些及时躲进小汽车里的人使劲摁喇叭,试图吓退恶狗。
军官看见了农场主,举起枪来,瞄也不瞄就开了一枪。
响起了玻璃破碎的声音。
“孩子们打破了厨房玻璃。”女主人回来了。
蜡烛燃尽了,蛾子在玻璃罐里扑腾。
“大家都没少看过警匪片,”瘦子捏着便条本挥动了几下,“什么样的人才敢放狗呢?这可是刑事案件。”
远处移动的灯光像萤火虫在闪烁。不速之客们照亮了道路,准备打道回府。
“明天还得再去找农场主。”胖子从桌子前站起身说道。
“这算不算做好事?”女主人咯咯地笑着打趣道。
女人们一边收拾餐具,一边把吃剩下的东西扔给在脚边蹭来蹭去的猫。
“你们不了解当地人,”男主人摇摇头,“而我们都看了十年了!他们能为一公斤土豆而打得不可开交,要是喝醉了酒还会无缘无故地打人。”
大家没有达成一致,都掉头来到了河边。在河岸的另一边,篝火早已熄灭,铁皮小车厢也已消失在浓厚的夜幕中。
日历上已经是秋天了,但九月份依然暑热逼人,秋老虎仿佛纠缠不休的女友。城市变得空荡荡的,避暑客都已经离开了,只留下那些门窗被钉死的房子及孩子们滚落在地板缝隙间的笑声。
不再需要牧人了,所以农场主赶走了他们。
莫斯科人兜起了圈子,胖子在犹豫了很长时间之后,字斟句酌地言语了一番,然后塞给科利亚一沓仔细捆扎好的钞票,深深地鞠了一躬。
“邪恶的城市。”塔吉克人在离开的时候嘟囔道。


第二年夏天,他们又回来了。城里正在大兴土木,老住户们惊讶地发现,一帮黑皮肤的亚洲人在给教堂的墙上抹灰泥。他们之中就有科利亚和扎法尔。男孩在和灰浆、递送各种工具,而斯维塔则在打扫人行道。“要是待在家里更糟。”塔吉克人双手一摊,说道。
河对岸的铁皮小车厢里又住进了新的牧人。田野上的篝火冒着烟,一个脏兮兮的男孩正在把一群牛往河边赶。铁皮小车厢被雨淋得破败不堪,牧人们在上面盖上了从工地偷来的防水毡布。
毡布上写着:“邪恶的城市。”

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Елизавет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Зорина,1984— ),俄罗斯女作家、评论家,俄罗斯文学“三十岁一代”的中坚力量。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现居莫斯科。她曾就读于圣彼得堡电影电视大学,专业是电影导演。后曾在多家杂志和出版社工作,目前主持俄罗斯某网站的文学频道。她21岁进入文坛,先后斩获北方文学之星、处女作奖等多个文学奖项。作品已被译为英语、汉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多种外语。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2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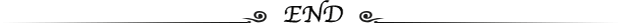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