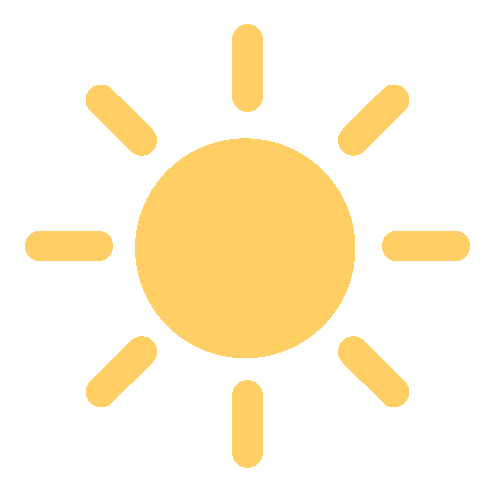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洛•高德【法国】:你会远眺大海,抽一支烟,最后一次注目你热爱的这片土地的风景……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当然,如果你早已知道,一定不会这么做的。你肯定会停下车,在高速路两侧的人行道上走一走,感受一下脚下的大地。你会远眺大海,抽一支烟,最后一次注目你热爱的这片土地的风景。至少你会把妻子拥入怀中,请求她的原谅。因为她也要死去——马上。
巴勒莫的坟墓(节选)
洛朗·高德作 孙圣英译
献给那些真正为西西里带来荣誉的男人和女人
你从机舱走出来,我的兄弟。尽管夜晚炎热,你还是穿上了在飞机上脱下的外套。你的妻子紧跟在你身边,然后是你的卫队,他们身着深色西装,面容冷峻。
你们从舷梯下来,一直走到停机坪。西西里的空气带着它的闷热扑面而来。今天天气肯定晴朗。空气中闻得到。一个美好的五月天,仿佛群山都在为此微笑。
汽车在飞机跑道上等着。三辆不同颜色的汽车。你和妻子以及贴身保镖登上中间那辆。在关上车门之前,你最后一次闻到了煤油的味道。
三辆车风驰电掣般奔向巴勒莫。你甚至没有时间看一眼佩里格里诺山,它正在满怀敌意地盯着你。
你们开得很快。和平常一样。已经有十多年了,你不管去哪里都走得很快;已经有十多年了,你都像今天这样和拉着警报的车队一起行走;已经有十多年了,你在高速公路上超过的汽车在你右侧颤抖着挤成一团。
你把拉伊西角机场【是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的主要民用机场之一】甩在身后,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这座机场会以你我的名字命名,因为我们是孪生兄弟,我的兄弟。法尔科与波斯利诺机场【为纪念在1992年被黑手党暗杀的两名法官乔万尼·法尔科和保罗·波斯利诺,拉伊西角机场改名为法尔科和波斯利诺机场】。至死也是孪生兄弟。你想不到跟你一起坐上中间和前面那辆车的人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好活了。
你开的车。你注意不让自己和前面那辆车之间拉开太远的距离。当然,如果你早已知道,一定不会这么做的。你肯定会停下车,在高速路两侧的人行道上走一走,感受一下脚下的大地。你会远眺大海,抽一支烟,最后一次注目你热爱的这片土地的风景。至少你会把妻子拥入怀中,请求她的原谅。因为她也要死去——马上。但是也许你无力承受她的目光,正如你无力承受那些日夜保护你的人的目光,他们很快就要留下一群寡妇和孩子,孩子们将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而学校里的其他孩子将会用一种敬佩中夹杂着害怕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不幸会传染一样。
也许你什么也不会做。如果有人告诉你你马上会死,就在这里,在这段高速公路上,你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思考,呼吸,作为一个坐在车窗紧闭的汽车里觉得有点热的男人而存在,或许你会决定什么也不做。不停车,不把妻子拥在怀里,不看周围的景色,只是继续把右脚踩在油门上,向前飞驰,就这样迈入死亡,以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没有颤抖,没有犹豫,如同一头进攻中的公牛。其实公牛和你最像了。



你看到高速路上面的路牌上写着去往“查帕西”的出口。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去这个地方。你不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地名将成为你的死亡之名。你不知道,很快,电视台的摄像机就会无数次拍摄这块路牌——为了给恐惧取一个名字。“查帕西惨剧。”你的死就这样传遍全世界。这里将没有什么可拍的,只剩下一些残骸和被烧毁汽车的骨架。没什么可拍的,除了一些穿制服的人示意禁止拍照,还有救护车停在这里,安静得像棺材。
奇怪地,一段童年的回忆占据了你的思想。你回想起在斯费拉卡瓦洛度过的星期天,回想起那些停滞的瞬间,大人们在把餐巾纸上弄满油点之后都会松一松腰带,几条鱼像被打败的敌人一样躺在盘子里——这是孩子们终于可以离开餐桌去沙滩上玩的信号。
你很强硬,兄弟。一个顽强的人。一吨的TNT炸药都没能结果你的性命。没有马上结束。十七点五十九分,爆炸震动了整个佩里格里诺山。你所经之处一切都被炸得跳了起来。埋在柏油路下面的炸药毫不留情地把你的身体撕碎了。十七点五十九分,你们刚刚在查帕西被谋杀。几分钟的时间里,这里只有惊人的宁静,然后电话铃到处响起,消息开始传播,救护车呼啸而来。
你是一个顽强的人。没有当场死去。你挣扎了两个小时后才让步。在救护车上顽抗了两个小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垂死挣扎了两个小时。
佩里格里诺山也差一点跳起来。有些人死在山脚下,人们惊慌不已,嚎哭泣涕。人从来都撑不了很久。留下来的唯有西西里的大地和空气中永远的潮湿。其他的一切都消散在夜晚的热风里。
我一边抽烟一边想着你,我的兄弟。我在法院后面的沃尔图诺路。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也没有权利一个人散步,购物,去学校接孩子。我还不知道自己只有两个月可以活了。但是自从他们在查帕西杀了你之后,我就知道我将如何死去了。我们是孪生兄弟。一辈子都是,过着同样孤独恐惧的日子,在死亡中也将依然是孪生兄弟。我们会被同样的打击结束生命。同样的烧焦的味道将在我们消失的一刻将我们包围。我也会粉身碎骨。我不知道到时有谁会陪伴我,我会携谁之手共赴死亡——路人,妻子,贴身保镖——我不知道,一想到这一点我就颤抖不已,然而有一点我可以确定,那就是他们会像杀你一样用炸药杀掉我,以宣示他们的罪行,昭告他们的胜利。
你葬礼的那天我没有哭。只是紧咬双唇。我一直在想那些谋杀者一定在看着电视上的葬礼,我不想让他们看到这一幕。不应该哭,不应该在他们面前哭。之后,是的,当我和家人以及我邀请的支部的人一起围坐在餐桌旁时,是的,我放声痛哭,你知道的。
我想到自己临近的死期。我知道自己被谋杀的日子近了。我希望一个人死去,不带护卫,不带家人,只带走爆炸产生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因此我才会远离那些爱我的人。你也是,你深知这一点:希望自己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冷酷——总是越来越冷酷——让他们对我们再也无计可施。但是我们能做到吗?……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难道不会是一种失败吗?


我碾碎香烟,走了几步。我沿着卡里尼门路走下来,走近市场。我哪里也不去,只是想走走,看看我的恐惧到底有多大。我一直前行。天气炎热。街边铺子的各种声音近了。我又想到你的葬礼,想到巴勒莫教堂前的人山人海,想到在电视机前紧握拳头嚎啕大哭的意大利。轮到我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么多人呢?谁会陪我女儿走在棺材的后面?谁会去操心我妻子是不是缺钱或者缺少其他什么东西呢?一开始我拒绝了邀请。时间安排在你死后数日,那时我还不想出门,只想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处理文件,好让那些杀掉你的人落网。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尽快找到他们,审判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一开始我谢绝了邀请,理由是时间不够,工作繁多,而几天之后,拒绝这件事一直让我心绪不宁。于是一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大学,告诉他们如果同意的话,我当天就过来。
当我走进阶梯教室时,你知道是什么让我心头一震吗?是学生们的年轻。我不易觉察地微微一笑。很好,我对自己说。我要的就是这个。大学校长以为我会长篇大论。他开始了冗长的介绍。我根本没听。我在想你,我的兄弟。我观察着面前的那些面孔。在这些年轻人中会有一个人被这场演讲打动吗?会有一个人在这个下午之后决定加入我们的行列吗?哪一个呢?是正在把笔转来转去的褐色短发的小个子吗?还是那个笑容严肃的年轻女孩?会有这么一个人吗?我来就只为了这个目的吗?为队伍物色新鲜血液?忽然,校长的声音重新吸引了我的注意。皮埃托·斯卡格里……尼尼·卡萨哈……这些名字我都知道。他在用沉痛的声音列举这些名字。埃玛纽埃尔·巴西莱。是的。我都认识。他们都死了。校长拉开架势开始了与野兽组织声势浩大的斗争史回顾。所有人都死了。所有人都死于野兽的打击。他继续滔滔不绝,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干什么:他以为是在褒扬这些人,然而听众们听到的却是斗争是徒劳的,最后总是野兽获胜。卡尔洛·阿尔贝托·达拉·切尔撒。凯撒·泰拉诺瓦,一九七九年与贴身保镖一起被谋杀。罗科·基尼奇,一九八三年与两个卫队成员一起在自己家门前发生的暗杀式汽车爆炸中被谋杀。你还记得他们吗,我的兄弟?我们都认识他们。我们曾经为他们工作,与他们并肩战斗。皮奥·拉·托雷。随后,他加上了你的名字。乔瓦尼·法尔科。要是他加上那些和你共赴死亡的人的名字就好了。弗兰西斯卡·莫尔维洛。维托·斯基法尼。罗科·迪·奇洛以及安东尼奥·蒙蒂纳罗。如果他们的名字也被提到,你一定感到很欣慰。安静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在想象他会加上我的名字来结束这份名单,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没有必要。阶梯教室里的每个人都已经明白。每个人都在想:我就是下一个。
我差点走出去。什么也不说。就是出去。但是我握紧了拳头,浑身僵硬。校长在用一种友好的姿势请我来到讲台前。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很想用这样一句话开始:“最好的人死了,剩下的在做讲座”,但是我没有。我不想惹人发笑,也不想撒谎,也不想说起我们梦想中的西西里就会到来的更好的时光……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梦到西西里了。我想变得强硬,我的兄弟。我知道你会懂得,我的兄弟。朱塞佩·因帕斯塔托。普拉西多·里佐托。我走近讲台。这份名单依然在我脑海中盘旋。我开始说话,先是慢慢地,逐渐越来越有信心。疲倦消失了。我说到培养一名好法官需要的时间。数年之久。数十年之久,先是学习,然后是执业。接着我又说起杀死他需要的时间:不到一秒钟。只需要有想法,机会和武器就够了。经常,为了使这三个条件都齐备,需要的是金钱。于是我又说起金钱,是为了说明野兽他们的钱要多得多,超过负责与他们斗争的政府机构不知道多少倍。天平总是不平衡的,不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方面。事实就是这样。应该知道这一点。听众鸦雀无声。我平静地看了看这些年轻人,然后继续往下说。在这一刻,我的声音坚定而有说服力。我感觉到了。“参加的人要多才行。”我这样跟他们说。“参加的人要多才行,因为野兽的人将会一直比我们有钱,比我们快。”
后来,当我沿着讲坛的阶梯走向出口时,整个阶梯教室的人都站起来。这让我有点不安。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是的,你知道的,我的兄弟:就是我的葬礼的样子。他们全体起立的样子就像是人们向经过的灵车脱帽致敬。一个男人给他们做了一个小时的报告,然后重返他防弹玻璃下的生活,等待着有一天留给他的一颗子弹打爆他的脑壳。他们起立是为了在他归于虚无之前向他致意。



一辆黄蜂牌小摩托车刚刚超过我。我听见它从我背后开过来,越来越近,然后向我鸣笛——也许是为了让我回到人行道上,因为我没有。现在它已经走远了。它从我眼前经过。一位年轻的女士开着它消失了,没有露出她的脸。我并没有害怕。在摩托车超过我的那一刻,我并没有颤抖。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这么多年来,这是最让我困扰的事情:一辆摩托经过,两个戴头盔的人,坐后座的那个人下车,抓住目标,往他脖子里灌进两颗子弹,然后重新坐上摩托,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我们的人中有那么多个都是这么死的。我害怕摩托车已经有十年了。而这一次却没有。并不是因为女司机按喇叭了,有些杀手也这么干。他们想让受害者回过头来,在死去的那一刻面对枪口。这种行为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买凶者的要求。有时候摩托车也会按喇叭,或者杀手会在开枪之前先借个火。这样是为了让受害人有时间感到害怕。这一次,我没有害怕。我又点上一支烟。这是因为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像杀你一样用汽车陷阱杀我。对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发抖,盯着人群中每张面孔细看已经没什么用了。我将会被一颗炸弹炸得四分五裂。在这种确信之中是否可能有某种形式的安慰?在我远离所有其他恐惧时,这种确信有没有可能让我在此生尚余的时间里重新活过?
我走得更远了。本来只打算走几步,但是现在我不想走回头路,不想回到法院面对我的保镖们的怒吼。我是不是已经逐渐习惯了关于死亡的想法?我会死去,而意大利将再次哭泣。另一个人将接手我的案卷。只有他才会真正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的生活是怎样永无休止的焦虑。只有那个我不认识的他才会知道我在活着的日子里每一秒钟都感到恐惧,但是我与这种恐惧进行了斗争。我们比天性所要求的更加相互仇恨。我们试图保持目光直视,诅咒有时会站立不稳的双腿。我们比天性所要求的更加相互仇恨,就是为了判定让自己过这种无法形容的防弹生活。


有人在忙着杀我。居然想到这一点,真是奇怪。我在努力想象他们的样子。他们聚到一起,考虑最佳的执行方法。他们忙忙碌碌,花费金钱——可能花很多钱。他们不辞辛劳,屡败屡试。让我死简直是他们的心头之患。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他们有多少人在忙这件事?他们是否已经确定了日期和地点?一个人在某个地方为购买把我撕成碎片所需的炸药而讨价还价。另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拧下他们塞满炸药的汽车的牌照。一些人在忙着让我去死的事,也许就是那些曾经忙着让你去死的人,我的兄弟。我还是能躲开他们的。只有一种方式:继续前进,不回头,再也不回法院。就这样在巴勒莫的街道上走下去,一直走到我家。谁敢批评我?谁敢把我当成胆小鬼?我还可以离开这一切。很简单。只需要向前走,远离材料堆积如山的办公室。为什么我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不留给自己看着我的孩子长大的机会?谁强制我去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躬身自问这种让我继续的疯狂到底有多深,然而我没发现任何我能理解的东西。
…………
二〇〇六—二〇一〇
(佩斯基奇-巴黎)

作者简介

洛朗·高德(Laurent Gaudé,1972—),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在巴黎三大获文学硕士学位。1999年发表第一部剧作《鬼魂附身的人的战斗》。2001年,出版小说处女作《哭喊》,第二部小说《宋戈尔王之死》引起广泛关注,获得2002年龚古尔中学生奖和2003年书商奖,而第三部小说《斯科塔的太阳》更使其声名大振,并获2004年龚古尔文学奖。迄今,高德已出版十二部剧本,七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
意大利是高德小说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土生土长的巴黎人,高德的许多作品却都以意大利为背景,而他本人也表示他在意大利才能找到创作的动机和源泉。《斯科塔的太阳》讲述的是意大利南部一个家族从1870年至今五代人的变迁,《地狱之门》的故事也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他创作于2011年的短篇小说集《尼格斯的橄榄树》更是一部写于意大利、关于意大利的作品。小说集共收入四部短篇,均以第一人称叙述,均涉及战争、死亡等作者偏爱的主题。短小的形式给予了作品更加强烈的情感震撼。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1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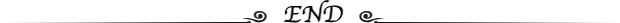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