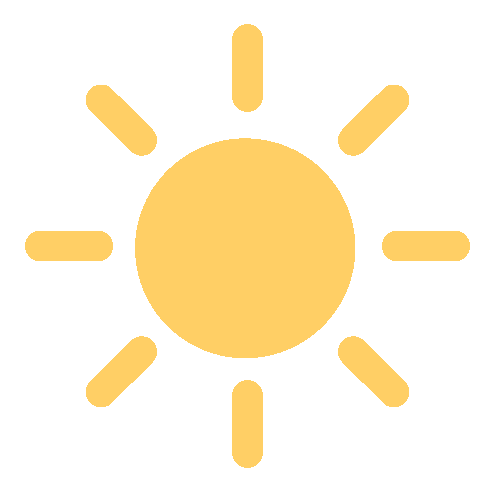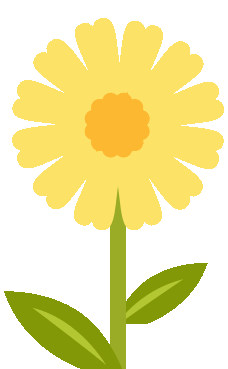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朱雨:无家之人——读《独白二则》与《魂归印度》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当我们阅读这些以移民为主题的作品时,我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那些徘徊在边境线上的幽灵,他们曾经努力过、挣扎过,只是为了找到一个能够容纳自己的“家”。“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移民们的故事还在书写,苍凉的歌声也将继续在古老与崭新的大地上传唱。

无家之人
——读《独白二则》与《魂归印度》有感
朱雨
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浪潮使越来越多的移民文学进入公众视线,跨国移民作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沿素材。俄罗斯犹太裔以色列作家季娜·鲁宾娜的小说《独白二则》与印度裔美国作家珍妮·巴特的小说《魂归印度》(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四期)同样描写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处境,而不同的是,《独白二则》关注移民进入新社会后所遭受的来自外界的边缘化对待,《魂归印度》则更侧重于长期处于反映文化夹缝中的人的“无家”状态,从灵魂层面上突显了移民群体的漂泊之感。


在《独白二则》里的第一篇小说《鲷鱼科的大眼皇帝鱼》中,来自俄罗斯的主人公米哈伊尔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却长期从事着照看特殊人群的护工行业。小说以较大篇幅描写了米哈伊尔与富家子弟丹尼及其家庭之间的互动,正是这段经历让米哈伊尔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艰难处境——自己如同一条生活在黑暗水域的大眼皇帝鱼,只能对着人群干瞪眼,却总是被人无视。米哈伊尔的艺术才能只能用来修复富人的私家藏品(因为俄罗斯修复师的要价远低于以色列修复师)以及陪伴患有精神疾病的丹尼学画画。陪媪般的尴尬地位使他不禁感慨自己与聚会上伺候吃喝的泰国女仆没有区别。他所服务的以色列富人们精于算计,冷漠虚伪,策划将亲人关进精神病院以剥夺其财产,却大言不惭地要教俄罗斯移民如何在“文明国家”生活。上流阶层的家庭聚会表面一片祥和,米哈伊尔和他可怜的看护对象们却被排除在这美好世界之外,他能做的只有像家乡传闻中的醉汉那样掀翻桌子,为自己在新环境里争取一个响亮点的“开场”。后来,米哈伊尔在冲动之下参与了一场街边斗殴并打碎了饭店的橱窗,可这一连串的破坏性行为又能怎样改变他的生活呢?“假以时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说在米哈伊尔受审前的喃喃醉语中戛然而止。
另一篇小说《那么,我们继续吧!……》中的主人公同样具备这种苦中作乐的坚韧品质。原电气工程师拉雅来到以色列后,在画室当人体模特挣外快,而其他的俄罗斯移民也都在诸如面粉厂工人和景区保安之类的低微岗位上艰难求生。拉雅性格要强,独立自尊,与参军的儿子相依为命,即使遭遇因卷入珠宝失窃案而被限制离境的挫折,也依然选择乐观生活。这两篇小说语言诙谐生动,主人公以自叙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自己的异乡经历,客居他乡的辛酸往事在经过沉淀之后增加了几分戏谑意味。作者将个人的亲身体验投射在小说中,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代表着作者本人的生活态度。


相比之下,《魂归印度》的主人公丹在美国工作生活二十余年却还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从来没有得到新国家的真正接纳,他的境况可能会是米哈伊尔和拉雅们悲观化的未来。令人叹息的是,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丹的身份仍然停留在“他者”这一层,异类的身份标记伴随着他的整个后半段生命历程。
在这篇叙事独特的小说中,作者刻意选用不同人物在警方面前的供词作为叙述语言,支离破碎的描述不但无法拼凑出受害者丹的完整面貌,反而使这位安身多年的印度移民形象更加模糊。人们只知道丹是一个安静的人,离婚后常年独居,生活简单,却从来没有人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世界。丹与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人们对他了解甚少,仅存的认识中也不乏一些对亚洲移民的刻板印象(如印度人都不尊重女性、中东男人残忍好斗)。丹渴望得到公司的信任,公司却将升职的机会交给他人——沿着标准轨道运行的美国社会自然不会去关心角落中的异乡人,尽管这是一位为公司奉献二十余年的老员工。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小小的房间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在房间以外,新社会的大门依旧对他紧闭。
精神上的无可归依更是深化了丹身上的悲剧性。作为印度移民,印度无疑是丹灵魂的根系所在,但他又反感家乡的包办婚姻与种姓制度,为此不惜与家人断绝联系;他早已适应在美国的生活,却割舍不下家乡的文化传统,这使他同时居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处和分裂处。对美国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外人,一个“他者”,而对印度来说,他的自我放逐又彻底将自己置于断蓬般的漂泊命运中。两种文化、两个社会里都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他踽踽独行在社会的边境线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成为凶杀案中的冰冷尸体。丹在小说中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酒后斗殴,这样潦草的退场方式倒也符合他的边缘人身份。当葬礼仪式上的火焰吞噬丹的身体,他的灵魂能否真的如标题所言回归印度,还是会继续在密歇根的上空徘徊,作者似乎给出了令人沮丧的暗示。




当然,这样的想法未免太悲观了些。人类从几百万年前就开始通过迁徙提高生存质量,移民们当下遭遇的困境丝毫不会减弱迁徙的动力。只要人类社会依然存在,区域间的差异依然显著,移民现象就不会终结。移民心理是具有超越性的文学母题,身为无家之人的移民们不懈追寻着可能的归属,一代又一代人的追寻历程不断拓宽着人类经验的边界。当我们阅读这些以移民为主题的作品时,我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那些徘徊在边境线上的幽灵,他们曾经努力过、挣扎过,只是为了找到一个能够容纳自己的“家”。“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移民们的故事还在书写,苍凉的歌声也将继续在古老与崭新的大地上传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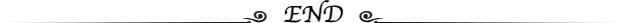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