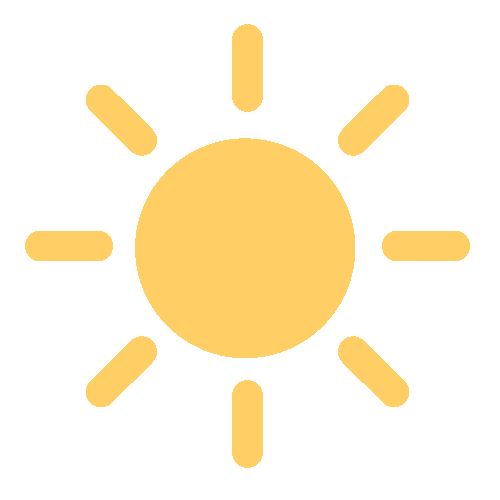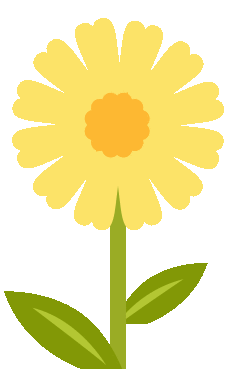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刘世芬:巴别塔下——读塞内加尔法语作家法图•迪奥姆的短篇小说《职业面孔》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巴别塔下
刘世芬
刊登在《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职业面孔》只有六千多字,袖珍、玲珑,却饱满丰盈,像历秋的果实,汁液四溢。
初读《职业面孔》所呈现的每一张面孔时,有滞重、郁积、压抑之感,宛如深夜行路。所幸故事最后有个黎明般的节点,让读者及时逃离了窒息,得以饶有兴味地欣赏“巴别塔”下的风景。



先看沉重的“这个”。
黑人女孩“我”从塞内加尔到法国求学。戴高乐机场播放着“最重要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一副接待有钱客人的妓女模样”。作为非洲人,作者对“面孔”给出了切肤的解读,一张张面孔“凝聚了基因与文化,犹如一个个代表种族和民族属性的牌照”,而作为黑人面孔,“整个非洲……都汇集在我身上,我的面孔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非洲朝向欧洲的一扇窗口”。当我走在斯特拉斯堡大街上,为了生存去一个家庭应聘保姆,肤色更成为标签,人们“使劲儿盯住我的目光似乎既要把我推走,又想叫住我询问一番”,天空那温暖的太阳都变成了“蛮横的目光”。
这样的面孔丛林,也让“我”产生了一连串的职业联想:风钻的声音一定属于某个非洲、土耳其或阿拉伯男人;吸尘器的声音则属于一个非洲、葡萄牙或者亚洲女人;“我”符合保姆所“需要的长相”,因为雇主夫妇已经“把黑人等同于无知和服从”……


在“我”去应聘的这个普通的法国家庭里,夫妻二人都有工作。在“我”之前,杜邦夫人已经“咔嚓”掉N个保姆人选。由于肤色,杜邦先生对“我”不屑一顾,执意让妻子雇佣“上周”或“前天”来应聘的那两个姑娘。可是,“上周那个”“好像刚从集中营出来似的”,“前天那个”则有两个孩子,杜邦夫人并不关心她如何“在那个廉租房的小隔间里照顾她的两个小孩”,只是不想“哪天看见她把我孩子的东西偷走给她孩子用”。况且,这里的姑娘都像“泼妇”,“去年那个”还“闹到劳资法庭上,就为了从我们这里坑点钱”……只有“我”,“拥有一袋子文凭,并且一贫如洗,愿意接受这点可怜的工资”。
男女主人的傲慢和轻蔑写在脸上,全天候地居高临下。女主人的举止可笑、笨拙,像个“恶毒的小丑”,“十根手指像香肠一样又粗又胖”,男主人则像个“有生命的骷髅”。他的目光扫视一圈,落在“我”身上,却不屑于与“我”握手,转身上楼,还是妻子追着他提醒“这姑娘是过来看孩子的”。
在男主人眼里,“我”不配拥有姓名,也不配被称作“女士”或者“小姐”,而是“这个”。我只是“这个”,甚至都不是“那个人”,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佣人。当然,女主人之所以雇佣“这个”,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因由:由于“我”的肤色,她不会有保姆变情敌的担心。
沉重的木地板,沉重的脚步,敲击着这起沉重的雇佣事件。在满世界的优越感面前,“我”的“受害者”心态不爆棚才怪。肤色,还是肤色,黑人的标签从肉体贴到灵魂深处,世间万物仿佛都走到了对立面,连每天接送、温情照料的孩子,也明火执仗地说“我不喜欢她”。但“我”不卑不亢,干起活来从不苟且:换尿布,给红彤彤的小屁股擦粉,一天往返学校两次,推着里面躺着一个金发宝宝的婴儿车出门,用吸尘器吸地,熨衣服,擦洗房间里的每一块地砖……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成为一个无可挑剔的非洲奶妈:勤恳、尽职,却也有骨气,凌厉,深藏不露。



一切始于那部录像机。大孩子想看《灰姑娘》,但“我”坚持不碰房间里的机器设备,因为女主人曾经因为我失手打碎一个瓶子而从“我”工资里扣走了五百法郎。平日里女主人就热衷于以知识分子自居,时刻准备着“点拨”“我”这个愚昧的黑人保姆,这次更是同情并蔑视“我”不会使用录像机,然而正当她想大秀自己的拉丁语和对笛卡尔所谓的了解时, “这个”非洲奶妈第一次在他们全家人面前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夫人,你错了,笛卡尔说的是Cogito ergo sum,意思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可以在他的著作《方法论》里找到。”
空气凝滞,世界静止。女主人放下手中的录像带,男主人正把饼干送到嘴里的手悬在半空,他们同时僵在同一个表情。旋即,男主人色厉内荏地教训她:你以为你是谁?夫人读完了高中,我是一名教育界人士,读过两年大学……夫人楞了半天,才试探着问:你好像读过高中?“我”告诉他们:自己已在两个月前拿到了文学学士文凭。
惊呆的是杜邦夫妇,他们一时不知如何面对这个曾令他们视如草芥的非洲面孔。不过,与第一次应聘时男主人拒绝握手而走上楼梯不同,这次伴随脚步的却是一场“头脑风暴”,他只能和随之跟上来的夫人商量“你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而这个“首次”以文学学士上岗的非洲奶妈,第一次不再提前半小时上班,夫人也自觉地提出为那半小时付费。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夫人开始彬彬有礼地把“你”变成“您”;随着“我”“时不时免费给准备考试的杜邦夫人上上法语课”,彼此间的“尴尬和仇恨也随之消失”。他们开始邀她同桌进餐,不再称呼黑人为“那些人”,而是“非洲人”;当然,还有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问题:杜邦先生开始对这位巧克力色的保姆产生了微妙的绮念……小心呵,搞不好保姆真的会变成情敌。


肤色、人种、国别,终于在敬畏知识的这一刻,做到了平起平坐。
作为女性作家,法图•迪奥姆对异域生存保持着天生的敏感,她的文字泄露了强烈的个性特征,这让她哪怕隐没在人群中也成为一眼识别的“这一个”。在她笔下,发生在异域的所有事件、冲突、矛盾、痛苦和欢乐都通过她独特的视角呈现。这样的文字背后,若想让她取悦、讨好,去干些贴翠拈花的事,毋宁让她去死。
这样的底气,让她讨回本属于自已的尊严,也为读者迎来一抹熹微中明快的笑意。
相传五千多年前,世界上多数民族还处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人们要建造一座可以直通天际的高塔——巴别塔。彼时人类只用一种语言,因此沟通无间,建塔的进度神速。谁知,上帝暗施法术,搅乱人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造成隔阂,巴别塔的建造被迫中止。从那时起,世人分化成不同的族群,散落到世界各地,纷争不断。
在二十一世纪,族群之间的交流呈现出既趋同又存异的态势。作为一名异域困境中的“他者”,迪奥姆在为世界呈现一种多元的跨文化视角的同时,更描绘了一幅巴别塔下最真实的风景。
作者简介
刘世芬,笔名水云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毛姆:一只贴满标签的旅行箱》《毛姆VS康德:两杯烈酒》等,曾荣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孙犁散文奖、首届贾大山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报刊转载,入选全国各类文学选本、年选、排行榜,并被应用于中高考阅读试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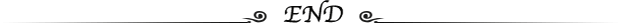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