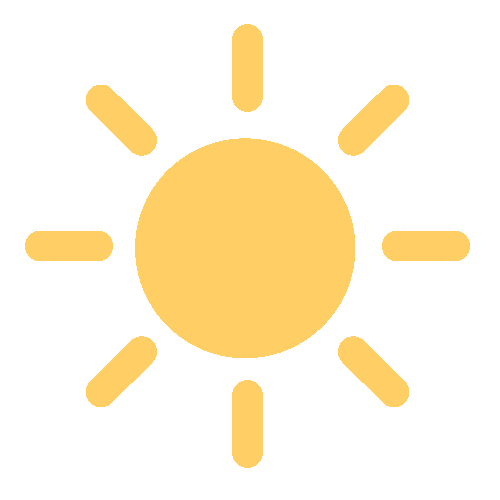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莉•特莱斯【巴西】:啊,黑压压的蚂蚁,把酒精瓶递给我……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在整个房间里洒上苹果花香水(让它散发着果园的芬香如何?),然后早早地上床睡觉了。我开始做另一种梦,做这种梦的次数不亚于考试的梦。梦中,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与两个恋人相约,第一个恋人到了,让我憋闷的是,我得在第二个恋人到达前,带他离开那儿。只是这一次,第二个恋人换成了小矮人。当我的梦境里只剩下沉寂的回声和黑影时,表姐的嗓音抓住了我,把我拉回现实中。我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表姐穿着睡衣坐在我床边,她的眼睛完全斜视了。
〔巴西〕莉吉娅·特莱斯作 丁晓航译
当表姐和我下出租车时已是黄昏。面对又老又旧的小楼,我们愣住了。顶楼的两扇椭圆形窗子就像一对凄苦的眼睛,其中一扇窗子的玻璃被石子打破了。我把箱子放在地上,一只手握紧表姐的胳膊。
“有点晦气。”
表姐推着我朝门口走去,说道:“咱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对两个穷学生来说,附近哪还能找到比这更便宜,又能在屋内用炉子的公寓房。房东太太在电话里说,只要不引发火灾,我们可以做些简单的饭菜。”我们登上极旧的、弥散着甲酚气味的楼梯。

“至少我还没见到蟑螂。”表姐说道。
房东太太是个肥胖的老妇人,她头戴比乌鸦翅膀还黑的假发,身穿一件褪色的日本丝绸睡袍。她的钩状指甲上涂了厚厚一层深红色的指甲油,露出脏兮兮的指甲尖。她点燃手中的烟斗。
“你是学医的?”她一边问,一边把烟雾往我的方向吹着。
“我是学法律的,她是学医的。”
老妇人冷冷地打量着我们,有些心不在焉地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我不得不背过脸去。小小的接待厅十分昏暗,里面摆满了老旧的、疏于维护的家具。沙发是用秸秆编织的,蜂窝状的座面上,摆着两只像是用古装改成的、刺绣面上点饰着小玻璃珠的靠枕。
“我领你们去看房间,在阁楼里。”伴随着咳嗽声,她示意我们跟着她。“你们之前的房客也是学医的,他把一个装着人体骨骼标本的小箱子遗忘在这儿。他经常摆弄那东西。”
“装着骨骼的箱子?”表姐回头问道。
房东太太没有回答,她专心致志地、吃力地爬着狭窄的螺旋式楼梯。她打开灯。房间再小不过了,它的坡顶很陡,靠墙那段我们行动得猫着腰。屋里有两张床、两个衣柜和一把刷成金黄色的藤椅。在天花板距地面很近的角落里,放着一只用塑料布盖着的小箱子。表姐放下手提箱,跪到地上,拉着绳把儿把小箱子拽了出来。她掀开塑料布,看上去很着迷。
“这副骸骨真小啊,是儿童的吗?”
“那人说是成年人的,是一个小矮人的。”
“小矮人?还真是的,看得出已经发育成型……够奇特的,小矮人的骨骼标本非常稀有。你看它多干净。”她一边赞叹着,一边用指尖抓起像石灰一样白的头颅骨:
“太完美了,牙齿全在!”
“我正要把它们扔进垃圾箱,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留着吧。浴室在这旁边,能洗热水澡,专供你俩使用,我的在楼下。还有电话。七点到九点提供咖啡。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餐具,桌上有只热水瓶,倒水后记着盖好瓶盖儿。”她一边提醒,一边挠着头,假发被挠得有些偏斜了。她离开时又留下一口烟雾,嘱咐道:“大门不能敞着,否则我的猫会跑掉。”
楼梯上传来高跟拖鞋的咯噔声和感冒引起的咳嗽声,我和表姐互相望了望,笑了起来。我取出手提箱里的物品,用衣架把一件起了褶的衬衫挂在百叶窗的缝隙中,把一幅格拉斯曼的肖像用胶条贴在墙上,并把一只长毛绒玩具熊放在枕头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表姐站到椅子上,拧下那只仅靠一根电线吊在天花板中央的、非常微弱的灯泡,然后从提包里取出一只二百瓦的换了上去。房间顿时欢快了许多。作为回报,我们发现床单并不像我们第一眼看上去那样干净,而表姐从小箱子里拿出的一小块胫骨倒挺干净。她仔细察看着它,随后又拿出一块脊椎骨,眼睛盯着椎骨中心那个小小的、像戒指圈似的洞孔。她小心翼翼把它们放了回去,就像把鸡蛋轻轻地摞在一只箱子里。
“一个袖珍人,非常稀罕,明白吗?我感觉一块骨头都不少,我会带回连接材料,看看到周末时,能不能开始安装它。”
我们开了一听沙丁鱼罐头,和面包配着吃。表姐那儿总藏有罐头,她常常学习到凌晨,然后吃夜宵。面包吃完时,她又打开一包玛利亚饼干。
“哪来的气味?”我一边嗅着空气,一边问道。我走到小箱子旁,闻了闻地板,又走了回来:“你没闻到一股有点刺鼻的气味?”
“是陈腐的气味,整幢房子都是这种气味。”她说着,一边把装骨骼的小箱子推到床下。


当天夜里我梦见一个留着中分头、身穿格子套装背心的金发小矮人,抽着烟斗进了房间。他在表姐的床上坐下,满脸肃穆,翘着二郎腿观看她睡觉。我欲呼喊:“屋里有个小矮人!”可没等喊出来就醒了。灯还亮着,表姐衣衫整齐,跪在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处地板。
“你在那儿干什么?”我问道。
“瞧这些蚂蚁,突然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儿,行动很果决,你看见了吗?”
我下了床,走近那些棕红色的小蚂蚁,看着它们组成密集的队伍,从门底下进入并穿过房间,爬上装着骨骼标本的箱子,进到箱内。它们就像一支正在操练队列的军队一样,纪律严明。
“成千上万只,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蚂蚁,而且它们只进不出,没有回去的踪迹。”我惊奇地说。
“有来无回。”
我告诉她我梦见小矮人坐在她床上。
“是在床下。”她说着,一边把小箱子从床下拽了出来。她掀开塑料布:“啊,黑压压的蚂蚁,把酒精瓶递给我。”
“想必有什么东西残留在这些骨头里,被蚂蚁们发现了。蚂蚁能察觉一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它们扔了出去。”
“可这些骨头非常干净,我说过的。骨头上没留下任何软组织,干净极了。我很纳闷这些匪徒来这儿寻觅什么。”
她把整个箱子洒上酒精,然后穿上鞋,像表演走钢丝似的,重重地、脚跟挨着脚尖踩踏着蚂蚁队伍,来回踩了两趟。她捻灭了香烟,拉过椅子坐下,眼睛盯着箱内:
“怪异,非常怪异。”
“怎么了?”
“我记得我把头颅骨放在这堆骨头的最上面,为防止它滚动,我特意把两块肩胛骨垫在下面。而现在头颅骨却在箱底,在它两旁各立着一块肩胛骨。难道你动过它们?”
“上帝能为我洗脱,骨骼标本让我恶心!更不用说是小矮人的。”我解释说。
表姐把塑料布盖在箱子上,用脚把它挪到一旁。到了用茶时间,她把炉子放到桌上。地面上,那条黑色的蚂蚁尸带不断地收缩着。一只躲过屠杀的小蚂蚁从我脚边爬过,当我要一脚碾死它时,它把双爪举过头顶投降了,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一样。我让它钻进地板缝里逃走了。
我又做起糟心的梦,这次是从前那种关于考试的梦。老师的提问没完没了,都集中在我唯一未复习的难点上,我被弄懵了。早上六点钟,闹钟急促地响起来,把我从梦魇中拖了出来。我关上闹铃。表姐还在蒙着头睡觉。在浴室里,我仔仔细细地看着墙壁,看着水泥地面,想找到那些蚂蚁,可我一只都没见到。我踮着脚尖走回房间,把百叶窗半开着。夜里那种可疑的气味消失了。我望着地板,那个被屠杀的蚂蚁带不见了。我往床下窥视了一番,在那只被遮盖着的小箱子周围,我也没见到丝毫蚂蚁活动的迹象。
晚上大约七点钟我回来时,表姐已经在房间里。她患有低血压,而我却在蛋卷里加了过量的盐,我感觉她挺沮丧的。我们一声不吭地吃着饭。到这时我才想起来:
“蚂蚁呢?”我问道。
“到现在为止,一只都没见到。”
“你把死蚂蚁打扫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问。
“我没扫,我挺累的。不是你扫的吗?”
“我?!早上我醒来时,地上连一点蚂蚁的痕迹都没有,我寻思是你昨晚临睡前把它们清理了……那,又是谁呢?!”
她眯了眯斜视的眼睛,每当她忧心忡忡时,眼睛会出现斜视。
“真怪呀,怪极了。”
我去拿巧克力,在靠近门的地方,我又闻到那股气味,难道只是陈腐的气味?不,我不认为那气味是无辜的。我想提醒表姐注意,但我看到她如此郁闷,不忍心再去烦她。我在整个房间里洒上苹果花香水(让它散发着果园的芬香如何?),然后早早地上床睡觉了。我开始做另一种梦,做这种梦的次数不亚于考试的梦。梦中,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与两个恋人相约,第一个恋人到了,让我憋闷的是,我得在第二个恋人到达前,带他离开那儿。只是这一次,第二个恋人换成了小矮人。当我的梦境里只剩下沉寂的回声和黑影时,表姐的嗓音抓住了我,把我拉回现实中。我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表姐穿着睡衣坐在我床边,她的眼睛完全斜视了。


“它们回来了”
“谁们?”
“蚂蚁们。它们只在夜里、在黎明之前发起攻势。全体蚂蚁又都聚集在那儿。”
它们的行迹与前一天晚上相同,队伍密集而又封闭,从门口到骨骼箱走的是同一路线,并以同样的方式爬上箱子,进到箱内,同样没有回程。
“那骨头呢?”
表姐蜷缩在毯子里,身体在发抖。
“奥秘就在这儿,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夜里我起来撒尿,差不多三点钟吧。回来时,我感觉房间里多了点儿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在地上看到密密麻麻的蚂蚁队伍。你记得吗?咱们进屋时还一只都没有。我去看了小箱子,所有的蚂蚁都聚集在里面,这倒没什么,发生了更蹊跷的事,差点把我惊得仰面倒地:那些骨头在不断改变位置。起初我还将信将疑,而现在我确信不疑,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把自己安装起来。
“你说什么,安装自己?”
表姐陷入了沉思,我也开始发抖。我紧紧抓住毯子的一角,并且用床单裹住玩具熊。
“你记得吧,昨天头颅骨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刚来时我可不是这么摆放的。现在整个脊柱一节节连接了起来,几乎安装完毕,每块小骨头都各就各位了,似乎有一位专业人士在安装它们,再过一会儿,就……过来看看吧!”
“我信,可我什么都不想看。小矮人正在被黏合起来,对吧?”
我们盯着快速移动的蚂蚁大军,队伍是那么的密集,在它们当中甚至容不下一粒灰尘。去热茶时,我小心翼翼地跃过它。我看见一只走散了的小蚂蚁(是不是上回那只?)在举起的双爪间摇晃着脑袋。我笑了,差点笑翻了,如果不是地面已被蚂蚁们占领,我会禁不住在地上打滚。后来,表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我去上第一节课时,她还在睡梦中。此时地上连个蚂蚁影都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蚂蚁,死去的和活着的,统统消失了。
晚上我去参加了一个同学的婚礼,很晚才回来。回来时我兴奋不已,很想唱歌,有点忘乎所以。直到上了楼梯我才想起小矮人。表姐把桌子挪到门边,正在那儿学习,茶壶在炉子上冒着气。
“今晚我不睡了,就在这儿守着。”她对我说。此时地板上依然很干净。我抱紧玩具熊。
“我害怕。”
她找来一片药帮我醒酒,让我伴着一口茶吞了下去,然后又帮我脱去外衣。
“我来盯着,你放心去睡。暂时没有蚂蚁出现,还没到时间,过一会儿它们才会出动。我用放大镜察看了门底下,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它们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倒在床上,我记得什么都没回答。我梦见在楼梯顶上,那个小矮人拽住我的手腕,把我拖进房间。“醒来,快醒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是表姐抓着我的胳膊肘。她面如死灰。
“它们又回来了。”她说道。
“真的吗?”我双手按住胀痛的头,问道。
她的音量很小,就像一只小蚂蚁在用她的嗓门说话:
“我困极了,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蚂蚁队伍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移动着,于是我去看了看小箱子,果然不出我所料……”
“怎么啦?你快说呀,怎么啦?”
她用斜视的眼睛紧紧盯着床下的小箱子。
“是蚂蚁们在安装小矮人,明白吗?它们行动迅捷,安装已进入尾声,就差股骨和左手上一些细骨了,顷刻间就能完成。咱们得离开这儿。”
“你这话当真?”
“真得走了,我已经把箱子收拾好了。”
桌子已经被收拾干净,衣柜已被腾空,柜门敞开着。
“大清早的,就这么走了,合适吗?”
“赶紧走人,最好在老巫婆醒来前离开。走吧,快起来!”
“咱们能去哪儿呢?”
“这不要紧,回头再说。走吧,穿上这个,咱们务必在小矮人现形前撤离。”


我远远地望着蚂蚁队伍:它们的行进速度比之前更加迅猛。我穿上鞋子,把墙上的肖像揭下来,把玩具熊放进日式女包,我们拖着箱子下了楼梯,房间里散发出浓浓的气味。我们没关上大门。那只猫用拖长的嗓音喵喵叫着,或许在抗议什么?
天空中,晨星已褪去光芒。当我回望那幢房子时,只有那扇被打破玻璃的窗子在看着我们,而它的另一只眼睛仍在黑暗中。

END

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Lygia Fagundes Telles,1923—2022),巴西著名女作家,出生于巴西圣保罗,193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地窖与小洋房》,此后陆续发表了《石人圈》《女孩儿们》等四部长篇小说,以及《野花园》《绿色舞会之前》《老鼠问题讨论会》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集。1985年起至今,特莱斯任巴西文学院院士。她获奖很多,获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2005),三次获巴西文学最高奖项——雅布蒂奖。2016年2月,巴西作联正式提名特莱斯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国读者对她不算陌生,小说《石人圈》多年前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第3期,责任编辑:傅燕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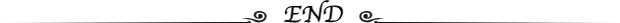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