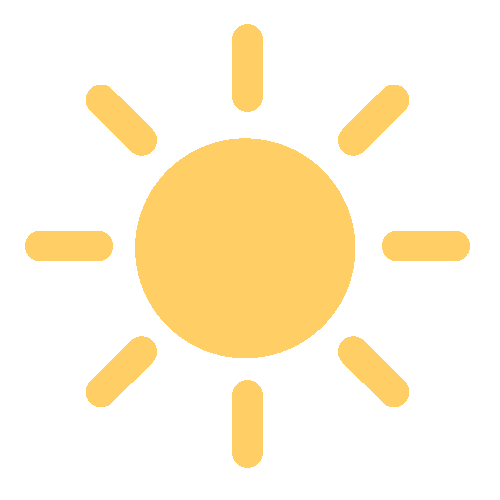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迈•拜厄斯【美国】:手足之争(节选)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停下来将意味着与众不同——不只是一丁点不同,也不是打擦边球,而是实实在在的不一样。切断心灵感应,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过。但其实并非不可想象。这与他们父母曾有过的梦想——搬到乡下去养一群走地鸡或别的什么东西——如出一辙。

迈克尔·拜厄斯作 刘智欢译
独生子女法生效十年后,合成人随处可见。在伯克哈特一家所在的社区里,休斯牌最受欢迎,伯克哈特家就有休斯牌全合成人:肌肉组织极为柔韧灵活,机体可以自行生长,拥有真正的人工智能。你把他们(连同两个装满配件和设备的蓝色尼龙手提箱)从生产部门带回家,从那天起,你就看着他们不断成长变化,这真有点不可思议。你惊讶地发现,他们看上去那样真实,要不是真人,还会是什么呢?几年后,开学第一天,你的合成女儿在幼儿园的蓝色旧大门外紧紧地抱着你的裤腿,不敢进去,满头金发在九月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她的哥哥则站在队伍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到处都是背着书包的孩子,每个人都知道(主要是通过交谈得知,光看外表很难分辨)谁是合成人谁不是,但你不会公开区分他们,这样做很不得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真的无关紧要。你的情感中枢被合成人的仿真身体所蒙骗,但他们的人工智能是实打实的,成长也遵循人类的身材比例——那么,到底有何不同呢?唉,有何不同呢?跟其他问题比起来,这更是成了哲学问题,至少是可以闲聊的话题——谁会不爱闲聊呢?
但大家总是聊起自己的孩子。
至于彼得·伯克哈特——好吧,现在他已经把梅丽莎当作自己的孩子了(这一切发生得很快,两口子早已把她视为心肝宝贝,要护她周全健康,教她明辨是非)。梅丽莎是个好孩子。长得酷似他们(经过无数次扫描,也应该像他们),年仅七岁,钢琴着实弹得不错,但和祖辈一样,并无音乐天赋。喜欢阅读,和她的父母一样。擅长攀爬猴架【供儿童攀爬游戏的单杠架。】。(看着她荡来荡去,他们感觉多么愉快啊,她的优雅动作真是赏心悦目。“这个我以前也能做到。”朱莉一边这么说,一边充满保护欲地看着她——有时候,这仍然是夫妻俩不自觉的行为——压根儿不去想他们的女儿并不是人类,不是他们亲生的。当然,就他们的父母,以及这一代之前所有人的感受来说,她确实算不上人类,算不上他们亲生的……)
一个吸引眼球的松手动作过后,梅丽莎就轻盈地落在铺了木屑的地面上,迫不及待地向秋千跑去。
“那个我也会,”朱莉说,“但可能表现得没那么好。”
梅丽莎转变方向,身子微微前倾,径直扑向彼得妻子的怀抱,撒娇道:“妈——妈——妈!”
然后,她爬下来又跑开了,就像她的哥哥马特几年前那样。

两口子之前戴着夹子接受了两周的远程脑部扫描,不太方便,有时还有点疼;事实上,这个过程足以让一些人望而却步,但不大要紧,因为背后的设想就是:如果连这个最低限度的投入都无法满足,就不该要孩子。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孩子。扫描的最后三天几乎完全不能动弹。除此之外,还需要所有细节——你小时候的病历,婴儿时期的照片,过去的谷歌搜索记录,所有推文、数据和图片——基本上你能收集到的一切资料。梅丽莎是他们的。来自他们,也属于他们。但像所有孩子一样,她也是自成一体的,只要她愿意,就可以把内心封闭、深藏起来,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虚构出新的自我。用手头的零部件组装自己。她喜欢诗歌,近来总是一边朗诵《致老妪》【可能指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写的诗歌。】,一边在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跳绳。她最近还养成了一种喜欢闹出大动静、大阵仗的个人做派——常夸张地一头扎进椅子里,用力甩动头发,或者习惯性地大步走进房间发表宣言,比如:“马特——一直——在烦我!我跟他好好说过了,别再跳出来吓唬我,可他还是这样!”
这时马特会泪汪汪地走到父母面前,他十一岁了,还是动不动哭鼻子,说他不是故意的,而且他没有——
“你有!”
(昂首阔步走开。)
在彼得看来——朱莉也同意——马特和梅丽莎的关系就像普通的兄妹:相爱相杀,彼此依赖,把对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和普通人一样。
梅丽莎有厌恶的东西。讨厌闪电和打雷。会发脾气。会为无关紧要或看似无关紧要的事而抗争不休。后背拼命顶在卧室角落的红色灯芯绒椅上,膝盖抵着胸口,不肯去洗澡:“我不脏。”
“就算不脏,每个人隔一段时间都要洗个澡。”
“不要。”她说。
彼得走进房间。她皱着眉头往椅子里又缩进去一点。
“梅尔【“梅丽莎”的简称。】,你现在出来,”彼得说,“不然就回房间面壁思过。不管怎么样,你最后都得洗澡。”
“我不需要洗澡!”她喊道,“这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了?”
“我不需要,为什么还得洗澡呢?”
彼得走上前,一把拎起女儿,不管她在胳膊下扭来扭去(她给人的感觉和马特不一样,重量在体内的分布有点不同,但彼得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也许只是男孩和女孩的区别罢了),把她带到浴室里。水已经哗哗地流入浴缸,彼得将她放下,她又朝门口冲去。彼得用膝盖挡住了门,她开始朝他挥舞拳头。
他和朱莉发现,碰到这种时候,临阵换将往往很管用。朱莉这时出现在走廊尽头,头发上插着一支铅笔。她默默地站到彼得身边。
“梅尔不想洗澡。”他说。
也许是女孩子的那点事,他后知后觉地想道。
“怎么了,马特?”他见儿子从走廊那头慢吞吞地走过来就问道。
“她疯了吧。”马特告诉他。
“你以前也会闹脾气,”彼得说,“也是这样。”
“好吧,”马特嘲笑道,“请接受我的道歉。”
和普通兄妹一样。


显然,他们所有人都冷不防身陷未来的生活。但法律仍然很混乱。条款东拼西凑,全合成人明确的法律地位因州而异;有一回,全家人一起开车去优胜美地,在度假牧场上待了一周,后来又徒步进入黄石公园,观察喷硫磺的巨大间歇泉,一路上不得不随身带着好几份文件——有原始编码的亲子关系证明——免得被密歇根和各个目的地之间的州巡警拦下来。
对彼得及其妻子,还有他们的朋友来说,这一切自然显得复杂而有趣,对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因为这些现象出现时,他们已经到了能从中获得新奇感或陌生感的年龄。但他们也意识到,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吸引人,即便可以,原因也不尽相同,甚至他们自己也不例外。合成人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了近三十年,不过,直到独生子女法实施后,他们才真正变得普遍起来。
超人存在的时间几乎一样长,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有意思。
彼得的妻子向来温柔、好奇又有耐心,喜欢思考这些事,喜欢跟朋友们讨论。她坚持要面对面交流,而不是使用古基【“古基”的原文为cookie,原指某些网站为了辨别用户身份而储存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加密数据,在本小说里指移植在人类(包括自然人和合成人)体内、用于远程意识交流的设备。】,这就意味着大家周六会过来,比方说,在前廊上享用一顿有鸡蛋、百吉饼和含羞草鸡尾酒【一种由冰镇橙汁和香槟酒或其他起泡酒混合而成的鸡尾酒。】的早午餐。这是老派的聚会,在他们绝对老派的门廊上,在他们绝对老派的社区里举办:这里,家家户户都凑份子在电话杆上安装了安全楔子【“安全楔子”的原文为piton,原指登山攀岩用的钢锥或岩钉,可以敲入岩石的裂缝或孔洞中,用来固定绳索或其他攀登装备。作者用这个词指称可以发出及接收信号的电子系统或安保装置。这里译为“安全楔子”。】,防止超人入侵。当地人步行去大学校园的路上免不了要经过彼得家的房子,夫妇俩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过路人,结果,他们的朋友就像溪流里的树枝一样汇聚在这里,在葡萄酒和薄脆饼干的漩涡中停留好一阵子,与此同时,孩子们在草坪上玩威浮球【一种改良过的棒球。】,姑娘们安坐在紫丁香树旁的阴凉处尽情聊天。自成一格的老式做派,甚至有点刻意而为,但彼得猜想大家之所以被他们吸引,就是因为这种风格。不过,这其实并非什么风格,只是他和朱莉喜欢的生活方式罢了。
朋友间最近谈论的问题是孩子们——不管是自然人,还是合成人——终将经历的性生活。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与另一类型的人约会,你会作何感想?



“我不介意他们约会,”深陷在柳条椅中的胖杰里直言道,“结婚就不好说了。”
“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嗯,我知道有人这么做,卡尔,我只是不太——”不太什么?艾玛皱了皱鼻子,又拿起了她的杯子。
杰里说:“问题在于性。”
麦克斯夸张又滑稽地放下手里的香槟酒杯。“好吧,我做过。”
“做过什么?”
麦克斯抬起下巴说道:“我——跟合成人——上过床。”
“嗯,你那些事我们都知道,麦克斯。”
“跟全合成人,还是跟半合成人?”杰里坚持问道。
麦克斯说:“半合成人。”
“哦,好吧,谁没有过呢?”
“我没有!”艾玛声音婉转地说道,随即满脸红晕,从椅子上坐直,伸手去拿杯子,“只是声明一下。”
麦克斯说:“愿意承认的人里面,有百分之六十四做过。”
杰里说:“好吧,但大多数对象都不是全合成人,对吧,他们年纪还不够大。克里斯·柯普现在多大了?”
“我想他刚满二十八岁。”朱莉说。
“他五月十一号满二十八岁了。”麦克斯查了一下克里斯·柯普的古基后说道。
“这么说,最年长的全合成人今年二十八岁,可是,只有大约一百个全合成人过了……呃……二十五岁?情况不大一样。”
“在跟半合成人上过床的那百分之六十四里,我也算一个,”麦克斯宣布,“所有参与者都收获多多。”
“还有我。”托妮咧嘴笑了。
“那也就是你们两个,我们这儿有多少人?”威尔数了数,“九个。百分之二十二。”
“我们这里有一些人不肯开口。”麦克斯说道。
“举手!”马丁坚决要求道,浓眉拧成一团,“举手示意。”
“还是真心话大冒险吧。”托妮表示反对,却举起了手。“快点,你们这些家伙,”她笑着说,“别让我一个人举手。”
“我有过一次,只有一次。”朱莉说。
“对我们的朱莉来说,一次就够多了。”托妮体贴地说道。
但朱莉心里有某种复杂的情绪在升腾。彼得知道那是什么,先笑了起来。据他所知,朱莉从没和别人说过那件事。
“其实,”朱莉脸红了,“他是个超人。”
桌子周围响起一阵喧闹声。笑声,惊叫声。瞟向彼得的目光。他扬起眉毛,耸了耸肩,从桌上拿起酒杯。
“噢,我的老天,”托妮喘着气说,“我们得听听这个故事。”
“那是在你们结婚之前吗?”
“之前,”朱莉说,“当然了。我是说,我知道自己不该那么放肆,那么疯狂。”她摸了摸衣服上的第一颗纽扣。“可是……”
“什么时候?在哪里?”托妮的手用力地按在朱莉的大腿上,“每个细节我们都要听到。”
“算了!”朱莉笑了起来。
当然,彼得很早以前就听过这个故事。为什么她现在要告诉大家?
她偷偷地向彼得投去一个轻佻、畏缩的眼神。
“她可体贴了。”彼得说,“你们知道吗?但凡有比床上高下的时候,她都不会向我提起那段经历。”
他的妻子又笑了起来,对他满是感激。“我想说的不是那个!”她大声说道,“我想说,你们知道的,我们的孩子将会一起长大,他们会觉得这很稀松平常,就像我们和——不管什么——一起长大一样。”
“像和古基一起长大。”彼得说道。
“像和古基一起长大。”朱莉又笑了,“古基对我们的父母来说,是个问题。我是说,对我们来说,也差不多,但又不完全一样。我只是觉得要意识到什么是新问题,什么不是,我只是觉得——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做出选择是件好事。”
“这可不地道,”托妮抱怨道,“你不能刚说你和超人上过床,就转移话题。”
但朱莉只是撅起嘴巴——娇俏中透着喜感——一言不发。
一群孩子尖叫着从门廊上狂奔而过。


艾玛主动说道:“好啦,我来帮你解围一下,说到古基,我妈现在还在抱怨呢。她说,我怎样才能把它关掉?我就说,妈,你不该把它关掉,一直开着才对。”
“你妈就喜欢抱怨。”威尔说。
“我的爸妈还没有古基,”朱莉说,“我是说,你们知道的,他们有点像嬉皮士。”
“有其母必有其女。”麦克斯暗示道。
“好吧!”朱莉又红了脸。她真好看,金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副欣喜又窘迫的样子。“怎么说呢,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仪器,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活得好好的。我妈还有一部真正的手机呢。有时候她还会给我发短信。”
“这就是我想说的。对吧?只是代沟而已。最终,合成人和自然人的问题只会……变得……再正常不过。”
“已经够正常的了。”托妮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坚定。她已经两次伸手去取香槟。托妮和麦克斯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合成人,都是男孩。“我是说,看看我们!有多少——”她伸出长长的指甲数了数,“光是这桌就有七个。”
不过,事情并不正常。他们都明白。
现在还不正常。
“我不敢相信你妈还有电话。”威尔说。
“我几乎从未在古基上感应到你,”托妮责备道,“你可真安静啊。”
“对啊,我很少用古基与外界交流。只是用来了解孩子们的行踪。哪怕这样,它——我也还是把它调得很低。”
大家都在思考这句话的意思,桌上又是一股暗潮涌动。当然,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把古基调至低档,几乎所有信息都滤除了,但大家见到彼得妻子那温柔的、略带窘迫的坦率态度,就明白了她说的是真心话。的确是所言不虚。也是彼得的真心话。两口子也许显得有点洋洋自得。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态度。彼得和朱莉对仪器做了设置,只有当恐惧或悲伤的读数超过一定范围,或是疼痛的程度突破某个阈值时,古基才会发出警报,这时,只要他们想查看孩子的位置,就可以用眼睛解锁地图。但仅此而已。没有用人工智能读取孩子的想法,没有预判措施。而且,通信只是从孩子到父母单向进行的。孩子的头脑中不会响起父亲的声音,或是母亲的细语关怀。
托妮说:“要是我也能这样做就好了。我是说,你们太酷了,呃,你们真是正统。正统得不行啊。但我就是……无法自拔。比如现在,我正在接收信息呢。哦,我的天啊,哦,我的天啊!”
她睁大眼睛,他们都向前倾了倾身子。
托妮发出一阵难以置信的狂笑。“哦,我的天啊。珍妮·拉森刚刚看到哈里·休伊特在停车场吻了一个干瘦的婊子!”
消息传出后,这群人骚动起来。彼得朝桌子另一端的妻子看去,她也正回望着他。一脸的无可奈何。她把酒杯放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咔嚓声,然后也一脸欢快地开始聊起来。


大家都怀疑哈里·休伊特有外遇,但一直没人能一睹那个女孩的真面目。她叫辛迪·西蒙斯。在图数据库【原文为gremlin,这里应该是指心灵感应设备上存储图像的数据库。】里,她看起来年轻、瘦削,但绝不是个美女(牙太大,头太窄,眉毛很细且局促)。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哈里的妻子特蕾莎非常漂亮。大家一开始以为,也许是特蕾莎不和哈里上床了,或是哈里想找个年轻苗条的小东西来把玩,或是机会刚好出现了,他没拒绝。有话题可以谈论,大家都很高兴。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特蕾莎·休伊特向所有人公开了她的信息平台,但没有告诉哈里,众人隐身围观了一会儿,结果发现休伊特两口子的确已经两年没过性生活了,原因是哈里两次从某国回来后,没有使用身体净化器,又不肯接受服药测试【特蕾莎很可能有洁癖,怀疑哈里在国外与人有染,不肯与他行房事。】,因为接受测试意味着有罪推定。然后大家开始觉得不安,真心为哈里感到难过,纷纷离开了特蕾莎的信息平台,发出各种表示不适和内疚的声音,还转向了别的话题,比如学校戏剧的排演进度等。几天后,特蕾莎上线向所有人和哈里道歉,并宣布他们将去接受婚姻咨询。
“真是荒唐。”朱莉一边揉着披萨面团,一边说道。
彼得基本上是带着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关注这件事的;他不喜欢哈里,也不想和特蕾莎(或辛迪·西蒙斯)上床,所以,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是这两口子将会当众作践彼此到何种程度。他寻思,哪怕如此,他也还是有点下作了。“是啊,”他说,“事情过后大家还能做朋友,真是难得。”
“没错。不过,大多数人行事还是很得体的。”
“你说的也没错,”他指出来,“但话说回来,所有人都有缄口不言的时候。”
“嗯,是的。”他的妻子有点脸红。
“好吧,不是每个人都有。”
“确实。你希望每个人都会有。”她微笑着说,“有些人,我只是——”她举起了两只沾满面粉的手,马特正拿着一个纸飞机穿过厨房。
“对,就算出轨,也是哈里自己的事。”
“是啊。”她叹了口气。
彼得通过古基不出声地问她:“你为什么提到超人?”
她笑了笑,微微耸了耸肩,说道:“我想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从未听过的事情,而且是当面说给他们听。”
他没有搭腔,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呢?”一分钟后,他提议道,“把古基关掉。”
“把古基关掉,然后呢?”
“我不知道,”他说,心中一阵激动,“互相打电话。”
她大笑着从厨房台面上抬起头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手机在哪里,彼得。”
“在我这儿,”他回答道,有点喘不上气,“在我的书桌里。还有你妈妈的手机。”
“我们可以发短信!”
“当然了。”他说。
朱莉若有所思地又揉了几下披萨面团。“你的意思是——彻底停下来吗?大家会发现的。”
他的体内突然涌起一股情欲。“我们彻底停下来,如何?就你和我,没别人。”
他的妻子眨了眨眼,脸上越发燥热起来。她咬着嘴唇,睁大眼睛看向彼得。
人们动辄斥之为蠢念头。
但彼得并不觉得。朱莉也一样。
停下来将意味着与众不同——不只是一丁点不同,也不是打擦边球,而是实实在在的不一样。切断心灵感应,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过。但其实并非不可想象。这与他们父母曾有过的梦想——搬到乡下去养一群走地鸡或别的什么东西——如出一辙。
人们动辄斥之为幻想。
然而,突然之间,它就不再是幻想了。


今年梅丽莎的老师是一位叫哈特利太太的女士——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神情充满忧虑,嗓音高亢而颤抖,在彼得听来似乎随时会哭出声来。但梅丽莎是她的忠粉。她趴在游戏室的矮桌边上,用铅笔给哈特利太太写长长的信:“您不光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您是很多人的朋友,因为您爱他们。您是公正的人,因为您总是公平对待别人。”
梅丽莎就读的小学有些年头,很温馨,离家只有两个街区远,家长会在一个有着高高天花板的房间里举行。“伯克哈特先生和太太,”哈特利太太在会上微笑着说,“你们的女儿真讨人喜欢。”
听到这话总是让人开心。没错,彼得听到“女儿”和“你们的”时,会感到一丝激动不安,但在场的两方都明白这是规范用语,都很清楚规范用语必须妥当使用。不过,哈特利太太的欣喜倒是明显发自真心的。“她很聪明,这点你们当然知道,她也很有社会意识和觉察力,能教她,我很高兴。”
“谢谢!”朱莉笑道,“她是个好孩子。”
“不少孩子都很崇拜她,”哈特利太太接着说,“她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会保护自己和他人。”
这话显然意有所指。彼得说:“说实话,她有时候会有点冲,对不对?她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
哈特利太太朝他们不温不火地笑了一下。“那么,你们在古基上听到了什么?”
夫妻俩互看了一眼。朱莉先开口:“我们把它调得很低。”
哈特利太太彬彬有礼地看着他们。
“我们想让她有自己的空间。”彼得说。
哈特利太太说:“噢。”
“就是说,”朱莉说,“我们能大致感应到她在做什么,但实际上并没有——并没有读取她的信息。”
“我明白了。”哈特利太太对着她的平板电脑说,“没关系。那是你们的选择。”
“我是说,只要和她在一起,我们就有感应,”彼得的妻子说,“这个孩子的感情非常……有点……强烈,是吧?就像彼得说的,她有时候挺冲的。”
“公平对她来说很重要。”哈特利太太提到。
“没错,”朱莉点了点头,“这是她最近关心的事情。”
哈特利太太没搭话,考虑着接下来要说什么。此刻,她显然比一开始看起来更年长,更坚定,更能掌控局面,这一点你从她毛躁的头发和低圆领连衣裙上可看不出来。“嗯,我想这是我们在消除人种隔离的课堂环境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有些问题会时不时冒出来,伤害到双方的感情。你们的女儿——她真的很棒。就像我说的,她非常护着朋友。”哈特利太太现在开始直面这对夫妇,“她的好朋友大多数……都是……呃……合成人。这种情况可能是目前合成人的数量造成的。班上大多数女生刚好都是合成人,而梅丽莎的大多数朋友都在这个群体里——不同群体的人数失衡就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情况。梅丽莎很了不起,她觉得需要提及某个问题时,从不怕大声说出来。”
“梅丽莎就是这样。”彼得说。
“比如,我们这里有个男孩,生物学意义上的孩子,名叫迪米特里。你们也许认识他。”
“是的。”朱莉说。
“呃,迪米特里,我跟你们说实话,不让人省心。但他只是个七岁的孩子,呃,不用说,他们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喜欢写歌,歌词内容尽是关于某某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东西。他可能从家里了解了一些信息,当然,从哪里知道的并不重要,但不得不说,这样做并不总是很友善。他上周写的歌与梅丽莎的朋友琼妮有关。她是合成人。歌词是这样的:‘琼妮是假货,琼妮是蠢货。’”
“不错。”彼得说。
哈特利太太苦笑了一下。“这不是他最糟糕的歌。”
“你知道这件事吗?”朱莉问。
“我吗?不知道。”
“好吧,”她说,“我也不知道。”


哈特利太太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们。“后来,梅丽莎就叫迪米特里别唱了。可以想见,他唱得更起劲了。梅丽莎非常、非常有礼貌。她说了一番话——我没听到他们全部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你这样做伤害了我的感情,也伤害了琼妮的感情,我们生来是这样的人,你生来是那样的人,但我们都是人。’”
这是可以接受的说法。带着梅丽莎的那种自觉和坚定。
“然后呢?”彼得问。
“呃,没有奏效。我看出来梅丽莎开始生气了。她停了几分钟,但我知道事情还没完。我喜欢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尽量如此。”哈特利太太舔了舔嘴唇,“他们当时在软质材料铺装的角落里活动,梅丽莎走到他跟前,一脸平静和严肃地说:‘嗨,你以后肯定会死,我们不会。’”
朱莉倒吸了一口凉气。“哦,天啊。”
彼得干巴巴地笑了一声。“呃,”他说,“好吧。这话倒是新鲜。”
朱莉说:“要是我们早点知道就好了。”
“我以为你们已经知道了,”哈特利太太说,“我以为这句话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
彼得的妻子领会了哈特利太太的意思。“我想我们应该坦诚地告诉您,我们读取了多少信息。是我们做得不对。”她说。
“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彼得解释道。
“没事的,”哈特利太太镇定自若地说道,“很高兴我们打开沟通的线路了。有些家长甚至喜欢时不时地查看我的状况,这一点我是允许的。”
但彼得意识到,自己绝不会那么做。永远不会。
“就像我说的,”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梅丽莎有时候有点冲。”
“嗯,她非常关注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哈特利太太合上平板电脑回答道,“我说过了,你们的女儿很聪明,也很敏锐。她什么都明白。你们知道吗?”这时候老师笑了:“在这方面,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女儿。”
有个问题在脑海中盘旋。哈特利太太的女儿是合成人,还是自然人?他们三人都感应到这个问题在眼前盘旋,但谁也没有说出来,接着它就慢慢地,极其缓慢地飘走了。因为它无关紧要。用套话来说,这样的问题无关紧要。
…………


迈克尔·拜厄斯(Michael Byers,1969—),美国作家,本科毕业于欧柏林学院,从密歇根大学获得创意硕士学位,目前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最为批评界称道的作品是199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善意之岸》,获得苏·考夫曼新人奖。此外,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命还长着》(2003)、《帕西瓦尔的行星》(2010)。《手足之争》(Sibling Rivalry)最早发表于半年刊《丘吉尔夫人的玫瑰花蕾手镯》(Lady Churchills Rosebud Wristlet,2019年,总第40期),后来收录于《2020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虚构的世界里,人工智能和人脑芯片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作者以此为社会背景,围绕自然人与仿造人的关系,展示、隐射或反思了一系列关乎人类或人性的现实问题,如有关自我与他者、正常与反常的刻板假设,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界限,人之本质与自由意志的关系,技术对人类感知世界方式的奴役等。
上文节选原文二分之一,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可以进入微店,购买纸刊阅读全文。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5期,策划及责任编辑:叶丽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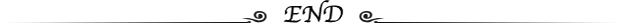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