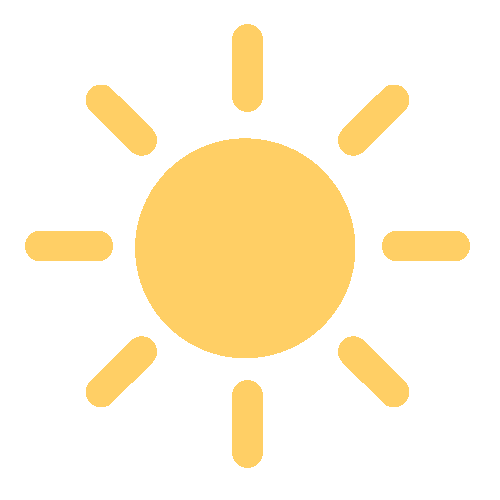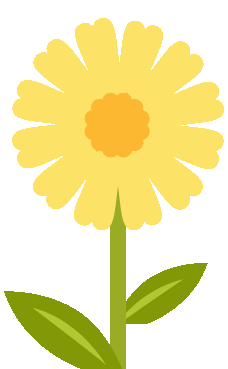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张新月:拔去名为孤独的刺——读《浮华世界》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作者借具象的房屋,不仅赋予了作品脉络清晰的主线以勾连移民生活中形色各异的趣事,更形象地展现出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情形。主人公两手空空地离开美国,代表“死神的刺”的最终拔去。而这根刺的产生,本就源于美国文化对初来乍到的主人公的冲击。作者不无悲观地暗示,或许对移民而言,这根刺将留存心中,只有对故土的回望能冲淡其中的孤独怅惘。


——读《浮华世界》有感
张新月
“您跨出一步——从地面上的这个幽暗、狭窄而又低矮的小盒子里钻出去,就来到一个半悬的露台上,露台比地面略微高出一点。左右两侧的墙壁——从地板到高高的天花板——全都是玻璃的,一直延伸到满眼绿色的花园,一只只红色的小鸟在花园里飞来飞去,绿植在轻轻地摇曳,盘绕在树上,绽放出花朵。”
在托尔斯泰娅笔下,如此荒诞而奇异的凉台是通往“浮华世界”的入口,惜其修葺未完,只能搁浅在沉闷杂乱的处所。大卫卖给“我”(小说的主人公和叙述者)的房屋简陋、阴暗、摇摇欲坠:厨房中污损的油毡,破旧的木地板,漏水的屋顶,无不展现出生活拮据的大卫无力整修房屋。然而,春日花园又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近乎野蛮的明艳热烈。“我”作为移居美国的俄罗斯人,对这座房屋的感受正如自己对陌生美国的感受。一九九二年,“我”离开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土地——大卫的房屋,安稳生活的基石——让“我”在美国重拾了安全感。沐浴绿灯柔和光芒下,“我”的声音温和,不无雀跃地提及西海岸盛放的鲜花,奇妙的折叠梯,乃至女主人遗留下的旧物。小说开篇行板般和缓松快的叙述中,唯一的不和谐音是时而闪露的戏谑口吻——体现于叙述者对过往事件的重新解读——冲淡了对异国稍显盲目的热望。



房屋的购买、整理直至出售,作为小说的主线贯穿全文。穿插其中的是“我”与邻居的相处细节,与学生的斗智斗勇,与建筑工人的拉锯战。这些生活碎片与“我”对于房屋的印象暗合,暗示着美国梦的逐渐幻灭。在与邻居的闲谈中,“我”受到了文化冲击——在被称作蓝莓的越橘与屠宰羔羊前,陌生的国度展露出野蛮的笑意。自此,戏谑的叙述口吻愈加明显。资质平庸而自由散漫的学生令“我”失望。最初“我”并不愿“在天平和测锤上动手脚”,不愿轻饶不预习的学生。然而学生的低评分迫使“我”改变策略,自嘲为了不离开来之不易的房屋,“我”“可不能承认自己为了博得学生的喜爱而趴在地上汪汪直叫”。
通往“浮华世界”的入口——凉台——在冬日里,是“我”休息的处所。冬日里,从家到学校,车程四小时,睡眠不足——幸福对“我”而言,如此遥远而不可捉摸。咖啡、薄荷烟、俄罗斯摇滚乐,以及“锻炼大脑思考能力”的量子力学讲义磁带,都是为漫长寂寞的通勤准备——“我”恐惧寂寞和孤独,独自咀嚼消化着冰冷的回忆。但最终,啃咬出生路的勇气战胜了恐惧。然而,对于大卫和诺拉遗存物的态度转变,暗示着“我”正除下玫瑰色眼镜:从不忍心弃置诺拉留下的破烂衣裳和贺卡,到直白地称呼其为“破烂玩意儿”。主人公不再一味美化异国生活,以旁观者的身份欣赏,而是成为参与者,或咒骂或嘲弄,正视生活本身。



正视生活后,“我”却愈发珍视乏味生活中某些打动人心的时刻:和有天赋的学生交流,读他们的小说,乃至发觉学生借口中的奇趣。“我”重修了凉台,暗示与美国浮华世界的联系有日渐加强的势头。然而在重修的过程中,装修工人、学校的工作都令“我”感到疲倦。浮华世界对于“我”而言,终究并非故乡。寻找房客后,“我”最终把房子租给了尼尔森——有洁癖的瘦弱年轻人,有孩童般的双手。“我”私藏了尼尔森的押金——“我”发觉自己已经习惯于移动天平和测锤,在与故乡截然不同的浮华世界中迷失。“我”随着心意给学生打分,慷慨地对待用功的学生,而对行为恶劣的学生绝不姑息。与“我”对美国留恋的日渐淡薄、同浮华世界的心灵距离愈发遥远暗合,房屋——通往浮华世界的入口——也惨遭破坏。尼尔森如蠕虫般损毁房屋,被“我”视为对自身的惩罚。售卖房屋不仅是“我”“拔掉心上的刺”后离开美国的前提,更是某种隐喻。
小说中,房屋不仅是叙述、描写的主要对象,更是主人公自身际遇的暗示。房屋及凉台的情况,自始至终与主人公和美国浮华世界的关系相契合。作者借具象的房屋,不仅赋予了作品脉络清晰的主线以勾连移民生活中形色各异的趣事,更形象地展现出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情形。主人公两手空空地离开美国,代表“死神的刺”的最终拔去。而这根刺的产生,本就源于美国文化对初来乍到的主人公的冲击。作者不无悲观地暗示,或许对移民而言,这根刺将留存心中,只有对故土的回望能冲淡其中的孤独怅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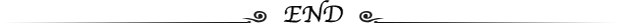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