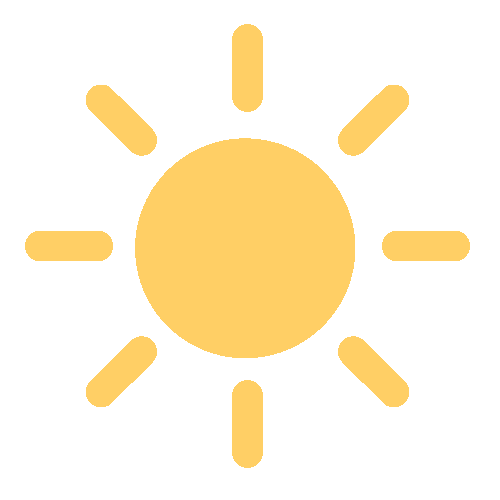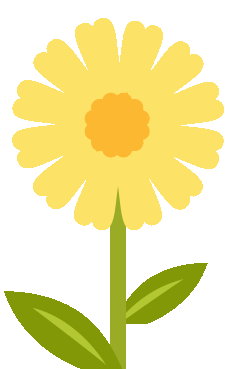移民小辑来稿 | 卢奕帆:“被看”者的看见——读《如幽灵一般》《职业面孔》《冲绳依旧在》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有关“看见”的故事应是一座灯塔,引领良知者自我觉醒、迷惘者获得关爱:百年前康拉德的小说中,作为“异乡人”的欧洲白人,透过非洲大陆的黑暗丛林,反观自己胸腔内“黑暗的心”;后殖民时代的今天,这些“被看”者的言说,若能获得更多理解,便是“看见”的胜利。
“被看”者的看见
——读《如幽灵一般》《职业面孔》《冲绳依旧在》
卢奕帆
“幽灵”可隐喻一种特殊的状态:穿梭于真实与虚幻之间,居无定所,流无定质。所谓“真实”,是指那些被拥有言说权力者“看见”之后,才具备存在意义的真实。当“被看”者由被动转为主动,也获得了言说自身的契机,他们又将如何讲述自己的“看见”?伴随着双方“看”与“被看”的纠缠,真与幻的界限也在迷蒙的心境下罩上一层雾色——“被看”者的“看见”,令人心安吗?


《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中“边境上的幽灵:移民经历书写专辑”,就是这样一群特殊群体的自画像。仿佛《旧约·创世记》中的神谕,“你必流离飘荡在大地上”,历史重担之下,异乡人身上种族、地域的烙印,宛如一副无可脱逃的原罪之枷,使得被主流文化话语所放逐的他们,在荒原上行吟、流浪。不过,“幽灵”作为“被看”的对象,并不等同于加缪笔下抽离的“局外人”,在与现实的磋磨之中,他们既能深入体验社会的游戏规则、乃至成为规则本身必要的一环,又因反思的惯习,而拥有超越于芸芸众生的清醒与冷峻。文学叙事,释放了这些长久以来沉积的经验、压抑的情志,赐予“幽灵”一条求索自我之路,其中塞内加尔作家布巴卡尔·鲍里斯·迪奥普的《如幽灵一般》、法图·迪奥姆的《职业面孔》以及秘鲁作家奥古斯托·比嘉·大城的《冲绳依旧在》,就记述了“被看”者三种不同的“看见”。


《如幽灵一般》塑造了一位潜伏于暗处的观察者。清洁工的设定,令主人公每日穿梭在城市街巷之间,他感官的触手便有很多机会深入常人所不能及的暗角。种族与职业为他带来的卑下处境,本来是“被看”的结果,但他也因此得以避开众人目光,在无限广大、未经开发的天地之间,重新获得了无限充盈的自由——小说中,当主人公站上护栏、俯视那蝼蚁般的真正囚徒之时,他是幸运的。自认为高出一等、实则丧失思考能力的人们奔波在流水线上,就像批量生产的商品,精致而空洞、妥帖而乏味,磨平了鲜活的棱角。在一切都被标准化的钢筋混凝土中,人类理性的过剩,恰恰意味着非理性的价值空虚;而“我”看见的“最后一块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却是布满酒瓶碎片与黑斑的荒地——破败,而非整洁与文明,触发了“我”的原始本能:关于童年和北非故乡的记忆。就“看见”的独立性而言,“我”无疑比跌在富贵温柔乡里的“高等文明人”更接近生命的智慧与人性的本真。
然而,这一“看见”仅主宰着内心的沉思,回到赖以生存的现实中,“我”就只得退居被动地位。主人公视角下众多的外物,均被赋予了强大势能,从四面八方对“我”重重施压:迎面扑来的清冷空气,有如“生活给我的耳光”;发动机的轰鸣,令城市像一头吃人的野兽;地下仿佛有死人复活,侵吞着活人的空间……“看见”的视野中,洇开一种漫不经心的窒息感,可爱的房屋内有没有诗人“那又如何”,赶火车的男孩“不关我的事”。“你在扫地。他们在杀人。”两个平行而孤立的句子,质感冰冷,似乎“扫地”与“杀人”的行为悄无声息溜过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处角落,在许多地方同时进行着,彼此却又毫不相干。但“幽灵”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不止于此。存在性体验的割裂感背后,又隐藏着一种纠结的、难以启齿却不言自明的依赖,这是一份轻飘飘的沉重、一份简单明了的残酷:“你不喜欢他们的城市,却不得不承认——今天早上,热面包和咖啡很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看见”姿态,在基本的物质生存面前,压根不堪一击。


如果“被看”者始终彷徨于无地,他们由“看见”而引发的呐喊,也只能沉埋于阴面。那么,当“被看”者选择直面风暴,又将如何呢?转向阳面的《职业面孔》,从明快的叙事节奏,到对不公命运的坦率议论,再到“妓女样的夏尔·戴高乐机场”“阴茎样的大教堂”等反叛色彩鲜明的象喻,主人公的“看见”无不充斥着积极的抗争意识。她所背负的“职业面孔”,是黑人与女性的双重“面孔”。作者似乎也抓住了读者对“弱势者”的心理预期,展现主人公内心的控诉,并与有意作出的柔弱、妥协构成不和谐感,直到临近结尾才以戏剧性的反转揭露主人公的身份:受过高等教育、斗争愿望强烈的知识分子,而非逆来顺受、毫无反抗能力的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本是关于主体存在性的判断,主人公纠正了杜邦女士对这句名言的错误记忆,暗示着“被看”者夺取存在价值的胜利,但就在主人公通过才学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工资、颠覆了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开启了平静的新生活后,一切似乎皆大欢喜,小说却在细思恐极处戛然而止:杜邦先生对她萌生了性幻想。故事是结束了,厄运也许刚刚开始——在种族与性别的双重“被看”之下,个人才能究竟是换来敬重的名片,还是进一步招来恶趣味凝视的祸患?


不同于《如幽灵一般》的潜伏感,《职业面孔》以夹带着辛辣和戏谑的平视姿态,用洞彻一切的从容,将苦涩融进荒诞;相同的是,“被看”者虽已觉醒、能够勇敢言说“看见”,其处境依然逼仄。两位塞内加尔作家提醒我们,移民困境与种族歧视,往往与更复杂的社会问题相结合:人的异化、女性权利、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但即便现实生冷如铜墙铁壁,文学也总能潜入多变的经验、捕捉到一些会呼吸的孔隙。《冲绳依旧在》就尝试挖掘“幽灵”群体在“看见”之时触碰真与幻的别样方式,借另一个世界的魔法化解困境。如果将三篇小说的“看见”视作“幽灵”探索自身的三个阶段,《冲绳依旧在》无疑是疲惫的现世之旅后的一次充满诗意的灵魂复归。日本战败的创伤,让现实中的“家”遭到消解,流亡秘鲁的日本难民,被抛掷到一条指向迷茫与未知的单程线上;而移民者向意识世界的出走,就以“家”为归宿,重新完成了旅途的闭环。
宫城奶奶的“看见”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与之相契的,是小说充满流动感的语言艺术。关于“家”的意识流,由蒙太奇式的色彩、物象拼接而成;关于死亡的神秘启示,游走在梦境与直觉的光影之间。当宫城奶奶面对少年挚友,徐徐打开她黄金时代的回忆录,压抑几十年的心力在短暂的会面中全部绽放,樱花般刹那而烂漫的凋零、日式“物哀”的轻盈之美,与机械沉重的撞击声,构成了一曲奇异的交响;但与此同时,文字柔软的流体也终止了生命,潮水撞上了坚硬的礁石,似在唤醒读者:幻境终究是易碎的。作为世俗意义上的越轨者,与现实的距离感并没有为宫城奶奶带来“旁观者清”的突破,反而让她在黏稠的感性记忆中越陷越深,走向幻灭。



问题悬而未决,最初的求索似乎依旧没有答案。但若将审判的目光限定于“被看”者身上,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的苛求?共同经验的阙如,筑成了自我与他者的天然畛域,投射于文化心理层面,就是关于“异乡人”的叙事。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中说:“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 随着人口流动大方向的扭转,“异乡人”由掌握主动权、居于优势地位的殖民者,变为弱势的、“被看”的移民者:移民者对“家”本能的流连,令他们无法迅速融入新的集体;而无知的当地人不经意间抛出无数个琐碎的伤害,又聚成一座压垮人与人之间关系纽带的厚障壁。有关“看见”的故事应是一座灯塔,引领良知者自我觉醒、迷惘者获得关爱:百年前康拉德的小说中,作为“异乡人”的欧洲白人,透过非洲大陆的黑暗丛林,反观自己胸腔内“黑暗的心”;后殖民时代的今天,这些“被看”者的言说,若能获得更多理解,便是“看见”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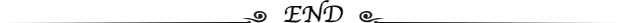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