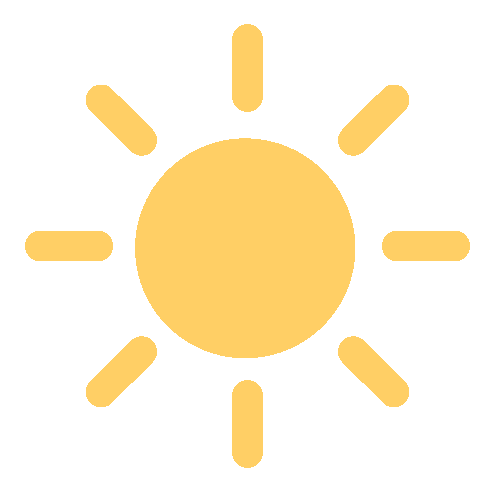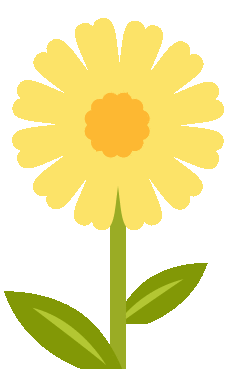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威•莫迪森【南非】:乞讨的尊严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虽然我要得到补偿,但是此刻我衣着光鲜,做乞丐日久年深,我深知人们是不会施舍钱财给比自己穿得还好的乞丐。人们救济乞丐,是想要在施舍与被施舍中建立等级间的优越感,就像我曾说的那样:做乞丐,我才是行家。

乞讨的尊严
威廉·莫迪森作 高俊鹏 郭继东译
法官大人从文件上抬起眼看向我,目光像匕首一样直直刺入我的心脏。他蓝色眼眸中流转的目光锋利尖锐,令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像布吉摇滚重击的低音。
“你们真让我恶心……恶心极了。这条街上混的本地乞丐,没有哪一个我不了如指掌,”法官大人说道,“你们其中有的还是我看着长大的。没有哪一个我不是多次尽力帮忙走上正路。尽管我是出于无奈把有些人丢进监狱,不过他们狗改不了吃屎……净想着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


法官大人言辞刻薄犀利,好像要把我们关上几个礼拜。我唯一不甘的是理查德·萨鲁鲁贝利,他不得不和我一样熬着这条贱命。倘若法官大人知道理查德与我们这些寄生虫并非同类,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饱受剥削的乞丐就好了。一场车祸后,萨鲁鲁贝利腿脚跛了。打那时起,他的父母就开始利用他的跛脚谋利。他们靠萨鲁鲁贝利乞讨来维持生计,也从未对他施舍过哪怕一丝半缕的爱与呵护。他父母待他牲畜不如,要他自生自灭。理查德二十一岁了,拖着一条跛腿,卑怜孱弱的脸上布满了全世界的哀伤。瞧他那样儿,比我丈母娘还苍老许多。
“你们这群乞丐让我很难做。尽管还没把你们改造好,不过我总是认为你们有必要改过自新……或者说,一个新开始。但我也确信,过不了几天,你们还得回来。”
法官大人语气有点缓和,我的自由触手可及。是我来表演一番的时候了。无非是些追悔莫及的神情,加之巧言辞令的小把戏。我清了清喉咙,顺便挤出一两滴眼泪。
“我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们乞丐中的大部分遭受家人排斥,无奈乞讨;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对待我们,”说着,我抹了抹眼泪。“别人施舍我们钱财,只不过是让我们俯身仰视,从来不鼓励我们自食其力。他们宁愿施舍救济也不愿意雇我们工作。这些人只是同情……可是我们不需要同情,只是想要一份和普通人一样的工作,证明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
法庭里鸦雀无声,我知道我骗过了所有人……他们此刻心生羞愧,深感自责。法官大人沉默无语,活像坐在灵堂中的送葬人。我能读懂法庭中每个人神情里的悔憾;或许最入戏的那个其实是我自己。我真是演技卓绝啊……这正是所有电影导演梦寐以求的吧!已经说得够多了……多到足够放我们出去,见好就收吧。
“你叫纳撒尼尔,你已经考上了大学,对不对?”法官大人又翻了一页记录,那是非欧洲事务部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的。“嗯,是你,纳撒尼尔·莫科歌梅尔,事务部建议你学些实实在在的手艺。明早你就去事务部大楼十四号房间报到。”



我从来也不指望能得到这些;这么一来,我的绝妙计划可就破碎了。我靠乞讨可以搞到普通人工资两倍多的钱,为什么要去工作?要是连我这个乞丐都去工作,还要那些牛工【原文中用“horses”一词,指“家伙们”,含贬义、戏谑意味,故在文中译为“牛工”,意指“打工仔”】干什么?我不去工作,这是乞丐的职业道德,我必须坚守乞讨的尊严。
“至于你,理查德·萨鲁鲁贝利,这次我就放过你,不过记着我的话:要是胆敢再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把你搞到班图难民营里。现在,从这儿滚出去,你们两个一起。”
如果法官大人看见我离开法庭时咧着大嘴笑,他一定会把我这个跛子扔进牢房,再故意丢掉钥匙,不放我出去了。不过,他没看见。
虽然万物有常,但出乎意料的结局有时也会有。我的好朋友萨鲁鲁贝利或许就是这世上活得最痛苦悲惨的人儿了。他的问题在于缺乏想象力,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聪慧明智。他似乎总是看到生活的阴暗面,而且骨子里浸着的愚忠,地上难寻,天上难觅。
“终有一天,我得杀了我自己,”萨鲁鲁贝利念叨着。“这样不死不活地耗着,我快活不下去了,生无可恋啊。为什么遭受这一切的偏偏是我?你说,纳撒,为什么啊?”
我答不出来,也不知道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个男人希望听到怎样的回答。恍惚间,我差点说出口:那就发封电报给生你的人,质问他何苦结下这样的孽缘。然而,我还算心地和善,知道这样说可能会狠狠伤了他。
“不知道,”我冒出这句。世事无常,有些事不是我们所能解释的。冥冥天注定,但是尽管如此,失去的时候,也会有所得……至少我这么想……不过,我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些呢?
这是唯一一次我当真挤不出只言片语;我想告诉他,残疾带来的伤害会得到补偿,可我并不能坦然触及此事。我记得,那时我就是被这些补偿逼得离家出走。


父母无法理解我,所以我离家出走了。他们几近让我变得狂躁神经质;然而现在,我猜想也许当时不是我的敏感让他们小心翼翼,做出看似荒谬的举动。他们似乎不敢随意踱步;每个人都呆坐着像是一屋子全是跛子。我像婴孩一样被照顾。什么都是伸手即来,甚至连端一杯水,也不需要我。极度的呵护逐渐让我狂躁……这些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个跛子。很显然他们像是要把食物嚼碎喂我,还要帮我咽下去。这些萎靡消沉的想法终于逼我离开了家。
新的生活向我敞开怀抱。我娶了老婆,养了两个调皮鬼,在潘普方丹【南非城市,滑翔胜地】置办了一处房产,在索菲亚镇也有一间房,还配了一架钢琴。两年来,我乞讨赚了几百英镑。那些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只是现在我依旧发愁,因为我还没讨到足够的钱防老……还要养活两个儿子。
“我的天呐,纳撒尼尔,”萨鲁鲁贝利惊呼,“你疯了吧,你怎么总是完全陶醉在自己的幻想中……待在这里的是我,记得吗?”
和他告别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吃了些东西,我就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事情了。工人们有各种保险,还有工会,联盟的保障,为什么没有乞丐联盟来保护乞丐?那样我就能召集城市里所有乞丐成立一个联合会,起个类似“美国乞丐联盟”的名字,每个乞丐每周得交十先令联盟基金。仅仅在约翰内斯堡就有过百的乞丐,如能说服他们都加入,那么一年赚上两千四百镑不成问题。
绝妙的主意啊……我就是个妙计天才。苍天无眼,有时我深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或许同一个时代里,在爱因斯坦和我中间,只能有一个天才。无论如何,也只能这样喽。
我可以承诺每年给每个乞丐分十英镑红利。这主意妙啊……没有乞丐能拒绝这样好的福利。或许我应该承诺为他们置办一处便宜的房产,估摸着每年为像萨鲁鲁贝利一样窘困潦倒的乞丐买一座房子,配上廉价家具,让他们不用再窝在垃圾堆里遭人漠视。这个计谋十分划算,至少能极大程度帮助乞丐们建立自信。不过只有一人可以得到房产;其他人必须继续等待,直到哪天我忏悔不做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愉快地来到十四号办公室。一个白人,坐在红木大办公桌后,百无聊赖。我自报家门,他径自抽出几张纸写了些什么,之后让我按照纸上的地址跑一趟。
窗外,阵雨淅淅沥沥,越下越猛。出来的时候,我还咒骂着鬼天气。一个穿着华贵的女士朝我款款走来时,我萌生了一个主意。她看起来就是一块唾手可得的移动金块……实际上,我的确瞧见了她镶金的牙。我佯装苦闷,佝腰弯背,丑陋的废腿哆哆嗦嗦。她停了下来望着我,就好像我的残疾是她造成的。
“怎么会弄成这样,可怜见的,你都快冻死了,”她惊声哀叹,“拿着,买点吃的去吧。”
我掂量着手里的钱,是半克朗,我照例念叨着上帝会如何保佑她,又说了许多祝福的话语(但是,就她这身打扮,显然她已拥有够多,无须这些祝福)。
一路上我一直在玩这个小把戏,顺便就到了地方,数了一下,五克朗只多不少。还不错,我和自己说。照这个速度,我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这座城市最富有、最知名的乞丐。想到事务部竟然要求我工作,这想法简直是犯罪,这还是最客气的说法呢。
年假中的一天,我突发奇想想写一本图文并茂的《乞讨宝典》。这本书将会富含感染力和吸引力,勾勒出乞讨生活的蓝图,细腻描绘乞丐的远大前景,展现世界上最古老、最高贵的一份职责简单的职业——乞讨!它会成为所有野心勃勃的乞丐的教科书,不论小乞丐还是老乞丐,都会从我的个人经历和聪明才智中汲取养分。实际上,它会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此类著作的唯一。即使是百万富翁也会在闲余时乞讨,寻求百无聊赖生活中的乐趣。
自然地,我会从描绘这门艺术的历史讲起,从古代,粗陋地把学龄儿童搞残疾,接受乞讨教育,一直到当代,连乞丐也能坐豪车进城……他们有一大笔存款,也缴得起税。我几乎可以预想,未来几个月这本书荣登畅销书榜单时的情形。
我找到了那栋楼。里面人头攒动,我的心跳几乎漏掉一拍。其中很多人,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都像我一样残疾。还有什么能抵得上此刻更美妙自在呢?我可以想见我的计划正在成形。
主管开始介绍打字员的基本职责。我假装感兴趣,还问了许多无关紧要的问题。我表现得极好,足以让主管对我印象深刻。直到五点,我还在敲字,像个机灵的敲字爱好者。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萨鲁鲁贝利乞讨的角落。他依旧待在那里,看起来还是那么痛苦失落。我提议我们一起回家。我诱引他走进我的房间。等到他进来,我像钢琴家鲁宾斯坦一样,开始弹奏一首塔兰台拉舞曲,只是我演奏时用了降A大调。他听得入迷,也许是我琴技了得,也许是我的朋友只喜欢悲伤的曲调。
“你可以拥有一座房子,就像这里,一应俱全。这些都属于你。明明你可以靠自己得到,为什么偏偏要乞求别人。”
“我已经得到帮助,有租来的地方落脚,也能填饱肚子,”他说。“你以为我该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拥有一座房子?我简直不敢奢望。”
“你不要妄自菲薄,你必须做计划,然后像我一样着手去做。我有一个计划,告诉你吧,只要不到一年……听着。”
之后,我向他描述了我的乞丐联盟,尤其强调了这个联盟为乞丐带来的好处。我瞧见萨鲁鲁贝利肥厚的嘴唇下闪闪发亮的牙齿。于是我安排他召集并组织乞丐们举行第一次会议。


昨晚我梦见自己在赛马场。在梦里,我看见翻番儿赢的情形,就像看见我自己残缺的腿一般清晰逼真。我搜刮了房间里的积蓄,动身前往特夫方丹【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赛马场】。到那儿以后,我行动格外小心,留意着警察的一举一动。警察并不在这儿,实际上我也没惊动他们,这样我就放心了。我押二号和七号赛驹一英镑,第一回合赢双倍。下注的时候,有个男人站在我旁边,他双眼似猫头鹰,大而无神,盯着我时目光却明亮愉悦,像个羞涩的新郎。
我十分紧张,六神无主,无法继续观看比赛,于是决定去散散步,瞧瞧风景。突然,我感觉好像有人正在盯着我。我转身,一下子看到了加洛维蒂安女士。这个女人在救济站工作。真是叫人匪夷所思,她总是出现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不用算命,我也知道自己大祸临头。加洛维蒂安臭名昭著,少说也把十二个乞丐丢进过难民营。在她还没叫来身手矫健的警察之前,我就该从这里逃掉,这可是唯一的机会。走到门口时,我听见人们正在议论二号和七号赛驹。我甚至忘记了加洛维蒂安这个大麻烦正要来逮我。我拖着跛腿,拼了命飞奔向赛马下注人那里。大喇叭里叫喊着“只卖出去了六张票”,可我并不关心。
赛马下注人把赌赢的奖金递给我时,“羞涩的新郎”看起来甚至比我还欢喜。他歪扭横斜的牙齿,被烟熏得灰黄。下注人每数到一百镑时他的牙齿都咔哒作响。他双唇肥厚,湿润润的,双眸满布血丝,眨来眨去,目光阴暗却又精光闪现。我简直难以直视他。就在我要把钱都装进口袋时,这个阴险的家伙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后背,大声却温和地对我说:“我们赢了!”
我一定是个白痴,刚才一直没明白为什么“羞涩的新郎”一直跟着我,而且不露半点声色。
“好吧,”我嘟囔着,“不过‘我们’,赢什么了?”
“别装了,”他说,“我们翻番儿赢了。来吧,这得庆祝一番。”他伸出手,自始至终都在笑着,好像他老婆刚给他生了四胞胎。
“瞧着,伙计,”我说道。“这次手气是挺不错,我自己从来没有赢这么多。堪称完美的赌注,不是吗?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下:是我一人,翻番赚了。你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打我钱的主意……我可没有那么好骗。”
这个傻瓜霎时收敛了笑意,像看到瘟疫病人一样瞟着我。他鼻子塌陷扁平,鼻孔里呼哧呼哧,像一头愤怒的西班牙公牛(可我并不想作斗牛士来耍逗他)。总之,他恼羞成怒,凶蛮得像头野兽。
“六百七十英镑是一大笔钱,”他叫嚷着。“谁也不能骗走我的赌利。你这个瘸子……”
“闭嘴!”我呵斥他,“再敢那么叫我一次,你……你!”我照着他的脸挥起一记右勾拳,但这个傻瓜灵活地闪开了。他拦下我的拳头,反手重重一拳捶向我的下巴。我被打得反弹起身,又一屁股闷闷坐在了地上。紧接着,一个手鼓硬生生地砸在了我头上。一会儿,我才清醒起身,憋了一肚子怒火。要是我够强壮,我就撕碎这个傻瓜。
“羞涩的新郎”已经卖力表演过一番;我们的观众也相当不错。一些白人佬威吓着要打出他的脑浆……我真希望他们砸碎这傻瓜的脑袋。
忽然间,一个警察推搡着从人群中挤过来,我已无处遁形。我猛地撞开人群,在缝隙中寻路逃窜。骚动一开始,人人都尽力逃散。我跑了一小会儿就摔倒了,脸着地。警察弯下身,牢牢压制住我的胳臂,悄声说:“冷静,你这家伙,别惹事。乖乖跟我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那种情形下,我别无选择,只得屈从。我母亲常常和我讲:永远不要拒捕,更不必说众目睽睽下,被一个穿制服的警官逮捕。因为“羞涩的新郎”控告我,我的钱最终被平分了。被逮捕后,我在班图难民营熬过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周末。他们安排审讯室一个心思细腻的小警官负责移送我。小警官纯真善良,没有把我丢进关百十来号罪犯的房间……那地方关着强盗、敲诈犯、职业扒手等等,鱼龙混杂,尽是些招人厌恨的角儿。坦率来讲,我倒希望他别多管闲事。我本可以在那里耍耍残废的把戏,捞点儿钱。
“我就知道过不了几天你就会滚回来,”法官大人说。应该有人告诉他,他还能大有作为……在算命方面。他盯着我看,扁平的脸活像压平的烤薄饼,一张嘴大咧着朝我蔑笑。这地方一定再找不出别的地方行政官喽,不然为什么一直以来总是他一人坐镇。
“赌马的乞丐真是祸害。他们滥用别人的善意。”
偏偏该我倒霉,此刻我不得不恭听道德说教了。法官大人陶醉在自己的说教里,但我不爱听。加洛维蒂安女士轻笑地瞅着我,得意得像个胜者。她大概想借这件事升迁高位。他们要求我站起来。
一个脸颊消瘦的男人要求我举起右手发誓坦白真相。待我发完誓,检控官开始质问我,紧紧相逼,好像“羞涩的新郎”许诺贿赂他百分之三十的赌马赢利似的。庭审质问完我,他传“羞涩的新郎”到庭对质。
“你认识这个人吗?”检控官问。
“不,我不认识他,法官。”
“那你是怎么拿十先令和他赌马?”
“我一早上都没赢过,所以我决定试试别人下的注。我看到他,就和他搭了几句话。”
“有人看见你和他搭话了吗?”
“我不知道,但肯定有人看见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问他有没有赌马场内部情报。他告诉我他有,还说消息千真万确。于是我问他拿十先令能不能换消息,他同意了。我不敢再下注,就把钱交给他,和他一起踱到了下注的地方,在二号和七号赛驹上押了一英镑。”
“为什么你不敢下注?”
“我想他比我手气好……况且,整个早上我一直输。”
“你为什么打他?”
“他想骗走我赌马的奖金,被我识破后还要动手打我。”
法官大人盯着我,目露蔑视。这次我不必在他面前演戏了。可是我也只能把那笔钱拱手相让,因为“羞涩的新郎”编的故事滴水不漏。


“我对你失望透了,”法官大人叫嚷着。“我从来不知道你竟然还是个贼。我不相信你一个人能买注;乞丐哪会有这么多钱。我相信他说的,事情原本就是那样。你们俩,钱平分。”
“我不相信你一个人能买注。”真是厚颜无耻。我会让那个无赖知道我一星期赚的比他一个月还多。还说不相信我……上帝啊!
看着法庭把我的三百三十五英镑交到“羞涩的新郎”手里,我感觉自己罪大恶极,要被押去屠场宰了。这个百年难遇的畜牲耀武扬威,欢天喜地。他再多干几笔这样的勾当就能退休,在里维埃拉【南非开普敦附近地名】给自己买套别墅了。
那个畜牲看似品行端正,令人信服。但他心狠手辣,无品无德,厚颜无耻,良知殆尽。他知道善恶的边界,早在大恶中炼化得炉火纯青,坏到登峰造极,这评价非他莫属。他不允许自己因为欺骗我这个跛子而踟蹰不定。若是我有幸能选个人当我兄弟,他就是不二人选。
我拿着剩下一半的钱离开了,以免法官大人和加洛维蒂安女士再虚构出别的案件来指控我。回家的路上,在某个忙碌的角落里,我还是忍不住停下来做起我的老行当。虽然我要得到补偿,但是此刻我衣着光鲜,做乞丐日久年深,我深知人们是不会施舍钱财给比自己穿得还好的乞丐。人们救济乞丐,是想要在施舍与被施舍中建立等级间的优越感,就像我曾说的那样:做乞丐,我才是行家。
回到家我才发现老婆留下的纸条。
“小汤姆病了。求你快回家……”
霎时间,想着我的小汤姆,我无比揪心焦躁,即便胖房东太太一再劝慰,我也不能镇定。
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事发生,我才了然自己到底有多荒唐。妻子和家庭远比一个男人的地位更重要。曾经,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像平常人家一样教养他们,而不是活成一个绝望无助的跛子的儿子……为他们寻求一片撒满阳光的乐园。或许我是一个乞讨大腕儿,可是作为丈夫和父亲,我却是最大的输家。
“要是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萨鲁鲁贝利,你,能不能……”
“嗯,我会解释给他听。房间我一直给你留着,只要你还回来。”
在心里,我当然想要回来。我有三百三十五个理由要回来。那个无赖的畜牲,还有约翰内斯堡愚蠢无知的人们,我会记着他们一辈子……我一定会回来。这是乞丐的职责,我定当履行!

END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5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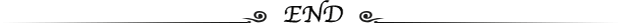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