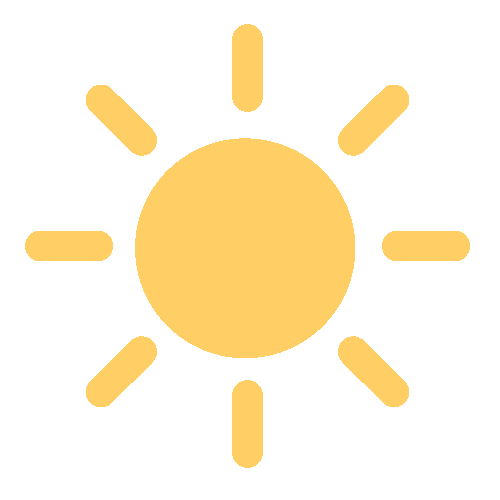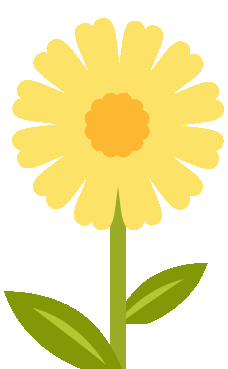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郅荟:沉默之场——拉丰《阿尔丰斯》《擅长激情》中的乡村形象书写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郅荟
置身于波诡云谲的后现代社会,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往往被物质与现实所遮蔽。1984年,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持编撰的《记忆之场》出版。这一鸿篇巨著以独特的史学研究视角,勾勒出一部法国的社会文化变迁史。在这部作品中,诺拉指出,当人们在谈论历史与记忆时,目光往往聚焦于城市记忆和官方史学的书写,而忽略了乡村的、地方的记忆。显而易见的是,在城市—乡村这一二元对立关系中,乡村一直以来都居于他者的处境。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愈发地扩大,被现代化社会遗弃、搜刮殆尽的乡村世界日渐走向没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沉默之场。
面对乡村地区缄默的现状,法国女作家玛丽-埃莱娜·拉丰写出了由19个短篇构成的作品《故事书》。出生于康塔尔省闭塞山区的她,用细腻入微的笔触向世人描绘了乡村这一日渐没落世界,向我们揭示了乡村那些“沉默者”或缄默或喧腾的内心世界。在此,笔者以拉丰作品中的《阿尔丰斯》和《擅长激情》(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5期)为切入点,尝试剖析拉丰笔下无言的乡村世界。



《阿尔丰斯》
在开篇故事《阿尔丰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冷漠生硬、利益至上的乡村社会。一位生性柔弱而敏感的男孩阿尔丰斯就生长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他“性子柔顺”,不擅长农事、生产等体力劳动,却“喜欢女人的活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这个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除了他的姐姐热尔梅娜,所有人都给他冷眼,奚落他,甚至对他暴力相向。连他的父亲都认为他“给这个家带来霉运”“有他这样一个儿子,就是不幸”。没有人愿意关心阿尔丰斯的感受,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他。阿尔丰斯是村子里的沉默者。
可是,阿尔丰斯也曾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也曾被人看见:当他以女性的温柔照顾家中的两个侄子时,人们看见了他的价值,他的劳动可以为他们省下一个女佣的工钱,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实际上的物质利益。然而好景不长,两个侄子长大后,不再需要阿尔丰斯的照顾,开始接触这个险恶而刚硬的乡村社会,并逐渐融入这个环境,转而加入了欺侮阿尔丰斯的行列。阿尔丰斯重新变得微不足道,转身归于长久的沉默。他早已无力反抗,只是“停留在痛苦里,像牲畜一样忍着,像缄默的物品一样忍着。开始是无言地忍,然后是自毁式地忍”。遭受了此次打击后的他,内心的沉默如锈迹般肆意生长,直至用身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嘴巴张开、扭曲,却没有喊叫”,因为“他做不到”,他“从颅骨深处和眼角流出几颗坚硬的泪滴,却没有哭泣”。他不想重新开始。
后来,少女伊冯娜出现了,她为阿尔丰斯暗无天日的生活带来了温暖与慰藉。伊冯娜的身世凄惨,在村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阿尔丰斯。她同后者一样沉默,一样有着温暖细腻的内心。可以说,伊冯娜是第一个被阿尔丰斯吸引的人。当村里人想方设法从阿尔丰斯身上榨取用利益和价值时,伊冯娜却对他怀着“小动物般怯生生而细密的爱意”。她愿意倾听阿尔丰斯的声音,也真正地走进了后者那缄默却温暖细腻的内心世界。
当人们徜徉在金钱和肉体中寻欢作乐时,在无人注意的小小角落,两位沉默者走进了彼此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交谈,却始终用他们的心灵去感知对方的存在,沉浸在彼此给予的柔情中。这份感情心照不宣,也无须多言。阿尔丰斯与伊冯娜“逐渐从自己身上消退,退隐到了世外,退隐到了很远的地方”。
就在二人满怀期待地生活在这一方沉默的天地中时,悲剧悄然降临。伊冯娜终未能逃脱命运的枷锁。借着月光,她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她和阿尔丰斯栖身的阁楼,诀别了她曾在那里蜷缩依偎过的庇护所。
在伊冯娜的惨剧发生后,阿尔丰斯敏锐地感知到了她的遭遇,他“在花园的小木屋里”,找到了用一根大粗绳套在“小鸟般脖子上”的伊冯娜,但他却再一次被沉默束缚——“别人会来,热尔梅娜会料理一切。”虽然作者没有将阿尔丰斯的内心世界向我们展现,但笔者认为,同伊冯娜一样,期冀的美好溘然消失,阿尔丰斯一时难以面对和接受这一事实,却没有办法逃开,因为无处可逃。
这是两位沉默者的悲剧。


在《阿尔丰斯》中,作者运用了一种朴素、记实的笔法,来描写乡村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值得注意的是,除开篇第二自然段中热尔梅娜哭叫着重复的那句“我可怜的阿尔丰斯!我可怜的阿尔丰斯!”外,全文再没有出现过直接引语。在处理人物的话语时,作者将其转化为平实的陈述句,将之融入文章的叙述中。譬如,作者在描写阿尔丰斯十八岁那年,第一次去圣—热纳维夫时,向读者铺陈了大段阿尔丰斯母亲的话语:

但母亲不愿意,她说他不知道路,说自己太老太累,不能再追着他跑了……说姐夫尤其是姐夫的母亲不愿意…说因为他的缘故,热尔梅娜不得不低声下气,沉默寡言,脊梁骨伏得比其他女人更低;话说回来,她能找到人嫁出去已经很好了……他爹如果还在,情况也许不一样…一个男人,他可以讨价还价,尤其是他爹那样的男人……但他爹走得太早,年纪还轻就被这一切拖垮……而她,一个女人,什么也做不了……让热尔梅娜结婚,哪怕嫁进这个因为阿尔丰斯而瞧不起她、利用她父亲的过世捞钱的家庭,也是天大的造化;不管怎样,热尔梅娜已经成家,总有一天会当上家……女婿为人冷酷,不想看到他们母亲和阿尔丰斯。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大段的话语用省略号间隔开来,形成了数个破碎的、不连续的分句,好似诉说着这个不幸的乡村家庭的万般无奈。通过自然的过渡,作者巧妙地将直接引语转化为了间接引语。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这位老妇人侧身穿过了冰冷的文字,带着她对命运不公的控诉,从窸窣的书页间抽离,迈着她颤巍的、缓慢的步伐,走到了读者面前,向人们诉说着自己内心的凄苦。这不仅仅是这位乡村老妪的内心独白,更是乡村社会中一个沉默的家庭的真实写照。而阿尔丰斯的家庭,只是沉沦在这个巨大沉默之场中的无数个家庭的缩影罢了。
这是两位沉默者的悲剧,也是乡村这座沉默之场的悲剧。



《擅长激情》
不同于《阿尔丰斯》,《故事书》中的另一篇作品《擅长激情》讲述了一个“激情反被激情误”的故事。
莫是一位阿拉伯裔青年,在法国一个名叫奥布拉克的村庄度过了童年时光。在莫的心目中,奥布拉克是天堂一般的存在。这一次,莫要带女友马丽娅去那里度假。在日常生活中,能干的马丽娅在二人世界中掌控着话语权,莫居于相对沉默的境地。但在“奥布拉克这件事”上,莫决意要证明自己是“最强的那个”。
奥布拉克是凝结和维系着莫童年记忆的场所,是莫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记忆之场”。他在那里寻觅到了自信,并逐渐构建起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学生时代的莫“不擅长拼写也不擅长学校里的任何科目”,加之他本身的理解能力有限,学校的老师大多对他没有耐心,这一切导致了他自信心方面的匮乏。弗朗索瓦老师出现后,某些事情在悄然间发生了变化。弗朗索瓦是莫的郊野课老师,在课上,他带领孩子们去了解奥布拉克的风土人情。这是一门别开生面的课程,因为学生上交的笔记分数与拼写正确与否无关。弗朗索瓦老师告诉学生:“拼写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激情”。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在学校中一无所长的莫终于找到了自己所擅长的事物——激情。从那天起,莫的郊野课笔记本便成了他关于乡村记忆的物质载体,是他在奥布拉克生长的见证。也可以说,它记录了莫的自我身份认同逐渐构建的过程。


莫将自己所擅长的激情在郊野课上发挥到了极致,也因此得到了弗朗索瓦老师的欣赏。虽然莫在这门课上的学习甚是投入,但依笔者之见,莫对于奥布拉克的认识,仅仅局限于这本小小的簿子之中,倘若离开了笔记本,他也许很难再说出些什么。譬如,在老师带领学生们去畜棚中看小牛时,大家都在笔记本上画下了牛以及它们身体各部位的样子,但这些莫都没有记住。再如,在面对广场上新建的雕塑时,一向热爱奥布拉克的莫却表现得异常冷漠,他“只是远远地看着,并未走近;他不喜欢这雕塑”,因为“雕塑是后建的,上郊野课的时候还没有,否则老师会和他们谈起,他们也许会把它画进笔记本”。对于莫而言,这座雕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它唐突地出现在“他的”奥布拉克。他甚至没有走近去细看这个雕塑。实际上,莫所热爱的是存在于他笔记本中的那个奥布拉克,是他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奥布拉克,或许也可以说,是被弗朗索瓦老师欣赏的自己的激情。
莫希望将将自己对奥布拉克的感情之传达给女友马丽娅,希望她能与自己实现“同频共振”。马丽娅虽说尝试着去理解,但她终究没有和莫一样在奥布拉克成长的经历,加之她本身对自然就有一定的抵触,很难感同身受莫的激情。故此,马丽娅不能理解那本郊野课笔记在莫心中所占据的分量。在故事的最后,看过莫笔记本的马丽娅在钟楼上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的笔记里尽是拼写错误。”她不知道这句话既否定了莫全部自信心的来源,也摧毁了莫对她的爱和期望。马丽娅的话语就像是放出去的利箭,一下子刺中了莫被各种情绪点燃的内心——“他生命的火焰在密闭的炉子里燃烧,热量无法从中逃逸。”(齐奥朗语)——在莫一向擅长的激情的催化作用下,他的愤怒在这一瞬间达到了一个极值,竟将马丽娅从钟楼上一把推下。
莫最终酿成的悲剧的根源,或许还应追溯到莫自身的性格或是人格。笔者认为,莫从小便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同阿尔丰斯一样,他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位格格不入者(misfit)。他始终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中,而不愿意去面对现实。在莫准备与马丽娅出发去奥布拉克前,他回到母亲家中取他的郊野课笔记,当他从母亲的话语中察觉出她对于衰老的哀伤时,却不敢抬起眼睛和母亲对视,因为他“不想知道她的年纪,不想知道她要死去,也不想知道没有了母亲的等待,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他要求女友马丽娅共情自己的过往,却很少体察她的感受。他的沉默是他只关注自己内心“激情”的结果。


《阿尔丰斯》和《擅长激情》讲述的都是沉默者的悲剧,除却自身性格的因素外,二者都指向了作为一个空间的乡村的悲剧。倘若将视阈置于整个法国社会,便会察觉到整个乡村都是一个巨大的沉默之场,而处在这封闭之中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无一不是被遗忘在城市化、现代化之后的沉默者。
纳博科夫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文学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微积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对等关系,而是从社会中抽取人类命运的种种,它是对人类命运的总体叙述。”在文本《故事——源头的故事与写字台上的故事》中,拉丰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开始创作的缘由和写作时的心境。依笔者之见,拉丰没有选择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以诗性的语言去虚构一个个拥有跌宕命运的传奇角色,而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现实主义笔法,去复现没落的乡村世界中一个个沉默者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她希望能用文字为他们赋形和代言,希望人们能向他们,以及他们所处的乡村世界投去一瞥,令这些沉默者,以及他们背后这个巨大的沉默之场不再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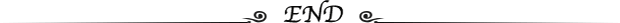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