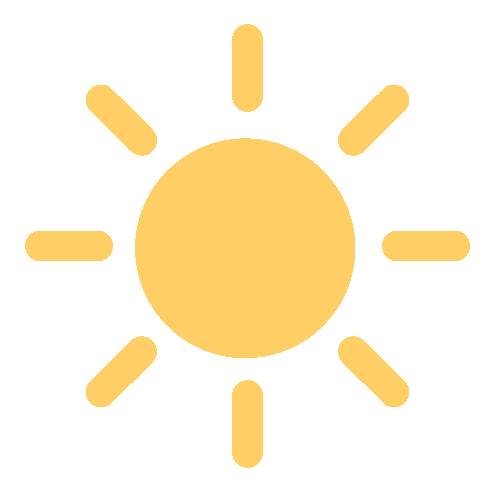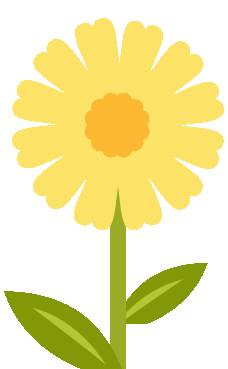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王嘉浩:语言的动力——读《终章》《重生记》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阿西斯在《终章》里不断强调时间的快速流逝,不断打断故事的叙述,并不仅仅是在模拟主人公在真实状态下的反应,更是在用一种同频的震动让读者逼近现实。而在《重生记》里,他……通过复杂的句法结构、叙述声音的变化以及其指代者(蒙席和克莱门西娅)在结构位置上的相似性创造出一种行将崩溃的效果。这两种语言手法都是叙事里的一种潜在力量,推动小说走向“终章”,并在读者反复阅读过程中得以“重生”。
——读《终章》《重生记》有感
王嘉浩
如果按照《终章》《重生记》的顺序一口气阅读巴西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的这两篇短篇小说,就容易产生一种胡思乱想:仿佛是《终章》中自称“大衰人”的马蒂亚斯在正午时分放下了笔,从窗户一跃而下——随即转生成为《重生记》中的若泽·马利亚,在神父面前倾诉自己此生的痛苦。虽然在文本的情节上,两篇小说并没有关联,但这种“胡思乱想”也并非全无理由。不仅仅因为两篇小说在情节的设定上一前一后,人物经历上也颇有相似之处。马蒂亚斯一生为“衰神”所困扰,一生中几乎没有一件事顺顺利利地成功,而是永远被命运所捉弄;作为死后到达“有德者的星球”的第一千个灵魂,他带着前世的阅历重新转生成为若泽马·利亚,却因为前世的糟糕经历而在新的轮回中畏手畏脚,最后对世界陷入彻底的怀疑。相似的“不顺”经历在此生导向了自我毁灭,而在来生造成了彻底的虚无。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或许并不足以将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讨论。但在这两篇小说中间,确实产生了某种更深层面上的联系。当我们不断尝试说清两篇小说的相似性的时候,这种相似性就会朝着语言的更深处延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作者本人也许并没有这样设计过,因为这种联系更像是出于一种文学底层的逻辑,一种语言的动力。




《终章》是小说主人公马蒂亚斯为自己的遗书写下的补充性小传。他希望用这个小传展现自己“衰人”的一生,并以此来解释遗书中那些怪诞的遗嘱条目。这篇小传的对象可能是即将回来的男仆,可能是遗嘱的执行者,也可能是社会公众——他知道遗嘱会被登上期刊。从他的叙述中,读者很轻易就了解到他确实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大衰人”。被朋友的情敌误伤后,朋友却在为自己躲过一劫窃喜;恋爱时被朋友骗走了五万雷斯和恋人;与鲁菲娜结婚,孩子刚一降生便夭折;妻子死后才发现她生前不忠的书信。他在工作上也十分困顿,但是工作上的不顺只是被简单带过,被作者或者马蒂亚斯详细讲述的是友谊、爱情、婚姻和亲情如何被“衰神”偷盗。鲁菲娜死后,马蒂亚斯意识到“依靠外力的东西自然转瞬即逝”,因此从死去的妻子中看到不朽,获得了一种似乎可以不依靠外力的自足的精神力量——“这是对凶星的挑战”。然而这一次输的还是马蒂亚斯,他在随后就发现了妻子生前与自己朋友的秘密通信。由此,马蒂亚斯对尘世失望,决定死亡;小说也由此被推向在一开始就设置好的象征物——靴子。一双靴子就是幸福。这部小传随着马蒂亚斯最后一句“晚安!记得穿鞋!”结束,读者自然可以想象马蒂亚斯的生命也由此终结。
马蒂亚斯写得十分克制,虽然他还是在衰事之外加入了不少自己的感受,但总是点到为止。一方面,读者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性格:善良,也懦弱。从不寻仇,死前还想着“衰人可真多呀”,要用靴子造出一大批幸运儿;但也总是捡起朱庇特扔过来的木头,即便有时说不出“木头万岁”。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马蒂亚斯写得十分克制,是因为他决定在正午死去,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一小时之内写完这封衰人自传。《终章》能对读者产生震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读者读着马蒂亚斯的一生,也在亲历着他的死亡。叙述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同速使得读者与主人公的行为距离更近,仿佛马蒂亚斯的书写正在发生。这种“即时性”端赖于叙述者对时间流逝的提醒,对话语组织方式(包括行文跳跃)的说明: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讲述童年与青年的其他不幸上。我想在正午时分死去,而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
我也不想说我遭遇过的病苦。就跳到我那位一生都很贫穷的父亲吧。
我不想尽吐我当时的痛苦,我只想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把这两个人都用枪毙了。
幸运的是——啊!在一个衰人的终章里,这一声“幸运”确实反常,但是请继续读下去,你们会发现这声“幸运”是写作风格,并非生活本身,只是一种行文过渡的方式而已。
又得说一次“幸运的是”,不过这次不仅仅是行文过渡。
快十二点了!我得赶快写完,男仆随时会回来,所以,再见!你们无法想象这种情况下时间过得有多快。一分一秒飞驰而过,仿佛帝国兴替。最重要的是,此情此景中,纸张随着时间消逝。
我不想细数那些开不出的彩票,做不成的生意,半途而废的关系,我更不想纠结于命运其他的捉弄。
就是在上述语句所烘托的跳跃感、急迫感和现场感中,读者犹如被洪水裹挟着不由自主地奔向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在这里解释了自己将靴子遗赠给他人的缘由。他在吁请相关人士执行这个遗嘱时,也在给自己的人生执行终结的仪式。




在《重生记》开篇,作者就将沙漏倒了过来:一段时间之后,警察就会到来,驱赶走喋喋不休的疯子。和《终章》的情况类似,由于小说中绝大部分都由人物的话语填满,叙述者对故事也没有过多的省略,因此叙述时间也是和现实时间同速的。一个外力在推动着叙述。
全文基本全部由神父与若泽·马利亚的对话构成。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若泽·马利亚的自说自话。他并不需要神父的回应,或者说,他并不在意神父做出什么回应,他需要的是将自己所承受的苦难倾倒而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篇以独白为主要形式的作品。若泽·马利亚一开始出于本能的阅历逃避一切风险,后来认识到自己浪费了青少年时期的冲动与放纵,最后彻底陷入对世界一切的怀疑,进而由于虚无而爆发疯癫。若泽·马利亚的遭遇与其自我认知的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主线。但是,阿西斯从形式上对语言的巧妙利用则让小说具有了一种蓖麻油般的不安。
需要注意的是引号之外叙述者的声音,这片领域成为了神父与疯子角力的战场。整篇小说中一共存在着六段叙述者作为旁白的声音。第一自然段作为小说的序幕,正剧尚未开始,因此不需要被计算在此列。在这六段旁白的声音中,发生了一种变化:随着叙述的推进,原本全部神父的视角、心理描写,逐渐受到若泽·马利亚行为和话语的“侵占”。神父一开始大段的对若泽·马利亚的观察、等待警察时听到的周遭声响、以及自己的内心独白,在对若泽·马利亚话语的间接引用面前,显得如此羸弱,以至于节节败退,最后只剩下“神父不住地后退……后退……”


实质性的变化出现在第三个旁白段落:
若泽·马利亚继续讲他的故事,他说,一连六天,他都没再去克莱门西娅家里,但没抵抗住她的信和眼泪。一星期后,他跑去她家,向她坦白了一切,所有事情。她饶有兴致地听完了,想知道要怎么做才能打消我这些胡思乱想,还需要她怎么做才能证明她的爱。若泽·马利亚用一个问题回答了她。
若泽·马利亚这一部分的间接引语占据了这个自然段的一半。间接引语的使用意味着引语部分与非引语部分之间没有引号隔开,缺失了这个最为明显的视觉符号,也就势必会造成引语与非引语之间界限的相对模糊。而这里,在若泽·马利亚的间接引语中,还套着一段若泽·马利亚的爱人克莱门西娅的间接引语。这就使得上述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以至于无法对间接引语和叙述者话语做出准确的区分。更值得注意的在于,在克莱门西娅的间接引语中,出现若泽·马利亚时,使用的代词是一个“我”。间接引语的套用使得这个“我”的出现完全不会干扰读者的阅读,不会使读者产生对其所指对象的困惑,但是也同时暗含了叙述崩溃的迹象。
第四个旁白段落时,若泽·马利亚掏出枪,“卡尔达斯蒙席大惊失色”。紧接着就是若泽·马利亚的直接引语中,克莱门西娅“吓坏了”。同样的反应接连出现,使得这两个角色之间获得了一种微妙的相似性。在上述两种技巧的交替使用下,这种相似性在后文中不断被放大,使得第六个旁白段落中,若泽·马利亚的间接引语与叙述者话语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若泽·马利亚的记忆与现实世界逐渐混为一谈,以至于最终读者无法从指代上区分二者,并随着他对克莱门西娅(她)的大骂后“扑向他”走到结局。
若泽·马利亚的疯子身份是被神父确认的。在小说的开篇,叙述者始终以神父为中心展开叙述,若泽·马利亚则成为被神父所观察、判断的客体。而到了小说的结尾,若泽·马利亚的声音则完全吞没了神父,其意识也由虚无走向了崩溃。


阿西斯在《终章》里不断强调时间的快速流逝,不断打断故事的叙述,并不仅仅是在模拟主人公在真实状态下的反应,更是在用一种同频的震动让读者逼近现实。而在《重生记》里,他通过形式上的变化,让语言在内容之外创造出了新的效果。这种效果几乎不依赖于语言所传递的内容本身,而是通过复杂的句法结构、叙述声音的变化以及其指代者(蒙席和克莱门西娅)在结构位置上的相似性创造出一种行将崩溃的效果。这两种语言手法都是叙事里的一种潜在力量,推动小说走向“终章”,并在读者反复阅读过程中得以“重生”。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