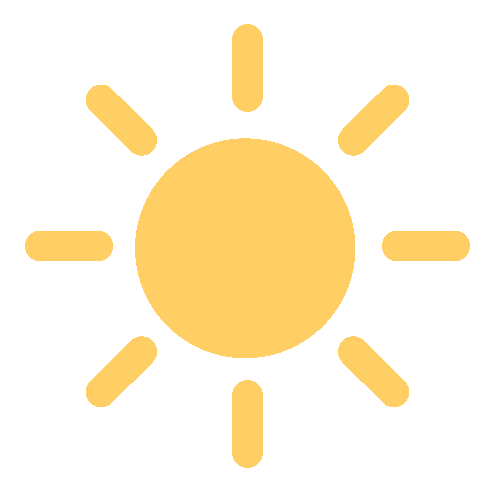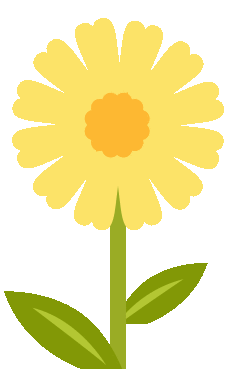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黄靖茜:我是动物,这是需要发现的事——读《兽医》和《海豚魂》有感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如果在阅读的时候将主角不视为海豚,而视为人类,将海豚对人类的感悟当作是人类对动物的观察,那么《海豚魂》读起来将是一篇符合常理的小说。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人本是动物,但作为动物中特殊的种类,却进化出了比很多动物更凶残的杀戮习性,究竟有没有离文明更进一步?


我是动物,这是需要发现的事:
读《兽医》和海豚魂》有感
黄靖茜
在通风不太好的房间里吃完一顿饭,衣服面料的孔隙中全都钻入饭菜的味道;将文字或浅显或深入地吞食后,它们也会在你的衣襟上留下气味。读完这两篇小说,脑海中残留着它们的气息,昏昏沉沉走到镜子前,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几乎被吓一跳——好陌生。和平日的样子别无二致的陌生。乱发间露出一双眼睛,那里面分明是有光亮,但让我感觉不到平时那个我的存在。刚刚阅读的文字带着藕断丝连的蛛网联结着我,我知道这样的感觉是那些蛛网的作用,但面对镜中的自己,还是有两个字几乎脱口而出——动物。
猛然想起作品中的一段话:“……海豚很特殊,是动物中的特例,而让我们(海豚)成为特例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会问这么个问题:我是人,还是动物?”而从未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的我,有多久没有那样认知到自己是一只动物了?


《我是如何成为了一名兽医》(以下简称《兽医》)和《致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封信:海豚魂》(以下简称《海豚魂》)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5期。这两篇小说的主角在他们的同类中都是怪异的存在。兽医的身份非常暧昧:他们安抚动物,让动物恢复健康,但取悦的却是动物的主人——或者说,他们的“人类爸妈”。由此来看,《兽医》主人公所做的事情显然有悖常识:她想知道接连在同一地点跳桥的狗的想法。而《海豚魂》的主角是一只海豚。它自述是一个“特殊的”物种,有灵有智,与人类经年累月地相伴左右。饲养它的人员与《兽医》中的主角是一个同样怪异的人:他带海豚看电影,给海豚读《银河系漫游指南》,用海豚的话说,他们的关系“是主体对主体而非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很和谐,情感很自然,以致我时不时忘掉这是海豚和人类之间的情愫,甚至将主角海豚误认为是人类。
我为什么会忘掉这是海豚和人类之间的情愫?因为在我的常识认知库中,海豚作为动物不会与人类生发如此自然的感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将人性与动物性看作对立的一组概念。


兽医是一个与动物产生联系的职业。在普通兽医那里,这种联系是不平等的。动物永远是被医治,被主人声明,就像文章中患鹦鹉热的鹦鹉,无论主角兽医如何解释,鹦鹉主人只会愤怒地喊叫:我家鹦鹉是一只独行鸟。在主人的认知中,他是宠物的唯一声明人;但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宠物却“插不上话”。然而小说的主角——怪异的兽医——想要理解动物怎么想。“理解”是个很重的词,我们通常只理解人类,对动物的行为却是加以解读。所以,她想要理解动物的想法在常人的世界中是不可理喻的事。但常人世界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本身就是不能为她所理解的。例如:
老师要求我们做一些基于想象的表演,有的简直太傻了。例如,教室里有一个纸板人,说是“住”在黑板后面(纸板人就藏在黑板后面),我们像念咒语似的喊三声他的名字,请他出来一期上语法课。
主角自述,她仿佛觉得“教室黑板后面那个痴迷于语法的纸板人一样不真实”。她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可为常人理解,正由于这个原因,她并不完全接纳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怪异的人,就像那个纸板人一样。小说中纸板人意象和再洗礼教派意象总是成对出现。主角这么解释再洗礼教派:
人们应该先和上帝有精神联系然后再洗礼,而不能说是洗礼造成了这种精神联系——当然如此。
她一方面接受再洗礼教派的信条,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业已消失的一片风景”。这个判断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她自己想要理解动物的想法——没人会想要将动物当作主体平等对待,但她却坚持着自己的这个理念,在人群中就像那个虚幻的纸板人。信仰着已经消失的再洗礼教派,她是孤独的,她怀疑自己。
主人公不仅渴望理解动物,还渴望理解他人。在蛮不讲理的鹦鹉主人给诊所所有人差评后,她企图在老板面前为这位顾客辩护;同事告诉她要拔掉他人的毒牙,她却不相信人类的毒牙能被拔掉。


如果以是否真正接受自己的动物性为标准,那么可以说《海豚魂》中的布卢明顿教官从出现在小说中的那一刻就是一位好兽医。小说包含了许多主题,例如母爱、动物与人的爱情,还有杀戮和捕猎。这些小主题全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人与动物并无分别。
在主角海豚斯普劳特的眼中,布卢明顿教官与她是“一种真正的我/你关系——是主体对主体而非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在这位男教官的认知中,海豚与自己完全平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特德·休斯似乎站在了他的反面,站在了海豚的对立面,甚至站在了他那从动物性中获得满足的妻子的对立面。特德·休斯忘记了自己也是动物的事实。在他的作品中,他穷尽一切方法寻找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大动物象征”,想尽办法获得动物性的感受。但这本身是一个悖论——人本身就是动物,动物性就存在在我们的一呼一吸中,何谈寻找?正是一套常人普遍接受的思维塑造了休斯的这个想法:常人普遍认为人是特殊的动物,特殊到可以从动物这个大集合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更高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休斯寻找动物性的行为其实很傲慢。
这个傲慢的代表在小说开始和结束都出现了,但在读小说的时候,整体的感觉没有那么焦灼,是因为在小说的其他部分,我们听海豚讲述的都是还没有忘记自己动物性的人。比如,作为母亲的普拉斯在“自己的身体及其机能中获得了极大的动物性满足”,她拥有着休斯梦寐以求的动物性能量。还有那名饲养员,就在海豚执行杀人任务的前夜,他长久地将听诊器放在海豚的皮肤上,“像是要努力记住这怦然心跳”。如果说这些片段是为了强调人与动物的相通,最后的杀人片段则是要讽刺人性与动物性的区别:海豚珍视人类的生命,人类却将海豚作为工具猎杀同类,多么有讽刺意味。
事实上,如果在阅读的时候将主角不视为海豚,而视为人类,将海豚对人类的感悟当作是人类对动物的观察,那么《海豚魂》读起来将是一篇符合常理的小说。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人本是动物,但作为动物中特殊的种类,却进化出了比很多动物更凶残的杀戮习性,究竟有没有离文明更进一步?


当我家小狗初来我家的时候,我慢慢从照顾它的基本需求中学习和它相处的方法。那时我发现,妈妈会对小狗说哄小孩子的话,认真的样子让我确信,她是对小狗说的,而不是说给我们听的。这可爱而怪异的习惯很快被我学会了,一直到现在。而不知从哪一刻开始,当小狗用它干净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时候,我不舍得和它用人类的语言说话,我更愿意静静地看着它。那时,我会感受到它的呼吸,温暖、湿润,和我们每个人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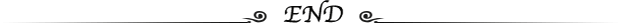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