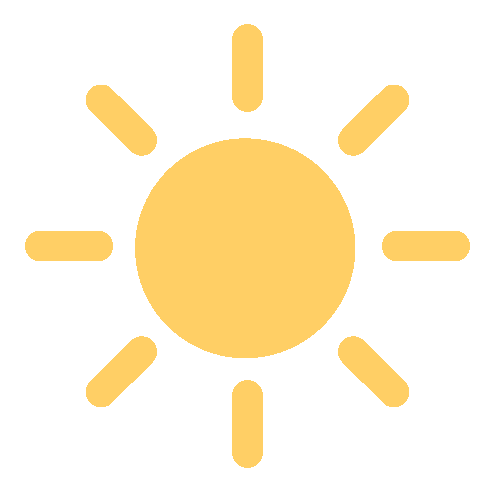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达•加尔古特【南非】:一次非洲布道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回来后,他把车停在教堂外面,在车里坐了许久。他不想进去;不动才安适。他可以看到坚硬的小尖塔和塔顶上高耸的十字架,但今天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安慰。它们似乎是奇特的象征,某种古老的失传的语言残留的符号,它们和他隔得那么远。
几年前,一个年轻人搭上了往返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之间的火车。他刚受命成为教堂里的一名牧师,准备搬到西海岸的一座小镇,到他的会众们那里。


他登上火车时,一个白人老头已经在车厢里了,正在喝葡萄酒,遮掩着把瓶中酒倒进一只塑料杯里。他递给年轻人一些,年轻人摇了摇头。老头似乎忧心什么事,火车开动的时候,他说:“我希望这节车厢里不要有黑人了。”
年轻人说:“什么?”
“我可不是什么种族分子,只是不希望和黑人同坐一个车厢。我以前没坐过火车。你觉得会有黑人吗?”
年轻人说不晓得。他没再和老头说话,等火车到了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走进他们的车厢,他高兴起来。上帝自有神机妙算,他觉得对老头来说,这或许是个教训,能教会他点什么。
黑人的年纪说不好,四五十岁的样子。衣着整洁,面容瘦削,俊脸上一副金边眼镜。打扮貌似老派,人却有点局促。就算小手提箱放好了,依旧坐不踏实。在位子上扭来扭去;站起来又坐下去;躲避着别人的目光。
老头说的那番话,让年轻人想有点作为。他站起身来,朝黑人伸出手。“我叫道格拉斯·克拉克,”他说,“幸会。”
黑人吓了一跳。伸手之前,愣怔了片刻。“伦纳德·萨加特瓦。”他说,声音非常温和。
老头貌似有点受挫。到了他介绍自己的时刻了,但时机已过。火车开动了。
很快,他们驶过一片褐色风光,热浪下小镇点缀其中。老头看着窗外,偷摸喝着葡萄酒。道格拉斯有篇布道文要写。他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若有所思地涂改,余光却一直瞄着黑人,此刻,他正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着。过了一会儿,他想搭个话,就问他:“你住开普敦?”
“还没。希望能在那儿定居。”
古怪的回答。整个人都是古怪的,拎着一个小手提箱上路,想定居在开普敦。道格拉斯问:“你家是哪儿的?”
“啥?”
“听你的口音,是别的地方的吧。你是哪国人?”
他不悦地叹了口气。“卢旺达人。”
“啊,”道格拉斯说,“是啊。是啊。我很想去……看看非洲。”
一阵尴尬的停顿,老头突然冒出一句:“卢旺达!那里发生的事,真是太惨了!”
一丝阴影掠过伦纳德·萨加特瓦的脸。仿佛地下的震动,旋即又给压住,他站起身来。“抱歉,失陪,”他说,“我必须去吃饭了。”说着离开了车厢。


道格拉斯有点不安。他不知道萨加特瓦先生缘何心情不佳(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但看得出其中必有故事。在牧师训练中,他曾是一名出色的开导者,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对别人的故事很能共情。
老头说:“他没事的。不会搞事。有些人会搞事,但那家伙是外国人。”
道格拉斯走了出去,沿着晃动的走廊到了餐车。萨加特瓦先生独自坐在双人桌旁。尽管别处有空位,道格拉斯还是对他说:“我可以跟你坐一起吗?”
他似乎又吃了一惊,却还是点了点头。道格拉斯坐下。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他想套出萨加特瓦先生的故事,开导一下他,但也知道不能问得过于直接。毕竟人家有伤痛嘛。所以道格拉斯决定迂回一下;他打算先谈谈自己。
道格拉斯点了鱼饼汉堡和炸薯条——菜单上最不让他反感的菜——然后,开始跟萨加特瓦先生讲起他搬往西开普敦省的事来。他开诚布公,显得十分自然,其实这故事他已经讲了很多回:讲到寻见上帝,讲到进入教会的决定,讲到此刻摆在面前的工作。他即将成为一所号称“有色”教堂里的牧师,那教堂位于一个小渔村,离开普敦三小时车程。一个艰难的使命。对他来说换地方有点难;他要离开比勒陀利亚的老母亲,离开所有的朋友,迈入未知的一切。然则凡事皆有布局,皆有安排,不依他的意志进行,他索性就随它去了,接受主的力量。
“我的麻烦在于,”他说,“我真的不太了解非洲。以往,我一直过着闭塞的生活。但是,主想让我学习,我想,所以他给我了这份特殊的工作。”
道格拉斯很年轻,有明确的信念,宗教简化了他的世界。他看待各种事情,都是简化为条条框框,简化为道德主题鲜明的阳光故事。他尚未意识到其他人对事情有不同看法。
他对萨加特瓦先生说:“我敢说你能告诉我一两件关于非洲的事情。我敢说你能教给我点什么。”
他故意这么说,为的是让对方说话。他已经毫不隐瞒地讲了自己的故事;现在他们两个都可以毫不隐瞒了。但是,阴影再次掠过萨加特瓦先生的脸。他迅速站起来,用餐巾擦了擦嘴,说:“实在抱歉,我头疼得厉害。得去躺一躺了。”




道格拉斯坐在桌旁良久,有些困惑,有点挫败。他毫无恶意——反而一片好意。但是,他现在知道了,任何示好都是徒劳。萨加特瓦先生只是不想开口。嗯,有时就是这样;准备好了,人们才会敞开心扉。
这时,大多数食客已经离开,一个阴郁的服务员正在擦拭桌子。音乐从天花板上某处的扬声器中溢出。外面,褐色的草野风景已经让位给了光秃多岩的地貌,时有孤丘穿插其间;他们到了卡鲁盆地。
他回到了车厢。萨加特瓦先生倚着靠背,双眼紧闭。老头睡眼惺忪,蜷在角落。道格拉斯没有理会他俩,又回到那篇困难重重的布道文。
周日就得布道,只剩下四天了。这是他的初次亮相;会众们将首次见他面听他说,他不能搞砸了。但不知怎的总是没词儿。或者换句话说,词儿没法聚在一起形成想法;它们漫布了整个页面。他需要点什么,某些中心主题,串联起所有。
通常,在牧师学习期间,他要布道的时候,他喜欢围绕某个故事来阐释经文。这是个引人入胜的好法子,耶稣自己也喜欢寓言,但耶稣总是知晓自己要讲什么。道格拉斯——尽管他有一些想法,想要谈谈非洲,就像他在餐车里跟萨加特瓦先生说过的那样——却没有一个非洲故事可讲。
于是,他写啊写,擦啊擦,最后恼火地合上了笔记本。彼时,已是向晚时分,外面的影子拉得老长。
晚上,萨加特瓦先生去餐车时,道格拉斯没有跟着。他故意等他回来后,方才走去吃饭。时间很晚了;火车开始显出疲惫沉闷之态。其他桌上,尚有喧闹和烦人的聚会,在黄色的灯光下,地板和墙上的污渍尤其发黑。道格拉斯吃了很长时间,细嚼慢咽,一边看着玻璃上的倒影,一边思考着未来。


当他回到车厢时,另外两人已经睡下。醉老头占据着上铺,鼾声如雷。萨加特瓦先生睡在他的下面,即便在蓝色的夜光里,道格拉斯也能看出他没睡着;他身形矮小,紧张地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
道格拉斯毫无睡意。不知怎的,他的思维依旧活跃。各种焦虑的画面在他脑海中闪过。他坐在窗户边,向外望去。月光下的风景一望无垠,就像是雕刻的海平面;一想到这平面就这样不断地起伏向前,他就有一种空洞、兴奋的感觉:一整块大陆,夜色覆盖。他在小车厢里,无足轻重地随着火车拂过万物的表面,他并不觉得与他所见的外面世界有什么联系。这就是非洲,他心想,我在这里了。我们是不一样的。
随后,火车停在了某地的小站,位于一条几乎无名的岔线上,跟一整天停停开开的其他三十个小站没什么两样。但现在,火车却不再动了。十分钟后,道格拉斯走出去,到了站台上。
白日的炎热已经散去;外面很冷。还有几个人走出火车,在外面转悠。车头引擎附近,道格拉斯看到,列车长和司机正在看着另外两名穿着工服的人,他们蹲着身子捣鼓着什么。他走了过去。
列车长苦哈哈地传达着坏消息。“先生,出了点技术故障,”他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他有点难以置信,居然要停这么久。在密集的星辰下,坚硬的蓝色土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没有任何房屋,没有任何亮灯的小窗户。道格拉斯走到站台边上,站在那里看着。但没什么可看的。他刚想转身回车厢睡觉,突然意识到身边有个人。
正是萨加特瓦先生。他似乎充满了紧迫感,即便没有先动。他随后开口道:“我想和你谈谈。”
“请讲。”
“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故事。”
“好呀,”道格拉斯点头,“好呀。”
他内心如释重负。他觉得,这一刻已经等了一整天了。
两人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他们的呼吸眼看着在空气中化成了水汽。天气太冷了,根本坐不住,两个人都不想回车厢。于是,他们就一直动着,为了暖和点,为了做个伴,彼此紧挨着。


“丑话在先,”萨加特瓦先生说,“我不是想和你做朋友。恰恰相反。我跟你讲我的故事,因为我知道不会再见到你。每天,我都带着这个故事,从卢旺达一路过来。我很想把我经历的事情告诉一个人,只要是另一个人就好了。我想讲讲我的故事,然后就走开。你明白吗?”
“明白。”道格拉斯说,尽管他觉得结果未必如此。根据他的经验,人们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后面往往会联系他。这只是一种招引他们的办法,引导他们更趋近真理。
“故事很简单,”萨加特瓦先生说,“就是一个两兄弟的故事。我哥哥,帕斯卡,还有我。”
“很像《圣经》里的【此处指《圣经》里面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道格拉斯附和道。
“小时候的事,我能告诉你什么呢?”萨加特瓦先生说,“一段快乐单纯的时光。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帕斯卡大我一岁。虽说是一块儿长大的,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他。他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他学习不太好;他没念完书。但他还是在基加利【卢旺达首都】。找了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为政府效力。他干得不错。
“离开学校后,我开始做小本生意,售卖种子和化肥。我从帕斯卡那里借了点钱,用以维持经营。我干得很顺利,可以连本带利还他钱,每月还上一小笔,生活还不错。
“帕斯卡在基加利结了婚,娶了个胡图族姑娘。他们有两个孩子,几年后搬回了村子。他依旧为政府干事,当了一名农业巡视员。他住在一所离我家不远的大房子里。
“那时我也结了婚,娶了个图西族女人。我有一个孩子。我不介意我哥娶了个胡图族老婆,虽然有时候她对我们家里人挺没礼貌的。她会说:‘你们图西人这样;你们图西人那样。’我妈不喜欢她,可我不在乎。他老婆那样没礼貌地说话时,我哥就是笑一下。对他来说,这就像是个笑话。
“关于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你听说了些啥。但是,骚乱也不是蓦然出现的。起初只是言论,大量仇恨的言论,出现在电台和报纸上。随后,这种言论也传到了街上。人们都在说那些可怕的事情。
“当然,由来已久了。以前就有宿怨。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宿怨。布隆迪发生过大屠杀。这是那个故事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另一个故事。但冲突来临时,就只发生在你的身上。”
“确实如此呢。”道格拉斯说。在接受牧师培训期间,他学过的,用鼓励性的小小打断帮助人说下去。但萨加特瓦先生甚至都没看他一眼;他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到那时,人们都在警告我。他们跟我说,我们最好离开。我去找帕斯卡,跟他说:‘我们带着全家人跑吧。我们可以去坦桑尼亚,等骚乱平息了再说。’但他却说:‘我现在是胡图人了,不会有事的。’我问他,他说这话时是啥意思?
“然后我哥吓了我一跳。他拿出身份证给我看。他的证件已经改了。他不再是‘图西族’;他是‘胡图族’了。
“我知道他是怎么弄到的。他老婆艾格尼丝的爸爸有权有势。就是他给安排的。我问我哥:‘能不能也给我们搞个新身份证?艾格尼丝的爸爸会护着我们吗?’我哥笑了。他说:‘我现在是胡图人了,我会罩着你的。’
“我信了他。我以为不会有事的。我不想离开。如果你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你对别的地方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等了又等。很多人走了。但我留下来了。”
“我能理解。”道格拉斯说。他壮着胆子挽起了萨加特瓦先生的手臂。他们在站台上走到头再掉转身。到这会儿,他们几乎是外面仅有的旅客了;其他大部分人都上车了。
“最后,我也决定离开。但为时已晚。他们封锁了道路,他们要检查身份证明。几个星期以来,联攻派民兵【原文为Interahamwe,意为“一起战斗的人”。这是由胡图族青年组成的民兵组织,在卢旺达大屠杀中主导了对图西族的杀戮】一直在街上游行唱歌。我们每晚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叫嚣着:‘杀死蟑螂!’这就是他们嘴里的图西族人——蟑螂。我们对他们来说就是虫子。
“总统飞机被击落的那晚,我们知道了。人人都知道了:现在就要开始了。那天晚上,没有电,灯都灭了。四周一片寂静。死一般寂静。
“后来,帕斯卡来找我。他说:‘这里不安全了。你家里不安全了。你必须跟我走。’于是,我们跟着他去了他家,我们一家人,还有我的母亲和父亲。
“他把我们藏在那儿,一个特殊的地方。房子下面的一个房间。我们在那里躲了许多天。外面,屠杀已经开始,但我们毫不知情。我哥跟我们说:‘情况非常糟糕。’但房子下面黑乎乎的,我们什么也听不见。我们很害怕。
“后来,帕斯卡来找我。他说:‘你欠我的钱在哪里?’我说:‘我的哥呀,你说的是啥钱呀?’他说:‘你知道我说的是啥钱。我借钱给你,支持你的生意。现在我们照应你;我们把你们给藏起来,我们太费钱了,你必须把欠我的钱还回来。’
“我没办法啊。我已经还给他了,所有的钱,老早就还清了。可我能有啥选择?所以,我给了他更多的钱,把全部的钱都给了他。那是我毕生的积蓄啊。可他还是生气;他说根本不够。
“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不再是我哥了。他不跟我一帮了;他跟他们一帮了。我明白了,可我无能为力。我在他的家里。”


道格拉斯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又闭上了。
“我老婆开始哭。她说:‘没救了我们。’我跟她说这不是我哥的错,都是他老婆让他这么做的。我这么说,可心里知道老婆说得没错,没救了我们。
“没多久他们就来了。也许帕斯卡正等着他们,等他们有时间过来呢。要不就是心里没拿定主意要做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可是,外面的杀戮持续好一段时间了,已经要消停的时候,他们来了。
“来了很多人。艾格尼丝在那儿。她的父亲在那儿。还有其他人,很多我认识的人。
“我哥跟他们一起。刚开始我没认出他来。他的脸变了,魔怔了一样。他跟着他们一块吆喝:‘杀死那些蟑螂!’他说:‘出来,从洞里出来。’我冲他喊:‘哥,我的哥啊!’他说:‘我不认识你。’”
萨加特瓦先生的声音变了。他说话一直很慢,透着浓浓的悲伤,此刻的语气却变得平淡。他好像正在读一份购物清单。他说:“他们先是强奸了我的妻子。然后砍断了她的双脚,她的双手。然后杀死了她。他们强迫我们观看。他们用砍刀和大刀。折腾了很长时间,比你想象的长多了。
“接着是我妈。如法炮制。我哥一样没落下,强奸和杀人。那也是他妈啊,但他就是跟畜生一样。
“接着,他们杀了我爸。他死得很快,他太老了。但是血,血从他身体里流出来。我想永远都流不完。
“接着是我儿子。他们把我俩拽到外面,拖向井边。他们想用石头砸死我儿子,但我哥说:‘别了,就把他扔井里吧。’于是,他们就带他走了,一个六岁的小孩,他们就顺着井口扔下去了。我能听到他的尖叫声,从地下深处传来。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人,我的邻居,我的朋友。其中一位,我每天都从他那里买面包。其中一位,还是我哥。”
道格拉斯脸色苍白。他们现在停下了脚步,可并没有看着对方。他们面朝空旷的风景,望向月亮落下的地方。
“然后,在他们杀我之前,我逃开了。我不知道怎么逃开的。我好像出了什么状况,我之所见让某种力量进入到了我的身体里。
“有一道白光,像太阳一样,就在头里面,然后我就跑了,跑啊跑。穿过灌木,越过岩石。我逃走了。”
道格拉斯清了清嗓子说道:“你逃走了?”
“是的。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个地方附近,有一条河,河边有一个洞。有人藏身在那里,他们有朋友来送吃的。我跟他们待了好一段时间,直到卢旺达爱国阵线【1990年由图西族人领导的反叛组织,后成为卢旺达的执政党。卢旺达大屠杀后,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侵入卢旺达,目的是结束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歧视和仇杀】来到。但我记不太清楚了。”
他突然比划了一下,就不再说话了。滔滔不绝的语流断掉了。好半天,道格拉斯才想起本该问的问题。他不知道,比如说,萨加特瓦先生是怎么离开卢旺达的,又是怎么到南非来的。但在那一刻,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比划的那一下,像是砍,又像是扔,似乎要把他的余生抛向一边。他似乎已经死去,随着他的家人而去,后面行事的就是个鬼魂。
他说:“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哥。他怎能做出那样的事。对我,对我妈和我爸。我以为我了解他,然而并非如此。他是个陌生人。”
道格拉斯说:“也许他只是害怕。”
“害怕什么?害怕被杀?死其实是更好的选择。”他语气平淡地说——俨然在做评论,“后来,我听说,他杀了很多人。他因此臭名昭著。他是民兵头目之一,一个大人物。我们只是他的开始。对我们干的那些事,他都是拿来练手的。”
“他怎么样了?”
“他消失了。”萨加特瓦先生耸了耸肩,“许是藏起来了。许是死了。”
“你还想再见他吗?”
“见他作甚?”
“去理解。试着去宽恕……?”
“宽恕?”他笑了一声,突然饶有趣味地看着道格拉斯。只是到此刻,被人用暗沉沉的深邃目光盯着看,道格拉斯才意识到:萨加特瓦先生此前一直跟他没有眼神接触。“告诉我,”他说,“这样的人会得到宽恕吗?”
“会。”
“会?”
“伦纳德。萨加特瓦先生。听着。”他想说话的时候却没有了词。刚才听到的故事让他心情太沉重了。何况并不是个故事。所有的一切都曾发生过——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发生在这个男人身上。这都是真事。他看到的事情道格拉斯此生从未经历过。他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经历。
“上帝宽恕一切?”萨加特瓦先生说,语带尖刻的讥讽。
“是的……是的!你若求告,必宽恕。”
“没人求告。”
“不一定是你哥。萨加特瓦先生,你可以代他求告。你可以代你哥哥求得宽恕。”
“我不会宽恕他。”
“不必是现在。宽恕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是因为这个你才幸免于难……”
他开始说话的时候,感觉那些老套话冒了出来,当下觉得好多了。主在传话给他。
但萨加特瓦先生照旧又比划了一下,又砍又扔。他把道格拉斯的话打断在了半空中。
“永远不会,”他说,“永远,永远,永远。”
一声哨响。似从梦中醒来,道格拉斯听到了列车长的吆喝。尚在四周晃悠的几个人赶紧回到车上。他们就要启程了。
“哦,”道格拉斯说,“瞧啊……这么快……本以为要几个小时……”
匆匆离去不失为一种解脱。



车厢里,醉老头还在睡觉。对一切浑然不知:故障,等待,故事。火车慢慢开动起来,声音嘈杂。外面小站台的灯光向后移动,消失在视野里。
此刻,萨加特瓦先生没有去看道格拉斯。仿佛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让他俩互不搭理。他迅速脱下衣服,钻进自己的被窝,侧身对着墙壁。
道格拉斯却还是睡不着。他坐在车窗前,把脸压在一条缝隙上,感受着钻进来的冰凉空气。他想病上一场。外面,月光已经隐去。景色就像一条黑暗的河流,无休止地奔流而过。
早晨,他们相互之间又变得十分规矩和礼貌。甚至老头也礼貌起来。他坐在自己的角落里,羞愧难当,宿醉未去,身上一股子酒臭味。
萨加特瓦和道格拉斯彼此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他们忙着穿衣服,整理床铺,随后道格拉斯去了餐车,火车快到开普敦时才回来。桌山在头上方赫然可见。
火车停稳之前,萨加特瓦先生已经拿起小行李箱说再见了。他和两人都握了手,道格拉斯和老头,好像他两人并无差别。他感谢两人的陪伴。
“保持联系,”道格拉斯说,“如果想的话。你知道哪里能找到我。”
萨加特瓦先生点头,但又像是在摇头。然后他就走了。道格拉斯要抓紧时间离开车厢,也就由着他消失在人群里。他胡乱收拾着包,看着车窗外,很高兴老头问他要不要帮忙拿一下行李,确实是太重了。
于是他知道怎么布道了。全都会讲到:最初的难堪和敌意,其后的午夜坦陈,两兄弟的可怕故事(就像该隐和亚伯),甚至那个带有偏见的老头。这是一次真正的非洲布道。
过程十分顺利。对于自己的话怎么被人接受的,道格拉斯有种天生的感知力,一种演讲者的直觉。起初,他开始讲的时候,一排排饱经风霜的脸仰面看着他——都是些渔民,过着艰苦的难以想象的生活——满脸都是困惑。但随后他就感觉到:他们在听。听他讲。
他信心大增。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言辞简单,但饱含激情,发自内心。再后来,他站在那座小小的木教堂门外,他们排队走过去,跟这位新牧师打招呼,他能从他们微笑和使劲握他手的样子里感受到他们的热情。这让他非常激动。


当然,他必须改掉某些情节。没有故事,没有寓言,那就太像真实的生活了。所以,那个白人老头,比如说——道格拉斯让他的心灵最终发生了改变。萨加特瓦先生的彬彬有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自己的种族主义和怀疑抛到了一边。
接下来是宽恕的问题。不能由着萨加特瓦先生冷酷且充满仇恨:这是错误的启示。因此在道格拉斯的版本中,萨加特瓦先生软化了。他听完了道格拉斯不得不说的话,然后——不情不愿地,痛苦万分地——接受了。他双膝跪地,痛哭流涕。他说他宽恕了哥哥。对他来说不容易,可他知道他必须宽恕。
再接着道格拉斯谈到了自己。他告诉他们,他总是隔着距离看非洲,把非洲看成是身外的东西。可自打萨加特瓦先生说出真相那一刻,道格拉斯说他自己改变了。当他回到火车上看着窗外闪过的乡村景色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把非洲放在了心里。他和这块大陆合为一体了。
所以,这是三重救赎。希望的启示。道格拉斯铿锵有力地传递了出去。“一切皆可宽恕,”他对他们说,“没有任何犯罪、没有任何罪过,没有任何行为,是上帝——或我们——不能宽恕的。这取决于我们。我们有选择权。”
道格拉斯知道自己稍微调整了现实,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内疚。在他的心里,他笃信自己所言会成为现实。不管萨加特瓦先生当时多么愤怒,他仍有可能改变心意。种子已经种下。承蒙主的恩典,所有的自傲和伤害都能克服。
对于自己而言,道格拉斯感觉离非洲更近了。确实更近了。刚开始,他一直惧怕新职位,惧怕进入一个陌生的社区。但他着手与他们建立联系,体会他们的生活。他走出门,出没在小房子和棚屋之中;他跟人们交谈,跟他们一起吃饭,倾听他们的故事。非洲接纳了他,反之亦然。
他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他的是非意识清晰而深刻。
所以,当他再次看到萨加特瓦先生时,他惊着了,惊得翻天覆地。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已是他抵达后的几个月。他正在小厨房里忙活着做晚饭,背景里是闪烁的电视新闻,突然间评论中的什么事,一个名字或是某个细节,钻入了他的耳朵。他看向屏幕,他就在上面。
萨加特瓦先生戴着手铐,正被推进车里。新闻播音员严肃而冷漠的声音说,帕斯卡·萨加特瓦,一个来自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嫌疑犯,被人追踪到开普敦抓获归案。他很有可能要遣送回国接受审判。
错了,全都错了。道格拉斯握着菜刀,无力地站在厨房里。他对自己说:“不,不。”接着感到一阵虚弱,不得不坐了下来。
有那么一会儿,对这些乱七八糟和莫名其妙,对所发生事情的不公,他心里充满了愤怒。他们完全搞反了,真是个荒谬的错误,也许只有他才知道真实的故事。他心里思忖着,自己现在是不是有义务去当个证人,去开普敦把一切告诉他们。
随后,道格拉斯觉得不对劲儿,有些事很不对劲儿——他明白过来了。
全都是真的。他们说的他都是真的。他干了那些事:那些恐怖得超乎想象的事情。这个事实重击了道格拉斯,就像有人锤打了他的头骨。他歪着脑袋斜靠在椅背上,直到眼花的感觉从眼睛里消失。
他此刻胃口全无。他留下做了半拉的晚餐走出门,没头没脑地在街上瞎转。温暖的黄昏里,人们坐在外面,说着话,他的一些会众在他经过的时候招呼着他。他机械地挥手回应,思绪却在别处:去往开普敦的火车之旅,一路上发生的事情。他能清楚地记得所有的事,几乎一字不差。他心里一直断不了那种感觉,萨加特瓦先生伸臂时细瘦的胳膊,还有那只手臂,那只手,干过的事情。
不断冒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呀。不是为什么萨加特瓦先生干了那些坏事——恶总有其理由——而是为什么他要在事后跟道格拉斯说谎?为什么要跟他弟互换角色?道格拉斯不知道答案。没有明确的道德主题,没有促进精神升华的教诲可资学习。有的只是晦暗的动机和更多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退回到黑暗之中——一片他无法穿透的黑暗,那里面没有上帝的恩典。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少。凌晨某个时段,他辗转反侧,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了,驱车前往开普敦,前往法院。昨晚的电视上,他们说今天早晨会有一个关于引渡萨加特瓦先生的听证会。道格拉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他就是想在场。他觉得有这个必要。对他来说,如果能跟萨加特瓦先生说上两句,如果能站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后面的事情或许会向好。对他俩来说,或许都是如此。
但事非所愿。他是看到萨加特瓦先生了,却是隔得老远看了一眼。通往开普敦的道路严重拥堵,后面他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寻找车位。他赶到法院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听证会结束了,萨加特瓦先生输了。他将被送回卢旺达接受审判。

道格拉斯发现自己置身于拥挤的人群中,萨加特瓦先生给押走的时候,法院外的窄廊里挤满了听众、记者和摄影师。他的双手给铐在身后。他一如在火车上那般衣着整洁,还是戴着那副小小的圆形金边眼镜。
他经过的时候,他们的目光相交了片刻。转瞬即逝,意外一瞥。但在道格拉斯看来,萨加特瓦先生的表情也有同样微妙的变化:一丝阴影掠过他的脸庞。然后他走了,人群在他身后合拢起来。
仅此而已;只是一眼。随后,道格拉斯不得不开车回家。
他挑了条不太常用的远路,走了孤寂的沿海公路。那是个宁静的秋日,日光柔和而清澈,海鸥在头上方盘旋鸣叫。通常来说,这样的画面很能吸引他,一切那么美丽,但今天不成。世界颠倒了,如此陌生。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此刻,他想起讲故事前萨加特瓦先生说过的话,就是他只想讲一次,然后就走开。现在,在道格拉斯看来,这也许是萨加特瓦先生洗罪的一种方式:只想短暂地,在另一个人的心中,消除他所做的一切。你无法对上帝撒谎——上帝洞晓一切——但你可以对人撒谎。于是他选择了道格拉斯。
回来后,他把车停在教堂外面,在车里坐了许久。他不想进去;不动才安适。他可以看到坚硬的小尖塔和塔顶上高耸的十字架,但今天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安慰。它们似乎是奇特的象征,某种古老的失传的语言残留的符号,它们和他隔得那么远。

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1963—),南非小说家和剧作家,非洲新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为止,写过9部长篇、4部话剧以及为数众多的短篇,两次入围英语文学布克奖短名单。2021年,凭借小说《承诺》获得当年的布克奖。加尔古特的写作,基本围绕非洲尤其是南非的社会现实,用小说的方式书写沧桑的非洲历史,对于非洲当代的种族冲突、后殖民状况以及各种权力的角逐皆有所呈现。他的写作风格,或许是因为同时创作剧本的缘故,大多镜头感极强,对话简洁而富有力量。这一点在他的短篇小说《一次非洲布道》(An African Sermon)中,表现得十分充分。《一次非洲布道》原载于加拿大《海象》(The Warlus)文学杂志(2004年7—8月号)。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6期,责任编辑:胡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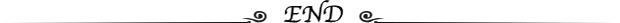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