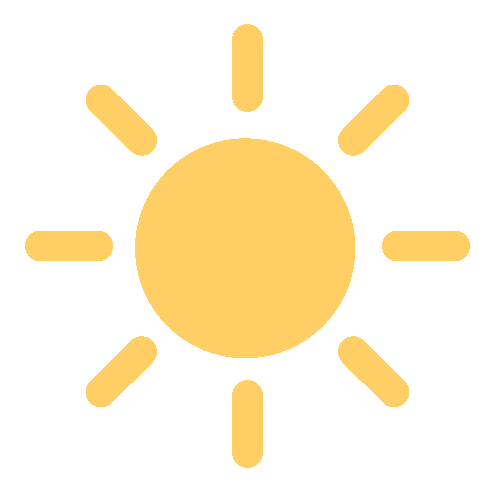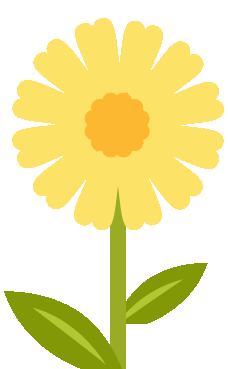新书快照 | 钟志清:《黑泽废墟》(S.伊兹哈尔著)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黑泽废墟》
【以色列】S.伊兹哈尔作 钟志清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当当购买链接请点击该文尾图

钟志清
伊兹哈尔(S. Yizhar)的《黑泽废墟》是我翻译的最为撼人心魄的现代希伯来语经典作品之一。
2008年秋冬之交,身为英国学术院访问学者的我从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最重要的英文译者、剑桥大学尼古拉斯·德朗士(Nicholas de Lange)教授手中拿到此书的英译本。德朗士教授还友好地在扉页上题写了“一位译者致另一位译者”几个字,我十分珍视译者之间的这种情谊,对这本小书更是爱不释手,甚至在从伦敦飞往北京的飞机上还在一丝不苟地阅读。但没想到,由于疲惫与匆忙,我到家后才发现此书不见了,几次致电机场,终究未果。尽管后来,我又从以色列合作伙伴的手中再次得到此书的英译本和希伯来文原版书(Zmora-Bitan Dvir Publishing House,笔者翻译时主要依据的便是这个文本);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我丢失德朗士教授赠书的遗憾。
值得回味的是,我第一次在以色列留学时,适逢奥兹在1996年冬天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讲的就是伊兹哈尔小说,但当时我还不能听懂奥兹的希伯来语讲座,只好在讲座之后回宿舍阅读资料,试图了解这位作家,也试图约见他,但他当时住在雷霍沃特,我住在特拉维夫,最终未能成行。
小说原名“Hirbet Hizah”指的是一个虚构的阿拉伯村庄。Hirbet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废墟”,Hizah是阿拉伯语的村庄名,此次采取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将书名译作《黑泽废墟》,能与文中描述的肮脏、阴暗的环境形成某种关照。最初阅读此书的感觉是,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但充分地体现了第一代本土以色列作家的创作特色,注重风光、景物与植被的描写,用优美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典型的巴勒斯坦地区风光图,为推进情节做铺垫。在语言上,伊兹哈尔的语言十分凝练,又不乏抒情之风。他喜欢把多个名词、动词、形容词连用,其间夹杂着大量的希伯来语日常用语、俚语、阿拉伯语词汇和《圣经》典故,给理解和翻译造成了极大难度。因此,当南京大学宋立宏教授推荐我把这部经典小说翻译成中文时,我开始十分犹豫。最后决定承担此项工作,也是出于我们这代学者对译介希伯来文学具有的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吧。在这里特别感谢宋立宏教授和浙江人民出版社汪芳女士的通力合作与支持。


伊兹哈尔(1916—2006)是公认的第一位以色列本土作家。以色列本土作家是指那些出生在巴勒斯坦,或虽然出生在流散地、但自幼来到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要研究当代以色列文学,他显然是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伊兹哈尔生于以色列中部的雷霍沃特,是俄国新移民的后裔,父亲杰夫·斯米兰斯基(Zeev Smilansky)既是教师、作家,又在农业聚居区务农,尽管他在果园里雇用阿拉伯工人,但是相信做“希伯来劳动者”乃犹太人回归土地的一个基本因素。伊兹哈尔的伯祖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最早表现阿拉伯问题的作家之一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其主张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舅舅约瑟夫•维茨(Joseph Weitz)则主张从阿拉伯人手里赎回土地,希望通过签订协议等手段使阿拉伯人放弃自己的地盘,让两个自然群体根据自己的自然属性与信仰分治而居。不过他们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做法感到震惊。在这样家庭长大的伊兹哈尔自幼把阿拉伯人视为巴勒斯坦天然的组成部分,就像他自己所说:“我看风景,并看到了风景中的阿拉伯人。”
伊兹哈尔曾系统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在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本人也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做过大学教授和国会议员。伊兹哈尔1938年便创作了第一个中篇小说《爱弗拉姆又变成苜蓿》(1938),标志着“本土文学”的诞生。在四五十年代,他相继发表《在内盖夫沙漠边缘》(1945)、《黑泽废墟》(1949)、《四短篇小说》(1959)等中、短篇小说集;《在洗革拉的日子》(1958)和《预先准备》(1992)等长篇小说,此外还写有儿童文学作品和大量随笔和非虚构类作品,曾获以色列奖等多种奖项。
伊兹哈尔既是以色列文学的奠基者,也是现代希伯来小说大师,他的创作标志着希伯来文学从犹太文学到以色列文学的变革。他曾亲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把这场战争称作“独立战争”,而巴勒斯坦人则将其称作“大灾难”。作为参战者,伊兹哈尔在创作中既写出了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也批判了以色列士兵在参与军事行动时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带来的灾难,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危机。其短篇小说《俘虏》和《黑泽废墟》堪称这类题材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俘虏》写于1948年11月战争后期,当时的战争局面已经扭转,以色列士兵已经从惧怕战争转为对取得胜利深信不疑。《俘虏》写的是一群以色列士兵在一位中士的带领下,前去执行抓捕阿拉伯俘虏的计划。在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驱使下,他们抓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贝都因人,即小说题目中所说的“俘虏”,对其进行轮番轰炸式的审讯,甚至用棍棒殴打他。后来,上方命令将俘虏转到另一个营地接受审讯,奉命执行转移俘虏任务的以色列士兵动了恻隐之心,想将俘虏放走,让他回去同家人团聚,但始终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篇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俘虏》在展现战争残酷性时没有大肆描写战争场面,而是刻意创造出与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格格不入的叙述方式。小说开篇,作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静谧淳朴的贝都因人生活画面,贝督因人作为一支游牧民族,与宁静的自然水乳交融:
远处的田间,人们正静静地牧着羊群,就像生活在没有邪恶,没有罪孽的美好往昔,看上去那么无忧无虑,悠闲自得。羊群在远处默默地啃着草,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时代的羊群一模一样。
作品中的“俘虏”是土著居民,与自然浑然一体。但是,战争破坏了宁静的田园生活,执行巡逻任务的以色列士兵破坏了这种宁静而和谐的生活。以色列士兵还将阿拉伯人从带有田园牧歌色彩的土地上带走,割断了阿拉伯人同土地的联系,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中蕴含的追求独立、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初衷。作者借讲述这一故事,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实现政治理想时造成的负面影响予以讽刺。
尽管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概念不同,但对建国后的以色列士兵来说均属于“他者”,增加了以色列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可以不无夸张地说,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负载着对以色列现实社会进行解说的功用,观念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在以色列“独立战争”的语境下,阿拉伯俘虏和以色列士兵分别代表着他们的民族。这两个世界的格格不入,象征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冲突的不可调和。以色列犹太人痛苦地意识到本民族的不足之处,这一理念不仅成为短篇小说《俘虏》的主导思想,而且成为日后当代以色列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


《俘虏》中反映出“独立战争”期间虐待阿拉伯人这一挑战以色列良知的事件,并触及新建以色列国家如何处理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黑泽废墟》则将这一系列问题更加明晰而尖锐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这部作品曾引起广泛争议。
这篇作品发表于1949年5月,当时正值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四个月之后。其情节围绕以色列人在战争期间驱赶阿拉伯村民展开。黑泽本来是一个虚构的阿拉伯村庄的名字,因作品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因而增强了现实感。加之曾经在1948年战争中做过情报官的伊兹哈尔本人一再声称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是他在1948年战争中亲眼看到的,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篇作品便带有了报告文学色彩。本质上看,小说是采用典型化的手法描写以色列1948年的战争对阿拉伯村民命运的影响,以及对参与战争行动的以色列士兵的心灵震撼。作品的细节是写实还是虚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所涉及的中心事件在战争期间具有典型性,黑泽废墟这个小村庄不过是战时被毁弃的数十个阿拉伯小村庄的冰山一角,村子里阿拉伯弱者的遭际代表着1940年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命运。正是从那时起,伊兹哈尔产生了道德危机意识。
小说所写的中心事件是征服、毁坏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其村民的军事行动。伊兹哈尔通过叙述人——一个年轻以色列士兵的眼睛详细地描述了以色列军队如何在命令到达之际朝黑泽废墟展开攻势,清洗其已经不见人影、空空荡荡的街巷,把尚未逃亡的一些村民带上卡车运走。与村子里阿拉伯老人、女人的正面接触成为推动情节并展开以色列士兵心灵冲突的一个途径。以色列士兵碰到的第一个阿拉伯人是一个长着白色短胡子的老人,他毕恭毕敬,摆出一副顺民的架势,希望以色列士兵允许他与自己驮着家居日用品的骆驼一起离去,但一个以色列军官却让他在生命与骆驼之间做出抉择,并承诺不会把阿拉伯人杀掉。以色列士兵在是否放走阿拉伯老人这件事情上意见不一,有些人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对于一个老人将其放走即可;但以阿里耶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称如果双方角色发生对换,那么自己肯定为阿拉伯人所害,竭力主张要置阿拉伯人于死地。从今天回看,这样的争论似乎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延续了数十年。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出,在阿以问题上,许多人依然坚信非黑即白、你死我活,表现出一种纯然的二元对立。折中主义或者左翼人士的主张尽管人道、理性,却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左为1948年萨法德被毁的阿拉伯房屋
右为1948年内盖夫被毁的阿拉伯村庄
PHOTO BY ZLOTAN KRUGER, THE ISRAELI NATIONAL PHOTOGRAPHS COLLECTION
以色列士兵面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阿拉伯村民而产生的心灵冲突,折射出过去数十年间以色列犹太人一直无法摆脱的自我意识与集体主义、良知与责任、个人信仰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围绕着究竟是否把阿拉伯村民从他们生存多年的村庄驱逐,运送到其他地方,使之永远不能回归这样一个放逐行动的争论、反省与类比中,这些矛盾达到了高潮。具体地说,作家描写了以色列士兵的心灵冲突,将这种冲突置于战争的背景之下,透视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具有道德意识的个体在国家利益与道德规范面前陷入举步维艰的二难境地。被迫参加驱逐行动的以色列士兵首先把驱逐阿拉伯村民之举视为“肮脏的工作”,随即向自己的指挥官发出抗议:“为什么要驱逐他们?”指挥官则回答说,“行动命令中就是那么说的。”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这在战争期间似乎成为一条准则。但是它与犹太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爱邻如己”的宗教理念、和阿拉伯人在一块土地上和平相处的复国理念、作为普通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发生抵触,因此以色列士兵对己方的行为发出谴责:“这确实不对。”“我们没有权利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说到底,叙述人所面临的这种道德困境实际上体现了伊兹哈尔本人在道德理念以及在1948年战争中身为犹太士兵应采取何种行动之间的冲突。在这方面,小说并没有给予清晰的审视,或者说,身为以色列犹太人,伊兹哈尔从内心深处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何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能否以道义手段对待另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问题始终无解的缘由所在。而近年的后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则直接认定以色列国家对巴勒斯坦灾难与创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理念中便有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计划。


战争挑战着人类良知与人类道德底线,难民问题是任何战争无法避免的问题。《黑泽废墟》涉猎的只是冰山一角。战争把难民问题白热化,阻止难民回归的政策也便应运而生,这便是战争的悲剧所在。从1948年阿以战争的交战结果上看,阿以双方均伤亡惨重。以色列阵亡人数约六千人,约占当时以色列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一;阿拉伯方面的阵亡人数约为以色列的二点五倍。在战争期间,有几十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遭到以色列士兵的驱逐,背井离乡,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近一半的阿拉伯村庄遭到毁坏。根据统计,在联合国分派给犹太国的领地上,曾经有大约85万阿拉伯人;但是到了战争结束后,只剩下大约16万人,这些阿拉伯人成为新建犹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而被毁坏的阿拉伯村庄有的成为以色列的耕地,有的成为犹太人定居点。
失去土地和家园无疑导致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也埋下了日后巴以冲突的祸根。小说通过对一个阿拉伯女子及其手中领着的一个七岁孩童的描写,典型地再现了被驱逐的阿拉伯百姓的悲伤、愤怒和潜在的仇恨。按照作家的描述,这位女子坚定,自制,脸上挂满泪珠,“似乎是唯一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人”。孩子也似乎在哭诉“你们对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的步态中似乎有一种呐喊、某种阴郁的指责。女子凭借勇气忍受痛苦,即使她的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废墟,可她不愿意在我们面前崩溃。而孩子的心中仿佛蕴涵着某种东西,某种待他长大之后可以化作他体内毒蛇的东西。
一些以色列作家在阅读这篇作品时,强调的是叙述人本身的人道主义敏感性,而不是驱逐阿拉伯难民的行动本身。比如,以色列左翼作家奥兹指出,这篇作品的主旨是叙述人剧烈的心理冲突,相形之下,阿拉伯人及其命运则退居到了从属地位。主人公所认同的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体系在这些冲突中面临着断裂。奥兹认为,由此可带来的经验并非将两个体系中的一个予以抛弃,而是要反对战争本身。



上图为:1948年的阿拉伯难民
下图为:1948年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人难民营
一部作品有时会唤起一个民族的良知。《黑泽废墟》不仅是希伯来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反映以色列独立战争历史的小说,而且成为以色列历史、至少是以色列集体记忆中一篇重要的文献,在以色列民族记忆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将历史书写、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历史含义这三个被犹太历史学家耶鲁沙米尔(Yosef Hayim Yerushalmi)视为《圣经》中相互关联的三个要素整合起来,且随着以色列社会与政治的变迁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历史学家阿尼塔·沙培拉(Anita Shapira)把小说所引起的公众回应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为1949年到1951年小说发表初期引起的争议阶段,当时的许多读者亲历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其关注焦点主要在战争期间的良知与道义问题上。当《黑泽废墟》与伊兹哈尔的另一个短篇小说《俘虏》在1949年9月结集出版后,很快便成为畅销之作。到1951年4月为止,便已经出售4354册,而且出现了大量的书评和评论文章,多数批评家赞赏伊兹哈尔作品的文学品质,比如,作家描述事件的能力、独特的风格、士兵们在会话中使用希伯来口语进行交流、自然风光的描绘乃至描写阿拉伯人的方式等,但对作品的内容与理解上却表现出多元倾向。其富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多数批评家称赞作家的坦诚,有勇气公开士兵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赞扬其道德立场。认为这篇作品向年轻一代表明,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人道主义意识不能麻木,反映出有良知作家的内在痛苦,等等;二、一些批评家相信,伊兹哈尔披露了以色列独立战争后人们不仅目睹了新建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同时又趋于野蛮、把基本的道德价值踩在脚下的过程。他敏锐地意识到“昨天受折磨的受难者变成眼下捡起皮鞭折磨人的人,昨天遭驱逐的人而今在驱逐别人。那些多少世纪遭受非正义对待的人自己变成了迫害者”;三、但也有一些批评之音,批评家们认为事件本身不具有代表性,伊兹哈尔过于片面,他把阿拉伯人描写为无辜的任人摆布的羔羊,没有提到阿拉伯人经常制造恐怖活动、屠杀犹太人的行径。1964年,这部作品成为以色列中学生的选读读物,但学校并没有让学生分析作品的道德冲突,而是分析作家创作的形式与审美。
第二阶段是1978年围绕《黑泽废墟》电视脚本的上演与否展开的激烈争论。事情的导火线在于1978年,一向对歧视、社会不平等、战争伦理与以色列的贫穷问题等主题感兴趣的导演拉姆·莱维(Lam Levy)将丹妮埃拉·卡米(Daniella Carmi)根据《黑泽废墟》改编的脚本拍成电视片,且邀请了四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担任演员,扮演包括带小孩的阿拉伯女子在内的角色。与小说相比,影片显得比较柔和,甚至加进了小说中并不存在的年轻女话务员达利亚与青年军官调情、相恋等细节,给乏味的军旅生涯带来了几分浪漫色彩。影片以充满乡愁的柔和的口哨音拉开序幕,随之画面立即转向嘈杂的军事基地,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士兵们接受命令前去征服阿拉伯村庄。对此,阿拉伯村民没有任何抵抗,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造成小说记忆与影视记忆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现实环境发生了变化。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范围内逐步确立了其合法性,舒缓了其民众的心理压力;其次,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使得以色列人意识到流亡中的犹太人在欧洲的无助,对犹太人的流亡体验报以同情和理解,乃至与当地阿拉伯人的生存境遇发生共情;第三,就在电影拍摄期间,以色列正在与埃及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进程的开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冲突。


但是,当时以贝京(Menaḥem Begin)为首的右翼政府将这部作品视为反以色列的宣传素材。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在电视片上演前夕下令禁演,20多位作家对此提出抗议。这一事件不仅涉及到媒体自由问题,也涉及到以色列公共生活是否有道德勇气进行真正的自我评估问题。人们甚至把请愿书送到了高级法院。反对派中一个名叫马克• 塞戈尔(Mark Segel)的新闻记者指出,电视片制作人的目的并非是要艺术地再现战争,而是要表明犹太人是侵略者,阿拉伯人是烈士,进而具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含义。一位以色列国会议员甚至主张,这部纪录片应该与阿拉伯人屠杀以色列人的纪录片一起上演。最后,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取消了禁令,电视片在以色列得以公演,引起轩然大波,作家、导演和编剧均受到了攻击。
如果说围绕影片能否上演的争论集中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否拥有媒体自由等问题,那么脚本内容的重构则表现出以色列一批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比如,在小说中,叙述人的反战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战友的认同,甚至遭到一些战友的质疑。但在影片中,以色列士兵似乎表现得更为人道。即使在射杀逃跑的阿拉伯人时,故意不瞄准,表现出不愿伤害阿拉伯人的主观愿望(而小说中的阿拉伯人显然被打伤)。影片中的军官曾给阿拉伯人送水,一个士兵甚至给阿拉伯人食物(相形之下,小说中的以色列士兵则显得比较冷酷,甚至听任瘸子趟过水坑)。从某种意义上,电影是把小说中以色列人内在的心灵冲突以画面形式呈现出来。同时揭示出清理村庄的真实目的并非把阿拉伯村庄赶走,而是要把阿拉伯村庄转化为犹太人定居点。由此引发了影片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影片中反映的事件是否在独立战争时期具有普遍性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其中还涉猎到为什么影片只表现了以色列军人驱逐阿拉伯难民,而没有表现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所施行的种种暴行?为什么要重揭旧日创伤?等等。一些人甚至对作品本身提出质疑,认为它曲解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形象。尤其是把以色列人用卡车运送阿拉伯人的行动比作犹太人在历史上被迫经历的死亡之旅,更令一些人无法接受,认为会给以色列的敌人以口实。从这个意义上,本来是根据反映个体以色列士兵的心灵传记改编的影片却变成带有集体记忆色彩的重构历史的文献。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则更多的是历史事件本身,而不是以色列士兵针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回应与心灵震撼。进而导致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这部电视片缺乏艺术优长。
右翼人士认为,犹太人渴望并应该回到先祖生存的土地上,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做法,这是历次中东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1948年战争对以色列人来说,确实是一场生死之战。影片却脱离了1948年的历史语境,使人们的讨论从以色列究竟可以继续存在还是会遭到毁灭的问题转向巴勒斯坦人的生存问题上来,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势必造成对作品本身的某种曲解。左翼人士则认为纪录片本身反映了战争悲剧,引发对巴勒斯坦难民这一必须直面的问题的讨论。
《黑泽废墟》的上演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以色列人对1948年战争的记忆,这部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上映后,以色列国内外的观众会认为自回归锡安运动开始以来,犹太人的行动基本上就是赶走阿拉伯人、杀害无辜、驱逐老人、妇女和孩子。但是,正像犹太历史学家沙佩拉指出,并非是《黑泽废墟》小说或影片本身破坏了以色列人的声誉,而是把一个民族从其土地上赶走这个行动本身是不光彩的,定居到人家的居住地的行动是耻辱的。伊兹哈尔的小说反映出独立战争时期的历史真实,批评这篇小说与阻止其电影脚本的上演无异于试图掩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实现自己返回锡安的梦想过程中的劣迹。就像奥兹所剖析的那样,“我们的做法就像把一具死尸藏在地下室里”,“我们正在掩饰将要化脓的伤口”。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以色列人正是在复国与负疚的困扰中不得释怀。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黑泽废墟》在参加过以色列独立战争的人们中间引发的是一场道义的争论,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色列经历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后,政治现实又发生了变化,新历史主义思潮兴起,曾经伴随着1948年战争结束而淡出人们观察视野的诸多问题此时又浮出地表,以色列人更为关注的则是由道义延伸开来的国家政治形象问题,以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问题。战争历史本身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对战争的解析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在这方面,以伊兹哈尔为代表的一批希伯来语作家,如塔木兹、奥兹、约书亚等人带着道德勇气,采用多种艺术手法诠释了七十余年来以色列历史、记忆与以色列人的心灵冲突。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既蕴含着深邃的历史记忆,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回响,表现出具有良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兹在访问中国时直陈其“两国论”的主张,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与以色列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则代表着左翼知识分子对巴以两个民族和平前景的期待。
钟志清
2023年2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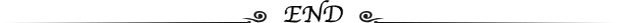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