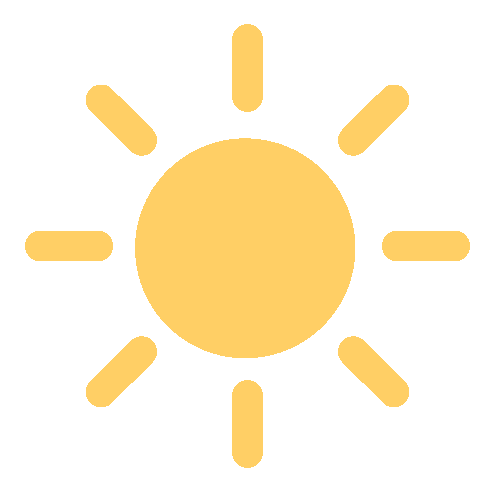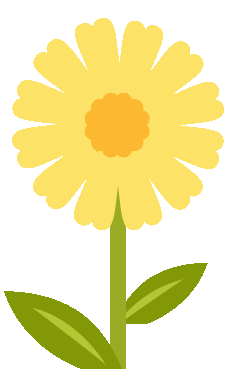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巴•道格米德【蒙古国】:面对逆境,人的生命就像用公牛的鬃毛编成的绳子,非常结实……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深受内伤,脸色苍白的逃犯心里乱如麻,他缓缓走向远处黑压压的森林。几刻钟之后,一声枪响震落了老松树枝头上的雪,像是在要填平世间的善与恶。躺在雪地上的乌鸦受了惊吓,扑棱几下翅膀,也没有飞起来。
恶魔
巴·道格米德作
照日格图译
夕阳西下时三头狼走出北边的山林,在大地下霜变白时顺着灌木丛一路小跑。它们已经有几天没有闻到血腥味了,个个饥饿至极。走在中间的那头狼抬起硕大的头,用饥饿的眼神小心观察周围。它浑身铁青色,后背高大,脖颈短粗,看起来雄壮有力。这只雄狼像是听到了什么动静,闻闻地面,在原地稍作停顿后又跑起来,身后扬起雪花。
一串脚印从远处来,穿过山林外的雪地,进了北边朦胧的高山上那片黑压压的原始森林。无意间看到一个人新鲜脚印的三头宝海【宝海:狼的忌称】。聚集到一起,各自舔了舔嘴唇,咬住牙,用沙哑的声音发出低沉而悠长的嚎叫。狼的叫声飘过深山上的松树梢,似乎引来了吹向山麓的暴风。
一轮红月亮从山梁黑乎乎的树林里升起来,在这荒野真叫人害怕。一个高个子急匆匆地迈大步前进,像是被人追赶,不时地回头看。他身穿带帽的棉斗篷,用皮带紧紧扣住腰部和肚子,毛线围脖严严实实地裹着头部,胡子上结了霜。




夜幕降临,风静下来,世界静得吓人。脚下变硬的积雪发出冷色的光,头顶的星群冷冷地闪烁着。月光下,积雪反射出微微的蓝光,河谷里的冰面崩裂,发出嗒嗒声。跑得浑身燥热的汉子停下来,解开裹脚布又重新包好,从口袋里拿出烟叶小心翼翼地卷在被揉烂的报纸里。他划一根火柴,用大手挡住风,点着了烟站起来,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某种肉食动物红红的眼睛。他打了一个冷颤,回头一看,发现一匹两岁牛犊那么大的雄狼正横在路上。他确定那是狼,吓得每一根汗毛都立起来,想大喊,嘴里却发不出任何声响。他后悔为什么手里没拿个家伙,哪怕是一根木棍。他果断从靴筒里抽出了刀。那是一把很钝的匕首。有这么一把匕首,就不必害怕了,一怕就出事。这一切这三头狼可都看在眼里。在大牢里,他可赤手空拳打倒过一起扑上来的三个盗贼,用他们的鲜血洗手,威震过四海。听说狼只在深夜或清晨的时候攻击人,现在时间还早呢,应该不会扑过来。想办法进林子里去,进了树林,肯定能想出对付它们的办法。他慢慢退步,接近了那片黑压压的原始森林。狼跟着他走了几步后,对着月亮和星星嚎叫,那叫声着实令人生出懔懔寒意。从没过膝盖的大雪里找家伙,这事儿想都不用想。对于又累又急的他来说,林子也并不在近处。他回头,发现夜幕已完全降临,那头狼也在一步步接近他,而前面的林子似乎自己在向后挪。他越想越怕,呼吸加速。逃犯的左边突然冒出了两条狼,像家犬一样鼻子贴着地面小跑着。有三头狼在明处,很难猜出暗处还有多少匹狼在等着他。左边的那两头狼眼睛发出绿光,翘起尾巴小跑,等待着富有实战经验的那头雄狼发号施令。它们闻着雪追逐嬉戏,显然是在为意外的夜宵欢呼,也嘲笑这个手无利器的家伙跑不了多远了。


他的脚碰到老松树的枝头,抖落树枝上面的雪,地上的火堆完全被扑灭,冒起白烟。三头饿狼守在树下,看他骑在树枝上默默吸烟,后悔没有在他上树之前结果他。狼都嘲笑那些不走运、一事无成之人。他没有在阳光下自由呼吸过。这里除了几头野猪再看不到什么别的了。不知道天亮之后那三匹狼会不会弃他而去。现在刮着大风,如果在树枝上这么一动不动地坐下去,估计一会儿就会冻死。该死的,如果我冻死,全是因为树下这三匹狼。等待一事无成的人的,总是这样的厄运。原来佛祖是会惩罚心术不正、恶贯满盈的人的。他刚刚还在出汗的身体开始冷却,湿透的衣服变得冰冷冷的。一阵阵的风吹过来,树枝在风中呼啸,“冻死”的念头在他脑海里像风暴一样打着旋儿。他靠着树,在两根较粗大的树枝之间坐好,试图打个盹儿,哪怕时间很短。现在不必怕落入狼口,怕的是冻僵。三头狼的好奇心逐渐减少,它们在灌木丛下撒尿标记,用利爪挠树根,争夺母狼,用力嚎叫,张牙舞爪,气势十足。听说,大冷天鸟儿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地坐久了,就会像秋天熟透的菠萝一样落下去。我不会也那样,活活成了狼的美食吧。如果那样,还不如趁自己还有点气力,下去和它们拼个你死我活呢。如果今天没这暴风肆虐就好了。不过天亮之后总会有办法,说不定还能遇见个人呢。他这样想着,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对于等待的人来说,冬夜多么漫长。如果手头有麻绳,就可以把树下的狼给吊死。愚笨的人总是喜欢马后炮,想到这些他懊恼不已。如果是无风的静夜,他双层的棉衣,手工毡靴,还有刚过三十的身体会带他见明日的太阳。可如今在树上,就等于在等死。如果大牢里的那些人知道我现在的窘相,一定会很满足,还会嘲笑我。他们根本不关心我的死活。也许有人会管,不过那一定是为了救死扶伤的美誉和抓住逃犯立功劳才肯那样做。他们说的逃犯,不过是一个无法赶走三匹狼的孬种而已。如果语言相通,狼和贼一定能走到一起。可是他们分属人兽两界,实在是没有办法。面对数头饿狼,用金银贿赂、晓之以利都是不可能的事,就像盗贼爱银子一样,饿狼需要吃肉,这毋庸置疑。就算它们前面有一头牛,它们也一定先把我干倒才安心,这是它们的本能。树下的两匹狼也疲惫不堪,竟枕着腿,伸个懒腰躺在地上等起来。嘴角又黑又下垂,狼牙细长的雄狼蹲坐在那里,用沙哑的声音嚎叫一声,挠挠自己,又舔了舔鼻子,看来已有些不耐烦了。对它来说,我比那些钱更实用。钱没有了可以再挣。任何一个笨蛋都不会为了钱卖了自己,好死不如赖活啊。谁死了,最后的命运都是化成一堆白骨。如果没有雪,就可以一把火烧了树下的草和干枯的青苔,我就可以趁着火势逃之夭夭。黎明破晓前风势变大,到了人与兽所能承受的底线。不知为什么,他天真地认为,如果能熬到日出,就可以摆脱这几头狼。如果能够活着逃出去,回去加刑也好。男人总会在小事上犯错。比起这里,躺在大牢的床上,盖着暖和的棉被胡思乱想舒服多了。
经历一些事情,人们才知道后悔。面对逆境,人的生命就像用公牛的鬃毛编成的绳子,非常结实。朦朦胧胧中,月亮已西下,星辰变得稀少,东方开始微微发白。黎明在树枝上摇曳。黎明像领着多条猎狗的老猎人,驱散了他心中的恐惧,给了他希望。胡子、眉毛、后背结霜发白的三头狼站起来,伸伸懒腰,愉快地彼此追逐。一只乌鸦悄无声息地飞过来,飞过他头顶时叫了一声,落在旁边的树枝上梳理羽毛,像是在等着饱餐一顿。逃犯抬起头,伸展僵硬的手脚。那只乌鸦警觉地飞出很远,落在另一棵树上,呱呱叫起来。狼和乌鸦皆是不祥之物。乌鸦的雏鸟洁白一身,可爱至极,只是有了思想和羽毛之后它就完全被黑色覆盖。做梦都想吃一口温热肉食的乌鸦还在那里叫着。人们都说乌鸦和警察聚集的地方一定不会发生什么好事。逃犯骂道,你们除了闻闻我的味儿,休想得到任何东西。浑身舒展之后三匹狼蹲在树下看树上的人。如果他们能够听得懂彼此的语言,那三头狼似乎有办法让树上的人下来。
约二百米以外的乌鸦忽然扑棱翅膀飞起来。与此同时,一声枪响,子弹呼啸而来。守在树下的饿狼们拼命逃跑,那头硕大的雄狼流着血,脚步踉踉跄跄,倒在雪地上。得意忘形的逃犯真想大喊一声,可张大了嘴,呼吸变得局促,喉咙眼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未能发出一点声响。逃犯擦了擦眼泪,看到枪响处有一个人正往这边跑过来。他身穿军大衣,脚上踩着滑雪板。走近了才知道那是年轻的狱警。他的睫毛上结了霜,喘着粗气脱了滑雪板,从树下眯着眼看了看他,说:“你还好吗?越狱的滋味不好受吧?都来了释放通知,你怎么还越狱了呢?是想成为狼群的美餐吧?别坐那儿了,快下来吧,我们回去!”
“我不下去,我哪儿有脸回去?被狼吃了倒干净。”
“少装了。不是告诉你,你的释放通知都下来了吗?”
树上的那个家伙并不怎么相信他,眯着小眼睛挤出微笑,说:“你当我是小孩子啊?我可不相信你的鬼话。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你把枪和食物留下,我们各走各的路。”
“谁骗你了?你还嫌麻烦不够大?如果再耗下去,我就开枪了。”
逃犯发出猫头鹰一样的笑声,说:“这主意不错。你给我一枪吧!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枪吧。死在狼嘴里,不如一枪被你给毙了。我下去也走不动,双腿僵硬,都不能动了。”
狱警拾起树枝点火,从手提袋里拿出马肉。
“我来背你,你赶紧下来。”
“我说过了,我不下去。如果你不把枪放在这儿离去,我就在这里吊死好了。我用皮带系好,往下一跳就一命呜呼了,到时候你可少不了官司缠身。”
“你是想吓唬我?那你就别费力气了。还不如下来吃点东西暖暖身子。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们还有一队人在巡山。想着给我官司吃,还不如乖乖地回去。”
“你别说得那么天真。就算有释放通知,可我现在又是逃犯了,不会放我出去的。”

这个年轻人想骗我回去。我不是狼,是人啊。这么几句鬼话,怎么能骗得了我?我可是老油条了。逃犯突然想下去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就说:“好了,我不为难你了。下去吧,饿死我了。”说着,顺着树干滑下来。
他们俩坐在有狼尿的石头上,在军用炊具里烧雪水喝,吃肥嫩的马肉。喝开水浑身热起来之后逃犯脱掉靴子,把毫无血色的腿脚伸进积雪里。年轻的狱警用雪给他搓脚,他的脚才有了一点知觉。他们准备走,逃犯刚站起来便大叫一声摔下去。
森林里的积雪还没有硬,年轻的狱警背着这位庞然大物艰难前进,浑身已被汗水湿透。装病趴在别人背上的逃犯困意十足,眼皮开始打架。他想到自己的钱,像喝了烈酒一样欲望迅速被点燃,一夜没有休息好的身子骨也精神了很多。年轻的狱警衣服已被汗水湿透,身体也在渐渐乏力。那些醉鬼和疲惫至极的人,只要往头上来那么一下,就会倒下,这一点逃犯再清楚不过。
恶人身后总是跟着邪念,草菅人命,把杀人当成是打盹。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而且还是狱警。你就这么走下去吧,等你走累了,你老哥我就给你那么一下子,你就可以彻底休息了。
年轻狱警疲惫不堪,把逃犯放下来,扇了扇衣襟。突然,后脑勺被什么钝器重击一下,身体找不到平衡,感觉乾坤倒转,双手抱头摔了下去。发狂的逃犯看着耳朵流血的狱警,取了他的枪支和手提袋,若无其事地点了烟,向远处朦胧的灌木丛那边大步走去。
逃犯在大雪里走了几步回头一望,刚刚还背着他前行的年轻狱警此刻躺在雪地里,纹丝不动。黄昏时分,这里的野狼会活活吃了他。逃犯想起他私藏的钱,走到昨晚过夜的那棵老松树下。松树的枝头又粗又大,阳光在枝头间愉快地闪耀,让人心生敬畏。雄狼躺在树旁,龇牙咧嘴,微风吹动它深灰色的毛,看起来还活着。如果你还活着,我会把你吊起来,活活给你扒皮,让你受尽折磨。
对于这个走在山林里的逃犯,棉衣的用处不亚于枪支。在树枝上冻了一晚上,他才知道棉衣这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他很后悔没有脱下年轻狱警的大衣。对死到临头的他来说,大衣完全多余,衣服只对活人起作用,死后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万物似乎都没有看到这白雪皑皑的森林里发生了什么,静悄悄的。
风雪四处肆虐,北方的灌木丛和森林黑压压地一片。
在清晨疾步行走的逃犯,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危险信号,立刻站住,回头望。他看到那只乌鸦就在近处飞起来又落下,这让他心中生疑。乌鸦落在年轻狱警身边,正梳理着它的羽毛。
清晨飞来落在树上的那只不祥之鸟,正准备用它那长喙啄食年轻狱警的眼珠。
逃犯大喊:“唉哟,别啄了眼睛!”紧跑了几步,卸下背上的枪,瞄准那黑色的乌鸦,扣动扳机。乌鸦惊飞,黑羽毛散落在洁白的雪地上。
逃犯跑过去,看到狱警微微张嘴说着什么,沾满鲜血的头部都不像是活人的了,脸上,鬓角还在流血。他不忍再看,枪口对准狱警的头部,扣动扳机。
一声枪响,子弹打到冰冻的地面,弹向天空。头部被打开花的年轻狱警抽搐了几下,拖长声音叫了一声,再也没有动弹。脸色苍白的逃犯,此刻已无暇顾及脱下狱警身上的大衣。他用石头般的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转过身,缓慢走远。


身受重伤,躺在雪地上的乌鸦用暗淡的眼睛看了一眼逃犯。他拿着枪,像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往前走。遭雷劈,浑身失去知觉的人才这样。
深受内伤,脸色苍白的逃犯心里乱如麻,他缓缓走向远处黑压压的森林。几刻钟之后,一声枪响震落了老松树枝头上的雪,像是在要填平世间的善与恶。躺在雪地上的乌鸦受了惊吓,扑棱几下翅膀,也没有飞起来。
这一切,谁都没有看到。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ND
巴·道格米德(1945—),蒙古国著名作家,记者,生于东戈壁省阿勒坦希雷县。1962年中学毕业,在中专就读经济学专业。主要作品集有《神马》(1970)、《蓝幽幽》(1974)、《火红的神驹》(1986)、《饮水思源》(1991)、《乱世活佛》(1992)、《终成眷属》(1993)以及长篇小说《视死如归》(2004),电影剧本《情泪未干》(1993)等。作品《饮水思源》1999年获蒙古国作家协会奖,2006年获苏赫巴托奖,2007年获“文化功勋作家”称号。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5期,责任编辑:秦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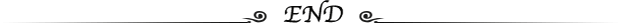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