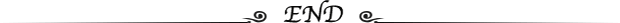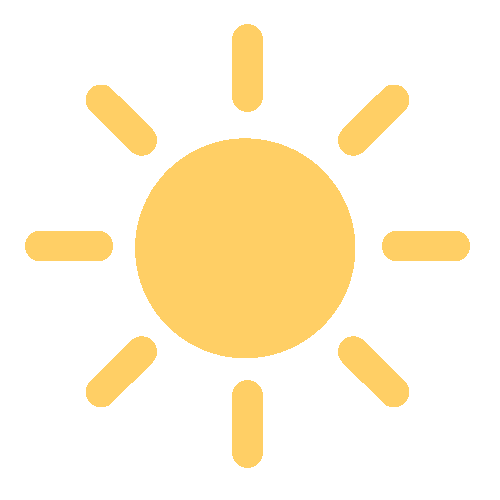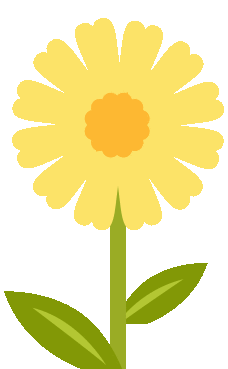众家言说 | 约•弗莱彻【美国】:对自由诗的理性解释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的回应是,自由诗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诗体获得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它让诗人自我建造形式的能力有发挥的空间,不用陈旧的形式(比如十四行诗)来妨碍他。它允许诗人随意改变节奏,只要基本的节奏还保存下来。

约翰·弗莱彻作 李国辉译
对于自由诗这种复杂的现象,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理性的解释。自从意象主义诗人大约在五年前走上舞台(他们随之讨论调子,以及他们自由试验各种形式的旨趣),人们已经写下为数众多的文章来支持或者反对自由诗,有很多英国和美国的作者——好的,坏的,或者无所谓好坏的——显示出从格律诗的旧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趋向。但是没人试图清楚、简洁地解释“自由诗”是什么,以便让普通人也能了解它。
在美国,坚守这个阵地的最新的理论,只是让困惑变得更深了。这是维廉·莫里森·帕特森教授【威廉·莫里森·帕特森(1880—?),美国学者,曾于1916年出版《散文的节奏》,随后得到过洛厄尔的响应】的理论,他现在是自由诗的后盾,在这一点上并不弱于埃米·洛厄尔女士。洛厄尔女士较早的理论,即诗节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圆环,有的进行得快,有的根据意愿进行得慢,它对于外行来说可能相当困难;但是帕特森博士的新理论还要难些。他告诉我们,诗体至少包括六种形式:格律诗、整体诗(unitary verse)、分行散文(spaced prose)、复调散文(polyphonic prose)、拼贴(mosaics)和混合(blends)。未来,大众显然必须要对着留声机念一念他们喜欢的每一首诗,以便弄清楚它是哪种诗体。测试、记录好它的时间间隔、切分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就能用上面的某个标签来给它归类。这种想法倒别出心裁,但是我们想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在这繁忙的日子里耗费这么多时间。



埃米·洛厄尔(左)与约翰·弗莱彻(右)
因而让我们离开这种实验室的氛围,试着弄清楚当诗人谈论自由诗的时候,他们指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要注意的要点,从逻辑上看,并没有绝对自由的诗体,这与不可能有绝对自由的散文相同。一个诗体(verse)必须具有某种形式和节奏,而且这种形式和节奏对眼睛和耳朵二者来说,必须比散文的形式和节奏更圆转,更强烈,更明显。举一个与此相应的音乐的例子。莫扎特的咏叹调(aria)可能有两个或三个不同的旋律,但是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们重复着、修饰着,最终汇聚起来,此时咏叹调本身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整体。另一方面,从瓦格纳的《指环》(尼伯龙根的指环)抽出的任何一个长的片段,都会揭示这种事实,即这里除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乐段,别无它物——我们可以称其为主题(motives)——它们不停地在变换。莫扎特的方法,因而是诗人的方法,瓦格纳的是散文作家的方法。
设置好这个重要的区别,我们随后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诗人要提自由诗呢?如果从逻辑上看,没有诗体是自由的——除了诗在没有形式、没有节奏、没有均衡的情况下写出来,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要对不存在的东西心烦意乱呢?顺便说一下,同样的争论,大约一年前就出现在英文杂志上,而我正好是唯一一个回应它的人。我的回应是,自由诗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诗体获得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它让诗人自我建造形式的能力有发挥的空间,不用陈旧的形式(比如十四行诗)来妨碍他。它允许诗人随意改变节奏,只要基本的节奏还保存下来。
举例说明。下面是是一首短的自由诗,它的结构相对简单些。我将重音标示在诗行上面,以便说明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I have fléd awáy into déserts,
I have hídden mysélf from yóu,
Ló, you álways át my síde!
I’cannot sháke myself frée.
Iń the frósty evéning
Wíth your cóld eyes you sit wátching,
Láughing, húngering still for mé;
I will ópen my heárt and gíve you
áll of my blóod, at lást.
我已经逃到沙漠里面,
我已经躲着你,
看,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无法解脱自己。
在结霜的夜晚
你用寒冷的眼睛看着我,
朝我笑,仍旧念着我;
我将打开心扉,最后
给你我全部的生命。
这首诗首先要注意的,是每行严格地有相同数量的拍子——即三个【注意第三行诗中出现了四个重音,而非三个。这其实与弗莱彻的拍子的一致性相矛盾,但并不妨碍弗莱彻整体层面的理论建构】。拍子间的音节数量是变化的——因而拍子的产生也不同,有时是轻重律,有时是重重律,有时是轻轻重律,诸如此类——但是一致性(即拍子的数量要一直等同)这个首要原则坚持不变。
现在分开来谈每一行。第一行相对简单,它给这首诗带来主要的拍子。第二行重复了它,但略有变化,倒数第二行又加以重复:
I have fléd awáy into déserts,
I have hídden mysélf from yóu……
I will ópen my heárt and gíve you.
我已经逃到沙漠里面,
我已经躲着你……
我将打开心扉……
这些诗行带来的效果几乎相同;由此,我们展现了一致性的第二原则,基本节奏的原则。
有人可能会问,剩下的诗行要怎样建造?从第三行到第八行,以及最后一行,诗行构造上有重重律和重轻轻的节奏群,这跟别的轻重律和轻轻重律诗行一样明显。这不会破坏你谈了那么多的一致性?



根本不会。第二个节奏群恰好让我们触及自由诗最为重要的法则——对比平衡原则(the law of balanced contrast)。不同音律起源的诗行用在自由诗中,正如贝多芬或者莫扎特交响乐中的第一和第二主题一样。让我们检验一下。
最早宣告诗歌第二主题出现的诗行,是下面的:
Ló, you álways át my síde!
看,你一直在我身边!
这个诗行与宣告第一主题出现的诗行完全相反,不仅在音律形式上相反,而且在情调上也是这样:
I have fléd awáy into déserts,
我已经逃到沙漠里面,
这两行诗共同构成了这首诗的核心。剩下的诗行是它们的变化、增广、修饰。比如:
Lo, you always at my side!
Laughing, hungering still for me;
看,你一直在我身边!
朝我笑,仍旧念着我;
这两行诗被中间的四行诗相互隔开【其实它们中间只相隔三行诗】,难道它们不是音律模式完全相同的诗行?难道相同的主题(中间的诗行稍有不同)没有在“我无法解脱自己”里重复?而“在结霜的夜晚”里难道没有一个不同的结尾,“给你我全部的生命”不也是这样?
如果我这样写:
In the frosty evening
All of my blood at last
Sorrowing and grieving
For the vanished past.
结霜的夜晚
我全部的生命最终
为消逝的过去
而忧愁、悲伤。
无疑,我就会写出打油诗来,但我做了音律学家要求诗人做的事情——我维护了重音产生的规律性,他们把这看作是诗歌所必须的。因而,谁能说(就像有些人说过的那样)自由诗没有音律的一致性,没有诗歌所依赖的规律性呢?Ars est celare artem(艺术就是要掩藏艺术)。我们不能根据节拍器来测量诗歌,更不能像帕特森博士想让我们做的那样,用留声机来给它分类。
还有一个诗行需要考察,这是:
Wíth your cóld eyes you sit wátching,
你用寒冷的眼睛看着我,
我给上面这行诗标了三个重音,明显,这种读法对某些人来说是不舒服的。一个长音节本身没有重音,但是因为语调强调了它,就获得了一个稍轻的重音,“with”(用)就是这种现象。“cold”(寒冷)可能也同样如此。这让人想起《麦克白》中的一句名诗:
Tóad that únder cold stóne
冰冷石头下的蟾蜍【该诗选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为第四幕第一场中的对白】
“eyes”(眼睛)也可能有重音,就像刚刚引用的诗行中的“stones”(石头)一样。因而我们就有了下面的诗行:
Wíth your cóld eyés you sit wátching,
你用寒冷的眼睛看着我,
这个读法带给我们四个拍子——或者三个半拍子,如果我们认识到“with”(用)上的重音,不如“cold”(寒冷)或者“eye”(眼睛)或者“watching”(看)上的重音那样重要的话——这种读法可能大多数读者会更加满意。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行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挂留的诗行(suspended line)【挂留(suspended)是和声学中的术语,它指一个正常的和弦中的一个音符延续到新的和弦中来——这随即能产生不和谐的效果。比如CEG的大三和弦,如果C被挂留下来,可能与新的和弦中的D或者F音构成不和谐的效果,因为这些音构成的是二度音程或四度音程,而非原来的三度音程。弗莱彻这里的“挂留的诗行”与挂留和弦有类同性,它指一个诗行保留了前面基本的节奏调子(比如轻重节奏、轻轻重节奏),但同时又含有新的节奏调子(比如重轻节奏、重轻轻节奏),因而产生出不和谐的效果。在弗莱彻的例子中,“with you cold eyes”,是新的节奏调子,属于重轻和重重节奏,而“you sit watching”则挂留了前面的节奏调子,即轻轻重节奏】,它同时具有第一组(由第一、二行和倒数第二行构成)和第二组(由剩余的诗行构成)的某些特征。它与倒数第二行有特别的联系:
I will open my heart and give you
我将打开心扉……
不用语词音乐的专家来判断,这一行的运动与下面的是紧密并行的:
With your cold eyes you sit watching,
你用寒冷的眼睛看着我,
因而,这里我们有了在音乐乐句中所称的“解决”【解决(resolution),和声学术语,当出现不和谐的挂留和弦时,恢复原来的音程关系,即为挂留和弦的解决。弗莱彻这里所说的诗行的解决,指的是倒数第二个诗行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轻重、轻轻重节奏】。这行诗是我们建立起来的语词拱形建筑的拱顶石。它将诗中相反的主题、情调、乐句结合起来,把它们焊接成一体。



我们因而可以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下面的规则,它左右着任何一首自由诗的写作:
(一)就像格律诗一样,自由诗体的诗篇依赖节奏的一致和均等;但是这种一致不是拍子的平均连续,像节拍器那样,而是音律来源不同的同等拍值诗行的对等。
(二)当一首自由诗中的一种音律重复出现,它往往有所变化,就像交响乐中的主题一样。这些变化和细微的不同主要用来代替押韵。押韵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干扰而非帮助这些细微变化的恰当运用。但是偶尔也有必要用押韵强调某些复杂的变化,或者将诗歌的节奏模式结合起来。
(三)挂留和解决是常见的。采用自由诗体来写作的诗人,他不受任何固定的诗节形式的指导,而只受整首诗的指导(假如该诗由一个诗节构成,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或者受每个诗节的指导(如果该诗由多个诗节构成)。在诗节范围内的一致性是他主要的关注点。几乎在所有的诗中都可以发现,诗节由两部分构成:一个起(rise),一个落(return)。
(四)每个诗人都会不同地对待这些法则。因为在英语中,诗人可以自由写作两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和五拍子的诗,难易程度相同,因而与法语自由诗相比,英语自由诗必定是一种更复杂、更困难的艺术,而在法语中,许多当前的自由诗仅仅是调整后的亚历山大体。因而根据各人的趣味不同,每个诗人都会略有不同地建造他的诗节。这即是我们说“自由诗”时的意思。
(五)至于“分行的散文”、“复调散文”、“拼贴”和“混合”——以及实验性或多或少的其它一切形式(我和其他人已经尝试过了)——它们根本不能也不应该称作诗体(verse)。它们与自由诗的区别在这儿:自由诗源自格律诗,源自旧的诗节形式。在自由诗全部的变化中,诗节节奏摆动和动力平衡的这种一致性保存下来。这些其它的形式源自散文,而散文不具有节奏摆动的一致性,它用段落来取代诗节。这些形式可能与真正的自由诗混淆在一起,但是事实仍然是这样:它们各自的起源是不同的。自由诗的起点是重复的节奏乐句,而这些其它的形式的起点是散文的句子。



约翰·弗莱彻(John Gould Fletcher,1886—1950),1886年1月出生于美国的阿肯色州,1902年进入莱利普斯学院,1906年父亲去世后放弃学业,1909年来到伦敦,并开始认真阅读惠特曼的诗和法国现代诗,1913年5月与庞德结识,次月与洛厄尔相遇。弗莱彻给庞德编选的1914年的《意象主义诗人》供稿,这是他作为意象主义诗人的首次亮相。他并不认同庞德的主义,但帮助洛厄尔编选《意象主义诗人们》,成为洛厄尔诗学上的盟友,但与洛厄尔仍有嫌隙。在此期间,弗莱彻接触中国诗歌,并获得启发,于是成为真正的意象主义者长诗《蓝色交响乐》代表了他中国风格的作品。1915年后出版诗集《光线、沙粒和浪花》和《精灵与宝塔》,在序言中反对自由诗,主张以旧形式为本。1917年艾略特著文否定自由诗,弗莱彻针锋相对,转而肯定自由诗,并在《对自由诗的理性解释》(A Rational Explanation of Vers Libre)里,把自由诗与音律的原则融合起来。1927年与美国南方诗人结识,参加反对现代主义的活动。1938年获得普利策奖。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6期,责任编辑:杨卫东。